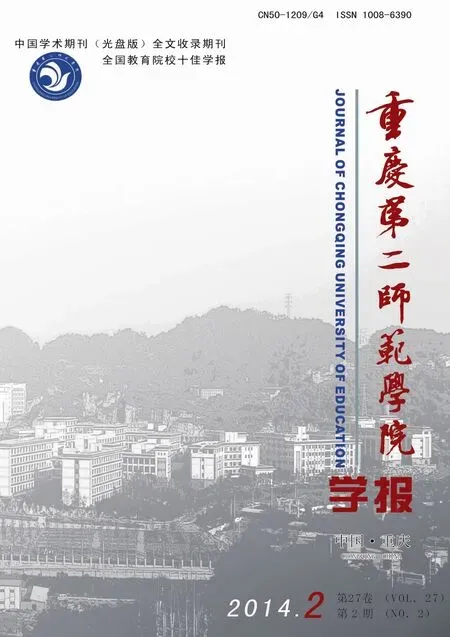“细读”溯源
2014-03-28付骁
付 骁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细读”作为新批评文论的核心概念,应该是文艺理论界近三十年来最受人提倡的文学研究方法。无论面对什么问题,研究者如果不以“细读”作为论述的基础,就有被人指责为学风不严谨的危险。然而,对于这个概念,我们的理解是有误的,我们也不清楚英美批评家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因此,虽然我们“拿来”就用了,但终未能得其精髓。所以,研究其原初意义,梳理其发展脉络,是重新认识、评价新批评的第一步,也是建构具有中西对话特色的文艺批评方法的一项基础工作。
一、“细读”的原义
据国内翻译新批评名家瑞恰慈的代表作《文学批评原理》的杨自伍说,“细读”一词最早出现在瑞恰兹的《实用批评》里[1]P (4)。但是,阅毕该书,并未发现“Close reading”,瑞恰慈的表述是“Closeness of reading”[2]x。“Closeness of reading”出现于《实用批评》的目录,但翻开所指的书页,不知为何瑞恰兹没有解释这个概念。在此之前,瑞恰兹提行写了一个小标题,介绍读诗方法:“复读(Re-read):如果诗歌没有乏味得让你将书仍到一边去。”[2]110接着,他论述的内容是,在阅读过程中,作者的欲达之意和读者的兴趣不一致,并影响着读者的“判断”(judgment),而其正是“值得仔细注意”(they merit close attention)的。“判断”一词,早已出现于西方文学批评文献,但在不同的理论家的笔端有着不同的含义,瑞恰兹所谓的“判断”可以概括表述为读者对一首诗的反应,既然“close attention”的主语毫无疑问是文学批评的研究者,结合原文明显可知其宾语,即“细读”的对象不是文本,而是读者的反应过程。那么,瑞恰兹的潜台词是:既然有很多因素影响着读者的阅读活动,使其对诗歌最终的“判断”超出作者的预期(同时,他也认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排斥读者的期待),因此这个“判断”就是值得“细读”的;反之,如果作者和读者对一首诗的判断一致,就不值得“细读”。这是 “Closeness of reading”出现前距离该条文最近的一处涉及“close”的表述。需指出,瑞恰兹的行文从来混乱,目录上“Closeness of reading”在正文中没有出现,但根据目录页码113页的提示,正文和“Closeness of reading”对应的行文出现“close”的句子是:
The writer feels the danger of misreading the verse form, but through not coming close enough, imaginatively, to “the boom of the tingling strings” and through not working out the contrasts in the poem, he is victimized by his imparted rhythm in the end.[2]113
显然,此处的“close”也是“贴近”、“靠近”的意思。可见,“Closeness of reading”出现的语篇谈的是读者和诗歌的关系,没有涉及重形式还是重历史等论题。
上文还原了“细读”出现的原始语境,分析了其原初意义,可以发现“Close Reading”并未出现在《实用批评》的原文中。在此书后面的附录里,作者对包括新批评另一个核心概念“意图”(intention)等诸多术语进行了解释,其中 “Close Reading”或“Closeness of reading”依然榜上无名;最后的索引里,更见不到两者的身影。这就说明了“细读”不是瑞恰兹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创造的一个重要范畴,更和所谓的排斥社会政治考察而对作品进行孤立绝缘的形式主义语义分析没有关系。
不仅如此,新批评另一位主将布鲁克斯也没有明确提出“Close Reading”。翻阅在国内能找到的所有布氏著作,“Close Reading”在他的笔端只出现了一次,那是在他出版于1972年的论文集《塑性的快乐——作家技艺之研究》的序言里:
有关我的文件夹里贴上了“新批评” 的标签。在如今的时代,生活在任何标签下都是糟糕透顶的,但像“新批评”——当然不“新”,这样一个几近毫无意义的标签,却有着特别的负面作用。对大多数人来说,“新批评”隐约表征着一种反历史的偏见,和对“细读” 的强烈依赖。[3]xi
这是一段理解、评价新批评相当重要的文字。首先,布鲁克斯本人对“新批评”的态度是否定的,原文中“The New Criticism”是打了引号的,说明不是由他本人所创造的词汇;其次,美国批评界确实在使用“close reading”(原文就是小写),但同样也被布氏打了引号,说明此表述亦从他处誊写,与己无关;第三,布氏承认他就是“细读”的实践者,但和瑞恰兹一样,他也是无意为之,只是其批评实践被后学总结为“close reading”。这篇文章写于1970年,此时布鲁克斯已经64岁,所有重要著作均已出版,“细读”的成果业已丰富,所以这则材料对整个新批评文论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既然布氏已经承认他之“细读”确有其事,那么“Close Reading”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其实,布鲁克斯也许自己都不知道,他在撰写学术文章时使用了大量的“细读”,不过原文是“Careful Reading”。如,在他与人合作出版的第一本细读著作《文学入门》里,评论莎士比亚剧本《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时说:
然而深入细读(careful reading)剧本,它会告诉我们安东尼最后认识了自己和世界,而且因此获得了一些正面的东西。[4]636
又如,在与潘·沃伦、罗伯特·海尔默合写的“细读”名作《理解戏剧》的导言中,布鲁克斯说:
对于大多数剧作,在每一幕的最后插入了评论和思考题:这种新颖的排列应该对细读和精读(careful and intensive reading)形成一种特殊的激励效果。[5]x
再如,《理解戏剧》中,“细读”又一次出现在莎剧《麦克白》后的思考题中:
仔细阅读(Read carefully)麦克白在第一幕第1到28行的台词。[5]699
另外,布鲁克斯笔下还出现过“careful examination”(细释)、“careful exegesis”(细析)等文字,均可看作是“Careful Reading”的同义表述。由于“Careful Reading”所出现的著作全为布鲁克斯与他人合著的教材,但遗憾的是书中并未透露分工之情况,因此“细读”一词是否为布鲁克斯所书就是一个值得考证的问题。以《理解戏剧》为例,从行文风格来看,对莎剧《李尔王》的分析很明显出自布鲁克斯的同事海尔默之手,原因是他喜欢用生僻词和复杂句,而其它则应由布鲁克斯本人执笔,所以这本书里的“细读”文字为布鲁克斯本人所写无疑。同理,《文学入门》中“细读”所出现的语境也符合布鲁克斯的文风。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就是布氏的细读著作大多为大学教材,一般均多次出版,而写作本文时所参考的相关书目不是这本书的第一版,因此书籍的第一版确也存在没有使用“细读”的可能。原因是,“细读”一词家喻户晓之后,布鲁克斯在书籍再版之前有可能将其神不知鬼不觉插入旧稿,以提高著作的实用性和知名度。就可能的情况而言,布鲁克斯应该插入“Close Reading”,原因在于学术界和教育界已经普遍使用、认可改词,而插入“Careful Reading”及其它相关表述对他本人的名誉、书籍的畅销并无益处。据此推断,后者在相关书籍的第一版里已经出现。
结论是, “细读”最早的英文表述应该是“Careful Reading”。布鲁克斯的好友、新批评另一成员艾伦·泰特在分析小说的著作《小说之屋》里,亦有“A careful reading of the stories”[6]64的表述,证明此语在新批评圈内或许有一定程度的流传。“Close Reading”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待考。鉴于布鲁克斯受瑞恰兹影响极深的事实,“Careful Reading”可能是“Closeness of reading”的转述,而“Close Reading”则是布氏同人或其他后学对前两种表述的转述或再转述。并且,有的学者在转述过程中又产生了讹误,如迈克尔·雷夫对细读的评价:“批评性修辞提醒细读法(closing reading)追随者,权力与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总是渗透进他们研究的文本之中的。”[7]289
之所以做以上的考证,是为了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其一,“Close ”和“Careful”同义,均意为“仔细的”,具体而言,瑞恰兹和布鲁克斯均要求学生在阅读时仔细研读作品;其二,正因如此,它实际上是一种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和所谓对作品进行语言形式的分析无关(小说、戏剧篇幅较长,如何分析其语言呢?);其三,本文的“细读”指布鲁克斯的“Careful Reading”,至于“Close Reading”如何具体操作,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兰色姆:细读之父
稽之西方文学批评史,如前布鲁克斯所述,“细读”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归纳一般戏剧法则就是以细读为基础;德国批评家莱辛撰写的美学名著《拉奥孔》也可以算是一部细读之作①。但美国新批评之“细读”,阅读对象主要是现代英语诗,具体操作方法与上述两者的完全不一样。美国南方的诗人、文学批评家兰色姆在“细读”的形成过程中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因此,与其称之“英美新批评”,不如说是“美国南方新批评”,因为新批评的诸代表批评家的细读活动和美国南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学教育制度有密切的联系。新批评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叶美国南方的一所著名学府梵特比尔大学②的英语系。彼时,距离南北战争南方同盟军之战败投降,过去了约半个世纪,南方的经济体制已趋于全盘工业化,而在思想观念上的特点可以用一个英语单词概括:Progress。写《哦,船长!我的船长》一诗来歌颂美国北方总统林肯的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还有一首不甚出名的有关南北战争的诗作,To a certain cantatrice(致某女歌手),其中有如下的诗句:
Here, take this gift,
I was reserving it for some hero, speaker, or general,
One who should serve the good cause, the great idea,
the progress and freedom of the race
……
诗歌还列举了“这个人”(who)身肩的使命,限于篇幅省略之。“这个人”当然在诗中是指女歌手,而实则另指南北战争后领导整个美国向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某人。不管他是谁,必须让美国“Progress”,即“进步”,与其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奴隶的自由”(freedom of the race),可以说让美国“进步”实乃战后美国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进步”的内涵是什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尔库塞在《单面人》里指出:
“进步”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术语;它是有特定前进目标的,这些目标是根据改善人类处境的种种可能性来确定的。发达工业社会已经接近于这样一个阶段,那时它的继续进步将会要求从根本上破坏现行的进步方式和组织。[8]14
在南北战争之后言“进步”当然是与时俱进的,而几十年后,“进步”过了头,无疑会遭到知识界的批判。早在马尔库塞之前,美国南方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进步”的弊端。在美国,它的对立面就是以种植园奴隶制为经济基础的南方一系列上层思想建筑。“进步”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理所当然影响到了文学研究领域,南方批评家在描述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文学研究界和文学教育界时关于把持“进步”观的学者称之为“进步主义者”,时任梵特比尔大学英语系系主任的埃德温·密斯就是这样的学者。总体来讲他对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态度是:
虽然他回避旧式哲学,但也没做好接受新美学思潮的准备。坚信社会进步和道德复兴,他十分强调勃朗宁和丁尼生诗歌中的与之相关的价值(密斯还是一名本科生时,两人都已经不在人世),要求他的学生背诵上千行诗句。……他对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及其所展现出来的科技上的先进未来印象颇深。……虽然他对科技知之甚少,但他深信,这一定会造就一个异常繁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文学家也会受益。[9]20
此时的密斯作为一个南方人,在思想倾向上却已北方化,迷信科技,认为它可以带来社会之进步。反过来说,南方各州之所以落后,原因全在把农业当作立州之本。应该说,持这种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并没有错,南方同盟军的战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密斯将文学作品和社会进步事业捆绑在一起,并在英语系的课堂上把活生生的文学作品变成呆板枯燥的社会思潮的注脚,犯了一个文学界的大忌:文学不是某种外在于己的事物的印证。从文学批评和教育的角度上看,勃朗宁和丁尼生的诗歌和“进步”思潮存在时空间隔,将两者强扯在一起有削足适履之嫌,如果用这种方法在英语系中教学,很难析出文学作品之精华,且让学生背诵大量的诗歌充其量只能让“进步”观烂熟于心,可以培养出很多在总统竞选中雄辩滔滔、引经据典的进步演说家,却无法培养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批评家或文学教育工作者。
不过,堡垒易从内部攻破。“像很多进步的系主任一样,埃德温密斯吸纳了许多优秀的年轻教授,这些人的光芒最终盖住了他。其中最杰出的是约翰·克娄·兰色姆,一个梵特比尔、罗德学者。”[9]20兰色姆是梵大英语系的学生,毕业于1909年,之后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获得文学学士学位(B.A.),1914年始回梵大英语系任教。此时,兰色姆只是一个资历尚浅的教师,虽然对“进步”恨之入骨,但无法从根本变革英语系的教学方法,而且也没有资料证明他这时对密斯的教学有任何不满。然而,也是在1914年,他在课堂之外,却和自己的学生罗纳德·戴维森等人“在纳什维尔第二十大街的西德尼·赫希家里组织聚会,开始哲学话题的讨论”,却直接导致了新批评文学批评派及其“细读”方法的诞生。
这个以梵特比尔大学青年师生为主体的文学、哲学、社会学民间学术团体就是后来扬名美国文学批评界和文化界的“逃亡者”学派。“逃亡者”其名源于这个团体于1922年开始出版的一部同人诗歌刊物——《逃亡者:诗刊》。初见此名,加上新批评是形式主义的先见,很容易认为这些人是一群与世格格不入的“愤青”,欲在文学的世界里畅游以“逃避”日益工业化的南方社会。但其实,第一,从词义上说,“这是西德尼·赫希的发明,其准确意义至今不明(康丁疑是赫希做了一个隐喻)[9]24。第二,从事实来看,这个团体的成员构成很复杂,既有南方贵族,又有普通白人,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观:资本主义化的南方并不是战后南方的最佳社会状态,南方诸多传统的优秀制度和思想被科学的蛮横斩断,整个南方社会和思想文化界需要某种温和的变革。第三,从实质来讲,这个团体的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其文学活动是主“外”的,如果“逃亡者”的涵义是《圣经》的“新生”,那么,后来的新批评在美国文论界活动的目的就是让整个美国文化来一次全盘更新。
“逃亡者”的核心人物是兰色姆。“在1915年夏秋之际,在他的带领下,这个每周举行一次的讨论会的主题,由赫希主导的抽象哲学,转向具体诗作的分析。”[9]23众所周知,兰色姆除了是一名文学教师,还是一名南方诗人,显然他的兴趣不在哲学,而在诗歌。由于没有录音和录像,他们分析诗歌的篇目和具体过程已不得而知,但可以从常理推测:其一,作为不甚出名的青年诗人,他们之间一定彼此相互切磋诗艺,并连带分析英诗名篇;其二,“逃亡者”团体不尽是诗人,且他们都对南方社会的现状忧心忡忡,因此分析诗作应该会夹杂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其三,这种分析诗歌的方法,兰色姆一定会把它引进自己在梵大的文学课堂。
事实确实如此,“细读”诞生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赫希的家,推广于同城梵特比尔大学英语系兰色姆的文学课堂。美国后辈学者有如下考证:
这种在校园之外聚会的形式很符合兰色姆的个性,那个时代,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是匿名的,他得到的分数当然很低。与密斯之沉湎于巨作之美的方法不同,兰色姆专事特殊篇章的细读(close reading),其嗓音通常是平淡的,缺乏抑扬顿挫的节奏。(利维斯·辛普森记得在暑期课程的某学期,他阅读《黛西·米勒》全篇的情景;见苏利文《艾伦·泰特》,第30页)他沿用苏格拉底的方法,做一些带有试验性质的断言,并不停向他的学生提问。[9]22
由此可以说,新批评派的“细读”之路上的第一个领跑人就是兰色姆。从引文中也可以归纳出“细读”的特点:首先,“细读”的对象一般是比较短小的英诗篇目,原因在于若选取鸿篇巨制,难免陷入印象批评,夸夸其谈不得要领;其次,在具体操作上,“细读”过程中需要不停地提问,这在布鲁克斯的《文学入门》、《理解诗歌》、《理解小说》、《理解戏剧》这几部细读名著中均以体现,所以,“细读”最核心的本质是一种独特的英美文学教学法,发展为文学批评的方法是之后的事;最后,事实上当时的学生对“细读”并不买账,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式的提问会让赫希家的聚会更显热闹,而对于文学课堂来说未免有些死板(当然,兰色姆本人的教学能力欠强也影响了细读教学效果)。
三、布鲁克斯:细读的实践者
布鲁克斯进入梵大英语系的时间是1924年,此时他18岁,距离纳什维尔“逃亡者”同人的首次聚会,已过去十年。在他当大一新生的时候,日后成为他终身好友的艾伦·泰特和罗伯特·潘·沃伦是他的学长,他俩和已经成名的兰色姆关系密切,并成为了“逃亡者”集团的一员,参与讨论,编撰杂志。布鲁克斯则规规矩矩埋下头来广泛阅读文学作品,有时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但始终没有进入“逃亡者”圈子。他和兰色姆发生关系,始于大二,当时选了老师的“现代文学”课,但遗憾的是,“事实上,课程的难度吓坏了布鲁克斯,不久便退选了。”[9]P (33)按常理说,布鲁克斯不是兰色姆“圈子”里的人,在老师的课堂上也没学到多少东西,由他接着“细读”似乎于理不通。可是,历史选择布鲁克斯成为美国文学批评界“语言转向”的关键人物,自有其机缘之处。布鲁克斯走上“细读”之路,有两个诱因,一个与兰色姆有关,出于偶然;一个和戴维森相连,出于必然。这是他自己回忆的那次偶然事件:
来得突然、来得简单。一天晚上,我在一个朋友的寝室里。随意闲聊之中,发现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兰色姆的诗集,我翻开它读了起来——真正的阅读(really reading),因为我曾读过无数遍。突然,一些标准出现在我眼前。代码被破解,诗作成为“可读的”。我的意思不是它们变成魔法般的透明之物,我继续寻找里面的深层意义(fresh meaning) 和之前被我忽视掉的深度。但一些严肃的障碍物荡然无存,那时我是一个真正的启下者。[9]34
虽然布鲁克斯终其一生都没有诠释细读的真正内涵,但这段文字表明,“细读”的目的在于寻找“深层意义”,实质是一种对语言符号的解码活动。然而,布鲁克斯可以在第二天找到兰色姆,询问这些诗的“深层意义”是什么,但他却坐在朋友的寝室里反复阅读,因此“细读”又是一种批评家的单独释义活动。
第二个诱因来自罗纳德·戴维森的一篇文章。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新批评源于艾略特和瑞恰兹,而在美国理论界,更倾向于戴维森“创造了新批评”[9]34。此人之声名虽不显于中国学界,但他却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逃亡者”集团最初聚会时的骨干分子,若论资排辈应仅次于兰色姆。戴维森是一个坚定的南方保守派、重农主义者,但与布鲁克斯等人一样,他们把对政治现状的关注和对文学批评的热爱分得很清。他是布鲁克斯的老师辈,二十年代中期亦执教于梵大英语系,其文学批评的关注重点在作家技巧的运用。布鲁克斯自传里有如下记载:
……戴维森对小说技巧的关注,是一种精确的批评(布鲁克斯和沃伦合编的教科书《理解小说》即题赠给他)。一天,在文学课上,克林斯·布鲁克斯听见一个毕业生在朗读戴维森的一篇文章,此君是谁他已记不清了,而文章是关于吉普林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在那一刻,布鲁克斯充分意识到细读作为一种批评技巧的价值所在。[9]34
这段材料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揭示了“细读”的师承关系:布鲁克斯祖述戴维森。如前所述,布鲁克斯和兰色姆师生关系一般,他没有从老师那里习得明确的“方法”,而日后作为一名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其学术应该有本所依,他依据的正是戴维森的小说批评法。第二,说明了“细读”的对象不止诗歌,小说也是重点,可以毫不夸张说,小说的细读才是新批评派发动的“第一战役”。第三,明确了“细读”的性质:“批评技巧”,即只有细读才能获取意义。如果从小处讲“细读”是阅读时的专注态度,那么就体现不出它的操作性;如果从大处讲“细读”是文学批评的方法,则过于泛化,难道其他的方法不细读?其实,“细读”就是对作家所用的文学技巧的关注,但细读者并不是就技巧论技巧,而是要从技巧的使用中发现作品的“深层意义”。细读必须首先关注技巧,如果批评家读的只是作品中的政治倾向,不管他有多么“仔细”,虽然可以算文学批评,但绝不是“细读”。这篇文章的意义在:
戴维森对梵大诸多届学生均使用此法。虽然布鲁克斯并未上过他的课,但这篇文章足够让他开始以全新的方法思考文学。[9]35
由于在国内暂未找到戴维森的相关著作,只能从布鲁克斯传记里知道,他曾在兰色姆的指导下于1922年撰文分析过康拉德使用的“倒叙法”。且不管他具体怎么分析,可以清楚的是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小说》分析吉卜林的《国王迷》时曾对此法有所发挥,足以证明戴维森对布鲁克斯影响的直接存在。另外,从这段材料中还可以看到,新批评具有显著的师承特征,其之所以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引起巨大反响,和一代又一代梵大英语系毕业生的薪火相传有重大关系。此后,这些学生熬成了老师,又执教于其它南方大学,甚至在北方的世界级名校教授“细读”,遂使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成为一种英美文学的教学方法。
由此观之,布鲁克斯从兰色姆的诗作中悟出了“意义”,使阐发深层意义成为“细读”的目的之一;从戴维森的论文中习得了方法,让阐发意义的过程不再空泛如也。
然而,不管作为梵大学生的布鲁克斯所进入的崭新世界如何有价值,都只意味着为个人的事业开启了一扇窗。众所周知,一个批评学派欲想登上时代的舞台,必须对某种旧方法进行批判。最初,与新批评本质冲突的,是从十九世纪开始流行于英美大学英语系的传统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语言研究、历史研究(包括传记研究)和文集编撰工作。由于专业性太强,中国学者基本没有翻译传统研究的著作,故暂不深究此问题。只举几例:布鲁克斯本人也是一名传统研究家,他的学术著作《美国南方语言》《美国文学:作家与作品》《托马斯·潘西和理查德·法内的通信》就属于传统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形态,传统研究虽略显枯燥,但自有其存在价值,所以也无可厚非。但是,彼时的英文系教师把这种方法运用于文学教学,久而久之弊端重重。对此,布鲁克斯日后的同事雷纳·韦勒克在《美国的文学研究》一文里曾对此做过尖锐的批评:
专家们把这些知识硬塞给美国大学生(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这种硬要求学生掌握古英语语法和英语音韵学史知识的做法,不仅影响了他们文学探索的热情,而且阻挠了许多学生完成他们的学业。[10]283
又如:
在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明显得看出这种文学研究的种种弊病:没有用处的烦琐的历史考证,干巴巴的事实罗列,……以及它所特有的批评趣味的缺乏等等。[10]282
简言之,传统研究的对象根本不是“文学”,这对于英语系的存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而往后,新批评家一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称为“文学批评”,说明这两个概念是对立的。究其原因,韦勒克在文章中认为:“当时的工业生产,那种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和产品标准化所显示的巨大潜力,也给这种学说帮了忙。因为大规模的生产是一种工业化的理想,而教师们方便给学生们的成绩给分也是一种实践的需要。”[10]281-282作为新批评阵营里的文论史家,韦勒克一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批判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科学主义文学研究,所以,传统研究在他眼中也是工业化社会的一项伪劣产品就不足为奇了。从常理考察,新批评家潜在的言说目的是揭露南方的工业化社会的弊端,而传统研究在看待问题的方式上与之合拍,因此借题发挥、言此意彼、指桑骂槐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从事实上看,布鲁克斯本人并没有明确地将两者联系起来,只是在后来的批评中才逐渐彰显南方的文化特色。所以,英美英文系的研究方法从传统研究转向文学批评,乃是依从文学批评史进化过程的内在法则,简言之,新批评之前,大学教授们过度标榜的方法,在兰色姆、戴维森、布鲁克斯等人看来已经不再重要。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行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批评,不过从十九世纪开始这种活动在英美大学的英文系里断裂,新批评的任务就是接续其血脉。促使他把工作重心从传统研究转向文学批评的最后契机,就是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学士学位期间培养起来的反思、批判现存批评体制的能力。1929年,他负笈英伦,入牛津大学教授戴维德·尼克尔·史密斯门下研究潘西(上文提到的《托马斯·潘西和理查德·法内的通信》即“研究成果”)。此时,牛津英语系的学术环境是:
牛津的英语体制重视传统的、哲学的学术研究,不欢迎文学批评。(虽然在尼克尔·史密斯剩下的人生岁月里和克林斯保持着挚友的情谊,这个苏格兰人很少使用文学分析,这个由他的学生布鲁克斯和沃伦实践的方法。)[9]67
而牛津大学的老冤家剑桥大学的学术生态,则完全与之相反:
然而,剑桥大学则是另一幅景象。……如果剑桥和梵大有所不同,就是剑桥的文学批评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与之相反,埃德温·密斯多年致力于让梵特比尔的文学批评处于地下状态,或者至少让它远离校园。[9]67-68
的确如此,牛津给予布鲁克斯以严谨的历史方法的训练,而剑桥大学的文学批评大师瑞恰兹则是他真正的“导师”。布鲁克斯和沃伦晚年在一次谈话中回忆这段往事,深有感触:
布鲁克斯:是的,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教英国文学的人,都没有学过这些(按:指诗歌的结构和内在生命)。较早习之非常重要。
……
布鲁克斯:我想你非常准确地简要复述了我在梵特比尔大学的经历(按:指关注诗歌本身)。这是一个大发现,从此我愈加爱上文学。……当时,研究生训练关注对象并不在此。清一色历史研究和传记研究。
沃伦:哦,当然显著的问题是,你如何操作的。
布鲁克斯:1929年秋天,你我重逢于牛津,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不过百思不得其解。你让我阅读I·A·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和《实用批评》。我开始读了,不是很喜欢,也未沉迷,但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在多问题上我不赞同他。我不喜欢瑞恰兹使用的术语。不过,尽管如此,他的所思所为还是令人兴奋的、醍醐灌顶的。[11]5
这段谈话录的节选足以让本节的内容连贯为一体。在梵大,布鲁克斯也许有某种反抗传统的冲动,几年后在牛津大学阅读瑞恰兹的书和听他的讲座后,便使这种冲动有所依凭、落后实处:运用并改造瑞恰兹的文学批评术语,撰写有关“细读”的论文、教材和专著。英美后学列举的瑞恰兹常用的学术术语有:
瑞恰兹的方法是,分析诗人的感觉、使用的意象、隐喻、节奏、语气、形式、意图、态度和反讽。这些方法为处理诗的组织、多义、自指、朦胧和言外之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70
而布鲁克斯在所有的有关“细读”的著作中,直接使用这些术语分析文学作品。上一个引文提到布鲁克斯说“我不喜欢瑞恰兹使用的术语”,应该是指瑞恰兹使用的一些心理学术语。将两人的著作对比考察,可以很容易发现术语的一致性、继承性。不过,这些术语古已有之,瑞恰兹增加了其心理学涵义,而布鲁克斯又对其作了去心理学的处理,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文学作品的细读。布鲁克斯从教后出版的一系列与他人合著的教材,如《文学入门》《理解诗歌》《理解小说》《理解戏剧》等,就是新批评细读实践的代表作。
注释:
①波兰批评家诺曼·英伽登在《现象学美学:试界定其范围》一文中把这两部著作为“客观主义”美学,见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最新西方文论选》第18页。
②梵特比尔大学在美国素有“南方的哈佛”的美誉,我国近代著名人士宋嘉树(宋氏三姐妹之父)即毕业于此。
参考文献:
[1][英]艾·阿·瑞恰兹.杨自伍译.文学批评原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2]I·A·Richards,PracticalCriticism:Astudyofliteraryjudgment[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由于这本书失版权页,不知其出版年代)
[3]Cleanth Brooks.AShapingJoy:studiesinthewriter’scraft[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2.
[4]Cleanth Brooks and John Thibaut Purser and Robert Penn Warren,Anapproachtoliterapture.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75.
[5]Cleanth Brooks and Robert B. Heilman,UnderstandingDrama[M].台湾:敦煌书局,1977.
[6]Caroline Gordon and Allen Tate,TheHouseofFiction[M].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0.
[7][美]迈克尔·雷夫.语言构成的世界:文本批评的思考[A].王顺珠译.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9]Mark Royden Winchell,CleanthBrooksandtheRiseofModernCriticism[M],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6.
[10][美]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M].丁泓,余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
[11]Robert Penn Warren,“A Conversation with Cleanth Brooks” in Lewis P. Simpson, ed.ThePossibilitiesofOrder:CleanthBrooksandHisWork[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