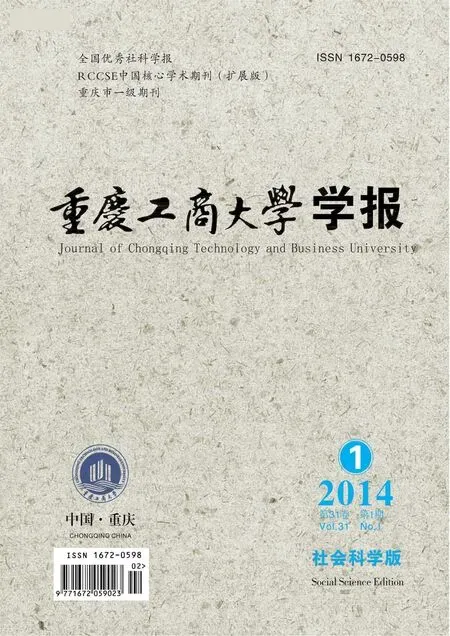政治文化语境与鲁迅晚期翻译*
2014-03-27骆萍
骆萍
(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重庆400067)
政治文化语境与鲁迅晚期翻译*
骆萍
(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重庆400067)
翻译总是与特定的语境有关,受到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印记对鲁迅晚期的翻译实践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其翻译目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都体现出译者的政治文化诉求。
30年代;政治文化;鲁迅;晚期翻译;苏俄文学;翻译策略
一、引言
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受到某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引入新思想和新观念,翻译既对原有的译入语文化造成冲击,又能帮助构建新的社会架构。另一方面,译者也利用翻译以求达到某种目的,且往往是政治目的。因此,翻译变成一种革新甚至颠覆性的力量,推翻和解构译入语文化长久以来的秩序或规范,引进新的异质因素,配合和推动一些政治活动,隐含着政治权力运作机制。从政治文化角度去看待20世纪30年代政治与翻译的特殊关系,以及翻译文学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与政治结缘;政治的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影响译者的政治态度、译本选择、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标准等问题,可以尽可能比较真实地再现该时期政治文化制度的运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的译者政治意识,以期找到许多翻译现象(包括翻译目的、译本选择、主题选择、翻译策略、重要的翻译论争的形成等)的重要依据,还原30年代翻译文学的生态环境。之所以选择鲁迅的翻译作为个案研究,是因为鲁迅的翻译带有较强的实用性甚至功利的色彩,突出翻译的教化和启蒙作用。尤其是鲁迅晚期的翻译,是他一生中译作数量最多、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着重于苏俄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探索,充分体现了政治与译者翻译活动的相互形态关系。
二、政治文化的界定
“政治文化”一词最初是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提出的。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朱晓进,2004:4-5)。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王乐理,2002:19)。具体地说,政治是一种客观的外部活动,政治文化则关注人们政治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价值取向,不仅是政治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也是政治体系中成员的个人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模式,即政治制度的内化。不可否认,在某些历史时期,政治会直接影响甚至操作翻译活动。但是,政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政治文化这一渠道进行的,即政治通过营造某种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翻译活动,而翻译则通过作为社会成员的译者,特别是有声望的身兼数职的精英知识分子,透过他们的译介,引入新思想,间接地营造政治文化语境和氛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化为政治与翻译搭建起了一座桥梁,使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窥探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
三、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文化
通常文学史意义上的“30年代”(1927—1936),是以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权的建立为其开端的(朱晓进,2007:14)。国民党为巩固其权力主体的地位,实行了种种文化控制方略和文艺政策,采取宣传、教育、查禁等措施施行文化专制主义,对进步文化和文艺机构进行破坏,对革命、进步的文化和文艺界人士不断地进行迫害。凡内容上涉及“赤色”的作品和译作均被查禁不能出版。但是,国民党推行的一整套政治文化方略却是失败的,他们的专制手段不仅没能控制文学群体的政治信仰,反而在公众中激起尖锐的对立。
30年代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造成了普遍的政治焦虑,在不少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思想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压力。当这种压力无法通过政治途径发泄和释放时,包括文学在内的传媒,也就成了重要的发泄和转移政治压力和政治焦虑的渠道。30年代的文学作品及其翻译都是源于对“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的政治形势而形成的特殊的政治心理。鉴于文学在政治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文学领域便成了需要积极介入并激烈争夺的战场。除了武装革命外,中共及其文化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文化方面从事另一种形式的革命,即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文学斗争。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战后经济的复苏,相对于爆发在20年代末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苏联向全世界展现了一幅工业突飞猛进的美好蓝图。两者相比较,学习苏联,成为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又一利器。苏联对中国的借镜作用掀起了苏俄文学的翻译热。在这场“赤色”翻译潮中,“左联”作为共产党文化战线进行政治运作的一个产物,译介苏俄文学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革命而非文学。
四、政治文化对鲁迅晚期翻译的影响
(一)鲁迅的政治文化心理与翻译的目的
根据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原则,任何翻译都是有目的的,如启蒙读者、引进新的表达法、传播异质文化等。任何一个译者进行翻译活动都有着一定的非翻译动机,而译者的翻译目的必定会受到特点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鲁迅几乎用大半生的精力从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借外国的火照亮中国的夜,其翻译思想是以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为目的的,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其翻译活动“始终是基于对现实社会深刻理解和理性认识之上的革命改造行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政治文化活动”(周宁,2007:45)。在鲁迅翻译活动的晚期,从早中期的“文学革命”到后来的“革命文学”,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兴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面对复杂的历史环境,鲁迅自1926年离开北京后,南下厦门、广州,亲眼目睹了中国的革命新形势,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和自己下一步该走的路。在1932年《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鲁迅痛斥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攻击,感叹“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太久了”(鲁迅,1981a:431),并清楚认识到“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信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会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鲁迅,1981b:18)。鲁迅坚定地把走苏联的路作为“我们自己的生路”(鲁迅,1981a:431),认同苏联、参加“左联”,投身革命文学的浪潮中,更不惜冒着查禁、逮捕乃至牺牲的危险。
自晚清从事翻译活动起,鲁迅便认定翻译外国作品能够“启蒙”“救亡”,改造国民性。在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前,他的翻译活动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1928年面对纷纷扰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主要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攻击,以及梁实秋为首的新月社的攻击,一方面迫使鲁迅大量阅读马列主义作品,并信服其中的观点,修正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从他对手的论争中暴露的弱点,使他想亲自动手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想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发展与阶级的关系、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阶级与文学的关系等基本的理论问题(王友贵,2005:229)。鲁迅后期的翻译活动主要是苏俄文学作品和苏联文艺理论著作。通过翻译,通过译介外来的新思想和新观念来学习、思考,厘清自己的头脑,解决国内的重大问题是鲁迅勤奋翻译苏俄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翻译目的。在他看来,与其陷入盲目的论争,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他指出:“有马克思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鲁迅,1981c:127)。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刚兴起时,在马克思主义有关文艺的经典篇章还未整理出来时,鲁迅自觉地输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克服“左倾幼稚病”、庸俗的机械唯物论、社会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思想理论武器,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李今,2009: 108-109),向中国读者及其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的任务,使翻译成为整个政治运动及斗争的一部分,充分再现了鲁迅的政治文化心理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
(二)鲁迅的政治文化诉求与翻译题材的选择
鲁迅晚期大量地译介了苏俄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如《文艺政策》《文艺与批评》、苏俄两种《艺术论》《壁下译丛》《毁灭》《十月》《竖琴》《死魂灵》等,把翻译看成是一种斗争和反抗的工具,政治文化因素与译者的政治文化诉求和政治价值观始终占据着译介选择的主要地位。
鲁迅首先翻译的是《文艺政策》,是苏联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会议记录和决策,诚如他所说:“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韧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鲁迅,1981d: 209)。从“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来说明翻译马列著作的动机,要自己对社会有些用处,这是一种明显的翻译政治观。
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是为了搞清楚与创造社论争过程中的许多疑问,以及纠正自己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1981e:6)。这里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重大转变,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艺术论》是普氏用唯物论研究美学和文艺的作品,并举例丰富地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间的矛盾对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的作用。在鲁迅看来,普氏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鲁迅,2007a:185),翻译该著作使鲁迅进一步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其观点分析和解剖中国社会。
除了苏联的文艺理论,鲁迅也着眼于反映苏联国内革命与战争主题的文学作品,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从鲁迅为这两部作品所写的后记和附记中可以看出他选取这两部作品是煞费苦心的。前者是无产者的作品,后者是同路人文学。鲁迅有意识地通过对苏联国内战争不同立场的人的视角,企图真实地再现苏联革命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的政治立场。这里有必要着重指出鲁迅选择无产者文学作品《毁灭》的原因是希望通过书中作者所塑造的革命先驱者莱奋生从对革命的时而动摇、茫然失措到最后的坚定的过程,向读者展示革命过程中经过锻炼、改造而产生的“一种新式的人”,“真实的英雄”,而非“无不超绝”的神人(瞿秋白,1981:379),通过对这样真实的人的描述,批评中国革命文学家所描写的浪漫革命幻想和乌托邦的革命情怀,指出“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鲁迅,2007b:210)。
鲁迅对无产者文学和同路人文学的译介基本上各占一半,强调两者间最终的汇合和殊途同归,他对这些作品的翻译是与其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的思考紧紧相连的,关注的是关于革命、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充分凸显出鲁迅的政治文化心理。
在鲁迅后期的翻译作品中,不得不提的是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巨著《死魂灵》,也是鲁迅毕生唯一译介的一部长篇小说,鲁迅为此投入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更是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都投进去了。鲁迅之所以选择《死魂灵》是由于果氏“以描写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鲁迅,1981f:64,87),其小说讽刺艺术的隐含性和象征性以及对于社会的意义使鲁迅潜心“拿来”,以表达自己对中国现实的关怀,并为中国人指明一条有价值的新的生存之路,与他的政治诉求紧紧相连。
(三)鲁迅的政治文化意识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译者生活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其翻译意识和翻译行为受到限制和影响,同时译者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以及翻译动机均影响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鲁迅早期的翻译沿袭晚清的“意译”风尚,但随着思想的发展和知识结构来源的改变,自《域外小说集》开始,就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直译绝不仅仅是翻译方法和语言形式的选择问题,更多的是通过保持异质文化的原汁原味,别求新声于异邦,唤醒中国民众,启民兴国,同时通过译介外国作品,丰富汉语,发展民族文学。鲁迅的直译充分地体现了其政治意识和文化目的。
鲁迅晚期的翻译更加强调直译,甚至是“硬译”。在1929年翻译的《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他说道“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有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这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鲁迅,2007c:167)。在与梁实秋的论战中,他说:“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即不曲,也不‘硬’不‘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能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鲁迅,1981d:210)鲁迅明知自己的译文晦涩难解,冒着骂名仍坚持直译,其背后的深沉原因是明显的,包括他与梁实秋的论战,与其说是关于翻译标准的论战,不如说是二人关于文学观与政治观的分歧。经过了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后,鲁迅可说是进入了“左倾”阶段,认为文学具有阶级性,而梁实秋则完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认为文学是最基本的人性的表现,是超阶级的。鲁梁二人的翻译论战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二人实则代表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人论争的不是翻译问题,而是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
深究其因,鲁迅直译观的背后是严肃的政治文化动因。在翻译《死魂灵》前,他自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也就是说,是“力求易解”,还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1981g:352)。在他看来,翻译旨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鲁迅,1981g:352),因此不赞成为了易懂,易读而将外国的人名和地名中国化。在翻译《死魂灵》时,作品中所描写的19世纪上半期烦琐的菜单、餐具、服装等,鲁迅都“硬着头皮译下去”,尽量忠实于原著。在他与瞿秋白的通信中,他也一再强调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鲁迅,1981g: 382)。由此来看,鲁迅煞费苦心地提倡直译,甚至硬译,乃是基于启蒙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大思路。他对俄苏文学的关注和译介,对原作原汁原味的直译,是因为俄国文学里蕴含着博大的人道主义关怀和深刻的人性的透视,是“为人生”的文学,苏联文学则是“忍受,呻吟,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王友贵,2005:299),经历忍受,挣扎,战斗,最后取得成功,在鲁迅看来,中国革命可以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
五、小结
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心理,使鲁迅最终在观念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接受革命文学的理念,并在其晚期的文学翻译实践中展现出来。怀着为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输入先进范本的政治文化诉求,他热情地投入苏联文学的翻译和出版事业,冒着被国民党当局迫害的危险,冒着国民政府严密的书刊检查制度和出版“赤色”书籍的禁令,创办专门发表翻译的期刊《译文》、主编《奔流》杂志,主持翻译丛书如后期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现代文艺丛书》和《文艺连丛书》,并常常自费出书,如在国民党加紧了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围剿,没有一家书店敢继续承印有关苏联书籍方面的时候,鲁迅不畏强暴,自己出一千大洋,以实际上不存在的“三闲书屋”为名陆续印了他的译作《毁灭》,绥拉菲摩维奇著、曹靖华译《铁流》,还有《梅斐尔德木刻敏士之图》(李今,2009:159)。不仅如此,他还大力扶持年轻人如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柔石等从事翻译活动,并先后校订了十几部苏联文学作品,为了把这些作品推向社会写了很多的编校后记或序,为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不遗余力,为中国窃取火种,对中国革命发挥了积极地影响和促进作用,以毕生精力通过翻译实践实现其政治文化目的和价值取向。
[1]李今.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苏俄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a.
[3]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
[4]鲁迅.文学的阶级性[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c.
[5]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d.
[6]鲁迅.三闲集·序言[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e.
[7]鲁迅.摩罗诗力说[A].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f.
[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g.
[9]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h.
[10]鲁迅.译文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11]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来信[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3]王友贵.翻译家鲁迅[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14]周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J].广大外贸外语大学学报,2007(1).
[15]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6]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校:朱德东)
Political Culture Context and Lu Xun’s Translation at His Late Life
LUO 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Translation is always related to some specific contextand is limited by specif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so on.The spe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marks in the 1930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act and limitation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Lu Xun at his late life,and h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ursuit was fully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purpose,text selection and strategies of his translation.
the 1930s;politics and culture;Lu Xun;translation in Lu’s late life;literature works of Russia and Soviet U-nion;translation strategy
I210.93
A
1672-0598(2014)01-0137-05
12.3969/j.issn.1672-0598.2014.01.022
2013-10-21
2013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3SKH14)“场域视角下的鲁迅翻译活动研究”
骆萍(1979—),女,重庆人;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