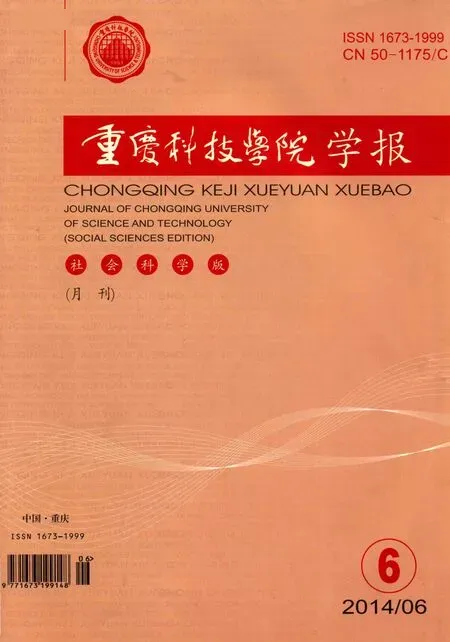论《连城诀》的反武侠性及其对丑恶人性的批判
2014-03-25梁圣涛
梁圣涛
《连城诀》原名《素心剑》,最早刊载于1963年的《东南亚周刊》,后编入2002年修订版《金庸作品集》为第二十册。在金庸所有武侠小说中《连城诀》篇幅不长也非代表性作品,一直以来也不太受重视,但它实际上是极其独特一部作品,并且在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复杂人性和反武侠性两个方面对它的重要地位进行阐释。
一、丑恶人性
金庸武侠小说向来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并进而试图对人性本身做出开掘,这正是其有别于一般武侠小说之处;“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情感比起社会意义和政治规范等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连城诀》正好是对这些主张的实践和探索。小说通过乡下人狄云的遭遇和视角,让读者目睹了一场江湖人士为争夺连城宝藏而人性扭曲的人间惨剧,极其深入地刻画了人性的贪婪和变态。小说最后一章“大宝藏”最具概括力,透过狄云眼睛看到 “这些人越斗越厉害,有人突然间扑到金佛上,抱住了佛像狂咬,有的人用头猛撞”,“他们个个都发了疯,红了眼乱打、乱咬、乱撕”,“他们一般地都变成了野兽,在乱咬、乱抢,将珠宝塞到嘴里”,这些找到宝藏的人都像野兽一样发了疯,中了毒,其实更深的毒是中在他们心中——贪毒,佛家所谓的三毒之首。文本就是以这种颠覆性的角度和姿态来旁观江湖,将江湖丑陋的一端和人性恶的一面加以放大和集中,不动声色地展示到读者面前;在这里,丑和坏成了主导力量,正如倪匡所说这是一本“坏书”,写尽各色坏人各种坏处,人性中善的一面被挤得无处安身。很显然这部小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寓言,它企图凭借对虚构江湖世界的描摹来映衬整个人性的弱点和生存的荒谬,从而更深入的探讨人类存在本质和意义。在这一点上《连城诀》已突破通俗武侠小说的藩篱而进入严肃文学的视域,这也构成了其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独特魅力,同时它也是狭隘的现实主义在大陆大肆风行时,用最为民族和通俗的方式,对世界文学潮流做出的一个悄然回应。
然而我们如果就此认为《连城诀》表达了作者对文化的虚无态度,那便是莫大的误解。《连城诀》的主题意图其实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极其相似,它不遗余力地揭露人性丑恶和物欲异化,是对世俗物欲和贪婪否定同时也是对人性和文化中正能量的一面的反向肯定。丁典为爱情自甘牢狱至死不渝,水岱为救爱女不惜身死雪山,狄云面对巨大宝藏无动于衷,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并未一味的沉迷于恶的深渊而更多的是对它的否定和反抗,最终导向的不是沉沦而是象征纯洁与美好的净土“雪谷”。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文本中塑造得最为出彩的人物并非主人公狄云,而是几个坏人形象,尤其是花铁干,这个人物即使拿到严肃文学的人物长廊中也毫不逊色。作者对这个人物显然极其重视,从名字设置上便可见一斑,名铁干,却冠以“花”姓,不无深意。花铁干是以一代大侠的形象出场的,且“一生行侠仗义,并没有做过什么奸恶之事”,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正面大侠在三位兄弟惨死之后,竟在已是不堪一击的血刀老祖心理战术之下屈服,以至跪地求饶,大献谄媚,甚至为求苟生大吃兄弟尸体,为掩盖丑行在灭口不成之后肆意污辱侄女水笙清名,简直卑鄙无耻,令人作呕,堪称小说中的惊人之笔。好端端一代大侠,雪谷一战如何就迅速的走到反面变成大奸大恶之人,对此,文中也给出了相应解释:“今日一枪误杀义弟刘乘风,心神大受激荡,平生豪气霎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受血刀僧大加折辱,数十年压制在心底的种种卑鄙龌龊念头,突然间都冒了出来,几个时辰之间,竟如变了一个人一般。”金庸在此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在正常秩序下被压抑和窝藏着的卑劣人性在特殊情况下骤然爆发的可能,花铁干性情的前后巨变不仅袒露出人性中所固有的弱点及其复杂性,同时也是对社会中普遍认可的文化道德一种质疑,这种在人身上业已形成的牢固的道德秩序不但不能有效地帮助花铁干度过难关,反而成了一种催促其自我毁弃的强大推力,不能不引人思考,这或许正是《连城诀》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反武侠性
武与侠向来是武侠小说公认的两大支柱,新派武侠开山祖师梁羽生曾提出“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主张。金庸在此之前的作品在这两方面都很突出,但到六十年代,金庸开始对传统的武和侠的神圣意义提出质疑,《连城诀》可谓是其突破传统写作模式的发轫之作,直至《鹿鼎记》,这种意识达到顶峰。
首先是侠形象的消解,《连城诀》无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没有一个气宇轩昂的大侠作主人公,狄云是一个不太被评论家和读者喜爱的人物,被陈墨归入“无侠”一类。纵观其一生,他其实常常处于失败的围困之中,他所能做的只是在这些困境中不停地忙着自救,除了要战胜数不清的外敌,还要艰难地对抗自己业已形成几十年的世界观。他原来认识的简单而善良的世界在他面前却完全颠覆,正对邪常常处于下风,以至于让他觉得这个世上最安全的地方反而是穿他琵琶骨的荆州大牢,这是多大的讽刺和悲哀,也反衬出善良主人公的虚弱和丑恶力量的肆虐。总之,这部小说读来并无行侠仗义的快感,而是郁积着一股压抑和苦难的悲愤之气,不得宣泄。
其次是对侠义江湖的解构,在传统武侠中,江湖虽然险恶,但更多的是令人神往的传奇和机遇,盖世神功、快意恩仇与风花雪月,江湖终究会归于一片光明;但金庸在《连城诀》中对此做了一些列的反讽和消解。文本中着力突出的是凡人品质甚至是恶的一面,梅念笙的三个徒弟机关算尽,杀师弃女,为夺宝藏,不择手段;各地英雄豪杰义字当先,共追血刀僧,却个个畏险避难、贪生怕死,雪崩之后,有些人暗暗存有一个念头“南四奇和铃剑双侠,这些年来得了好大的名头,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死得好,死得妙!”。原来所谓大侠和江湖正义之士内心里竟是如此阴险狠毒、卑鄙怯懦,本来应有的侠义光彩荡然无存。有情如丁典和凌霜华生不得同衾,只能寄希望于死能同穴;青梅竹马的铃剑双侠也经受不住流言蜚语,毁于一旦。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如此一个正义不一定必胜,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压抑的江湖世界,带给主人公狄云及读者的感受只是恐惧和厌恶,自由的江湖甚至不如臭气熏天、阴暗潮湿的荆州大牢,以至于主人公最后无奈地选择人迹罕至的藏边雪谷。英雄和理想退居其次,侠义敌不过强权和阴谋,英雄救世的情节被破除,理想化的江湖神话被解构。但反过来说,这样的江湖正是世俗社会某一形态的隐喻和象征,更接近生活和人类真实,同时也是金庸武侠从“侠”的文学向“人”的文学的一次有意靠拢,更多指向的是人性本身和生存意义的探寻,同时也是对传统武侠规范的一种突破和对武侠小说出路做出的一次有益探索。
三、结语
与金庸其他光彩照人的武侠作品相比,《连城诀》确实缺乏纵横捭阖的历史气魄,也没能塑造出脍炙人口的经典武侠人物形象,甚至没有了他一贯注重的文化气息,但这一切并不能抹杀其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独特地位。尤其是作者尝试用武侠小说这种通俗文学形式承载厚重的人文思想,对武侠小说出路和人类生存本身所做出的有益探索,都构成了这部小说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1]金庸.神雕侠侣·后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1431.
[2]金庸.笑傲江湖·后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1451.
[3]金庸.连城诀[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4]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60-161.
[5]陈墨.陈墨评金庸:人性金庸[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34-38.
[6]金庸.金庸散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7]金庸学术研究会.名人名家读金庸[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8]吴晓东,计璧瑞.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孔庆东,蒋泥.醉眼看金庸:北大醉侠点评金庸人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0]倪匡.我看金庸小说:金庸茶馆[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1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2]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3]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查良镛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词[J].通俗文学评论,1997(1).
[14]吕进,韩云波.金庸“反武侠”与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J].文艺研究,2002(2).
[15]缪海荣.“无侠”的江湖:论《连城诀》在金庸武侠创作历程中的价值和意义[J].安徽文学,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