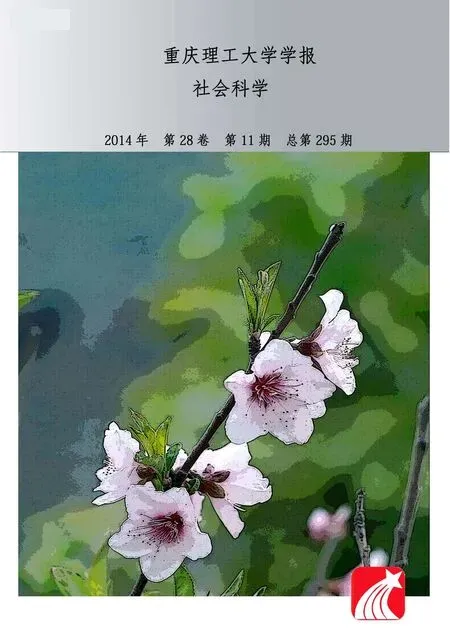“钱学森之问”与教育自由的探讨
2014-03-25朱火弟曾婧婷
朱火弟,曾婧婷
(重庆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重庆 400054)
2012与2013年,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智慧思维学术研讨会”以激发教育发展活力、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水平、坚持智慧学校创建以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主题而召开,教育界人士屡度聚首,试图为破解“钱学森之问”作出新尝试。“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1]2005年,钱学森在病榻上对总理的坦言表达了这位一生为国为民殚精竭虑的科学家对教育事业的极大关注与担忧,由此也产生了引起众多领域研究者热议的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中国的科技与产业发展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已成共识,而钱学森所关注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则是其基础乃至决定性的力量,具体到创造求新的精神、方法和模式。本文主要从办学、教学与求学三个角度来探讨教育通向“自由”的变迁与革新。
一、历史上大师级学者的产生
2000年中国设立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截至2013年共有24位获奖科学家,其中21人是1956年前大学毕业的。纵观中国建国以来60多年教育兴国之路以及近代、古代教育史,可从当期代表性的教育思想中探析未有先进科技的时代却大师级人物辈出的原因。封建社会时期,孔子倡导通过教育传授知识、教化百姓,将教育与人口、经济并视为立国三大要素,欲以德教治国。民国时期,梁启超指出教育目的是为培养有“国家思想”和“公德”,并勇于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国民;蔡元培认为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达到使“共和国民”具有“健全之人格”是教育最终目的;陶行知等在教育界积极践行学生为教育活动中心的思想……教育思想奠定了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使教育科学文化出现空前繁荣,产生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大师、巨匠。钱学森先生曾感慨多年培养的学生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与民国时期的大师相比。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归因于当时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权威性影响,另一方面则因已疲于应对国家战乱的政府无暇对教育过度干预,客观上给了教育界尤其是大学自由创造空间。最初主持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人大都留学回国,对发展教育有殷切希望和献身精神,在早期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历史中成就显著。
交通、通讯相对落后的人类社会早期,杰出人才在小国间竞争激烈的社会条件下涌现并成长,古希腊和春秋时期的中国是典型。各国为生存发展而最需智勇双全之才,会尽力为大批杰出人才的培养及其才能的发挥提供支持,因而国内通常能有比较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
二、中国高校培养“杰出人才”的现状分析
教育文化是民族、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教育观、学习观、人才观等方面形成、积累下来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既有独特和先进性,也有保守和落后性。传统教育文化体现着“政教合一”“学而优则仕”等自古盛行且至今影响社会各层面的思想。这在经济、军事不发达且教育强调德育的时代环境下可以理解——让有智者从政、有德者当政对国家和民族或为幸事。“记诵文化”“条框划定”等观念对稳定社会阶层、缓和阶级矛盾和营造“重教兴学”氛围等具有支撑和维系作用,促使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延续。
借鉴历史,也应意识到现代社会发展模式、技术条件与人才需求等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人才培养文化及制度变迁成为必要。钱学森认为中国大学受封建思想影响,还未能按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上述教育传统已不符合创新价值凸显的社会发展要求,教育却仍受原有人才价值观影响。民国时期大学里一些享誉学界的人物对封建思想有充分的警惕,解放后的大学反而受封建思想影响更深。从早期教育开始迫使学生耗费宝贵精力去掌握本无关高深科学原理却设计得弯绕而不切实际之题的解决技巧,直至消磨掉对知识的天生兴趣。这种教育恰恰以牺牲学生的学习乐趣为代价,长此以往,“人出于本能需要的创造欲望必然降低,更难成为理性信念去自觉超越原有状态”[2]。中国大学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受上级政府垂直管控,受官僚体制和官本位思想直接影响,体现为中国高校发展受各种“统一”束缚。
国家1992年将教育明确作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面性、先导性的基础产业”[3]。许多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步入了“教育产业化”误区。教育本质和目的是什么?持“幸福教育”观点的学者认为“钱学森之问”实质是教育本质问题,将教育重新定位为关乎国民幸福指数的公益事业,学校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基于人自身的发展[4]。近代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曾被视为一种事业、理想和渴望真理的信仰,因而才有众多科学大家的诞生,教育应旨在促进理想人格塑造、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其初衷应是造福他人、社会乃至全人类,而非局限于谋利。
三、如何培养“杰出人才”
(一)办学的自由
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学校、用人单位为各自所求而行动,会最终促使教育效率提高,正如“看不见的手”指引着社会利益的增加。同时,教育市场表现为供求不平衡与正负外部性存在的失灵,使得政府有必要进行适度干预。而现行体制下,政府部门不仅管着高校的人、财、物,还包揽着教学评估、重点学科评审、博硕点设置等具体工作——高等教育被当作公共物品了。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加公共物品供给,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与厂商投资则会减少,进而降低收入和消费,也就降低了政府的税收基础。社会的公共物品增加到一定程度则不能继续增加,否则收效适得其反,将同时减少私人和公共物品供应,甚至导致可能性边界移到无人愿工作、无生产的点。公共物品的提供有上限,那么本非公共物品的东西就更不该由政府来提供了。相对许多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教育水平并不高,尤其是义务教育该解决的农村失学儿童众多等问题仍存在,义务教育是一种由政府提供会更有效的公共品。在对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却把本该作为私人物品的高等教育包揽下来,自然会挤占资源、降低效率。
世界名校办学在意识形态上自由、开放且多元化,耶鲁、哈佛等知名大学多为私立,民办高校更易摆脱行政权力的过分干预,实现自主办学权。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都出自被联合国经济指数调查列为教育水准世界第一的美国,其中80%到90%出自其民办大学。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要想培养出“杰出人才”,其大学要想取得创新意义的发展,就需先摆脱各种“统一”的束缚,让政府有限度地发挥作用。大学将其价值追求及行为取向交由教授和学生自主选择,国家创造良好环境使高校可依据自身认可的逻辑和规律办学。实现高校自主办学意味着从持续发展的角度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其收效和影响远非政府面面俱到的监管之力所能及。为尽量避免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脱节,甚至造成社会危害的情况,政府应坚持制定反映人才需求大方向的教育方针,关注相关部门和学校的执行情况,并推行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杰出人才”的培养中来。
(二)教学与学习的自由
教师在教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学生以怎样的方式学习,这类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教学质量与成果。传统的“教师讲着,学生听着;教师传授,学生接受”使学生对“问题的解决成了对教师、考试设计等外在权威的迎合,而与内在创造本质失去联系”[2]。2013年,教育研究者 Sugata Mitra公布了他1990年起在印度许多经济极其不发达、教育相当落后的地方做的一系列被称为“墙里的洞”实验的成果,即在墙洞里置入存有诸如生物等领域专业知识的计算机与监控器,然后离开那些极低概率会出现懂计算机者经过的地方。数月后,研究者回到实验地,发现当地年龄各异、对此全然未曾听闻的孩子们从发现“墙里的洞”,到因好奇而去揣摩,直至在相互讨论与“教自己”的过程中学会使用计算机,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存在计算机里的专业知识,他们感叹“您这里面都是英文,我们要看懂还得先自学英语”。这正是一个因为好奇、兴趣而主动探索、集体思维、克服困难的无形中近乎全方位自主学习的过程。研究者第一次在数月后返回实验地时,发现孩子们虽对此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摆弄计算机,此学习过程进展却相当缓慢。于是找到当地一位同样对此一无所知的成人,请求她只需站在孩子们背后,说一些表示鼓励和赞赏的话。此后又过数月,实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效果。那成人所为的实质就是关注、认可与激励,这是作为教师有必要做并且可以做到的。即教师启动教育自主化的过程,然后敬畏地退到后面,就引发了探索中学习——学生在没有管制与正式教育的情况下“教自己”和“互相教”,在好奇心、兴趣驱使下成就自主教育的产物。即使在没有任何直接教师灌输的情况下,一个能激励和保护好奇心的环境就能使学习通过自我指导与同龄人知识分享来实现。正如爱因斯坦曾指出的:“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这株脆弱幼苗,除需要鼓励外,主要需要自由,否则会夭折。人在青少年时期好奇心的产生和增强,使人形成并始终保持自己的内心自由,在观念上不受既有理论权威、社会成见和思维定式的束缚,才能取得成功。”[5]所以,当今教师可以是一位提问者、引导者、激励者与建议者,这些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引导学生拓宽知识面与个性发展范围,发现其长处所在而因材施教,适时给予帮助或建议以成就学生的天赋和兴趣。只有符合人们内心冲动和需求的制度安排,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尤指青少年在学习、工作过程中,各种情感、兴趣和目的是其行为动力。学生充分发挥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生命活力,以人类间接经验和自己直接经验为基础,作为主体在思维和实体活动中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活的、有价值的知识,进而服务社会、成就人生。同时,客观实际中的问题往往具有综合性,拓宽知识面对人一生发展意义重大。钱学森先生不仅是科学大师,且在音乐、摄影和绘画等方面都有较高造诣。他认为自己在科学上取得成就,得益于小时候对科学和艺术的多方面学习,培养了全面素质,开阔了思路和视野。
第二,提出问题让学生去揣摩和解决,此过程中培养学生乐于学习、善于阅读、勇于质疑的品质,给予学生自由思考、言行的空间,充分激励其创造力的发挥。当学会运用所学知识来作为安身立命的本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时,学生会将其学习活动指向未来生活的目标而非考试本身,做到课上畅抒己见、课下勤奋阅读,此时教师不是真理宣讲者,而是作为学习活动的组织和参与者,与学生一起能动地在平等探讨中理解和创造,共同进步。
第三,重视鼓励与鞭策学生,特别当其遭遇挫折、信心缺失、止步不前时,培养其承受挫折、承担责任的信心和勇气。马斯洛认为:只有在真诚、理解的师生人际关系中,学生才敢于和勇于发表见解,自由想象和创造,热情地吸取知识、发展能力,形成人格[6]。教师对学生的适时激励与鞭策会促使实现遵循自然规律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与自主发展的智慧教育模式。
本文认为钱学森所指的“杰出人才”应是能够认识人和事物本质、判断其发展变化和处理其是非矛盾,能够有理有据地提出并坚持新想法和观点,富有创新和开拓精神而不拘泥于公认模式去做学问、搞研究与从事相应行业工作,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只有当广阔的自由空间和充裕的自由时间得以实现,青少年、知识分子们研究问题的好奇心和兴趣才不会被扼杀,“杰出人才”才能在自由开放的内外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
[1]查有梁.钱学森给我国教育事业的科学设计[J].教育研究,2009(12):9-11.
[2]刘华杰,崔岐恩.我们的教育有利于创造力的培养吗——对创造力阻滞因素的审视[J].教育发展研究,2010(6):8-11.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EB/OL].[2005-02-17].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17/content_2586400.htm.
[4]张和生.钱学森之问与教育本质问题的探讨[J].求索,2012(4):252-155.
[5]周德海.论大批杰出人才成长和涌现的必要条件——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1):25-28.
[6]王力可.回应“钱学森之问”:让孩子成为完整的“人”[EB/OL].[2013-01-23].http://www.edu.cn/zi_xun_1170/20130123/t20130123_89655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