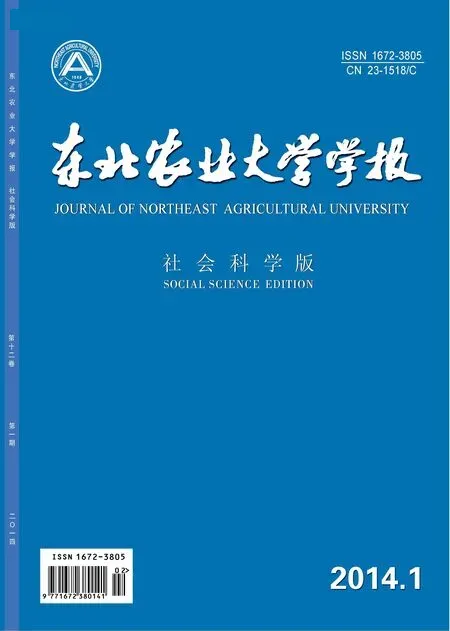上帝与诸神相遇古罗斯
——宗教视野中的《伊戈尔出征记》
2014-03-24刘淑梅
刘淑梅
(黑龙江科技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22)
上帝与诸神相遇古罗斯
——宗教视野中的《伊戈尔出征记》
刘淑梅
(黑龙江科技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22)
《伊戈尔出征记》是古代俄罗斯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虽然已被众多文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等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考证和评注,但总的来说关于这部作品的宗教阐释还不多。在这部作品中体现的是基督教与多神教的碰撞与融合,尽管在10世纪古罗斯就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禁止信仰多神而改为一神,但是在民众心中12世纪的古罗斯基督教并没有战胜多神教,而是二者并存且相互渗透和融合,至今仍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方方面面。
《伊戈尔出征记》;多神教;基督教
一、引言
《伊戈尔出征记》(1185—1187)(《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另译为《伊戈尔远征记》)是12世纪古代俄罗斯文学最杰出作品之一。因其深刻思想内容及独特诗学特征至今仍为俄罗斯人民传诵。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它是“斯拉夫人民诗篇中最美丽、最芬芳的花朵,值得关注、纪念和尊重。”[1]这部古罗斯(又称基辅罗斯)文学作品创作于12世纪末,可是直到18世纪90年代初,《伊戈尔出征记》一个比较早期的手抄本才被当时俄语古文物爱好者和收藏家穆辛-普希金(Мусин-Пушкин)发现,由他整理并于1800年出版。别列维泽采夫(С. Перевезенцев)说:“《伊戈尔出征记》就其罕见的独特性及神秘性而言是古罗斯文学哲学思想的一个奇异的纪念碑。”[2]的确,文学家、诗人、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等都从不同方面对之进行了广泛研究、考证和评注。可以说,自《伊戈尔出征记》手抄本被发现时起,二百多年来,被译成了七十余种文字,研究内容之广更令人惊叹:从历史背景、语言特点、文体特点、作者、文本、重音、翻译等方面入手,已有很多成果,当然其中也不乏对许多问题的争议。
可以说,俄罗斯文字和文学都起源于宗教,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因其蕴含着厚重的宗教精神而成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宗教性是俄罗斯文学特别是俄罗斯中世纪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伊戈尔出征记》也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特点。我国关于这部作品的宗教阐释不多,甚至存在错误观点,比如有的文章里谈及《伊戈尔出征记》中宗教问题时仅看到多神教和基督教这两种宗教斗争,显然有些片面。也许的确如奥勃诺尔斯基(С. Обнорский)院士指出的:“这是古罗斯第一部用文学语言撰写的世俗性文学作品。”[3]但是,其中的宗教思想不容忽视,特别是在那样远古的时代,在古罗斯文化形成之初,因为可能就是这样的思想才能准确地体现出现代俄罗斯民族特征,帮助我们认识和了解俄罗斯。
在接受东正教洗礼之前,古罗斯人经历了自然崇拜和多神教信仰时期,然而自988年罗斯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起,表面上看多神教的罗斯终于转变为基督教引领下的“神圣的罗斯(святая Русь)”,似乎与多神教的民族传统断裂了,而事实上在人民意识深处多神教没有彻底消亡,而是如春雨润物般淡淡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与占主流的基督教不断碰撞,而且其中有的部分被保留下来并与基督教融为一体。这样,11世纪便出现了罗斯的“双重信仰”和“双重文化”现象。笔者认为,在《伊戈尔出征记》中突出地展现出多神教与基督教的碰撞与融合这一主题。
二、无处不在的多神教
马克思在评论这部作品时说过:“整首《远征记》具有基督教的英雄性质,虽然其中也有鲜明的异教因素。”[4]这里的异教因素现在看来主要指的是多神教。
在《伊戈尔出征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与多神教的碰撞与融合。这部作品写于12世纪,在罗斯受洗二百年之后。俄罗斯民族皈依了基督教,准确地说是皈依了东正教,因为随着东西罗马的分裂,在1054年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正式破裂,产生了东正教和天主教,1453年拜占庭灭亡后东正教没有灭亡,主要被保留在俄罗斯。“对于基督教,国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5],此时基督教作为国教的地位已经确立,多神教诸神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没有人可以保证让原初多神教思想立刻从人们头脑中消失,人们意识中依然保留着某些多神教的印迹。当时古罗斯多神教信仰的主要内容是万物有灵论。更多时候,古罗斯人将自然现象视为神灵,对其顶礼膜拜。古罗斯人相信这些自然神灵会施展魔法,显示神迹,可以保护人们免于灾难和困苦。特别是在古罗斯时期,人民在现实生产实践中看到有些自然现象可以帮助生产活动,而有些自然现象却阻碍甚至破坏生产活动,使其勤勤恳恳创造的一切都毁灭。由于当时古罗斯人对世界认知水平有限,科学发展极为落后,因此他们对大自然中各种现象和变化极为关注,对大自然中一些异常现象更是诚惶诚恐。所以,不难理解古罗斯人会把很多自然现象神灵化,风雨雷电、花草树木、日月江河都成为古罗斯多神教信仰中的崇拜对象。
由此看来,在罗斯受洗之前,“大自然与各种自然现象是斯拉夫-罗斯人及其他民族的宗教基础”[6]。当时的百姓崇拜各种自然现象,信奉很多神,崇拜偶像,比如水、火、地、风、雷、太阳等等。除了太阳神达日博格(Дажьбог)、大地润泽的母亲及女性劳作之神莫科什(Мокошь)、雷神佩龙(Перун)、风神斯特立博格(Стрибог)、火神斯沃罗博格(Сварог)等之外,还有树精(Леший)、水妖(Водяной)、水仙(Русалка)、护林神及家神(Домовой)等等。与古希腊人民相似,俄罗斯人的祖先曾经深信不疑的是,在自然界中威力无比的统治者时时处处都在,他们有的善良和蔼,有的凶神恶煞。古罗斯人一般把所信奉的神明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创作自然之神,另一类神则代表着祖先们的灵魂。在古罗斯人的民俗中、文学作品中、雕塑中、北方少数民族的刺绣作品中都经常可以看到这些神明的象征图案,他们通常会把自己所信奉的诸神雕塑在木头或者石头上,用来避邪或者祈福。
古罗斯在受东正教洗礼之后,自上而下地让古罗斯的百姓接受了一神教信仰,原始自然宗教必然会改变最初形态与很多内在的精神质素。具体地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洗礼之后立刻着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力兴建教堂和发展国民教育事业。比如他在雕刻有雷神的木雕建筑旁边修建了天使圣瓦西里教堂,毁掉了大多数的神像雕塑,保持完整的只有少数几尊笨重的“扁脸女人石雕”;还专门建造一些学校让男孩子们去学习翻译成斯拉夫语圣书,但是这些男孩子去学习圣书是被强迫的,家长们也都不情愿,因为当时的人们仍然坚信文字一种巫术的书面表达方式。因此,一想到这里,这些家长们就仍然会绝望地失声痛哭起来。尽管在接受东正教之后很多神像雕塑被破坏,人民外在的被迫顺服与内心的坚决反抗势必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矛盾冲突,而这种冲突也必然在文化上留有痕迹。因此,受洗一个多世纪之后,在古罗斯的宗教生活中仍有多神教烙印,也就不足为奇了。
多神教的影响在《伊戈尔出征记》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这部英雄史诗性的作品创作于罗斯受洗一百多年之后,作品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作者广泛运用大自然主题的表现形式,使大自然在充满了灵性的同时再现了多神教中各种古老神灵。随处可见的是,大自然中的万物在《伊戈尔出征记》中是鲜活的、有灵魂的,也是参与到俄罗斯人现实的历史生活中的存在物。伊戈尔率兵出征的时候,动物们似乎领悟了上苍启示,都急忙向队伍发出了警示:
“鸟儿在橡树上窥伺灾祸;
豺狼在幽谷里嗥起雷雪。”①文中作品的引文均出自《伊戈尔出征记》,李锡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与大军出发之前出现日食的天象相比较,动物们的预警更能表现它们直白和迫切的心情,预示着未来可能要发生的不幸。不仅如此,文中还把大公们直接比作动物:
“他们纵马如飞,
好似原野上的灰狼”、
“‘莽牛’符塞伏洛德!
只见你一马当先,
泼水般溅出万枝神剑”、
“啊,雄鹰!你飞得太远了。”
当伊戈尔从被俘处出逃时,动物们再次积极参与到英雄的命运之中,它们为伊戈尔或者探路,或者放哨,或者引导,或者欢呼:
“啄木鸟用自己的叩啄声指引通向河边的道路”
“水面上的白颊凫、急流中的海鸥、天空中的野鸭替他守望”。
在古罗斯人的意识里,人与动物的关系不是主宰与被主宰关系,而是平等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客体,因此在人遇到灾难的时候动物作为天然盟友必然会出手相助。也正是这个原因,此时的伊戈尔甚至被赋予了丰富的动物性:
“他一会儿白鼬般窜身芦丛,
一会儿野凫般浮到水面;
一会儿快马加鞭,
一会儿跳下,
狼也似地奔跑,
直奔顿涅茨河湾。”
这种将人动物化的描写体现了12世纪古罗斯时期多神教对历史生态风貌的影响,表现了在古罗斯人意识中人与动物相互依存的关系。
另外,史诗中还把他们比作其他的自然界客体,如天空中的太阳,说“两个太阳暗淡了”,这同样预示了伊戈尔的这次远征在先民意念中是悲剧性的,这里将自然现象人性化还折射出作者人道主义理念、对国家保卫者们强烈的爱及对其命运的关注与担忧。
相比之下,在作品中植物形象虽然不如动物形象那样丰富和充满灵性,只出现了几次,但是植物形象同样与人的心情和境遇融为一体,体现了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比如,在伊戈尔出征失败的时候:
“青草同情地低下头来,
树木悲凄地垂向地面。”
在伊戈尔出逃的时候,“野草在沙沙作响”为他打掩护,担负救助英雄的使命,而青草地和绿树荫则温柔地爱抚疲惫的英雄。由此看来,在《伊戈尔出征记》这部作品中,整个宇宙都是和谐的,花草鸟木和走兽飞禽不仅在形式上与人共存,更是在灵魂上与人相通,是决定人命运的重要参与者和直接帮助者。人、动物和植物在自然界中唇齿相依、互为盟友。
多神教诸神从自己的功能上来说是与大自然力量有着相互对应关系的。“当伊戈尔大公凝聚当地‘诸神’力量回到基辅的小丘时,他经过了精心挑选,他们都与大自然力量相关,首先就是火、水、大地和风。”[7]而他赶到顿涅茨河时,河水发话了:
“伊戈尔公呀!
莫大的荣誉归于你,
康恰克该受轻视,
罗斯大地将得到欢愉。”
伊戈尔大公被俘之后,他的妻子雅洛斯拉夫娜在哭诉时,哭诉的对象不是上帝或者圣母,而是三个自然界的神灵:风神、河神、太阳神。这位王公夫人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显然是多神教的,没有丝毫基督教观念。以上不难看出,这些自然界中的诸多形象,各位神仙,不仅仅是装饰文本、使之充满诗意的手段,它们在文本中频繁而充分的使用还证明了作者生活在受多神教影响的世界里,他用这些形象去思维,并借助它们去描述那一时代现实。
完全可以说《伊戈尔出征记》中“显示出俄罗斯人的民间多神教世界观”[8]。至此,多神教的诸神在《伊戈尔出征记》中的地位已清晰可见。9—13世纪古罗斯多神教是俄罗斯中世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就无法理解俄罗斯乡村和城郊民族文化,也无法理解俄罗斯封建主义鼎盛时期复杂多面的文化,雷巴科夫(Б.А.Рыбаков)曾指出,在《伊戈尔出征记》中“渗透了民族多神教的世界观,并且比文艺复兴时代的诗歌更早地去关注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9]。
由此可见,罗斯受洗之后多神教时代虽然表面上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多神教并没有完全消亡或者说立即衰落。在广大人民模糊的潜意识深处,多神教像是被保留到了某个历史地下室中,依然继续着隐秘生活,这样在现实生活中自然就出现了信奉两种宗教现象。后来也有人说实际上形成了两种文化,即“白昼文化”和“黑夜文化”。因为在现实中,外来的拜占庭基督教文化不可能马上就成为“全民的”文化,它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少数文化人的财富。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白昼基督教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完全而彻底地包容全部的俄罗斯精神命运。在社会的下层一定存在和发展着“第二种文化”,这种文化主要源自俄罗斯本土多神教的传统,只是后者是隐秘地流传,在历史的表层很少突显出来,可是在历史的表层之下,人们却时常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
三、作为主旋律的基督教气息
如引言中奥勃诺尔斯基所指出的,《伊戈尔出征记》是俄罗斯第一部用文学语言撰写的世俗性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事件。作品中不仅记述了古罗斯国王公伊戈尔出兵征讨游牧民族波洛夫人的真实历史事件,更极力赞扬了伊戈尔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这里也表现出作者支持诸大公们团结,反对异教异族分裂思想,而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中忠实于上帝反对异教思想、与基督教中弥赛亚意识紧密相连。
在基督徒的心中,上帝是全能者,是全宇宙最有能力的一位惟一的神,他的力量无可匹敌、至高无上。未来的新世界邪恶、战争、罪行和暴力都将消逝,天下都会太平,因为上帝将要“平息战争,直到地极”(《圣经》以赛亚书第2章第4节)。
启示录情结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内核,而其中更重要的是包含了弥赛亚救赎意识。因为在俄罗斯人民的自我意识中,坚信自己是诺亚的子孙后代,东西罗马灭亡之后,莫斯科便是第三罗马(也被称为“神圣罗斯”)了,认为自己与犹太人一样是被上帝拣选的弥赛亚民族,肩负有拯救世界的使命。在基督教《圣经》的《新约》部分,上帝用自己独生爱子耶稣自我牺牲为赎罪祭,洗清了世间凡人所有罪过,耶稣就是救世主、受膏者的意思,是弥赛亚。因此,从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之日起,俄罗斯人便从基督教那里接受了宗教拯救观念。
胆碱(Choline)广泛存在于植物界及人和动物体液内,是生物体代谢的中间产物。富含胆碱的食物有蛋类、动物的脑、动物心脏与肝脏、绿叶蔬菜、啤酒酵母、麦芽、大豆卵磷脂等。胆碱属B族维生素,是目前世界公认的14种维生素品种之一。胆碱现以化学法合成。
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作为一种宗教,基督教使受洗后的古罗斯封建化加速。同时,接受基督教文化也拉近了古罗斯与西欧国家的距离,使古罗斯很快成为中世纪比较先进的国家之一。可好景不长,在罗斯发生了内讧,同时,游牧民对罗斯的侵略越来越频繁。内讧使罗斯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受到严重阻碍。公元12世纪末,各公国林立,古罗斯失去了往日强盛,封建割据的局面已然形成。罗斯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是国家却依然出现了封建割据局面。可见,宗教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未能阻止古罗斯国家权力分散,也未能缓和社会经济的尖锐矛盾。借着罗斯诸大公之间纷争不断的矛盾,波洛夫人趁机不断进犯罗斯领土,严重影响了罗斯人的正常生活和国家形象。历史上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率领诸大公曾经猛烈回击过波洛夫人,但是波洛夫人又经常利用诸大公之间内讧卷土重来。所以,各大公之间的团结变得尤为重要。
伊戈尔的出征是为了保卫罗斯不受异族侵犯,表现的是一种爱国主义,也表现了伊戈尔反对异教的思想。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敌人不仅出于爱国之心,还有明显宗教原因。格奥尔吉耶娃就曾经指出,在《伊戈尔出征记》这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当时几位都主教强烈号召各位王公停止内战并严厉回击波洛夫人进攻的事实:
“先生们,快登上战马奔向前……
勇敢地去为罗斯而战!
快用你们手中那锐利的弓箭/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
在当时罗斯人和伊戈尔大公的宗教意识中,游牧民波洛夫人是异教徒,因此伊戈尔出征是为了基督教利益,为了捍卫基督教信仰,伊戈尔和众将士心中装着基督,盼望的是上帝恩典。他们大无畏的勇气也来自于基督徒对异教徒的仇恨。
在这部作品中有一个重要角色——上帝,贯穿于《伊戈尔出征记》全文。正如前面马克思所言,整首《伊戈尔出征记》有基督教性质。首先,全诗在形式上采用宗教文学典型的“讲话”(“слово”)体裁,并且以“阿门”作结,整体上使人感受到了基督教气息。卷首便直接用基督教教会举行宗教仪式前惯用的对教徒的称呼“弟兄们”开始,作者讲述内容就像牧师对虔诚的信徒布道一样。特别是文中借先知(Вещий)博扬的话说:
“不管多么机灵,
不管多大本领,
博扬本是一个歌手,通过作品中提到他歌颂过王公们的事迹可以判定,11世纪下半期他仍然活在世上,而此时基督教已经在罗斯传播一百多年,博扬信仰上帝,才会说出前面那番话。这里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博扬是“维列斯的子孙”,维列斯是多神教中牧人之神和诗歌之神。那么,博扬既是多神教的后代又是基督教信徒,也就是说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因素在歌手博扬身上结合在一起了。
如果文中这一处证明基督教作用力度还不够的话,那么接下来,在临近结局时出现的两件事则关键且意义重大。伊戈尔在被俘后,本无望返回家乡,但是:
“上帝给伊戈尔指路——回罗斯故土去,
回到祖传的宝座去,
从波洛夫草原出逃。”
在伊戈尔成功出逃,回到罗斯后,他首先来到毕洛戈什圣母大教堂,而此时众人喜悦,山河欢腾。歌唱老一辈公爵,也歌唱年轻诸公:
“光荣呀,戈列伊戈尔·斯维亚特斯拉维奇!
光荣呀,符塞伏洛德和符拉季米尔·伊维奇!
向你们致敬,为正教事业而与污秽之众战斗的公爵和亲兵!
光荣归于公爵和亲兵!阿门。”
特别是最后结尾处那句点题的诗句:
“那卫护基督教徒、反对邪恶的军队的王公们和武士们万岁!”
更是明确地表述出罗斯人是基督徒,入侵的波洛夫人是异教徒,并形容伊戈尔的军队是“勇敢的”,波洛夫人则是“邪恶的”。作者把伊戈尔大公等出征将士称为“正教事业”而与“污秽之众”战斗的勇士。这一点值得思考,之后便不难猜出,这里的“正教事业”显然是基督教,而“污秽之众”则指多神教。
四、基督教与多神教的碰撞和融合
正如别列维泽采夫所说的:“《伊戈尔出征记》证明了12世纪以前俄罗斯人心中存在着多神教与基督教信仰。”众所周知,俄罗斯民众接受基督教是强制性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于公元988年发布诏令宣布,凡俄国臣民,在接到诏令后,必须立即去第聂伯河中受洗,以表示其皈依基督决心。违背者和逾期不至者,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也无论乞丐还是奴隶,都是他的仇敌。
然而,人民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内心却无法完全根除古罗斯多神教意识,基督教教会认识到这个问题后,也不得不迁就多神教。有的多神教信仰还被保留下来并与基督教融为一体。比如,在宣传新的基督教时,把大地润泽的母亲及女性劳作之神莫科什(Мокошь)拿进来崇拜,教会的神职人员去主持多神教的仪式等等。那时人们对上帝的观念是模糊的(这也难怪,因为17世纪才有斯拉夫语版的《圣经》),就前例而言,尽管是上帝指引伊戈尔返回故乡,但返乡后的庆祝行为却是通过多神教方式表现出来的:是山河欢腾,歌唱伊戈尔及其亲兵。
任光宣曾经指出:“在当时的古罗斯,基督教和多神教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未解决,这就形成了罗斯社会的双重宗教信仰现象。”[10]但在《伊戈尔出征记》中,伊戈尔及其军队所遭受的不幸都是在多神教神话征兆的伴随下发生的,而最后拯救伊戈尔的却是基督教的上帝。是上帝指给他出逃之路,当他返回到毕洛戈什圣母大教堂时,快乐也随之来到国家与百姓之中。这样的结局似乎就意味着基督教对多神教的胜利,一神对多神的胜利。伊戈尔大公本身就是罗斯的基督徒,因此,他的出征从另一种形式上来说也是罗斯基督教反对异教的表现。正如《伊戈尔出征记》的作者呼吁年轻一代的公爵不要为自己的荣誉而战,而应为基督而战,不仅反对波洛夫人,还要反对多神教徒。因为“поганый”一词不仅仅有“异族的”之意,在古俄语中还有“多神教徒”“偶像崇拜者”的解释。至此,《伊戈尔出征记》中俄罗斯人民的基督教世界观可见一斑。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说:“基督教的诞生永远地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面貌。”②George Sarto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M].Baltimore:Williams and Wilkins,1927.转引自[美]施密特(Alvin Schmide).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同样,接受基督教对俄罗斯影响也很大。当时,随着对基督教接受的广泛和深入,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使整个俄罗斯公国意义增强,特别是加强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权利,促进了古罗斯公国文化发展、繁荣,也因为有了共同的宗教而使古罗斯与欧洲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可是,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多神教已经消失,因为这种信仰曾经存在过,所以在人民的记忆中、在生活习惯上,在人民气质上还长久地保留着它淡淡的,但有时又是十分独特的痕迹。当时的罗斯虽然受洗,但是宗教教育还很缺乏,这样罗斯的基督教化会在漫长的数百年里与原来的多神教传统斗争和融合。以至于后来的俄罗斯东正教在很多方面都留有多神教传统元素,比如宗教仪式、圣物崇拜和圣徒崇拜等等。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在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平原上高耸着许多教堂,挺立着无数圣者和长老。但这片土壤仍是自然主义的,生活仍是异教的。”[11]简单地说,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古罗斯人日渐形成的多神教崇拜已经稳定地在民间保存下来,而现实的俄罗斯人精神生活中,又把系统的基督教意识和观念确立为国教,这便是《伊戈尔出征记》出现双重信仰的原因。
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俄国思想家布尔加科夫已经能够正视基督教在俄罗斯大地上融合并吸纳很多多神教元素的历史事实,作为东正教神甫他却非常推崇多神教中“神秘的敏锐洞察力”,认为“多神教”与“上帝”二者的关系在于前者是通过有形物认识无形物,通过具体世界来认识后者,在受造物中发现后者。当然,布尔加科夫的这种观点遭到当时俄国教会的严厉批评,然而事实上,正是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使俄罗斯的基督教具有别样的活力,同时具有了俄罗斯民族的固有特征。
在《伊戈尔出征记》中即使有基督教战胜多神教意识,也是浮在表面的一种胜利,基督教与多神教、上帝与诸神不仅在12世纪古罗斯相遇,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恐怕现在、甚至将来仍然会存在。比如,直到今天,俄罗斯人还保持了这样一个传统:每逢复活节,他们都把受洗礼的鸡蛋当作贡品带到亲友墓地。另外,作为节日,谢肉节也是多神教时代流传下来的习俗之一。而基督教先知伊里亚的形象与雷神的形象融汇一体,圣徒莫杰斯特、弗拉西和格奥尔吉都成了畜业守护神。圣母玛利亚在基督教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圣母崇拜的基础便是对古代繁殖女神的膜拜,圣母形象,如同母神形象一样,是土地、土地的孕育力和一切繁殖力的化身。基督教的很多节日也定在多神教农历节日上,与农业劳动特定阶段相吻合。
五、结语
宗教本身充满了使命感和弥赛亚意识。在《伊戈尔出征记》中,多神教和基督教这两种看似对立的信仰在拯救民族英雄、拯救国家罗斯和人民的使命中实现了统一。全世界对于这部俄罗斯古代文学经典之作的研究已有二百多年,成果丰富多样,本文只是对《伊戈尔出征记》相关研究的补充和再认识,尚不能够诠释这部作品的全部宗教特色。后续研究拟分析神话批评视域下《伊戈尔出征记》的宗教特点,特别是其中的母题“俄罗斯大地”(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宗教神话的统一性,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都离不开看似对立的多神教和基督教。
其实,无论是否愿意承认,多神教和基督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影响着俄罗斯,已经不用也没有必要一定让二者决一胜负,也许正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宗教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言:“我觉得世界上存在两种真理:基督教关于天国的真理和多神教关于大地的真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天和地的真理合二为一,那才是宗教的至臻完美境界。”[12]
了解了这些,或许就可以更多地理解俄罗斯、俄罗斯民族性以及俄罗斯人。从古罗斯到俄国、到苏联、再到俄罗斯联邦,作为中国最大的近邻,俄罗斯有太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赫尔岑说过:“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13]这也可视为挖掘古代文学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
[1]任光宣,张建华,余一中.俄罗斯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Платонов О А.Святая Русь,Больш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M].Мockва: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04.
[3]左少兴.《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评介[J].中国俄语教学,2003(3).
[4]伊戈尔远征记[M].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格奥尔吉耶娃Т.С.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Колесов В В.Язык и ментальность[M].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2004.
[8]金亚娜.期盼索菲亚——俄罗斯文学中的“永恒女性”崇拜哲学与文化探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9]Рыбаков Б А.Язычество древней Руси[M].Мockва:Наука, 1988.
[10]任光宣.《伊戈尔远征记》及其表现的双重信仰[J].国外文学, 1994(1).
[11]别尔嘉耶夫.《别尔嘉耶夫集》[M].汪剑钊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12]郑永旺.梅列日科夫斯基“第三约”研究[J].哲学动态,2010(9).
[13]张建华.俄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I106
A
1672-3805(2014)01-0072-06
2013-03-04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什梅廖夫小说的宗教文化思想研究”(12532015)
刘淑梅(1975-),女,黑龙江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