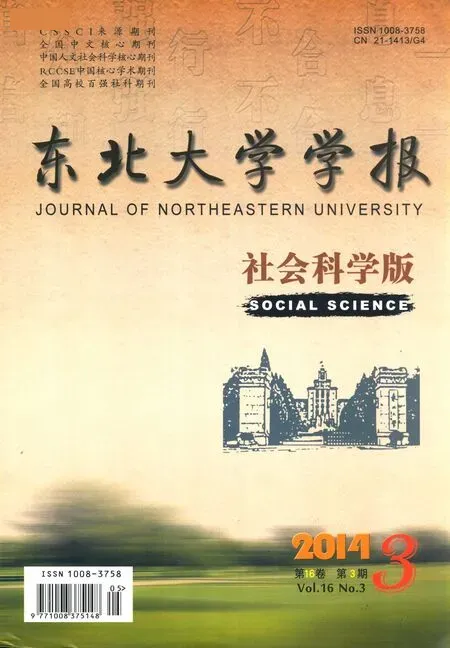道德运气与刑罚分配:问题与出路
2014-03-22马乐
马 乐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自从威廉姆斯和内格尔提出“道德运气”这一概念以来,它一直是伦理学家们热议的论题。事实上,关于道德运气的讨论已不再局限于伦理学领域,其理论影响已经延伸到了法律领域。对道德运气问题的理解与回应从根本上决定着我们对相关法律问题的态度。针对刑法学而言,只要我们仍将以道德应得(moral desert)为基础的报应视做刑罚不可或缺的正当性根据,道德运气问题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对于现有刑罚分配中的诸多问题的反思而言,道德运气问题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本文试图以道德运气概念为核心针对两类问题展开分析:第一,运气是否影响道德应得并导致刑罚分配的差异?第二,我们应对现有刑罚分配模式作出何种变革?
一、运气与道德应得
人类生活中的行为和事件总是由人们可控制的和不可控制的因素共同塑造的,我们将这些不在行为人控制能力范围内的因素称作“运气”。根据内格尔的定义,“凡在某人所做之事有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我们仍然在那个方面把他作为道德判断对象之处,那就可以称之为道德上的运气”[1]28。道德运气之所以成为问题,在于它揭示了人们普遍持有的道德信念与道德实践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人们直觉地确信,任何人都只应在他控制能力的范围内对行为承担道德责任,运气不应影响道德应得的判断。因行为人无法掌控的情形的出现而在道德上赞赏或谴责他则是违背我们的道德直觉的。正如我们不会要求行为人对在精神病发作时实施的伤害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因为伤害行为不能被视做他自由意志的选择。另一方面,“在道德实践中,正如内格尔和威廉姆斯所说,人们的确部分地按照运气这种主体不能控制的因素来评价主体及其行为,给予他们赞扬、谴责、奖赏、惩罚”[2]。例如,两个同样闯红灯的莽撞司机,一个不幸将人行道上的行人撞死,另一个则因为行人躲避及时而平安无事,我们通常强烈谴责前者,而对后者却表现出更多的宽容。然而,在实施了同样莽撞行为的前提下,司机是否将行人撞死完全取决于行人是否躲避及时这样一个其无法掌控的因素,两人仅因运气好坏的不同而获得了不同的道德评价。这显然与上述人们关于道德责任的理解存在冲突。所谓道德运气的难题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并解释这一悖论性现象?
在伦理学领域,主流性的见解主张通过对上述道德责任概念作出修正甚至否定以解决道德运气悖论。坚持道德责任应当免于不可控的运气的立场源于康德式的道德信念,它“强调道德‘应当且能够’免于意志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干扰,如此方能彰显道德的尊严和价值,从而彰显人的尊严和价值”[3]。威廉姆斯和内格尔等人的初衷也正是借道德运气现象批判甚至颠覆康德式的道德责任概念。在威廉姆斯和内格尔等人看来,康德式的道德责任概念扭曲了伦理生活的真实样貌,它是一种纯粹理想化的抽象观念,事实上,道德评价不可能免于运气的影响,运气具有道德价值。道德运气有多种样态,可以将其粗略地划分为两类:即境遇性运气和结果性运气[4]。前者涉及行为人作出行动决策时无法选择的客观境遇,如身体状况、脾气秉性、生存环境、性倾向等。境遇性运气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所谓自由意志并非是不受限制的,行动的意愿同样受到运气的影响。如后文将论及的,得到当代学者普遍认同的“期待可能性”概念涉及的最深层次问题正是境遇性运气。
结果性运气关注的则是行动结果的偶然性,如前述莽撞司机案例所表明的,人们基于有限的自由意志作出的行动决策并非是行动结果的全部原因,结果如何仍取决于诸多行为人无法控制的因素。结果性运气与刑法学的关联颇为紧密,这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刑罚制度是建立在对“理性人”的假设上的,即便绝对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也不影响我们将刑法的对象视做能够自由选择守法或违法的理性个体;第二,结果性运气对刑罚分配的影响十分明显,且被各国刑法实践所认可。侵害结果是否发生,不仅影响刑罚的轻重,甚至会决定刑罚的有无。例如,对故意杀人未遂的处罚通常要比故意杀人既遂的处罚轻得多。设想甲和乙的杀人意图及行为完全相同,其中甲既遂,乙则因为恰好有一阵狂风将子弹稍微吹离原有轨迹而未遂。毫无疑问,甲和乙将面临迥异的刑罚分配,而这种差异完全是运气所决定的,两人对结果是否发生的掌控程度并无差异。在刑罚分配中,本文主张弱化结果运气的角色。笔者认为,行为人对法益所持的态度(敌视或疏忽)及由此态度支配的行为本身构成了其道德应得的全部根据。至于结果如何,并不影响道德应得的轻重或有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仅因缺乏侵害结果而减轻或免除处罚是无法从道德应得的差异性上得到证成的[5]。肯定诸如“一阵狂风”这种纯粹偶然的因素对行为人的道德应得产生影响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就刑罚分配而言,康德式的道德信念是不可舍弃的,因为“正是康德式道德责任概念,使人们不至于偏离公平,不至于因为境遇性运气、飘忽不定的结果性运气,而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和打击”[2]。刑罚是一种不得已的恶害,它意味着对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的剥夺,这决定了我们必须以严肃、理性的态度对待其适用,过分依赖盲目运气的刑罚分配模式是难以经受深刻的理论反省的。笔者认为,所谓道德运气悖论源于我们对受运气影响的日常道德评价的真实性质的误解。
二、道德运气的破解
威廉姆斯等人以行动者之憾(agent-regret)的存在为由肯定运气的道德价值。例如,将行人撞死的司机通常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和自责,而未撞到人的司机则常常缺少此类情感反应。在威廉姆斯看来,“既然行动者对自己的行动感受到行动者遗憾,就证明了运气能够影响行动者的道德情感和自我道德评价。因此,运气具有道德价值”[6]。刑法学者们也通常以此为由来为既遂犯的处罚普遍重于未遂犯提供辩护。根据这种见解,当侵害结果发生的场合,一方面,被害人及旁观者对行为人表现出更强烈的憎恨和厌恶;另一方面,行为人也往往怀有负罪感。因此,道德应得的轻重理应受结果的影响,以此为依据的刑罚分配也是正当的[7]。
在笔者看来,以上论述暗含着对日常道德评价的真实性质的误解。侵害结果的发生固然会引起憎恨、厌恶和自责,但此类情感的存在与行为人的道德应得并无必然的关联。事实上,即便是无道德过错的行为也同样可能引发此类情感。设想一位父亲将女儿送去国外留学,而女儿恰恰在飞往目的地的航班所发生的空难中丧生,不难想象,这位父亲或许会因他的决定而永远陷入痛苦的自责中,即便他对女儿的死亡并无任何过错可言。由此可见,侵害结果的发生所引发的憎恨和自责并不等同于道德性的谴责,它可能与行为人的道德应得无关。例如,上述情形下的情感反应显然与道德性的谴责无关,而是在转嫁悲伤[8]。与此同时,在未发生侵害结果的场合,类似情感反应的缺失也不意味着行为人缺乏道德应得。与既遂犯和造成侵害结果的疏忽行为相比,公众对未遂犯及无侵害结果的疏忽行为表现出的宽容并不是因为行为人的道德应得有所不同,只是这类行为并未引起同等程度惩罚意愿。
由此可见,我们完全可以在坚持康德式的道德责任概念的同时对道德运气现象作出合理解释:我们关于道德责任应当免于运气的信念与道德实践中以运气为主导的评价模式的冲突只是表面的,它源于我们对相关道德评价的真实性质的误解。一方面,在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并导致了侵害结果的场合,人们表达道德谴责的意愿更为强烈,这种及时且强烈的道德谴责对于表达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尊重而言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道德谴责意愿在缺乏侵害结果的场合则不那么明显,于是便产生了结果运气影响道德应得的错觉。另一方面,结果所引发的额外的憎恨和自责正如我们在听到美妙音乐时感到的愉悦或看到某类食物时感到的厌恶那样是非道德性的。由结果引发的谴责并非纯粹的道德谴责,而是掺杂了厌恶、痛苦情绪的宣泄。与此同时,在缺乏侵害结果的场合,取而代之的则是庆幸、宽慰的感受,谴责强度也理所当然地减弱了。这再一次给人造成运气影响道德应得的错觉。总之,运气影响的只是人们进行道德裁决的方式与强度,而不是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
三、道德运气与刑事责任的认定
如前所述,“结果是庆祝和悔恨的恰当对象,但只有行为本身才应当是道德赞赏和谴责的对象”[9]。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憎恨、悔恨和庆幸等情感并不因为其“非道德性”而丧失正当性。毕竟,现实生活并非只有单一的维度,道德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非道德性的理由也时刻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塑造着我们的生活。问题在于:既然这种非道德性的情感与道德应得无关,那么它是否应当影响罪责的判断和刑罚的分配?对此问题,我们必须区分不同情形加以回答。限于篇幅,本文仅拣选几类典型问题展开论述,权当抛砖引玉。
1.作为刑罚上限的道德应得
由结果运气导致的憎恨情绪不可作为超过行为人的道德应得进行加重处罚的依据。以侵害结果作为加重处罚理由的刑罚分配模式体现的是一种粗野的复仇式的报应观,这种刑罚观与强调人权保障、平等公正的现代刑法水火不容。将刑罚视做犯罪人对侵害结果的“补偿”或“赎罪”的观点是一种缺乏现实意义的形而上学式的说辞。遗憾的是,令犯罪人超过其道德应得对侵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现象在现代刑法制度中并不少见,各国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即是典型例证。
“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过重,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10]这种处罚“过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乃至现在,不要求对加重结果具有故意与过失的立法、实践与观点仍然存在”[11]194。例如,日本判例所采取的立场正是:结果加重犯的成立不以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存在过失为前提,而只需要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此种立场在日本理论界也不乏主张者。又如美国各州刑法普遍规定了“重罪谋杀罪”,依照此规则,当犯罪人在实施抢劫、入室盗窃等重罪的过程中致人死亡时,即便其对死亡结果没有故意甚至完全无预见可能,也同样成立谋杀罪[12]。这实际上就是突破行为人道德应得的上限实施刑罚分配。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同样存在此类问题。虽然学界一直主张行为人必须对加重结果有过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出现因行为人对加重结果不能预见而对加重结果不承担责任的案例”[11]196。另一方面,即便要求结果加重犯的成立以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有过失为前提,“其法定刑却远远重于基本犯的法定刑与过失犯的法定刑之和”[13]。以我国《刑法》中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为例,其法定刑与故意杀人罪并无实质差异。然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行为人对死亡结果仅有过失,这与故意杀人在罪过上有质的差异,仅以加重结果为依据对其适用与故意杀人罪相当的刑罚显然超过了犯罪人道德应得的上限。总之,在行为人实施了相同的基本犯罪的前提下,是否成立结果加重犯完全取决于结果运气,现有刑罚分配模式严重违背报应正义,亟待反思和纠正。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刑法中之所以死刑罪名泛滥,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结果加重犯的死刑规定过多[14]。因此,在中国语境下,强调道德应得作为刑罚的上限、排斥结果运气对于削减死刑并从根本上扭转重刑主义倾向具有特殊意义。
2.惩罚意愿的减弱与未遂犯的处罚
由结果运气导致的惩罚意愿的减弱可以作为对犯罪人施加少于他道德应得的刑罚的理由。例如,比照既遂犯对未遂犯减轻处罚是被允许的(但不是必须的)。道德应得虽划定了刑罚的上限,但不意味着道德应得必须不打折扣地转化为等量的刑罚。如前所述,在未遂的场合,人们的惩罚意愿不如对既遂犯那样强烈,以此为由减轻刑罚来表示对犯罪人的宽容也是一种在道德上令人欣慰的态度。这种见解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关于未遂犯的论述,依据柏拉图的主张,杀人未遂者“应当同杀人者同样处理,以谋杀罪受审。但我们必须给把他从全部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好运以充分的尊重,并且也尊重他的守护神,是守护神怜悯攻击者和受伤害者,使后者免受致命的伤害,并把使人受伤的人从悬于其颈上的诅咒中及悲惨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我们应该充分感谢他的守护神而不去阻碍它的期望:那个使人受伤的人将免于死刑,但是他必须终身被驱逐到某一邻国去”[15]。抛开其中的泛神论观念,柏拉图在此处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见解:我们有正当理由(甚至有义务)因好运气而对未遂犯网开一面,因为他毕竟没有造成令我们痛苦和愤怒的侵害结果。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宽容与犯罪人的道德应得无关,未遂犯的道德应得并不轻于相应的既遂犯。换言之,如果单纯从报应正义的角度看,既遂犯和未遂犯理应得到同等处罚。因此,只要刑罚的程度并未超过犯罪人的道德应得所设置的刑罚上限,基于功利论的考量将未遂犯和既遂犯同等处罚就不违背报应正义。例如,对于以特别残忍手段造成被害人严重伤残的故意杀人未遂而言,拒绝对犯罪人从轻或减轻处罚更有利于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由此可见,在未遂犯的处罚模式上,相较于同等主义和必减主义,我国刑法采取的得减主义是妥当的,它兼顾了道德应得、公众的惩罚意愿和犯罪预防,使三者能够在相对灵活的量刑模式中得到均衡的实现。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这种得减主义似乎并未得到真正贯彻,未遂犯基本上一律被处以较轻的刑罚,而未造成任何实害结果或仅造成轻微法益侵害的犯罪未遂(如故意伤害未遂)甚至常常不会被追究刑责。在本文看来,这种过分依赖结果运气的司法实践不但偏离了正义理念,也不利于刑罚效用的最大化。
3.道德应得与过失犯的处罚
与故意犯罪不同,过失犯罪的成立通常以侵害结果的存在为前提,各国刑法普遍缺乏对过失未遂的处罚规定。这种刑罚分配模式值得质疑。如果行为人表现出了对他人法益的同等程度的漠视(如上文提及的两个司机),就意味着他们理应受到相同的道德性谴责。在未发生侵害结果的场合,以惩罚意愿的减弱或缺失为由一概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并不妥当。就过失未遂而言,行为人对他人福祉的漠不关心态度,以及令他人陷入巨大风险的行为本身就奠定了他对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亏欠。尤其在某些涉及重大公共法益或人身法益的场合,更有必要削弱结果运气对刑事责任认定的影响。设想一个疏于检验食品安全而将混入有毒物质的食品呈给顾客的厨师仅因碰巧无人食用而被绝对地免除责任,这种恣意的刑罚分配明显辜负了正义理念。此外,从功利论的视角看,对于过失未遂而言,行为人往往缺乏对其行为方式的反省,甚至可能因为一时的侥幸而更加肆无忌惮,放纵此类行为显然不利于法益保护。一旦行为人出于法益侵害意图或疏忽的态度实施了相应的危险行为、制造了不合理的风险,无论结果是否发生,他都应当成为刑罚威慑的对象。
当然,与故意犯不同,对过失未遂不宜作出一般性的处罚规定,否则难免会导致犯罪认定过于宽泛。因此,我们需要在兼顾刑事政策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具有高度危险性的疏忽行为作出单独性的规定。这种立法模式的探索依赖我们思维方式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我们摆脱纯粹的思辨而深入到对复杂且多变的经验事实的探究。在本文看来,我国《刑法》并不缺少关于过失未遂的创新性规定,危险驾驶罪即是其范例。该罪所规定的行为样态在统计学上具有相当程度的法益侵害风险,立法者特意将其类型化并独立规定刑责,实际上追究的正是过失未遂(或过失危险犯)的责任。
4.结果运气与正当防卫
依据通说理论,正当防卫的成立以真实的防卫效果的存在为前提。在假想防卫的场合,由于假想防卫人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虚假的防卫结果,因此不存在援引正当防卫条款的可能(可能因无预见可能性而被免责)。按此逻辑,一个基于合理信念的假想防卫人即便在主观认知和行为方式上与典型的正当防卫人完全相同,也会因不可预见或不可控的客观结果的好坏不同而得到截然不同的规范性评价——一个被正当化而另一个仅被免责。设想典型的“借警察之手自杀”的案例:
甲身绑炸药手握引爆器进入人数众多的公共场合,声称将引爆炸药,警察乙对其警告无效,在甲即将按下引爆器之际,警察乙开枪将甲击毙。事后查明,甲身上的是假炸药。实际上,甲意图实施自杀却又没有勇气亲自实施,于是借上述方法迫使警察开枪以达到自杀目的。
从事后获知的信息来看,甲并未实施客观上的不法侵害,警察乙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假想防卫,依据通说,其行为不可被认定为正当防卫。问题在于,根据当时可获知的信息,警察乙对甲正在实施危及多人生命安全的不法侵害的判断,以及基于该判断而开枪的行为显然是合理的,其防卫行为是任何处于与警察乙相同认知地位的第三人都会选择的。设想警察丙恰巧在另一个辖区巡逻并遇到丁在实施与甲类似的行为,不同的是,丁携带的是真实的炸药,此时警察丁击毙丙的行为则会被毫无争议地认定为正当防卫。可见,依据通说,警察乙和丙虽基于同样的合理信念实施了相同的防卫行为,但其行为是否能被认定为“正当”则完全取决于运气。
在本文看来,既然应当在对行为的规范性评价中排斥结果运气,我们在假想防卫问题上的结论理应是:当防卫行为是基于合理信念而为时,防卫结果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不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上述警察乙的行为理应得到与丙相同的规范性评价(即“正当”而非“免责”)。刑法规范针对的是认知有限的人类,而非全知者,因此它理应允许并鼓励国民依据事前对客观情形所做的审慎判断采取最合理的行动方式,而不能要求防卫人在对客观情形作出完全无误的判断后才采取行动。一个基于合理信念而行动的假想防卫人并未辜负刑法的期许,仅因运气不佳而将他的行为宣布为“违法”是不公平的。
综上,如果行为人对其所面对的客观情状履行了谨慎观察义务并进行了客观审慎的判断(即行为人对客观情状的误判并无过失可言),那么,结果的好坏不影响行为人援引正当防卫条款进行抗辩的权利。通说见解以结果运气来决定行为正当与否,缺乏合理性。
5.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境遇性运气
人们的行动抉择总是在特定的境遇下做出的,而境遇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控的。如内格尔举例说明的,纳粹政权下的多数德国公民因无反抗勇气而身不由己地选择了某些恶行(如歧视、迫害犹太人)。他们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没能通过道德考验,但与从未面对这种道德考验的其他国家的公民相比,德国公民之所以要为恶行承担道德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幸”地生活在德国。不难想象,如果纳粹在其他国家掌权,那些国家的公民完全可能会做出相同的恶行。可见,“这里人们在道德上又一次受命运的摆布”[1]37。
在传统刑罚分配模式下,裁判者并不对境遇性运气给予特别关注。原则上,刑罚分配的有无和轻重不受境遇性因素的影响。然而,一旦我们进入到反思层面就会发现,当不可控的境遇性运气对行动的抉择或形态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时,如果不对境遇性运气对刑罚分配的影响加以限制,就会使刑罚丧失正当性。在本文看来,现代刑法学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的转变正是源于对境遇性运气之于刑罚分配意义的反思。
根据以往占统治地位的心理责任论,如果行为人存在故意或过失,便可以肯定其有责性。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规范责任论逐渐成为主流见解,依其主张,有责性判断的核心在于对“期待可能性”的认定。如果刑法不能期待处于与行为人相同境遇的一般人在当时的情形下选择适法行为,就理应否定期待可能性的存在,从而免除或减轻行为人的罪责。正如在司法实践中,某些已婚妇女因被拐卖或受到生命威胁而被迫与他人形成事实婚姻的,理应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被免除罪责。不难看出,期待可能性理论表达的正是对犯罪人不幸境遇的同情,它暗含着对境遇性运气之于刑事责任认定的意义的限缩甚至否定。在量刑实践中,对犯罪人境遇的关注不但有利于裁判者做出更加科学的量刑,而且能够对人性的弱点给予应有的法律救济。从实质层面来看,限制境遇性运气是现代刑法走向理性和公平的应有之义,因为境遇的好坏在极大程度上恰恰是“不平等”的。当然,这不意味着裁判者要事无巨细地考量所有境遇性因素对行为人罪责的影响,而是要特别关注那些对行为决策产生支配性影响力的因素,如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家庭背景等。一个因遭受不幸命运而选择犯罪的犯罪人不应只是惩罚的对象,而更应该是被关怀的对象。对犯罪人而言,真正的不幸并非糟糕的境遇性运气,而是裁判者没有对他的境遇表现出应有的同情和关怀。应当坦承,我国现有刑法理论和实践对犯罪人境遇的关注并不充分,这导致现有刑法实践主要是在事后被动地对犯罪作出应对,而缺乏对犯罪的深层原因的探究。在这种背景下,对境遇性运气问题的反思对于现有理论和实践的革新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四、结 语
道德应得不应被盲目的运气所左右,这是我们关于道德责任的基本信念,所谓道德运气现象的存在无损于这一信念的合理性。本文的结论可概括如下:在行为的其他方面相同的前提下,结果运气不影响行为人的道德应得,道德运气现象源于我们将非道德性情感与道德性谴责相混同。从理论反思的层面看,结果运气和境遇性运气对刑罚分配的影响理应被限定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并且应在不同问题上予以区分对待。诚然,人类生活无法摆脱运气,但理性的刑法体系不可为运气预留重要的位置。这种拒斥或削弱道德运气的刑罚观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有刑罚分配体系作出全面的反思和根本性的变革。
[1]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M].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王旭凤.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J].广西社会科学,2008(2):62-64.
[3]唐文明.论道德运气[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7(3):74.
[4]Zimmerman M J.Luck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J].Ethics,1987,97(2):376.
[5]Zimmerman M J.Taking Luck Seriously[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2002,99(11):562.
[6]曲蓉.论运气的道德价值——威廉斯与内格尔道德运气理论之异同[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6(2):52.
[7]Kessler K D.The Role of Luck in the Criminal Law[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94,142(6):2188.
[8]Bennett J.The Act Itself[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60.
[9]Morse S J.Reason,Results,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J].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2004(2):383.
[10]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9.
[11]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2]高长见.美国刑法中的重罪谋杀罪规则评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11(6):38.
[13]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13.
[14]张明楷.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范围与刑罚[J].法学研究,2005(1):84.
[15]柏拉图.法律篇[M].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