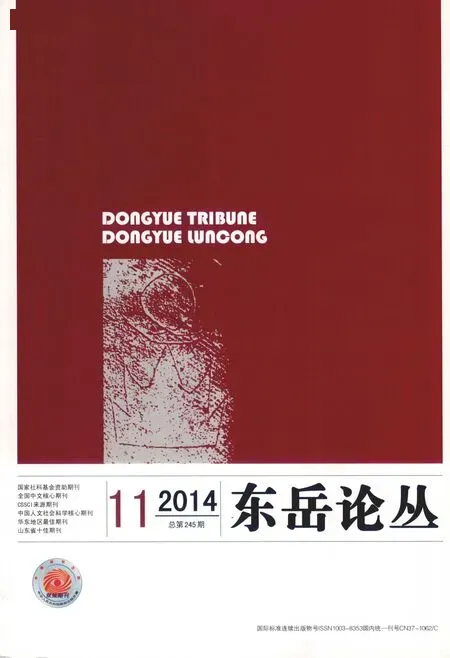论华文新生代散文的历史书写
2014-03-22章妮
章 妮
(青岛科技大学 传播与动漫学院,山东 青岛26606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与马来西亚华文界出现一种集束性的散文创作现象,以鲜明的代际特征引起高度关注。大陆以“新散文”、“新潮散文”、“新生代散文”名之,台湾、香港地区与马华文学界则以“新世代散文”、“后散文”、“新生代散文”名之。经过创作界与批评界的不断阐释,“新生代/新世代(New Generation)散文”因其对“代际”特性的彰显而获得公认。相较于“中生代”、“老生代”等散文话语言说主体,“新生代散文”的创作主体通常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突破了此前文坛存在的现实主义式的文学“真实”观,散文创作手法、文体精神等方面更具拓展性与先锋性。华文“新生代散文”的主要作者包括中国大陆的张锐锋、钟鸣、庞培、周晓枫、马莉、祝勇、苇岸等,香港的樊善标、凌钝、杜家祁、黄灿然、游静等,台湾的简媜、林燿德、林彧、杜十三、庄裕安、唐捐、郝誉翔等,马来西亚的钟怡雯、林幸谦、辛金顺、林金城、禤素来、寒黎、林春美等。
一
从时间维度观察,华文“新生代散文”蓬勃发展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与马来西亚文学场域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政治力量对文学的宰制力、掌控力、渗透度都迅速弱化;各地资本经济迅速繁荣,促进都市化进程全面展开和价值观多元化发展,经济资本强有力地渗透文化资本;各地之间、各地与国际之间的文化互动逐渐频繁,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定期召开、不同区域作品得以跨区域出版等,都促进四个空间的文学由隔断走向了解和相互渗透。文学场域中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凝聚、平衡,文学的政治意味与预期弱化,回到文学自身的理念得到普遍认同,文学生产、批评、消费等领域召唤新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言说策略。在这种文学场域和社会思潮中诞生并壮大的“新生代散文”,其写作主体天然地逸出狭隘的政治话语形态,突破此在的散文生态和话语状况,呈现出蓬勃的青春姿势和不可遏止的超越激情。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文散文语境中,老生代、中生代书写的历史通常是某种寓言的载体,叙述者往往采用全知视角或“类亲历者”——“我”的“写实”想像,具有相对统一性。如在中国大陆,历史是政治寓言的载体和人性力量的通道,“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①。大陆之外,历史更突破时间维度,进入空间维度。在台湾,历史既是政治寓言的载体,又是对大陆乡土和乡村乡土的“乡愁”寓言的呈现。在香港,除政治寓言和乡愁寓言,历史更多是对香港自体性的言说和诠释。在马来西亚,历史不仅关乎政治寓言与乡愁寓言,更是华人自我身份的追寻、塑造与确认。
这样的历史叙述构成强大的场域力量和群体意识,并影响到新生代的文学叙事。相对于新生代小说、诗歌对刚刚逝去的“国家历史”的“戏仿”②、“遵循正史言说的法则,而呈现出正史言说的抽象、空洞乃至悖谬”③,四地新生代散文作家都自觉地规避了此段历史,而聚焦于文化或种族层面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执著于历史的“实录”或“史录”,而是秉持基于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在歧义、多元甚至可疑的叙述中,从“存在”层面塑造历史面貌,阐述“历史”真意;调整叙事,跨越文类,抛弃单一叙述视角,不再采用现实主义式的统一叙述者;回归语言,在语言符码中寻求自我意识的确认。
二
基于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代表人物斯潘诺斯认为:“历史是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认识和反思,是行动和反行动的亲合体,是传统积淀的变体,而不是现代主义者凭藉一种虚设的已丧失根基的同一性去反抗假设的传统”④。在斯潘诺斯的理论系统里,历史突破时间性而具有了存在主义的“历史性”。首先,被认知的历史不是既成的客观事实,而是被当下解释的历史碎片。其次,以当下解释历史并不是为了返回历史本身,而是透过历史变体拷问“存在”超越于历史的“真相”,如生命、人性、原乡等。
华文新生代散文作家普遍接受了这种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式的“历史观”,不约而同地在历史书写中拷问“存在”的“真相”。阐释历史构成华文新生代散文很具代际特性的一个叙述主题。在他们笔下,“历史”不再是当时文坛流行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思维模式中“统一”的历史或整体,而是寄身于叙述者话语、叙述之中的碎片、小历史、叙述史等。历史永远只是被解释的历史,充满了不确定性、非客观性。在新生代散文主体的历史思维中,文学接近历史的途径是多样化的,但都充满隐喻与修辞,并最终指向“存在”的“真相”。虽然四地历史思维背景不一样,他们接近历史的途径却具有共性,主要表现为:由历史通往生命存在向度,统一过去与现在;嬉游历史文本,呈现既定逻辑的荒谬;以现代都市人的眼光回溯历史,深入人类和宇宙的内核。这样的书写方式迥异于现实主义式地“复现”历史,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式地“建构”历史:华文新生代散文的历史书写是以历史发现“存在”,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则是为了重塑“历史”;新生代的“历史”是碎片式、个人化、载体性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历史是整体性、公共性、本体性的;新生代散文历史书写中的主体是前置的、根本的,现实主义历史书写的主体是隐匿性、工具性的,现代主义历史书写的主体是前置的、工具性的。
由历史通往生命存在向度,统一过去与现在,以大陆张锐锋最为典型。他认为:“我们似乎更易于在流逝了的时空的折皱里找到一些关于今天的实证――那是关于现实的生活的隐喻”⑤,“原样的事实常常不在我们的讲叙中,而是在遥远的时光里隐隐地摆放在暗淡的盘子里,让我们感受它的存在,它的力量”⑥。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剥离了历史本身,接近与传达的只是叙述者的视域、自我与世界。基于此,他转身面向“历史”,用文字锋利的刀刃划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与同一性,将其塑型的形象与思想肢解、拼合、重组与诠释,以注入现代式的血液。通过解读古典诗歌、意象、人物、神话等,多角度想象寓言、历史故事等的可能性,在历史中看到当下、以当下解释历史,是张锐锋非常坚持的历史态度。他携带的“解释”并不是线性地解释历史本身,而是解释亘古就有的真实。但这种“真实”并不是“历史”本来的样貌,而是历史式“存在”的真实,或者说,是他对“存在”真相的发掘与思索。其长篇散文《飞箭》是以《绘图千家诗注释》中的十八首诗为契机,于“同情”中寻找历史断片掩藏的勃勃跳动的存在真相。文本不以解说诗歌为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返回诗人写作的历史现场。面对每首诗,叙述者都兴趣盎然地“解释”诗句的由来与内涵,但聚集点都是诗歌美妙旋律掩藏的“心灵的完美虚构”⑦。所以,所谓的“解释”更像诗人心灵的“释读”,或曰叙述者个人智性的诗意表达。叙述者充分调动视觉、嗅觉、听觉和文学想像力,纵横出入于诸多诗歌文本时空、诗歌写作时空和叙述者的个人时空,挖掘波澜壮阔的生活图景,铺陈它们的悖反与延异,以窥见生活的内核——存在“从过去蔓延而来直到完全地覆盖了现在”⑧。文本《古战场》不断跳荡在历史故事、当下现场与个人小历史三重时空之中,讲叙历史之死与大地之生、英雄之强与俗者之弱、英雄之战与朝堂之昏、英雄之死与皇帝之逃等细节。文本不讲故事,也不着意于展现金沙滩古战场的历史与当下,而是以故事的材料为引子,哲学式地思考生与死等生存真相——“一个人的历史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样相似,一切发生的仍在现在”⑨,正如杨业在富有哲学意味的历史情境中悲壮地自尽于李陵碑上。这一类历史书写将历史作为思考的材料,历史只以零星、点滴、琐碎、纷乱的样貌出现,无以自我指涉,而是指涉历史与当下共通的“存在”。
同样是对生命、历史的存在主义式的理性考察,张锐锋式的知性思考通常离不开感性想像与具象关怀。因而,这类散文以理性的、哲学式的讲叙为主,又不乏丰富的细节想像,“存在”也就具有了理性与感性的整合性。钟鸣式的历史书写则讲究语言叙述的趣味性、解构性与语言自身的想象力,不以知性讲叙为主,追求“说得有趣,多讲一些轶事。扯得越远,风景越好”⑩。这一类散文涉及的历史轶事、生物、书籍等,都变成“说”的素材和“游乐场”。在叙述者近似游戏的叙述中,它们隐匿了具体性与完整性,而代之以支离破碎的词语/语句形式,割裂地存在着。因而,在貌似笑嘲的叙述中,轶事、故事等被相互歧异的文本解构着,从而显出叙述逻辑的荒诞性。所以,轶事、故事等具有强烈的寓言性,“寓言性对象的意义,诚如商品的意义一样,总是位于别处,离心到它的物质存在之外;但它愈变得多重性,它的破译现实界(the real)的法定权力就愈成为不拘一格的和创造性的”⑪。钟鸣在《圣人孔子,里尔克,苏格拉底和独角麒麟》一文中,叙述者利用中西方多种传说故事,周游于《论语》、里尔克诗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圣经》、韩愈《获麟解》等文本之中,漫画式地想像着苏格拉底、孔子、秦始皇等与麒麟的关联,从而在多种叙述声音中解构了孔子、麒麟的神圣性:叙述者一方面以传说的形式声明“仁慈而长寿”的麒麟是孔子的显形,一方面又用白话版的《论语·泰伯第八》说明——孔子的信念是不去充满危机和混乱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淡淡评价——“这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信念,但却很像孔子,更像麒麟,因为传说麒麟在人类相互残杀和破坏生态平衡时便会隐而不见”⑫。这一类历史书写主要利用文化、种族历史诸多既有文本的参差对照,叙述者不着痕迹地解构历史叙事的逻辑性、权威性与可靠性,道出存在与生存的本质。在中外多种文本的错杂并置和肢解式的转述中,“历史”化身为符号,所指消形,成为存在的“寓言性对象”。
新生代散文的历史书写除了知性讲叙与文本戏谑,还有林燿德式的漫游。这一类散文漫游历史时,不仅携带生命视角,还隐含着大陆新生代散文缺乏的都市视角,常见于台湾和香港新生代散文。都市视角使作家观察世界、想像历史时,很自然地将其纳入都市叙述中,醉心于历史“当下性”的思考,生活琐事、历史故事等都被置入坚硬且有金属质感的文本中。这种风格往往源于作家对都市思维的定位,即题材、主题、风格、思维的现代质感。所以,这一类历史书写的叙述者常用抽象化的语言,结合朦胧的诗意,将哲理思考“迷宫”式地植入其中。林燿德的《铜梦》一文使用地质、地理、化学、生物等名词,以“蛰伏”、“结晶”、“分身”、“诅咒”、“象征”、“镜面”、“时间”、“铜梦”、“流变”分别对应铜元素、铜化合物、大铜、铜器、铜的多变、铜镜、铜与时间、铜山、铜的梦、现代铜。十个关键词象征着人类历史的地球存在的十个阶段,如“蛰伏”象征着尚无人类的太古鸿蒙期,现代铜象征着现代人类快速变化的政治、经济与战争等。这些名词平添了行文的冷峻峭拔,又似乎与文化发展史对应。林燿德的叙述巧妙结合冷峻与浪漫,如“铜元素安谧地蛰伏在地球之中,聆听沧龙和蛇颈龙斗争时拍击海水的凄厉音响,聆听腕龙家族狂奔通过旷野的恐怖震动”⑬。此句不仅是历史的诗意叙述,也是叙述者历史观察的诗意表达——历史存在于当下。铜元素的成长历史中,充满不断熔铸的历程,如各种铜器、现代化导线、电铸版、铜像,直到最后被铸成子弹寂灭一切梦境和历史。历史的纵深感被铸成平面的当下,以“子弹”的决绝形式洞穿历史,归于虚无。其《工地》《路牌上的都市》等直接利用现实都市空间思考都市的历史。这类历史与中生代、老生代的历史怀旧式书写不同,目的不是为了用文字再现或建构都市的前身,而是着重于发现都市历史的虚构性。《工地》以大厦喻都市,以建设中的工地喻都市的往昔,隐喻都市的当下与历史正是一体两面的统一体,都市历史不过是当下的幻影罢了。这种历史的虚幻感在《路牌上的都市》有更清晰的展示。因为“乡愁”、“怀旧”,都市台北用了很多大陆名城命名街道,并呈现在街巷路牌上。这些名城虽藉着历史教材、影像资料等在叙述者心中构成一些拼图,但每一幅拼图都在中心处留下空白,空白很快地扩张,伸出触须,画面的残余部分瞬即龟裂、幻灭。所谓的拼图只不过是幻灭,所谓的怀古世界只不过是架空的感伤而已,被纪念的历史空间与厚度在“我”的叙述中完全压平。华文新生代散文集中探寻都市历史身份时,往往采取林燿德式的叙述策略,以纪念行为沉淀历史记忆的都市因“历史”本身的龟裂、幻灭而变得可疑起来——历史身份与记忆旋即变得虚化,甚至是一种虚构。历史已不再是历史,而是沦为现实的符征、修饰与无谓的指称!
三
历史的构成包括民族、国家、文化层面的“大历史”,也包括个人的小历史。上述三种历史书写不论涉及民族、国家、文化层面,还是都市记忆层面,叙述者采用的都是“小历史”的切入方式。小历史是个人的自我认识,“个人的自我认识所涉及的范围不受个人经历的限制,也不受他自己寿命的限制”,“个人关于自身的形象由记忆的沉淀所构成,在这个记忆中,既有与之相关的他人行为,也包含着他本人过去的想像”⑭。故而,个人的历史、与个人相关的家族、种族的历史,都构成自我认同的根基与参照。华文新生代散文在个人小历史的书写中,共同营造了“原乡”意象,即由童年、故乡、家族史等升华而来的精神和文化原乡。相对于中生代、老生代建构式的原乡书写,新生代散文的原乡书写也典型体现了他们的历史文化性格。
在新生代散文中,由故乡升华而来的精神原乡呈现四极分化。一是乡村原乡,往往与童年交织一起,大多数大陆新生代散文营造的都是基于乡村思维的乡村原乡。二是大陆作家苇岸的大地原乡,以自然意识、人与自然的极度和谐视角建构而成。三是林燿德式的“都市”原乡,台湾和香港新生代散文作家多立足于都市立场,在追索都市空间的历史叙述中,充满探询与浓烈的迷宫情结。四是马华新生代散文中充满困惑、追索、颠覆与多重可能性的精神原乡,在四类原乡形象中最能体现其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式的历史观。
作为富有20世纪文化特征的原乡形象,“童年的净土”是写作者“在现实苦难、人性沉沦中力图在内心深处”保留的一方人类净土⑮。在写作者的浪漫追忆中,童年往往被建构成远离当下、远离苦难的温馨乌托邦。即使有苦难,也在叙述者因时间流离而变得婉约的关照视野中,呈现出恍惚而令人回味的况味。但在新生代散文中,童年的面目就要丰富复杂得多,有欢乐,亦有痛苦;有儿童视角,也有成年视角;有回忆,亦有解构。成年视角与解构思维的介入,令钟怡雯、辛金顺等的文本用语言虚构了种种生命影像,在生命原乡中充满歧异地寻找、建构叙述自我和华族自我。
新生代散文作家不仅书写童年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非常清醒的虚构意识:“虚构使我逐渐触及比履历表更为真实也更为有效的东西”⑯。他们站在“今天”的位置上回望童年,在回望中虚构。张锐锋以中年的理性穿透童年,坦称“站在今天说话”⑰,而不是站在童年说话,描绘的童年只能是“此时此刻的这一个”。在虚构意识的笼罩中,童年只是组织书写和发现历史真相的原材料。如张锐锋的长篇散文《皱纹》涉及的童年素材有灯盏、声音、语言、蒸汽、庄稼、照片、拉风箱、玩陀螺等,但它们并不是为了“复制”鲜活的童年记忆和生活幻影。在作者刻意添加的括号标注、字体变化、破折号中,这幻象和叙述的真实性、连贯性时时被打破,彰显的是超越时间魔咒的存在真相。
由于历史情境的特殊性,马来西亚华人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经历了身份认同的艰难转变。至八九十年代,新生代散文的文学“原乡”开始转向本土生活空间、本土的童年原乡、故乡原乡和历史文献、祖辈讲述的文化中国等,面目纷繁、歧异。他们在认同本土生活记忆的同时,无法割舍或者清除家族的历史记忆。当文本叙述个人小历史时,往往采用双线结构,即父辈/祖辈的讲述、想像与叙述者的追寻同时展开。父辈或祖辈的讲述往往是细节性的琐碎,细节之间充满断裂与互异。追寻的叙述者具有当下意识,当进入历史线索时,因细节的断裂与互异,又会生发出对历史的质疑、溯源的动力与认同的困惑、焦虑。因而,其小历史叙事意在确立自我认同的时空、文化坐标,“他们的痛苦或矛盾更体现在族性记忆的失落和边缘话语的尴尬”⑱。游学台湾、香港的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原乡形象最为复杂:“我认同台湾,也认同这块土地(引者按:马来西亚)。”⑲由于身处多重空间,文学空间也多样化。当进入回忆与历史,原乡指向“故乡”马来西亚——改写过的、抽身其外的隔层关照。当进入当下生活时,原乡又化身为台北。钟怡雯《可能的地图》就通过祖父详尽的追述和叙述者依据祖父口述的“地图”寻找构成。祖父的口述充满逝去的细节,而叙述者却一再失落祖父在马来半岛的“故乡”,在“困惑和沮丧”中质疑了祖父的原乡想像。不同于同辈拥抱本土与追寻文化中国的复杂认同,林幸谦的散文指向浓郁的“文化中国”认同。“中国”是他的精神原乡,也是真正的“祖国”⑳。其《溯河鱼的传统》对溯河鱼置生命于不顾回到出生地传统的赞赏,正是其文化乡愁的寓言书写。在追寻与实践文化乡愁的过程中,他不断通过繁复意象、身份错位、寓言象征等表达乡愁的幻象性与悬置性。马华新生代的“原乡”书写充满细节,并在细节的相互碰撞中模糊、放逐了祖辈业已失真的历史幻象。
汉字在历史中联系几代华人,也在新生代的文字言说中沉淀了共同的圣餐和共有意识,“作为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即使他们从未见面或从未会话交谈,但却都怀着一个信念,即认为大家都在使用‘一个’共同的语言。这种无法以经验一一确认的语言共有意识,和政治共同体一样,毫无疑问是历史的产物。”㉑华文新生代散文生发于由语言织就的特定文化场域,在语言、精神与历史书写方面体现出多层面的共有意识。具体到历史书写,表现为基于存在主义的历史感,即历史虚构感与历史建构性,既在一定层面上体现出鲜明的代际意识与特征,又与新生代其他领域的创作一起拓展了华文文学的审美空间,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华文文学生态转型的重要参与者与主要推动力量。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②张琴凤:《论台湾地区及马华新生代作家的“戏仿”历史叙事》,《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
③魏天真:《新生代历史叙述:被播弄的人与是非》,《文艺评论》,2002年第2期。
④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页。
⑤张锐锋:《今日比昨天更遥远——我的一种写作态度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⑥张锐锋:《河流·讲叙者》,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讲叙者》是本书的“自序”,但整个自序都没有页码,也不隶属于全书页码。本句所引在自序第二页,故权且标为“2”)
⑦⑧张锐锋:《河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第8页。
⑨张锐锋:《被炉火照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
⑩钟鸣:《徒步者随录·我是怎样的一个徒步者(自白)》,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页。
⑪王一川:《寓言乌托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⑫钟鸣:《太少的人生经历和太多的幻想》,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⑬林燿德:《林燿德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⑭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67页。
⑮黄万华:《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⑯周晓枫:《收藏·想像中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相像中的回忆》是本书的“自序”,但整个自序都没有页码,也不隶属于全书页码。本句所引在自序第四页,故权且标为“4”)
⑰张锐锋:《皱纹》,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⑱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1页。
⑲钟怡雯语。见刘育龙:《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座谈会会议记录(上)》,《星洲日报·星洲文艺》,1999年10月23日,第39版。
⑳1989年他在台湾时报文学奖得奖感言中宣称:“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一次启程有人称是回归祖国,回到主流,应是这一群变种蒲公英族的信念”。
㉑转引自藤井省三:《日本文学越境中国的时候——茅野裕城子论》,见茅野裕城子:《韩素音的月亮》,王中忱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