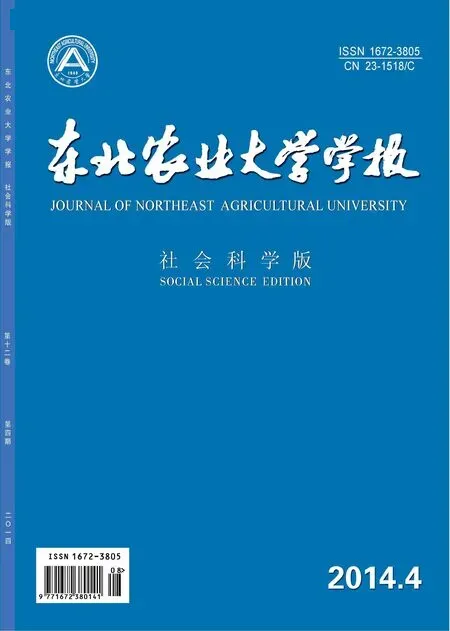托妮·莫里森作品中母爱文化阐释
2014-03-22张凡郑辉
张凡 郑辉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
托妮·莫里森作品中母爱文化阐释
张凡 郑辉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
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迄今为止的十部作品堪称经典,而在这些作品中蕴含着同一主题——母爱。母爱缺失与追寻是贯穿莫里森所有作品的内在线索。莫里森对于母爱伤痛的描述以及对弥合伤痛方式所做的探索,揭示出她对黑人妇女问题的深切关注。其作品中展示出多种母爱,让人或感动、或震撼、或动人心魄。莫里森认为,母爱缺失和扭曲并不是黑人女性本身母性的沦丧,而是黑人传统文化的缺失;小说人物对母爱的追寻也不仅仅是为了达成对母亲的谅解与宽容,而是为了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母爱的追寻即是对自我的追寻,也是对在充满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中生存的精神力量的追寻。
母爱;文化缺失;文化追寻
自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一直是评论家瞩目的焦点。从《最蓝的眼睛》到《秀拉》,从《所罗门之歌》到《柏油孩子》,从《宠儿》到《爱》,再到她近期作品《慈悲》,莫里森通过对非裔移民的关注,以独特的观察视角,自由的想象力和深刻、细腻的写作手法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美国非洲裔群体生活画卷。托妮·莫里森像魔术师一样,能够把不同声音结合并组织起来,从而构筑成不同人物形象。她从不把自己的观点生硬地塞给读者,而是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真正走进作品,与其一起品味主人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一同探寻人物内心世界的奥妙。可以说,莫里森是一个让人百看不厌、充满激情的作家。而在她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包含了一个永恒主题——母爱。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20纪后半叶各种批评主义相继兴起,对莫里森作品的整体评价和诠释一直处于变化之中。20纪八九十年代批评家多从种族意识、女性意识和神话原型等方面,运用解构主义和女权主义方法进行分析,同时出现与人类学、叙事学等相关学科结合的趋势。其中代表作品有卡罗尔·戴维斯所著《黑人女性:书写和身份》[1]和奥伊·莫丽专著《托尼·莫里森与妇女主义话语》[2],在这部专著中莫丽运用“妇女主义”理论阐述了莫里森如何恢复非裔美国人身份并发现自己的艺术形式。苏珊·S·兰瑟在《无以言说的声音:托尼·莫里森的后现代叙事权威》一文中讨论莫里森从《最蓝的眼睛》到《宠儿》的所有作品,指出其小说中叙事声音的变化[3]。近年来,评论家开始着重研究莫里森对黑人历史的重构,以及对历史、记忆、伤痛之间关系的阐释。莫里森研究在西方学界经历了从最初的以白人主流文学为批评标准的传统批评方法,到逐步引入女权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和文化批评等方法的过程,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性特征。
中国学界对莫里森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初主要是针对小说进行作品译介,而对其文论、剧本、诗歌等翻译较少。1993年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出现了一股莫里森研究热潮。1999年王守仁、吴新云发表了第一部研究莫里森的专著——《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这部作品对于国内莫里森研究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该著以小说为单位,分别从性别、种族和文化三个维度对莫里森作品予以评析,并对作品与传统文化的承继关系进行研究[4]。近年来,对莫里森作品的研究方法和角度越来越丰富。其中有不少学者运用女性主义批评观点和理论阐释莫里森作品中的人物和主题。同时,在黑人文化主题研究方面,国内评论者也表现出较高的热情,但基本上没有突破国外学者研究范围。在作品的社会历史主题方面,国内研究者表现出较大研究兴趣。如胡全生、陈法春等都曾以具体文本为例,探讨莫里森小说的社会历史主题[5-6]。莫里森小说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叙事话语同样是国内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焦小婷、杜志卿等做了相关探讨[7-8]。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方面,国内有些研究者已开始尝试以新的理论视角解读莫里森作品,把一些与当代西方叙事学、语言学、文化批评等有关理论引入莫氏小说研究。如巴赫金“对话理论”、福柯和多罗茜·史密斯话语理论、后殖民理论等等。
虽然国内对莫里森研究日益深入,但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研究面有待拓宽。许多研究者局限于莫里森某一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缺乏整体和宏观视角,缺乏比较分析。二是选题较为单一,过于集中,有重复研究现象。多数关注《秀拉》女性主义主题研究和莫里森代表作《宠儿》。三是对莫里森其他作品形式如文论、戏剧的研究尚为空白。四是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尚未有效开展。
二、母爱主题
莫里森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黑人妇女世界。黑人女性尤其是黑人母亲是莫里森关注的焦点。很多评论家认为只有自《宠儿》起,莫里森才开始将写作重心聚焦于母爱主题。但是,通过对莫里森十部作品及莫里森访谈录深入阅读与研究,母爱失落与追寻事实上是贯穿莫里森所有作品的一条内在线索。莫里森对于母爱伤痛的描述以及对弥合伤痛方式所做的探索,揭示了她对黑人妇女问题一以贯之的深切关注。其在1977年的一次访谈中曾言:“我始终在写一个主题,那就是爱与爱的缺失。”[9]而母爱缺失实际上展示的是黑人传统文化的失落。追寻母爱即是寻求自我,寻求在充满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中生存的精神力量。
(一)缺失的母爱
母爱的缺失在莫里森很多作品里都有所体现。“黑人母亲是黑人文化传承者,她们应该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环境下学会如何养育孩子、保护孩子,指导孩子在种族歧视下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并向种族歧视主义发出挑战。”[10]
1.《最蓝的眼睛》中迷失的母爱。由于美国白人在经济、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他们的文化也成为主流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一些黑人女性心灵发生了扭曲和裂变,开始以白人文化观、审美观审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否认黑人身份,抛弃本民族文化。《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母亲波琳就是这样的代表。初到北方这个种族歧视盛行的地方,她发现自己无法融入当地黑人妇女社区,因为这些黑人女性已经完全被洗脑,全盘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而波琳也日益受到影响,她逐渐被白人文化浸染,最终被白人文化驾驭,抛弃本民族文化,丧失自我。被白人文化内化也导致她自我否定和对家人的否定。
而十二岁的佩科拉就是在这样一种缺少母爱的环境下长大。在成长过程中,她不被社会所接纳,就连生母也离弃了她。母亲波琳厌恶自己的黑皮肤孩子,当看到刚出生的女儿时,竟然觉得女儿丑陋不堪,像一个“介于死人和小狗之间”的小黑团①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当佩科拉和白人女孩在一起时,波琳更喜欢白人女孩。在白人主人家里,当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果酱,波琳对她又打又骂,吓哭了白人雇主家的小女孩。波琳丝毫不理会自己女儿佩科拉的委屈立刻去安慰白人家的女孩。波琳在经过白人文化洗脑后,认为丈夫、女儿又黑又丑,对女儿产生了厌恶情绪。这使佩科拉充满了“对成长的恐惧,对他人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
由于母爱缺失,佩科拉的幼小心灵因生活在歧视和嘲笑中而扭曲。由于母亲没有传承让佩科拉得以坚强生存的黑人文化,她没有形成对自己和黑人的正确认识,一直认为母亲不爱她是因为她没有漂亮外表、白皙的皮肤和蓝色的眼睛;她每天都想着白皮肤和蓝眼睛的事情,活在自己虚拟的美丽世界中,一心以为只要拥有一双蓝色眼睛就可以变得漂亮、可爱而获得母亲的爱。现实世界中母爱的缺少导致在她生活的环境中没有也无从获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因而陷入对自我的否定,最终导致精神崩溃,精神恍惚中还在幻想终于拥有了一双漂亮的蓝眼睛。
2.《秀拉》中残缺的母爱。在《秀拉》中Peace一家的母爱同样扭曲、残忍、不近人情。美国黑人女性的境遇通常比黑人男性更悲惨,除了种族歧视,还要面对性别歧视。且在充满艰辛的环境下很多黑人男性选择逃离,使得女性处境更加悲惨。秀拉祖母——伊娃在丈夫遗弃她之后,展现的是一种牺牲性母爱。为了使三个孩子生活下去,她牺牲了一条腿换取保险金;为了救儿子“李子”,她耗尽了自己仅有的食物;为了救汉娜,她义无反顾地从三楼跃下②托尼·莫里森:《秀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可是这种惨烈的母爱并没有得到孩子们的理解。因为生活困窘,她只能给孩子们提供物质层面的需求,而没有时间和精力与孩子们交流沟通,导致女儿对她不理解,甚至对她的母爱产生怀疑。因此,汉娜选择了放荡的生活方式,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填补缺少的母爱。
秀拉的母亲汉娜,由于自身没有感受到深切母爱,同样也不能带给秀拉充实的爱。她每天忙于应付形形色色的男人,无暇顾及秀拉,只能带给秀拉一种疏离的母爱。虽然小说没有着过多笔墨描述汉娜的母爱,但从她和朋友的对话可以窥见一斑,“我爱秀拉,我只是不喜欢她。”对于十二岁秀拉来说,这样的话使她心中充满痛苦,母女深情就此割裂。而后当秀拉失手把她朋友“小鸡”甩到河里淹死时,她选择逃避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生无常和生命脆弱。“自从母亲的话深深刺激了她,她的主要责任感被根除,她便要过一种实验性的生活。没有母爱做坚强后盾,她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而好朋友在她眼前被淹死使她意识到自己也靠不住。而这种母爱缺失使她在目睹母亲落地死亡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饶有兴趣”地观望。在这之后的十年中,秀拉所过的生活无疑受母亲影响——在丈夫死后,汉娜搬回娘家与镇上男人做爱,随意地挑选异性而后再把他们甩掉、跟好友丈夫上床等等。母亲的行为告诉她男人不值得女人向往,而母亲的话使得秀拉失去了成长中心,缺失母爱的她以极端方式追寻自我。
3.《所罗门之歌》中畸形的母爱。虽说《所罗门之歌》是托妮·莫里森突破女性题材,开始塑造男性进而关怀美国黑人种族命运发展这一深刻主题的颠峰之作,但是莫里森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忽略女性的作用和力量。莫里森在男主人公奶娃的周围塑造了一系列女性角色,她们形态各异,思想和命运各不相同。其中奶娃母亲露丝值得同情。作为母亲,露丝一直默默无闻地照顾和帮助奶娃。但是,强势的父亲使得家庭缺少和睦,没有一丝家庭温暖。父亲对母亲的辛苦劳作、对家庭以及孩子们的全心全意奉献视而不见。露丝在丈夫身上得不到丝毫的温情,在生活中感受不到幸福。而且,不仅奶娃父亲麦肯厌恶她,时常冷眼冷语对待她;就连儿子奶娃,也对母亲的存在和痛苦视若无睹。虽然奶娃对母亲露丝的感情淡漠,但露丝却对儿子产生了一种畸形母爱。
露丝对儿子怀有非同寻常的强烈的爱,然而这种情感是畸形的,是一种颠倒的“俄狄浦斯情结”。对于露丝而言,奶娃不仅仅是她的儿子,还是她对丈夫的一种依赖的补偿。她把奶娃当作脱离深潭唯一的稻草,拼命抓着,但是这棵救命稻草太轻,承受不起她的希冀与渴望。她一直坚持自己喂养奶娃,可能她不知道,这种下意识的行为是为了弥补丈夫对她性与爱的剥夺。而奶娃从小生活在父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中,他觉得自己和父亲一样是一个强者,而母亲毫不反抗,就是一个弱者。他认为母亲是一个满足于日常琐事、意志薄弱的女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弱者。这种扭曲的母爱使得奶娃难以从母亲那里继承黑人文化,继而找不到自我。
4.《爵士乐》中扭曲的母爱。小说《爵士乐》中,男主人公乔是一个在生活中和精神上缺乏归属感的人。而这种安全感和精神归属感的缺乏源于他自幼被生母抛弃的经历。乔来自于南方,在刚出生时就被母亲遗弃,他始终无法摆脱因母子感情缺失造成的心灵空虚、寂寞、孤独。然而,当他知道母亲还活着时,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母之旅。乔一生不停寻找母亲,追寻自幼缺失的母爱。
小说中,乔与妻子维奥莉特为了逃避贫穷、苦难和暴力,从南方乡下来到大城市谋生。在城市生活的二十年,他痛苦地寻找母亲,努力适应城市生活。然而,对于乔来说,这两件事都不尽如人意。在寻母过程中,他那近乎疯狂的寻找,使他接近精神崩溃边缘,但是上天丝毫没有眷顾他,多年寻找一直未果。在生活中,从南方乡下到北方大城市后的失落与不适应,使本就空虚而缺乏安全感的乔倍感痛苦与无助。在精神与生活的双重压迫下,乔与妻子沟通越来越少,加剧了孤独感和失落感,直接导致他后来爱上只有十八岁的姑娘多卡斯。在多卡斯身上,心灵压抑的乔重新感受到爱情的温暖。在与多卡斯交往中,寻找到了他多年来一直追寻的母爱。虽然在年龄上差距很大,但多卡斯带给乔的活力与热情使他找到了多年来一直缺乏的安全感与归属感,成为乔的精神港湾。多卡斯带给乔的爱并非母爱,这种畸变母爱却给了他因母爱缺失而丧失多年的存在感与归属感。
5.《宠儿》中触目惊心的母爱。《宠儿》中展现的母爱压抑而惨烈。贝比·萨格斯——塞丝的婆婆——一生中有八个孩子,而这些孩子一出生就被奴隶主掠走,到底是被卖还是被杀不得而知。奴隶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只是奴隶主的财产,萨格斯被迫与子女骨肉分离,对孩子仅剩的记忆就是大女儿“爱吃糊面包底”,她想爱不能爱。白人处于统治地位,黑人被剥夺了一切——包括做母亲的自由。一次次失去孩子、一次次痛苦与无助,使她的爱变得迟钝而麻木。
塞丝母亲作为一个遭受白人百般蹂躏的黑人女性,作为一个同白人一样有强烈母爱的母亲,在母爱遭到无情践踏后,采取了极端方式——把被白人强奸生下的孩子扔掉,以反抗所谓的权威。母亲只留下了塞丝,因为塞丝父亲是个黑人。她给塞丝起了一个纪念黑人父亲的名字,来表达思念和怀念。而这样一位被践踏了尊严的母亲在贩奴运动中丧生,她只存在于塞丝朦胧的记忆中。从小没有享受到母爱的塞丝无比坚强,母亲虽然没有给她完整的母爱,但是却把黑人母亲那种不愿向逆境低头,对命运强烈反抗的精神和对孩子炽热的爱传递给了塞丝。
塞丝受其母亲影响,独立坚强,对孩子怀着深深的爱。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再被奴役,她拖着被毒打之后伤痕累累的孕身铤而走险,毅然出逃。此时,死亡于她并不可怕,她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当奴隶主寻踪而至时,为了不让女儿重复自己悲惨的奴隶生活,她毅然决然地割断了爱女的喉咙。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黑奴,当母爱遭到无情践踏,母性被残酷蹂躏时,只能采取这样极端和独特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被扭曲的母爱。同时也只有这样,她才能最大限度地捍卫黑人作为人的尊严。黑人像白人一样,也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孩子的生命做出选择。
而宠儿在十八年后以成年女性形象出现时,母爱的多年缺失使她对母爱的需求极为强烈,“她才是我所需要的”,宠儿如饥似渴地吸收母亲身上的一切,来填补内心情感空白。从萨格斯和塞丝的悲惨经历可以看出,“奴隶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就连爱他人,包括爱自己亲生骨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11]。母爱失落加剧了黑人文化的失落,也反映了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文化的扭曲和剥夺。
(二)母爱的追寻
黑人母亲,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无论在非洲社会部落,还是美国黑人社区,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的社会职能、家庭职能和母性职能是其所处社会结构中的主要社会活动,尤其是母性职能,关系整个族群的未来,孩子的健康成长。黑人母亲通过履行母性职能传输给孩子自爱观念和自我价值,使之成长为自豪的非裔儿女、非洲传统文化传承者和美国现代文明的汲取者。正是在这种被主流文化恶意中伤的日常经历中,黑人母亲授权自我,以确保孩子在功能失调的黑人社区和贬低黑人的白人社会继续存活。黑人母亲的母性是发展授权观念的场所,建构自我认同的源泉。一个母亲的责任并不只是赋予孩子生命,更重要的是对孩子心灵的培育。
1.《最蓝的眼睛》中母爱的延伸。莫里森作品中展现的母爱并不是完全绝望的,每部作品在展现母爱缺失的同时,又都体现出对母爱的追寻。而母爱的追寻即对自我的追寻。《最蓝的眼睛》中克劳迪娅姐妹的母亲麦克蒂尔认同自己的身体特征,觉得黑皮肤是黑人民族生理特点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无可改变的事实,热爱自己的民族就要热爱这个民族的一切。她努力保持自己黑人本性,继承黑人传统。同时,当佩科拉在自己的母亲那里得不到母爱并被父亲强暴后,麦克蒂尔收留她,承担起非亲生母亲或社区母亲的责任,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精心地呵护她,等待她和家人团聚。这种延伸的母爱具有愈合伤痛、救赎一切的力量。
麦克蒂尔的这种母爱给克劳迪娅姐妹俩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使她们内心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当周围的黑人不顾一切地吸收白人文化价值观时,她们肯定自己的黑皮肤,拒绝用白人标准评判自己的生活。姐妹俩对自己的相貌毫不自卑,甚至将很多黑人孩子梦寐以求的白人布娃娃撕毁,以此表示对白人审美标准及白人文化的反抗。同时她们积极主动地反抗种族歧视,维护自己和黑人的尊严,获得了正确的自我认同。而只有实现了黑人的自我认同,才能使黑人的民族性基础得以保全,才能实现个人生存的持续和发展。
2.《宠儿》中母爱的救赎。对于母爱的追寻在《宠儿》中也同样有所体现。塞丝由于过去的杀女之痛而对丹芙过度保护。她从小教育丹芙过去具有摧毁性,过去的创伤会无限繁衍自身,过去将永远在那里等着她。使得丹芙对社区生活充满恐惧,总是喜欢把自己禁锢在家里,享受孤独。当宠儿无休止地对母爱进行索取,即将把塞丝吸干,而塞丝也沉溺于满足宠儿对母爱的索取难以自拔时,丹芙意识到了必须“保护她妈妈不受宠儿危害”,也意识到照顾和救赎母亲的责任,因此她终于鼓足勇气走出家门,寻找黑人社区的帮助。当丹芙依靠黑人的团结将宠儿的鬼魂驱走后,才理解和接受母爱,拥有了寻求自我独立的勇气和力量并形成了正确的自我。黑人只有正确认识自我,认识本民族文化,才能抵制白人文化侵蚀,为本民族权力不懈斗争。
3.《慈悲》中母爱的蜕变。在《慈悲》中,索萝(Sorrow)是一个非理性,甚至有点神秘感的人物。人们对她的身世知之甚少,只知道她是一个船长的混血女儿,在一次沉船事故中幸存。不幸的生活经历给她带来了精神创伤,使她性格忧郁、举止怪异、有心理障碍。但她却是小说中最有希望的人。原因在于她在两次生育经历中完成了人生蜕变。第一个孩子被莉娜溺死,使她悲痛万分,但她勇敢地生下并保住了第二个女儿。分娩时她从容镇定,恰当地寻求帮助,表现出极大的智慧,这使她获得自信,完成生命的救赎。有了孩子的索萝获得了自我。
小说中的莉娜虽然没做过母亲,但并不缺少母性。她对自然界的生命有一种原始的、本能的爱。对弗洛伦斯的爱使她实现了做母亲的愿望。而弗洛伦斯一直无法释怀母亲对她的抛弃。直到小说最后一章事情才真相大白。原来母亲是害怕女儿像她一样,成为奴隶主泄欲工具、生育机器和赚钱商品才忍痛放弃刚刚八岁的女儿。小说以母亲对弗洛伦斯的深情呼唤结局,再次彰显母爱的伟大。小说中的女性对母爱的追寻同样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只有寻找并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才能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
三、结语
对母爱主题的诠释与莫里森对黑人文化的理解密切相关。她认为母爱缺失与扭曲只是一个表象,所反映的并不是黑人女性本身母性沦丧,而是黑人传统文化的失落。而小说人物对母爱的追寻也不仅仅是为了达成对母亲的谅解与宽容,而是为了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母爱的追寻也是对自我的追寻,是对在充满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中生存的精神力量的追寻。
自我追寻一直是莫里森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非裔美国人既渴望加入美国主流社会,又要保持自身的黑人文化传统。因此,美国黑人总是在自我和异化之间痛苦挣扎。莫里森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一直致力修复黑人文化。对莫里森而言,黑人的过去是无法割断的纽带,过去是黑人文化精髓的宝库,只有回归过去才能找到黑人灵魂的寄托。在她的作品中,很多黑人形象在面对被白人文化同化的生存困境时,往往忘记过去,放弃了自我追寻。
本文在学者对莫里森作品母爱缺失这一主题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对母爱追寻展开研究,发现莫里森作品中展现的母爱并不是完全绝望的,其多部作品体现出对母爱的追寻。莫里森作品中缺失的是正常的、健康的母爱,存在的是变态扭曲的爱。母爱的追寻体现在黑人母亲努力保持黑人本性及黑人传统,收留并精心呵护缺少母爱又受到伤害的孩子,使她们能够正确认识自我,抵制白人文化入侵,保护黑人文化。
[1]Davis Carole B.Black Women,Writing and Identit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
[2]Mori Aoi.Toni Morrison and Womanist Discourse[M].New York: Peter Lang,1999.
[3]Susan S.Lanser.Fictions of Authority[M].New York:Peter Lang, 1998.
[4]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胡全生.难以走出的阴影——试评托妮·莫里森《心爱的人》的主题[J].当代外国文学,1994(4).
[6]陈法春.西方莫里森研究中的几个焦点[J].外国文学动态,2000(5).
[7]焦小婷.话语权力之突围——托尼·莫里森《爵士乐》中的语言偏离现象阐释[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6).
[8]杜志卿.托妮·莫里森研究在中国[J].当代外国文学,2007(4).
[9]占敏娜.论《慈悲》中母爱的缺失对弗洛伦斯的影响[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3(7).
[10]黄晖,王影.《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自我认同[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11]董晓烨.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评莫里森的小说创作[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4).
I106.4
A
1672-3805(2014)04-0068-05
2014-03-10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面上项目“跨文化语境下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爱的主题研究”(12512021)
张凡(1979-),女,东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功能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