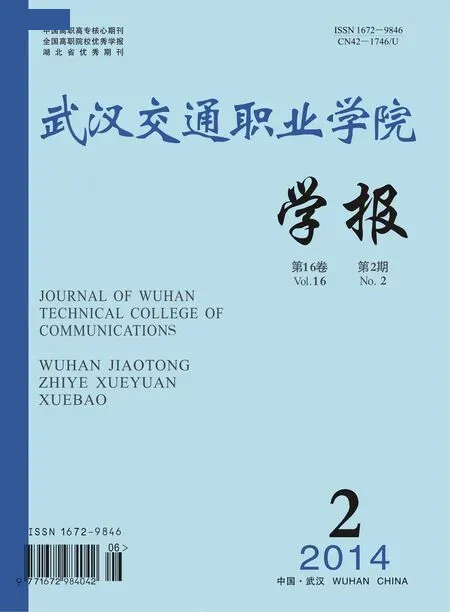从方平译《呼啸山庄》看译作的创造性叛逆*
2014-03-20陈安慧
陈安慧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1847年,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以化名出版了小说《呼啸山庄》。出版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这部不同寻常的小说一直不为世人所理解,受到了评论界猛烈的谴责,直到20世纪,其艺术魅力和价值才逐渐被人们所领悟和研究。随着西方“艾米莉热”的出现,我国不少译者陆续将其译成中文,为我国读者能读到这本英文经典名著做出了贡献,其中尤以方平先生的译本影响最广。他的第一版译本是在198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后来在1988、1993、1995、2000、2001、2006、2009、2010、2013年,多次由不同出版社再版,可见其译本受欢迎之程度。
方平先生(1921-2008)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主攻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由此成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国际莎士比亚协会执行理事。除莎剧外,也间或翻译一些诗歌和小说。他对翻译有自己的见解和追求,一些译作在我国文学翻译史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次,方平先生在文学研究方面是一名出色的学者,撰写了大量有关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文章,正是他对文学的潜心钻研,使得他能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原作,透彻领会原作的精髓。还不得不提的是,方平先生曾是一位诗人,早年在国内一些著名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新诗和译诗,1948年出版了诗集《随风而去》。又正是他的诗人气质,使得他的译本不仅文笔优美、富于诗意,而且极富创造性,堪称一名主体性极强的翻译家。在译者的主体性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方平先生无疑会成为许多翻译工作者的榜样。
一、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传统的译学理念把“忠实”置于首位,“忠实”指在语言层面上对原文不增加一分,不减少一分,亦不改变一分。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就提倡翻译要“因循本旨,不加文饰”。[1]到了近代,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多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为翻译准则,三者中仍以“信”排于首位,即译作要忠实于原作。然而,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要做到绝对忠实,何其之难!但凡从事过翻译的人都有过切身的体会。我们知道,“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凝固与给定的关系”,[2]意义的生成有赖于多方面的因素,小到发音,大到文化都会参与意义的建构,这就决定了翻译不只是字词层面的对等转换。
文学翻译又尤其之难,因为文学翻译不仅要把原语言最基本的表意功能传达出来,还要通过传达原文的表意手段来保留原文的表意效果,即保留原文的神韵,力求带给译入语读者与原语读者同样的美感享受。如此一来,在翻译中只求语言形式的简单对应,往往会失其神韵,甚至导致意义偏差;但若一味追求神韵,又恐背离原文形式太远,因此,译者总处于两难的境地之中。这种“形”与“神”的悖论就引出了译界的“忠诚”与“叛逆”之争。越来越多的译者已意识到,由于原语和译入语本身的语言特征和文化背景的不同,翻译要做到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译文要保持原作的文学价值,就要充分发挥译入语的语言特色,以译入语的规律来传达原作的风格和旨趣,这使得文学翻译成为一种再创造,而再创造无疑意味着对原文的背叛。许钧在探讨文学翻译时写道:“‘忠诚’与‘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双重性格,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这也许就是‘相似处犹显平乏,不似处倒见魅力’的翻译辩证法吧。”[3]其实早在1961年,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就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4]简单复制语言表达形式,这样的忠诚只会让文学翻译走入死胡同。一旦将原作、原语言、原语文化、作者个性、译入语、译入语文化、译入语读者等因素综合考虑的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客观必然,是不可避免的”。[5]与传统追求绝对忠诚相比,译者在这种创造性叛逆的翻译活动中更能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从隐身的地位走向前台。
创造性叛逆给译者提供了发挥个性的空间,虽然就翻译而言,译者发挥个性的创作空间很小,但只要涉及创造、涉及叛逆,就不能忽视译者主体性的存在。屠国元和朱献珑这样定义译者的主体性:“总体上说,译者的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创造力。”[6]译者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可以表现在对翻译标准的判断取舍上。翻译标准归纳起来大体上为两类:“一是传统的把原作本身视作是翻译的绝对标准,要求理想的译文是完全等同于原文的(‘等值论’);二是将接受理论或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概念引入翻译学研究,置目的语读者于核心地位,以获得读者的最佳反应为翻译的标准。”[7]其实,无论选择哪一种标准都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但不同的取舍,创造性叛逆的程度就会不同。主体性还可表现在对原文的审美过程和对译文的创造过程中。译者以自身的审美意识来发掘和理解原文的美,再把这种美转换到译文中去,无论是发掘、理解还是转换都不是被动的,尤其是转换的过程无疑是具有创造性的,只是有的译者受制于原文的束缚太多,审美创造力相对较小;有的则相反,不甘于被原文束缚太深,审美创造力发挥较多。事实上,在整个的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把“忠实”和“叛逆”看做翻译标准的两个极端,那么,译者主体性呈现出的审美创造力程度就表现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选择更靠近哪一个端点。
其实,在“忠诚”与“叛逆”两个极端之间无论选择靠近哪个点,文学翻译都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优秀的译作需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来实现翻译价值的最大化,进而实现译作文学价值的最大化。这个问题既涉及理论,也关乎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操作。从操作层面来看,笔者认为方平先生译《呼啸山庄》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方平先生在翻译《呼啸山庄》时,取的第二类翻译标准,即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更注重目的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获得的快感。这个翻译标准决定了他的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归化的策略无疑会使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有偏离,也就是说,方平先生选择了更靠近“叛逆”的那一端。但他的叛逆并不是无理由的、绝对的离经叛道。因为,即使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也“并不意味着‘忠实的’翻译标准的过时,只是‘忠实’的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8]方平先生以自身的文学素养敏感地把握住了原作的风格,并且充分利用了自己作为译者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了二度创作。但通过原文与译文的对比,我们发现,译文中的改动、添加等正是为了符合与原文相同的叙事风格,读译文时体会到的主人公的爱之深,恨之切,包括我们读者自身的感情波动,与读原文时的感受是很接近的。所以,他的“形”的叛逆,是为了忠实于“神”,正应了许钧的那句“不似之处倒见魅力”。换句话说,方平先生在“忠诚”与“叛逆”之间把握住了一个平衡点,他的叛逆并非纯粹的叛逆,而是一种基于忠实的叛逆,有如一个带着镣铐的舞者,在原著与译语读者之间这个狭窄的舞台上,凭着自己创造性的智慧与过人的技艺,舞出了一曲人人喝彩的妙章。
下面,笔者通过对方平先生所译的《呼啸山庄》的具体分析,来看方平先生是如何在译文中充分发挥他的主体性,以创造性叛逆的方式来忠实于原作。
二、方平译《呼啸山庄》中的创造性叛逆
《呼啸山庄》的大部分情节,是由女管家纳莉以讲故事的方式一段一段呈现出来的,这种叙事方式,使全文语言平易朴实,通俗自然,方平先生的译文也正是以这种语言风格为基点,经过二度创作,成就了这篇语言地道的佳作。
(一)语气助词的添加,使语言更具生活气息
上面提到过,整部书大部分都是纳莉与洛克乌在拉家常,古今中外,只要是拉家常,没有谁会用到很正规的书面语,女作家勃朗特注意到了这一点,译者方平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英语与汉语在口语的表现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如何体现原著的口语特点呢?我们看看方平先生是怎样做的。
例1:…it pleased him rarely to see her gentle—and saying—“Why canst thou not always be a good lass,Cathy?”And she turned her face up to his,and laughed,and answered,“Why cannot you always be a good man,father?”[9]
看到她居然这么文文静静的,他非常高兴,说道:
“卡茜,你为什么不能永远做一个好姑娘呀?”
她就把头抬起来直看着他,一边笑,一边回答:
“爸爸,那你为什么不能永远做一个好男人呀?”[10]
这是老欧肖与女儿的最后一次对话,当时整个屋内的气氛温馨宁静,话说完不久,欧肖就躺在壁炉旁的椅子上安详地去世了。译文中,欧肖问句后添加的一个“呀”,尽显了父亲对女儿的慈爱;卡瑟琳回答中添加的“那”和“呀”又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卡瑟琳顶嘴时的顽皮与撒娇。如果没有加进这三个字,相信会使语气变得生硬,缺少了生活中口语的生动。
例2:“You shall not meddle with him!”I continued.“He hates you—they all hate you—That’s the truth!A happy family you have;and a pretty state you’re come to!”[11]
“你别管他吧!”我接着说道。“他恨你——他们全都恨你——那可是一点儿不假的事!你的家庭多么美满哪,你做人做得真好哪!”[12]
这是纳莉对亨德莱的讥讽之语,可是,如果没有句尾的那两个“哪”,又怎能淋漓地表现出这讽刺之意呢?与方平先生同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杨苡女士是这样翻译最后一句的:“你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却给你弄到这样一个糟糕的地步!”[13]对比之下,杨苡采取了更忠实于原文形式的翻译策略,但从表达效果上来看,方平的版本更口语化,更具生活气息。
方平译文中像上述例句那样添加进去的语气助词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因为原著中没有,就简单地称这种添加为对原著的纯粹叛逆,因为这种神来之笔,实在是基于对原著文学效果忠诚的创造性叛逆。
(二)汉语词汇的精心选用,使语言更地道传神
一部小说能打动读者,很大一部分功劳在于其语言,原创小说如此,翻译小说亦如此。对于方译《呼啸山庄》的成功,其精彩词汇的选用是功不可没的。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例1:Ah,I thought,there will be no saving him—he’s doomed,and flies to his fate![14]
我在想:唉,他是没救了;他是劫数难逃了;他要往命中注定的圈子里钻去了![15]
埃德加·林敦在目睹了卡瑟琳对纳莉的野蛮行径之后仍愿意回到卡瑟琳身边,以上这句就是纳莉在看到埃德加的这一举动后所发的感慨。原文句子简短,意思明确,但意味深长。如何把这种意味用汉语表达出来不是件简单的事。方平先生把“doomed”(本意“命中注定”)译为“劫数难逃”,“劫数”是汉语佛教中的用词,让人不免想起命运的既定和生命的轮回,“难逃”则体现出对陷入劫数之人的痛心感,这样,把“doomed”的余韵传达了出来。后一句更精彩,“fate”改译为“命中注定的圈子”显然是为了好与动词搭配,而把“flies”译为“往……里钻去了”,更是把埃德加义无反顾、迫不及待的心情传达得与原文中的“flies”别无二致。对比杨苡的译文:“他已经注定了,而且朝着他的命运飞去了!”[16]杨译虽忠实了原文,但语气平淡,没能把纳莉的痛心感传达出来。
例2:…you will escape from a disorderly comfortless home into a wealthy,respectable one;and you love Edgar,and Edgar loves you.All seems smooth and easy;where is the obstacle?”[17]
你可以脱离一个乌七八糟、没有乐趣的家,来到一个富裕体面的家庭里;你爱埃德加,埃德加也爱你。一切似乎都很美满称心呀,阻碍又在哪里呢 ?[18]
我们知道,中国人很偏爱四字词,方平先生在这里连用几个四字词“乌七八糟”“没有乐趣”“富裕体面”“美满称心”,使译文显得地道传神,很能迎合中文读者的口味。杨苡的译文是:“你将从一个乱糟糟的、不舒服的家庭逃脱,走进一个富裕的体面人家”。[19]杨苡直译“comfortless”为“不舒服的”,但与“家庭”搭配,应该还是“没有乐趣的”作定语更地道,“没有乐趣的”虽改变了字面义,但译出了“comfortless”的实质意义。可见,愚笨的忠诚是要不得的,方先生的译文之所以更富神韵,正在于他在叛逆之中追求文学翻译的“化境”。
(三)语句顺序的调整,使语言更流畅自然
只要是懂得英汉两种语言的人都知道,英语与汉语在句子的组织与排序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在语序的选择上,译者的主体性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被动接受译文语序,克制“忠诚”的译者,只会使句子译得艰涩拗口;反之,主动大胆改动,充分发挥主体性的“叛逆”译者会译出明白流畅的句子来。看看方平先生的译文。
例1:On returning,I whispered to Catherine that he had heard a good part of what she said,I was sure;and told how I saw him quit the kitchen just as she complained of her brother’s conduct regarding him.[20]
回来之后,我悄悄告诉卡瑟琳,她说的那些话,我敢说,他大半都听去了;还说正在她埋怨她哥哥待他刻薄的当儿,我看见他溜出了厨房。[21]
原文前半句是有着多重从句的复杂句,汉语中没有这种结构,因此方平先生把它分割成了四段小句,这样的短句很符合汉语的习惯。杨苡将这半句译为:“回来时,我低声对凯瑟琳说,我料到他已经听到她说的大部分话”,[22]核心句子过长,不大符合汉语口语的特点。另外,原文前半句的“I was sure”放在句尾,方平译文中“我敢说”放到了句子中间;后半句原文的时间状语在后,方平译文中把时间状语改放到前面,这样的调整也是基于汉语的语言习惯。可以说,勃朗特在写作时,肯定是完全按照英文的文法习惯在写,而方平先生在翻译时,主动地按照汉语文法在译,因此,这里原文与译文在句子形式上的差别,实际上是英汉两种语言在行文习惯上的差别。想要有自然流畅的译文,做一些改动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动正是为使目的语读者读来顺畅,从而保留原作的文学价值。
(四)句式的灵活转换,使意义更清晰明了
有时英语读起来很明白的句子,可汉语照那个说法,就是让人不明白。方平先生很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翻译中做出了许多成功的转换。
例1:I’m not sure whether he were not at the door this moment.[23]
这会儿他就在门口也难说呢。[24]
这句话之前,纳莉在告诉卡瑟琳,约瑟夫来了,希克厉也要跟他一起进来了,所以推测希克厉此刻或许就在门口。但英文用了一个双重否定,直译过来就是:“我可说不准他这会儿是否不在门口。”这样译很可能会中断读者的阅读过程,因为需要停顿个两三秒琢磨这句话的意思,不如索性翻译成肯定句,让意思更加明了。
例2:…one day,I had the misfortune,when she provoked me exceedingly,to lay the blame of his disappearance on her:where indeed it belonged,as she well knew.[25]
有一天,活该倒霉,她惹得我发急了,我就把他失踪的责任怪在她头上——说实话,不怪她又怪哪一个呢?这一点她自个儿也很明白。[26]
此句译得精彩之处在于,分句“where indeed it belonged”被译成了“说实话,不怪她又怪哪一个呢?”将肯定句译成了反义疑问句,这不能不称之为“叛逆”,但这个叛逆却让人读得眼前一亮。这反义疑问句不正好将纳莉对此处的义愤填膺表现得一清二楚,将纳莉拉家常的语气描绘得惟妙惟肖吗?一个句式转换,不仅表意到位,还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读到此,不禁为译者灵活的处理拍案叫绝。看杨苡的译文:“的确这责任是该她负,她自己也明白。”[27]与方译比起来,义愤感就欠缺一些。
整部译著中,佳词妙句比比皆是,限于篇幅,不在此一一列举。其实,大多数令人赞赏钦佩的佳译都是在牺牲原文形式的前提下得来的,但这种牺牲,实是为了保留原文的精髓,如此做法,即可称得上是“创造性叛逆”。
三、结束语
在《呼啸山庄》的诸多译本中,方平先生的译本具有与其他译家译本的相似性,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生活画卷等大方向的把握上都能做到忠诚于原作的风范。但方平先生在人物语言、故事的叙述语言方面的翻译技巧能更胜一筹,使译作更易被汉语受众接受,原因就在于他的译作切实实现了忠诚与叛逆的的有机结合,从而使该译作更为译界与小说读者所接受,其间透发出的译家的思想文化素质、对汉英两种语言受众的掌控以及娴熟的翻译技巧,都值得译界称道、总结和研究。
方平先生在他的翻译生涯中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标准,挥发着自己的个性。在给谢天振的《译介学》所作的序中,他这样写道:“‘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所引进的一个命题,作者用专章讨论,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谈到文学翻译,立即会想到‘翻译者,反叛也’这一句来自海外、广为流传的名言。翻译工作者都能体会到这句话的讽嘲口气而心有不甘。对于以认真严肃自勉、把‘信’和‘忠实’看作文学翻译第一要义的译者,最怕的就是译文出错,而‘错误’和‘叛逆’在我们心目中,不分彼此,同样可怕又可耻。现在作者提出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并引用了法国专家的论述:‘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28]此段话中可见方平先生对译者主体性的推崇、对“创造性叛逆”的赞赏。如果说,他的学者的严谨态度、诗人的文字功底,使得他能做到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家的话,那么,他在翻译过程中对主体性的发挥、对创造性叛逆的把握,使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翻译家。值得一提的是,对创造性叛逆的把握,涉及主体性发挥的度的问题,若发挥过度,一味叛逆而全然不顾原著,那就称不上是翻译了。方平本人也说过,翻译应该是“既和原作者倾心相交,成为朝夕相处的师友,同时也不忘其本,心悦诚服地做原作的忠实的追随者。”[29]译者之难,正在于既要用自身的主体性再现原著的审美特征,又不能脱离原著的审美框架,如此在狭小的空间舞出自我的个性。
[1]支谦.法句经序[C]//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7.
[2]胡东平,魏娟.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3.
[3]许钧.我和翻译[M]//戴立泉,杨怀宇.江苏学人随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42.
[4][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5][8]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51,12.
[6]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11):9.
[7]袁莉.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J].中国翻译,1996,(3):6.
[9][11][14][17][20][23][25]Bronte Emily.Wuth ering Heights[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33,59,78,62,65,63,70.
[10][12][15][18][21][24][26]勃朗特.呼啸山庄[M].方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6-47,82,78,86,91,88,97.
[13][16][19][22][27]勃朗特.呼啸山庄[M].杨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68,65,71,75-76,82.
[28]方平.序二[M]//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5.
[29]方平.他不知道有己是一个诗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