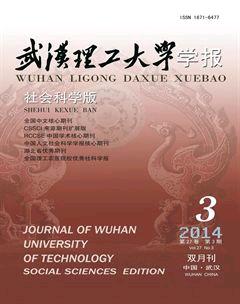理念重塑与制度实践:社区矫正的性质之反思*
2014-03-20张健一
张健一
(江苏警官学院 法律系,江苏 南京210012)
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起步于上海,历经十年探索渐成勃兴之势。因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立法者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社区矫正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有其不足之处①,但毫无疑义,历经十年沉淀所成的这些规定,在我国社区矫正法治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②。自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学界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从多角度、多侧面对社区矫正的运行机制(模式)的建构以及社区矫正的立法的完善积极建言献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界对于社区矫正的性质则缺乏足够的关注。笔者认为,明确社区矫正性质具有重大意义。制度建构的目的决定具体制度的性质;制度性质则制约着具体制度的建构模式。社区矫正工作机制(模式)的构建以及社区矫正的立法的完善都离不开社区矫正性质的合理定位。社区矫正性质的合理定位则需要依赖社区矫正制度的建构目的。以《刑法修正案(八)》的施行为契机,本文力图澄清社区矫正的性质。
一、犯罪治理范式——责任本质的制度化展开
犯罪治理范式是特定时期刑事立法有关罪刑关系、刑罚裁量、执行相关制度的系统化称谓。启蒙时代以降,饱受中世纪黑暗奴役的民众,在时代精英所高扬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旗帜下不断发现主体性品格。与之相对应,犯罪治理范式也开始了近代化的变革。从宏观上来看,犯罪治理范式的演进早期深受学派之争的影响;在实证学派盛极而衰之后,由于经验性研究方式的式微,价值学重新构成了犯罪治理范式的基础理论。
“中世纪的刑罚制度是以死刑、使人残废之身体刑和驱逐出境为中心,以彻底地保护社会免受刑罚处罚的个人的犯罪危害为目的”[1]。由此可见,人道主义理念的缺失与刑罚残虐性的结合彰显出中世纪犯罪治理范式的威慑本质。姑且不论威慑作为目的的正当性,仅仅实现目的的手段的不适当性就给这种威慑蒙上了一层阴影。换言之,这种威慑不过是血腥的同义语,是同态复仇的遮蔽物。
作为犯罪治理范式近代化引导者的前期古典学派对上述非合理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且以自由意志论为基础在道义责任的立场上提出了报应主义的刑罚理念。尽管在个别古典学派论者的著作里仍然在反坐原则的意义上解读报应主义,但是,以对理性的推崇为基础,从社会伦理意义上理解报应观念的前期古典学派仍然体现出其巨大的历史进步性。本源于其基本立场的罪刑法定主义、责任主义、罪刑均衡等基本理念构成了现代刑法理论的基本框架。因此,前期古典学派的上述思想在欧洲很多国家的立法上一度占有绝对的话语权③。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古典学派在法秩序维护方面的基本思想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相契合也是其受青睐的重要原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建构在前期古典学派思想之上的刑事立法在应对青少年犯罪、累犯等问题上的乏力逐渐招致人们的批判。“在要求制定刑法的个人乃至国民欲求的背后,是存在着同类的不良行为并已达到一定规模这一事实的”[2]。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加之受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刑事实证学派逐步登上历史舞台。从社会对个人的关系上建构起来的社会责任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与古典学派重视行为不同,社会责任论重视行为人的危险性格,强调特殊预防。实证学派实质上主要是犯罪学,该学派试图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明晰犯罪的原因以利于犯罪预防。也正是因为其犯罪学的实质,导致了实证学派对犯罪治理范式的渗透并不是全方位、系统性的。在其影响下,刑事立法出现了包括缓刑、假释制度的确立、累犯处罚加重等一些新的动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保安处分被纳入到刑事制裁制度当中。
由于实证学派关注行为人危险性格的主张所蕴含的侵犯人权的危险被法西斯色彩的立法所放大,另一方面,“古典学派从防止犯罪的立场出发,也意识到必须考虑犯人的人身危险性”[3]。因此,古典学派和实证学派出现了相互靠拢、相互融合的局面。以期待以可能性思想为基础的规范责任论秉持行为责任的基本立场,在行为人不按照规范的期待实施行为能够反映行为人缺陷人格态度的意义上也能够同社会责任论相协调,故而为多数学者所支持。以行为责任为基础,吸收行为人责任的思想成为主流的立法取向。以德国为例,“刑事政策……根据符合预防目的的制裁的适用,追求罪责原则的要求与希望之间的均衡”[4]。
从上文论述可见,近代刑事立法在犯罪治理范式上的沿革深受同时代责任本质理念的影响。在规范责任论立场上,如何在犯罪治理范式的桥梁作用下实现责任与刑罚的协调至关重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乡土社会已然被肢解得四分五裂,陌生人社会的降临带来了更多类型的纠纷。在价值多元化引发的纠纷多样化的时代,对规范效力的期待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融入了义务性思考的规范责任论,形式上是增加了一个责任的评价要素,实质上是在承认主体能力受制约的思想下将主体作为社会人而非自然意义上的人来看待。上述思想中体现出规范责任论对人性的尊重以及对人类弱点的承认。与道义责任论相比,刑事义务观念的引入因其明确性而在陌生人社会中相应地扩大了公众的自由。由此可见,确定并稳定(被破坏后)被公众(包括行为人)对规范效力的信赖应当成为责任谴责的目的论基础。无论是刑罚的裁量还是刑罚的执行都应当以恢复被动摇了的公众(包括行为人)对规范效力的信赖为归依。“在任何一种不能通过至少是为了将来而改变态度来弥补违反规范的行动的令人失望的效果,不能通过适当的措施把违反规范的行动的可能性减少到决定性不重要的轻微程度的体系中,通过归属来实现秩序的稳定就是必要的。任何一个不强迫或者不劝告服从规范者达到完全顺从的系统,都需求这种必要性”[5]。
二、监禁矫正的弊端丛生——规范效力信赖的制度性障碍
(一)实践困惑——监禁矫正的现实困境
一般认为,现代自由刑起源于16世纪的荷兰监狱。现代意义上的监禁矫正的发展史就是监禁矫正被不断批判的历史。虽然经历了世界监狱改革运动的洗礼,监禁矫正仍然因其各种弊端而备受质疑。
监禁矫正因其本身目的设定与固有功能的冲突而受到诸如受刑人欠缺受刑意愿、切断具有社会化功能的人际关系、受刑人的监狱化、高刑罚成本以及徒刑所可能具有的反效果等批判[6]。有学者对监禁矫正的各种弊端作了系统的总结[7]。在笔者看来,监禁矫正的各种弊端,均以这种罪犯处罚措施在防止行为人再次犯罪上的无力为前提。如果监禁矫正可以很好地预防再犯,则包括犯罪标签、增加财政负担等字眼在利弊衡量的基础上都将显得不是那么地刺眼。监禁矫正无法有效预防再犯的弊端,从功能论上来看,是源于短期自由刑中的“交叉感染”和长期自由刑中的“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前者主要体现为,短期自由刑的犯罪人往往因彼此之间交换犯罪资讯、传授犯罪技术、固化犯罪心理而冲淡甚至抵消该类刑罚的矫正效果。后者主要表现为,犯罪人在刑满释放或者假释之后往往面临着歧视、适应社会的心理障碍等再社会化方面的问题。
(二)理念错位——监禁矫正的困境根源
监禁矫正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其背后所蕴含的立法者思维的灵魂并不能脱离其基本的功能构造。制度设计背后目的取向的适当性欠缺则是引发监禁矫正困境的根源。毋宁说监禁矫正作为一种制度构造,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背负着许多本不应由它承担的期待。
与犯罪论脱钩的刑罚论不是真正的刑罚论。责任的本质因其与刑罚的相生关系而成为联通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纽带。刑罚的裁量和执行不能脱离责任原则的制约。洞悉责任的本质不仅提供刑法裁量的标准,而且可以为刑罚的执行提供目的论指引。
从道义责任论的立场出发,刑罚是对犯罪行为道义上的报应。更为重要的是,监禁矫正在报应的理念之下虽然使得犯罪人的主体性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但这种个体的尊重对社会期待的安全而言毫无意义。在道义责任论之下的一般预防可能会因报应刑罚的严重性而导致强化犯罪心理的负面效果。因此,道义责任论寄希望于通过报应的正义性来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的初衷是无法实现的。作为其实现手段之一的监禁矫正也会因目的与功能的错位而饱受责难。刑事实证学派所坚持的社会责任论强调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对犯罪人的矫正不是对孤立的个人的矫正教育。犯罪人在监禁矫正时以及刑满释放后面临的是不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这些不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需要配套制度来消除。这些社会关系、社会环境中的因素可能阻碍着监禁矫正中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由此可见,刑罚目的定位的误差以及配套制度的缺失共同导致了监禁矫正当下的困境。其中,责任本质的错误定位导致的刑罚目的的错位具有根本意义。
从规范责任论的立场出发,刑罚的裁量不仅应当考虑到行为人偏离规范期待的程度,而且需要考虑导致行为人偏离规范而行为的诸多因素中是否存在着可以原谅行为人的成份;不仅应当考虑义务违反的认识,而且要考虑到认识的违反义务性。在刑罚执行相关制度的建构中,也应当以恢复规范效力的信赖为目的。因此,为了弥补监禁矫正由于存在短期自由刑中的“交叉感染”和长期自由刑中的“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而无法实现上述目的的缺憾,作为新型的罪犯处遇制度的社区矫正应运而生。
三、社区矫正的性质——目的论思想的制度实践
(一)聚讼不断——社区矫正性质争论
法学理论对于社区矫正的性质争议较大。围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基本形成了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各种观点基本上都承认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但又各有其侧重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8]。第二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仅是刑罚执行方式,并不是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方式,被判处监禁刑的罪犯经过法定程序裁定,也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9]。第三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只是前者为主属性后者为从属性”[10]。第四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不仅是刑罚执行活动,而且是对非监禁措施的监督管理活动,更是一种对非监禁刑和其他非监禁措施的罪犯予以矫正、培训和安置帮教的活动,具有矫正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性”[11]。
笔者对上述有关社区矫正性质的观点作出如下评价。首先,从《刑法修正案(八)》所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来看,将社区矫正视为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不尽合理。虽然管制是法定的刑罚种类,但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假释、缓刑都不是刑罚种类。因此,社区矫正就不会涉及到非监禁性质刑罚的执行问题。其次,将社区矫正视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的观点可以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社区矫正的定义相协调。但是,将社区矫正视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却无法解决长期自由刑中“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因为对长期自由刑中的刑满释放者进行社区矫正是解决“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的必要手段。由此可见,将社区矫正视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的观点虽然能够实现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协调解释,但却使得社区矫正缺乏开放性。再次,将社区矫正视为刑罚执行活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社会工作的公益性明显和社区矫正是包含关系而非对应关系。最后,第四种观点将社区矫正视为一种监督管理活动是有疑问的。就长期自由刑而言,面对“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将犯罪人释放(含假释)之后,作为弱势群体的刑释人员需要的是社会从保护者的立场出发的保护观察,而非从管理控制者的立场出发的监管。社会应该从强者的立场出发保护刑释人员免受不良影响并确保已然建立起来的规范信赖不被破坏。如果从监督者的立场管控其行为,则必然导致其逆反心理,既然将其释放,就应该给与相当程度的信任。更为重要的是,刑法规定对假释的犯罪人监督管理、社区矫正,但是只规定了对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假释犯收监执行。由此可见,至少在立法所承认的假释犯这里,社区矫正并不等同于监督管理。
(二)性质明晰——目的论思想的现实展开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功能性客体,是以主体的需要为基础,在一定的效果预测前提下建构而成。较之于传统的监禁矫正,社区矫正应当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脱离社区矫正制度设计的目的谈论社区矫正的性质。从前文的论述来看,社区矫正的兴起正是源于监禁矫正存在短期自由刑中的“交叉感染”和长期自由刑中的“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而无法实现恢复规范效力的信赖这一目的的缺憾。其中,短期自由刑和长期自由刑又各有不同的问题。就社区矫正而言,由短期自由刑和长期自由刑不同的问题导致目的实现的不同障碍,目的障碍的多样性使得因对象不同而出现目的侧重点的差异,目的侧重点的不同导致性质的多重性。
一方面,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表现为,由于“交叉感染”的危险性而导致监禁矫在构建规范效力信赖上的无力。短期自由刑的执行场所中容纳了各种各样的犯罪人。由于矫正期间的有限性,往往在尚未出现矫正效果之时,犯罪人之间就已经因相互同病相连的心理而彼此合理化对方的犯罪行为,进而通过犯罪方法等的交流导致监禁矫正将犯罪人“无色化”的努力付之一炬。作为监禁矫正置换物的社区矫正,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改变矫正对象的矫正环境。对短期自由刑的罪犯而言,矫正环境的改变不仅可以避免监禁矫正可能带来的“交叉感染”,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犯罪人的自我标签化。矫正环境的改变是为了矫正效果的达成,矫正环境的改变只具有形式意义。由于矫正目的的稳定性导致矫正环境的变更并不能对矫正内容作出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罪犯而言,社区矫正原则上应当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此外,缓刑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具有其特殊性。虽然缓刑不是短期自由刑,但是其适用的对象包括拘役这种典型的短期自由刑。缓刑的这种特殊性质以及其适用的实质条件④反映了,虽然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已然破坏了法秩序稳定的形象并因此彰显出行为人对规范效力的态度,但行为人事后的行为已然表现出其试图回归法秩序的行为取向。正是行为人这种外部行为之间的冲突状态使得法秩序应当给与行为人一个展示自己对法秩序态度的平台。此外,在这一平台之上,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应当对行为人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由于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限制,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缓刑犯罪人因其罪行及事后行为的相似性而可以和拘役的情形做相同的解释。因此,对缓刑犯的社区矫正应当定性为监督管理措施。
另一方面,对被判处长期自由刑的罪犯而言,如何破解长期自由刑中“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是社区矫正制度面临的课题。由于减刑、假释制度的存在,从理论上讲,监禁矫正的对象总有社会化的那一天。被判处长期自由刑的犯罪人往往主观恶性较重,并且其人身危险性远高于短期自由刑的犯罪人。虽然经过长时间的监禁矫正,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程度也很难把握。加之现行刑法规定对立功行为的规定并不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成正相关关系,这就容易导致减刑的适用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不成正比。对长期自由刑的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实质上是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观察以避免因外在原因导致已经通过监禁矫正建立起来对规范效力的尊重被破坏而重新犯罪。因此,对长期自由刑的犯罪人而言,社区矫正应当是一种保护观察措施。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外在不利因素冲击已然建立起来的行为人的规范意识。
四、结 语
在恢复规范效力的信赖目的之下,社区矫正针对监禁矫正的弊端而建构起来。因对象的不同,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方式、监督管理措施以及保护观察措施等多重性质。社区矫正的性质影响着社区矫正的模式。以社区矫正的性质为基础,从社区培育以及实现同监禁矫正协调的视角出发,社区矫正的主管部门应当是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将刑满释放人员以及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纳入到社区矫正的对象中来;应当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立法。
因为应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的时代潮流,社区矫正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社区矫正基本理念的探索关系到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根基。对社区矫正制度性质的探讨不能脱离对责任本质的理解以及监禁矫正的弊端。社区矫正性质的多样性导致社区矫正运行机制的复杂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社区矫正运行机制的合理构建影响到社区矫正制度效果的发挥、社区矫正目的的实现程度。作为一种“舶来品”,社区矫正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如何适应时代精神,努力实现社区矫正的本土化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 比如,社区矫正制度的性质不明、主体不清、权责错位、保障无力,等等。
② 这不仅体现出刑事立法对社区矫正正面肯定的基本态度,而且还展现出立法者在刑罚思维上的微调。
③ 例如,意大利1889年刑法典可以说是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理论体系的集中反映。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著,陈忠林译评的《意大利刑法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④ 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是根据其悔罪表现,没有再次犯罪的危险并且宣告缓刑对其社区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1]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02-403.
[2]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顾肖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8.
[3]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M].黎 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1.
[4]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904.
[5]格吕恩特·雅科布斯.行为 责任 刑法——机能性描述[M].冯 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3.
[6]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472-473.
[7]王顺安.论社区矫正的利与弊[J].法学杂志,2005(4):102-106.
[8]程应需.论社区矫正与刑罚制度改革[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539-543.
[9]王 琼,等.行刑的社会化(社区矫正)问题之探讨[J].中国司法,2004(5):67-71.
[10]但未丽.社区矫正概念的反思与重构[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57-64.
[11]王顺安.社区矫正的法律问题[J].政法论坛,2004(3):1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