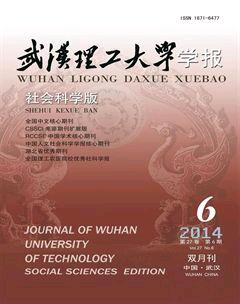“地狱之门”与“天国之门”*——刘再复对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再评价
2014-03-19古大勇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4YJA751004)
摘要:刘再复从“原形文化”和“伪形文化”的角度,认为中国的“四大名著”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具有天壤之别,«红楼梦»和«西游记»体现的是中国的原形文化,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体现的则是伪形文化.刘再复同时依据“人”的价值标尺,认为«红楼梦»折射的是“人”的文化,«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折射的则是“非人”的文化.刘再复对“四大名著”的评价乍看石破天惊,不合常情,但事实上有理有据,切中肯綮.他的观点不免遭到一些批评,但纵观这些批评文章,却不同程度地犯了“个案反驳论”、“偷换概念论”和“上纲上线论”的毛病.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 i.ssn.1671-6477.2014.06.034
收稿日期:2014-07-15
作者简介:古大勇(1973-),男,安徽省无为县人,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刘再复研究.
一、“地狱之门”与“天国之门”
«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是人们公认的中国“四大名著”,一向被视为比肩而立、质量等高的优秀文学作品,其各有千秋,各具特色,难分伯仲.如果一定要一比高低的话,那么在“四大名著”中,«红楼梦»可以说相对略胜一筹,但这其中的差别也只是悬殊不大的“毫厘”,并没有根本性的悬殊,也即是说,即使有差别,也是同在优秀之列范畴内的差别.但是这一评价现状却被刘再复先生打破并颠覆了.刘再复自“第二人生”以来 ①(1989年之后)转向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分别出版了研究«红楼梦»的四本著作,统称«红楼四书»(包括«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四部著作),研究«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著作«双典批判: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刘再复虽然没有出版关于«西游记»的研究著作,但在«红楼四书» 和«双典批判»中,都有不少关于«西游记»的评价.刘再复在中国人都看重“四大名著”的背景下,发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石破天惊”之语:认为不可以对“四大名著”等而视之,其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非艺术方面)有天壤之别,是“天国”和“地狱”之间的差别:“如果天国是指美好人性的终极归宿,那么«红楼梦»正是导引我们走向天国的‘天国之门’,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都是把我们引向天国的诗意生命,即帮助我们走出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之地狱的诗意生命.而«水浒传»、«三国演义»却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1]5-6«水浒传»、«三国演义»“固然是‘大才子书’,但又是‘大灾难书’.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两部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格.现在到处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到处是具有三国文化心理和水浒文化心理的人.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1]5而关于«西游记»,刘再复虽然认为它与«红楼梦»有一定差距,但是把它视为与«红楼梦»同类而不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同类的作品,“故国的几部经典长篇小说……唯有«西游记»和«红楼梦»总是让人喜欢,愈读愈感到亲切,«西游记»具有童心,«红楼梦»则具有‘爱心’.” [2]8
特别值得提出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的是:刘再复在对“四大名著”进行比较评价中,主要采取的是文化批判的视角而不是传统的文学批评的方法.所谓的文化批判,它的重心是一种指向“善”的伦理判断,而不是指向“美”的审美判断,“文化批判的对象则是蕴涵于文学作品文本中的文化意识,它只涉及精神内涵,不涉及审美形式,它与心灵有关,但与想象力、审美形式无关.换句话说,在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必须悬隔审美形式、想象力等要素,而直接面对文学作品的精神取向、思想观念、文化意识、人性原则等价值要素.” [1]1因此,刘再复认为“四大名著”在审美形式、艺术层面上都是同样优秀的作品,其差距主要体现在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上.
二、“原形文化”和“伪形文化”
在比较评价“四大名著”时,刘再复受到史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的影响,提出了“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概念.所谓“原形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原汁原味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则是指丧失本真本然的已经变形变性变质的文化.每种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风浪颠簸中都可能发生蜕变,考察文化时自然正视这一现象.” [1]10史宾格勒论证的中心是异质文化或外来文化侵入之后使原质文化(阿拉伯文化)产生“伪形”,而刘再复则认为不仅外来的异质文化,而且民族内部的沧桑苦难,尤其是战争的苦难和政治的变动,也会使文化发生伪形.«山海经»是“中国真正的原形文化,而且是原形的中国英雄文化.«山海经»产生于天地草创之初,其英雄女娲、精卫、夸父、刑天等等,都极单纯,她(他)们均是失败的英雄,但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她们天生不知功利、不知计算、不知功名利禄,只知探险、只知开天辟路、只知造福人类,她们是一些无私的、孤独的、建设性的英雄.她们代表着中国民族最原始的精神气质……(他们)都是世界的‘修补者’,全是救人英雄.” [1]13-14刘再复认为«红楼梦»和«西游记»连接的是«山海经»的基本精神,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远离和违背了«山海经»的原形精神,走向了伪形化,“其英雄已经不是建设性的英雄,而是破坏性的英雄,其生命宗旨,不是造福人,而是不断地砍杀人.他们不是要‘补天’,而是自己想成为‘天’或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无法无天.他们已经失去«山海经»时代的天真,或把天真变质成粗暴与凶狠,或埋葬全部天真与全部正直,完全走向天籁的极端反面,耍尽心术、权术与阴谋.人的全部智慧,不是用于补天与填海,而是用于杀人与征服.” [1]15
刘再复以具体的文本细读为基础,以“双典”中的具体事件和人物言行为依据,对小说中的暴力、权术、义和欲望等内容进行抽丝剥茧、剔骨见肌的剖析,真实展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涵和伦理价值.具体而言,在“双典”中,暴力使英雄发生了严重的“伪形”,权术使智慧发生了严重的“伪形”,“兄弟伦理”的“小义”使“义”发生了“伪形”,“欲望有罪”使女人走向“伪形”.
暴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其本质是极不文明的,不值得提倡.但是人们在暴力的价值属性的判断上,却更多地依据暴力产生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来判断暴力的价值,如果这种暴力是为了实现一个正义的或看似正义的诉求,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或看似崇高的目的,那么暴力就会成为侠义或革命的化身,暴力的实施者就会摇身一变为“英雄”或“革命者”,暴力亦被视为实现人类正义的合理化途径.“双典”中特别是«水浒传»中到处充斥着血腥的暴力叙事,但正是由于作者为暴力寻找到一件正义性和合法性的“伦理外衣”,就使暴力行为变得合理,这件“伦理外衣”在«水浒传»中主要体现为“造反有理”.刘再复在书中对“造反有理”的“伦理外衣”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挖掘其隐含的“反人道”本质.在梁山好汉看来,他们之所以走上造反之路,是因为奸臣当道,社会太黑暗,他们要“替天行道”,有了“替天行道”这一占据道德高位的伦理原则和崇高旗号,梁山好汉仿佛就拥有了至高的正义力量和绝对的道德优势,于是他们使用一切无法无天、反人道的手段,放开杀戒,残杀妇孺,殃及无辜,惨不忍睹.如武松在“血洗鸳鸯楼”事件中的那场大屠杀,他有理由杀害的至多不过是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人,可是他却滥杀了十五人,连不相关的丫鬟和女子都不放过.李逵可以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把一对正在谈恋爱的青年男女剁成肉块,把四岁的小衙内砍成两段.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这些“反人道”的暴力行为均被视为天经地义,没有受到作者与读者的谴责.刘再复转而分析了“天道”的本质和逻辑特征,即认为它不过是为暴力寻找一个掩人耳目的漂亮口号,其本质不过是“社会规则不合理,所以我用什么手段对付社会均属合理……社会恶,我可以比社会更恶,社会黑,我可以比社会更黑.在此逻辑下,造反有理变成抢劫有理,杀人有理,吃人有理” [1]48,滥杀无辜也有理,从而使“反人道”的暴力行为堂而皇之地走向合法化和正义化,产生了一个个以暴力为基本内涵的所谓“英雄”.这些“英雄”与«山海经»中的建设性英雄原型已经南辕北辙,走向了严重的“伪形”,但竟然能得到后世读者的普遍喜爱与崇拜,更有批评家金圣叹和李卓吾,对武松、李逵的杀人行为赞不绝口,金圣叹干脆把武松视为顶天立地的“天人”.“武松杀人杀得痛快,施耐庵写杀人写得痛快,金圣叹观赏杀人更加痛快,«水浒»的一代又一代读者也感到痛快.” [1]44“嗜血”的行为事实上反映了中国人国民性深处积习难改的暴力崇拜倾向及特点.
如果说«水浒传»体现的主要是“暴力崇拜”,那么«三国演义»体现的主要是“权术(诡术)崇拜”.权术是中国传统智慧变异后呈现的“伪形”,它来源于智慧,但是当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时,当它和利益、权力发生关系时,智慧就会发生变质,就会异化成社会生活中特别是政治场域中的机变性、诡诈性手段.叶适的«宝谟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中说,“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时期,没有权术,只有至诚,属于中国的原形文化.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纵横家、兵家、法家、道家登上历史的舞台,出现«鬼谷子»、«孙子兵法»、«韩非子»、«战国策»等著作,在刘再复看来,中国文化在此阶段发生了“伪形”,出现了权术文化的第一次高潮.三国时期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权术文化第二次高潮,«三国演义»就是对这种权术文化“集大成式”的形象化表述,它全面展示了中国权术文化的各种形态.诡术无孔不入地进入到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进而泛化到一切人际关系领域,到处是诡人诡士、诡舌诡言.在沙场上施行的是诡计、诡谋,在日常生活中则充满诡情、诡态、诡行……‘诡’进入了婚事、情事、儿女事.” [1]106刘再复随即在文中细致剖析了刘备的儒术、曹操的法术、司马懿的阴阳术以及各方枭雄都惯用的出神入化的“美人术”.诡术面具下的三国“英雄”们,早已远离了中国传统原形文化的“至诚”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变质,是属于“伪形”的英雄.
刘再复认为“双典”中的“义”也发生了严重的“伪形”.在他看来,孟子之“仁义”和伯牙、钟子期之“情义”代表着中国“义”的两种“原形”,“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利’作为‘义’的对立项.把利益原则与道义原则加以区分,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义的‘原形”是非功利的” [1]130,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普世性价值.但这种具有“原形”特征的“义”在历史进化过程中逐步变质,走向“伪形”,由“义”而蜕变为“结义”、“聚义”和“忠义”,两者的内涵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如“结义”,就有两个明显的局限:“(1)对内的凝聚性和对外的排他性; (2)团伙之内的小义取代了团伙之外的社会大义.” [1]133这种“义”缺乏爱、道义与关怀的普遍性,只在团伙之内讲“义”,团伙之外则不讲“义”,把加盟的兄弟利益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置于一切利益包括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可以为了兄弟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其它任何利益.刘再复对“双典”中“伪形”之“义”的发现同样具有“石破天惊”之感.
而«红楼梦»体现的则是一种原形文化,“«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和他心爱的诸女子,以及浸透于全书的精神,都是«山海经»的精神与赤子情怀,是远离«山海经»之后的泥浊世界,特别是巧取豪夺的世界.贾宝玉这个人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用他的天真挑战着一个庞大的泥浊世界,与夸父、精卫一样呆傻.«山海经»所呈现的中国原形文化精神是热爱“人”、造福人的文化精神,是婴儿般的具有质朴内心的精神,«红楼梦»连接、呈现并丰富化了的正是这种精神.” [3]
«红楼梦»呈现的是一个与«三国演义»截然不同的世界,“«红楼梦»给中国人提供了心灵体系; 而«三国演义»却提供了权术体系.” [1]210如果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戴着面具,充满心机,工于算计,巧于伪装,互不信任,人性布满计谋的毒瘤,那么«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如贾宝玉,则是一个“至诚”之人,质朴善良,为人宽容,人性丝毫未受污染,极为纯粹,不会算计,不知猜忌,完全没有心机,具有老子所谓的“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的特质.在世俗世界中,他不懂人情世故,甚至不懂得与人交往,他的心灵向一切人开放,绝不设防,绝对信赖,就是从偏僻乡下赶来的刘姥姥“信口开河”的故事,他也信以为真,他永远保持着一种庄子所谓的“混沌”的状态.贾宝玉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他爱身边的所有人,他具有一颗慈悲之心.如他自己被雨淋了,却只顾关心他人在雨中被淋着.玉钏不小心把滚烫的药汤泼到他的手上,他却不顾自己的疼痛,反而忙着问玉钏有没有烫着,痛不痛.大观园中几乎所有的人对赵姨娘的行为都不齿,只有他却从不说赵姨娘的一句坏话.贾环憎恨宝玉,企图用滚烫的油灯烫瞎宝玉的眼睛,最后宝玉的眼睛虽然没有被烧毁,但是脸却被烧伤了,但他没有计较,还要竭力为贾环掩盖恶行.刘再复对此作出评价说:“这与基督原谅把钉子钉在自己的手上的行为相似,也与释迦牟尼原谅曾砍掉自己手臂的哥利王的行为相似,均带有‘神性’、‘佛性’,所以我说贾宝玉是个准基督准释迦.” [4]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宝玉是引导我们走向美好人性天国的“导师”.«红楼梦»也描写了一个与«三国演义»“权术世界”以及«水浒传»“暴力世界”截然不同的“诗意世界”,大观园中的林黛玉、晴雯、鸳鸯等如日月星辰的女子,不但外表美丽,而且具备真性真情,纤尘不染,纯洁透明,富有内在的诗情,贾宝玉称她们是由水做成的“净水世界”.
关于«西游记»,刘再复认为,“悟空与唐僧所形成的心灵结构,是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结构.孙悟空如同不死的刑天,而唐僧则给他慈悲的规范,只能保护人、不可杀人的规范.唐僧所要造就的英雄是造福人的英雄.这一基本精神与«山海经»完全相通.因此,«西游记»完全属于中国的原形文化.” [3]
三、“人”的价值标尺及对于学术界批评的反批评
刘再复评价“四大名著”还有一个基本标尺,即“人”或“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价值标尺,判断一部作品的基本标准是看其所体现的价值观是人的、人道的、人文的,还是非人的、反人道的、反人文的.刘再复认为:“如果说,«红楼梦»是真正的‘人’的文化,那么,‘双典’则是‘非人’的文化,是任人杀戮的文化.” [1]18«红楼梦»中发现了“人”,特别是发现了女人的价值.而«水浒传»则无论是官府和造反者,皆把人不当人,所以武松在“血洗鸳鸯楼”事件中滥杀十余人.而女人在“双典”中,更没有“人”的价值,“她们要么是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要么是被杀戮的对象;要么就是哑巴工具和武器.” [1]18对待婚外恋妇女的态度,«红楼梦»和«水浒传»更具有“天渊之别”, “«红楼梦»把她们送入了天堂”,“«水浒传»则把他们打入了地狱” [1]70,“秦可卿得到«红楼梦»作者与读者的充分同情与爱慕,而潘金莲却得到«水浒传»作者与读者的憎恶与咒骂.作者的价值观不同,笔下人物的遭遇也大不相同” [1]71.«水浒传»认为“欲望有罪”,«红楼梦»则肯定“情欲合理”,«水浒传»表现了对女性的蔑视和排斥,«红楼梦»则表达了对女性的关怀与尊重,所以刘再复认为,“曹雪芹才是女性的伟大解放者” [1]71.
刘再复的«红楼四书»和«双典批判»出版以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对于刘再复“高评”«红楼梦»的立场,除了极个别人(如孙伟科)外,学术界基本持赞同的态度,肯定刘再复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但是对于刘再复“低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价值立场,就目前出现的若干篇批评文章来看,除了个别人(如洪治纲) 外,绝大多数都不同意刘再复的观点,从而对«双典批判»提出针锋相对的批判. ②纵观这些批评文章,其批判的靶子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针对刘再复提出的“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概念,二是针对刘再复“双典批判”中的具体观点.这些批评文章,虽然有的在一些局部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首先,这些批评文章都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缺陷,笔者将之称为“个案反驳论”.所谓“个案反驳论”,就是针对刘再复著作中提出的某个观点,寻找出某个能反驳该观点的个别案例,但仅仅是个别案例,作为反驳刘著中所立论观点的根本证据,企图来驳倒该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主张.众所周知,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自然也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自然现象和技术现象,“一是一,二是二”的确定性和科学性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而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四大名著”的研究中,因为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乃至“人”的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更具有主观性、内向性、变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因此,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不适合完全采取自然科学那样的标准化、模式化的归纳法,也就是说,一个观点的产生,不一定如自然科学那样,非得拥有绝对百分之百正面材料的支撑证明,极个别的不利于立论观点的材料证据并不妨碍观点的整体性成立,换句话说,只要有研究对象内部基本数的乃至绝大多数材料的支撑或证据的证明,一个观点就大体可以成立.例如,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善于玩弄“权术”,是著名的一代“奸雄”,“奸”是曹操性格的一个核心,这个结论是在总结小说中绝大部分关于曹操为人处事的典型事例的基础得来的,但是也能在小说中找出个别能反映曹操具有“诚”的精神的个案,但这个“个案”的存在并不妨碍曹操整体上具有“奸”的性格观点的成立.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是一个闪耀着人性光辉、具有赤子之心的“至诚”之人,甚至如刘再复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带着“神性”、“佛性”的“准基督准释迦”形象,这也是从小说中诸多材料中得出来的结论.但是小说中也有贾宝玉大闹学堂、踢袭人、流荡优伶等反映其纨绔气特征的个案性材料,但这并不妨碍前面总观点的成立.孙伟科就是抓住宝玉这个体现纨绔气的个案材料,认为不应该如刘再复那样对宝玉作出崇高的评价,无疑是犯了这个“个案反驳论”的毛病.胥惠民在反驳刘再复的“曹操观”为曹操“翻案”时,也犯了类似的毛病.同样的现象出现在刘季冬的文章中,刘季冬针对刘再复的观点,即刘再复认为“«山海经»中的女娲、精卫、夸父、后羿等都是世界的‘修补者’,全是救人英雄”,反驳说«山海经»并不缺少“残酷杀戮的行为” [5],但事实上这种杀戮行为在«山海经»中只是个案的存在,并不影响«山海经»在整体上表现建设性英雄的特点.刘季冬还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中华文化的伪形” [5],“«西游记»、«红楼梦»并非只体现优秀文化精神” [5],然后在文本中竭力寻找相关证据来证明,同样犯的是“个案反驳论”的毛病.孙伟科反对刘再复抬高«红楼梦»贬低«三国演义»,认为«红楼梦»也有权谋描写(如王熙凤“计杀”尤二姐),但事实上,权谋描写在«三国演义»中是核心内容,而在«红楼梦»中不过是枝节性的内容,且曹雪芹对之采取鲜明的批判态度.第二,这些反驳性论文有的犯了“偷换概念”、“转移目标”的毛病.例如胥惠民认为,“刘再复彻底批判否定«水浒»和«三国»,实际是在否定从明至清的文学传统,尤其是否定长篇小说的优秀传统.” [6]刘再复“用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彻底批判武松的‘非人’行为,进而达到彻底否定«水浒传»的目的.” [6]实际上,刘再复根本没有彻底否定«水浒»和«三国»的文学传统,而认为“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应承认它们是非常杰出、非常精彩的文学作品,不愧是文学精品” [1]3,是“有才气、有艺术魅力的‘大才子书’” [6].刘再复是在承认“双典”文学成就的前提下,批判“双典”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和文化意识,因此,胥惠民的批评无疑有“偷换概念”、“转移目标”之嫌.第三,个别论文具有“上纲上线”式批判的特点.胥惠民的批评文章,有些地方断章取义,主观猜测,附会联想,甚至进行意识形态化的“上纲上线”,有文革大批判的遗风.例如,他质问“刘再复‘暗示人们要图大事,就必须结成死党’,究竟何所指?他的‘青帮红帮,都是社会的毒瘤’没有指明是什么组织,他心里明白,我们心里也明白” [7].他在文末引用了李劼的一篇全方位批判毛泽东的文章«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中的部分内容,然后进行比附,认为两者“思想语言如出一辙.只有在这时,我才明白刘先生是在用文化批判掩盖政治批判.其深曲的心,委实为常人所不及” [7].言下之意是刘再复借“双典批判”而达到批判毛泽东的险恶目的.
四、结 语
刘再复对“四大名著”的评价毫不含糊,态度鲜明,乍看石破天惊,不合常情,但事实上有理有据,切中肯綮.也许刘再复的某些局部观点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上来说,其基本主张和观点是能站得住脚的.刘再复对“双典”的批判所引起的震动尤为巨大,在中国,无数的“«水浒»迷”和“«三国»迷”喜欢这两部小说,为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所深深吸引,但是往往忽略其基本价值观的负面性,高超的艺术将“双典”有问题的价值观掩盖起来,“就像毒药之中加了糖丸,喝的人只赏其甜,而不知觉毒素随之进入体内”. [8]28所以,刘再复无异于是给这些“«水浒»迷”和“«三国»迷”乃至最广大的国民一声当头棒喝,起到一种震聋发聩的警醒作用,促使他们从沉迷于“双典”的状态中走出来,重新全盘审视并辩证评价“双典”的价值.也许刘再复对于“双典”文化价值批判的姿态太激烈了,太不留余地了,使中国广大的“«水浒»迷”和“«三国»迷”在情感上难以接受,所以遭受了较多的抵制和反对的声音,喜欢中庸思维的中国人不习惯刘再复这样不留余地的批判.但作者的批判眼光、批判精神是深切的,值得称道的,而理解和接受其观点可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注释:
① 刘再复曾经说:“我把48岁之前(1989年之前)的人生,视为第一人生,把这之后到海外的人生视为第二人生.我把人生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不是刻意的.因为在48岁的那个瞬间,我的生命产生了一次转折,一次裂变.”参见刘再复、吴小攀的«走向人生深处»,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② 这些批判性文章主要有:刘季冬的«<山海经>文化精神的再认识——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学术界»2013年第1期;高利民的«文化原形论批判——兼与刘再复商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胥惠民的«违反常理的批判——刘再复彻底否定‹水浒传›、‹三国演义›究竟意欲何为»,«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 2011年第4期;胥惠民的«杂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欧阳健的«‹水浒›的成书与“水浒”的精神——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孙伟科的«红学与红楼美学———评刘再复“红楼四书”中的美学思想»,«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