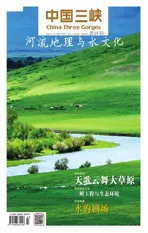癸未三峡记③
2014-03-15
癸未三峡记③
文/于 坚 编辑/罗婧奇、吴冠宇
无论你走到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听到人们谈论这条河就像谈到他们的神。
——于坚《河流》
遇到一个干瘦的老头牵着一匹马从山上下来,踏着碎砖走过,我心里动了一下,差点就问出“杜甫无恙”?
夔门是从西向东进入三峡的开始之处,“三峡传何处,双崖壮此门”(杜甫)。平淡无奇的江岸在这里忽然崛起,耸起两座南北对峙的垂直岩壁,北岸的赤甲山呈红色,南岸的白盐山呈灰白色。犹如巨大的钢铁之门刚刚缓缓拉开,“三峡传何处,双崖壮此门。蛟龙屈窟宅,愁畏日车翻”,“西南万壑注,劲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杜甫)。伟大与光荣开始了,后面就是奇峰怪石层出不穷的三峡,犹如巨石组成的鸿门宴两边排列,远处是变幻莫测的云雾和滚滚大江。只等着“天降大任”者前来赴汤蹈火,培养浩然之气,天地雄心。夔门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座造物主在河流上创造的凯旋门,但它与罗马的凯旋门不同,它不是结束而是混沌初开。
一个有心灵的人,从前只是在书本上理解“雄浑”、“大气”、“混沌初开”这些形容词的,来到这里,他立即就“胸含元气,眼穷大荒”,觉悟到那是什么。一个诗人,由此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豪杰,由此会抛弃草莽,萌生逐鹿中原之志。昔日的诗人无不意识到长江对他们生命的意义。这河流流淌着的东西是书本上永远找不到的,那种隐蔽着的东西可以启发人的心智,令诗人在人群中出现,令诗人在诗人中成为伟大。去夔出峡是一种伟大的中国经验,它曾经造就了许多伟大的诗人,李白去夔出峡,从此进天下,“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杜甫来到夔门,诗歌更多了悲壮沉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伟大的青铜之声,过了千年,我这个刚刚诞生的读者进入夔门穿过三峡的时候,依然像陆游感叹的那样“顷来目击信有证”,被那语言的能指力量所震撼。
大坝蓄水后,水位上升,夔门就看不见了,“水面增宽,流速下降,峡感减弱”,水位上升30-40米,枯水季节水位更高,相当于十多层楼那么高。白帝城也要淹没。夔门、白帝庙将成为库区的群岛之一。夔门旁边就是夔州,现在叫做奉节,是四川省的一个县城。公元766年,杜甫带着家人来到这里,一住就是两年。

左:2010年10月,航拍175米水位的三峡夔门。 摄影/刘曙松/CFP
在这里,中原诗人杜甫彻底成为一位长江诗人。“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州一系故园心”,长江诗人的意思就是像河流那样成为了时间本身,“逝者如斯”,杜甫的诗歌是生长的,越来越重、越来越深、越来越宽阔深厚。“巨积水中央”、“神功接混茫”,他的诗歌进入了不灭的自然之道,像季节那样循环,日日新。
奉节旧城已经拆除,新城建在山顶上,比白帝城还高。昔日,白帝城是夔州最高的地方,“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飘渺之高楼”(杜甫)。我明白了为什么是“白帝彩云间”,因为如果在江面的船上,白帝城就是在高山顶上,从江岸到达城中至少要爬一个小时。我们踩着瓦砾残砖,沿着也许是杜甫曾经走过的石级,登上白帝庙,放眼望去,长江灰蒙蒙的,“峡圻云霾龙虎卧”,南岸停着许多黑乎乎的运煤船,山坡也是黑乎乎的,这是多年从事煤炭工业的结果。但“江涛万古峡”,看见的还是杜甫看见过的那种地形,他在这里写下的诗歌也仿佛是笔墨未干似的。
遇到一个干瘦的老头牵着一匹马从山上下来,踏着碎砖走过,我心里动了一下,差点就问出“杜甫无恙”?“旧俗存祠庙,空山立鬼神”,白帝庙是杜甫经常来的地方,建筑已经不是杜甫时代的,但“旧俗”使祠庙毁了又建,现在的白帝庙是明朝留下的,依然供奉着刘备、关羽、张飞和赵云。我以为这里面应该是供奉李白和杜甫,是他们的诗歌使白帝小城名垂千古,而不是这些正襟危坐的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和将军,但是没有。文史馆的人领我们去参观,问我们看出什么异样之处没有?都看不出来,他笑道:文革时期,红卫兵把刘备、关羽、张飞和赵云的头都砸掉,只留下在一边胁肩谄笑的侍候主子的小官人的头,说他们是劳动人民,所以这些小人的头都是原装的,而刘备、关羽、张飞和赵云的头则是文革后重塑的。

2002年,奉节依斗门。 摄影/颜长江/FOTOE
忽然想到,此时代的许多事情看起来都像是行为艺术。行为艺术玩的就是一招鲜,但河流不是一招鲜,它是存在,是我们的宿命。
到达忠县的时候大年三十,也是一个水泥城。100年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博尔德·约翰·立德所见到的“最令人瞩目的是众多的庙宇和亭子”已经消失。我们原来以为可以在长江边放炮仗进入癸未年,但县城里也禁止放炮仗。天一黑街上就没有什么人了,家家都关门看电视。没有炮仗声音的小县城,安静得令人孤独感倍生,我们摸黑出城,去到郊外,在一个大桥上偷偷摸摸地放了一把,像是游击队炸桥似的。一个支炮,一个点火,另两个放风望哨。寒风呼呼,隐约听见爆竹声音从大地的深处传来,与我们的爆炸声呼应着,那边是乡村,心里温暖了许多。忽然想到,此时代的许多事情看起来都像是行为艺术。行为艺术玩的就是一招鲜,但河流不是一招鲜,它是存在,是我们的宿命。
大年初一前往石宝寨,去那里的陆路很不好找,在长江两岸,人们习惯的交通是水路,上水或是下水,在岸上问路,经常是语焉不详。我们好不容易问到了路,非常可疑,路顺着长江边,土路,泥泞,坑坑洼洼,一辆车也没有。偶尔,“岁时伏腊走村翁”(杜甫),问问,都说这路就是去往石宝寨的。在泥坑里跌撞前行,慢得要命,经过一个一个美丽的村庄,风景看得很清楚,想起魏晋时代的人物,在马上看风景都嫌快,要坐牛车看。虽然建筑雷同,但地势、植物各有千秋。偶然还会出现一片青瓦,陌生,令人眼睛一亮。人们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田野里再没有人劳动,年猪已经煮熟,酒已经酿就。大家都闲下来,新衣裳已经穿得开始合体,或坐在房屋外面聊天、打牌、玩麻将,或站在公路两边晒太阳、嗑瓜子。昔日,春节仪式烦琐,活动丰富,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是中国社会祭祀祖先,敬畏神灵,交流感情、交流文化的重大节日。现在除了吃,就是看电视,每个地方都一样。在土路上磨蹭了几公里之后,忽然又找到了水泥路,原来这才是去石宝寨的正路。我们问的是去石宝寨怎么走,农民告诉的就是他们走的路。而去同一个地方,农民有农民的路,政府有政府的路。一上了政府的路,速度就快了,没有什么车辆,汽车都停下来了,我们得以风驰电掣,刚昏昏欲睡,已经到了。
石宝寨名声显赫,重点保护,但在我看来,只是差强人意。也就是把一个十二层的楼宇依着突向江面的巨岩建造,木梁子都固定在石壁上,犹如脚手架,把外观修成了庙宇的样子,小聪明。古代建筑,精美伟大的多了,要不是已经拆得所剩无几,石宝寨也不会“世无英雄,逐使竖子成名”。倒是这里的一个典故很有意思,岩石中有一个石头叫做流米石,典故如下:“相传,石穴有米出,可饭一僧。僧嫌孔小,凿大,米绝。”在许多方面,人类今天不是正在干着“嫌孔小”的事情么?

左:重庆巫山,神女峰下青石镇上的游客。 摄影/微光

重庆巫山县青石村晨景。 摄影/颜长江/FOTOE
现代主义拒绝迷信死亡,对死亡的仪式毫不讲究,一切从简,死亡冷冷清清,文化系统里面没有鬼城这种象征性的阐释体系,死无定所。
鬼城丰都所在地叫做平都山,苏东坡曾写诗赞美:“平都天下古名山,自信山中岁月闲”。远远看去,却一点都不闲,很是热闹,山前人声鼎沸,山顶修建了一个白色的巨人头像,坐落在鬼城上面,非常抢眼,令周围的一切都小掉。问当地人,那是什么?告曰:是开发商搞的旅游项目,修了一个鬼王的巨像。又悄悄地附我耳朵说:“那个老板前几天出车祸了,胆子也太大,敢在鬼头上动土。”
鬼城很有意思,进去的人无不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过一个桥叫做奈何桥,桥有三座,其中一座是奈何桥,导游不出气,看你走哪一座,走了不对的那一座,就是做过坏事。我恰恰走得不对,又叫我把一个镍币扔到一个水缸里去消灾,落下去要正好进入缸底的一个洞口,扔了几个,才进去了,松了口气。又过一个门叫做鬼门关,男左女右,而且过门的时候不可碰到门槛,碰到门槛就成为“关门鬼”,我不记得是否碰到了门槛。又经过黄泉路,东地狱、西地狱什么的。
来到阎王殿,殿前有一个脚跟大小的鹅卵石叫做“考罪石”,你要单脚站在上面若干时间,并且正视大殿前面写着“目光如电”的匾,如果站不住,就是心中有鬼。进了阎王殿,柱子上的对联说的是“不涉阶级从这里过行一步是一步,无非贵贱都向个中求悟此生非此生”,“善恶昭彰”、“黑白分明”。然后就到阎王面前,烧香点烛,搞得非常阴森,很有氛围,和想象的阎王殿差不多。唯物主义者把这些视为迷信,有一个当代人的对联说“三三两两,笑谈鬼城牵强附会”。
其实这并非“迷信”两个字那么简单,在我看来,它是一种仪式,经历了这个仪式,对人的心理会产生某种暗示作用,从而对人的行为有所规范、限制。这是一种中国化的民间的教育仪式,它的作用未必不如那些课堂里的一本正经的宣讲。在虚拟的地狱场景中,人们身临其境,我看出来很多人确实是脸色发白,沉默不语。戏剧性的是,在进入阎王殿之前,山上还有财神庙,可以保佑生育的百子殿什么的,在那里,热闹非常,烧香求卦的争先恐后,香火弥漫,大殿被熏得黑漆漆的。最后却来到阎王殿,那里安静得出奇,虽然也是摩肩接踵,鱼贯而入。

丰都鬼城展示的地狱。 摄影/微光
鬼城下面的丰都老城大部分已经拆为瓦砾堆,剩下的几栋也已经搬空,这些建筑一看就是匆忙简陋的那种,根本没有好好搞,像是没有完工的毛坯板。一边是空旷的瓦砾堆和人去楼空的水泥房子,阴森森的。另一边则是人气沸腾、庙宇香烟的有着千年历史的鬼城,穿长袍马褂绫罗绸缎的鬼住在里面。古代文化对于死亡是有交代、有去处、有说法、有仪式的,所以死亡非常热闹。现代主义拒绝迷信死亡,对死亡的仪式毫不讲究,一切从简,死亡冷冷清清,文化系统里面没有鬼城这种象征性的阐释体系,死无定所。
有很多小贩人卖冥钱、冥纸、土香什么的,随便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鬼,都笑着说小时候见过的。同样的问题换个地方问,人家恐怕大惊失色。他们描述的鬼与根据《聊斋》改编的电视剧里面的那些形象差不多,蒲松龄创造的话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实在广泛,其实哪里有鬼,鬼就是文化上关于死亡的一套话语系统。我在神秘主义、知识的有限性上相信鬼世界的存在,我确信并非一切都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世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在到达他们复杂的计算之巅的时候,总是发现他们成为了神秘主义者,鬼神游走在科学的最深处,只是在科学以为一切难题都已经演算完毕,答案出现的时候,忽然露出一张鬼脸来,咧嘴一笑。
我看见了那两条唐朝游过来的石鱼,水灵灵的,我慢慢靠近,蹲下来,摸了摸,它体温冰凉。
我一直喜欢黄山谷的书法,少年时期就一直看,有一本《黄山谷书墨竹赋等五种》,每年都要拿出来翻翻。到了长江边的涪陵,在江水中间的石头上看见他的字,才知道他晚年被贬到涪陵,“落木千山天远大”,“出门一笑大江横”,就住在白鹤梁对面的江岸,据说每天写字,流下来的墨水把长江染黑一片,那一带的鲤鱼都是黑的,称为墨鲤。在长江边,他的书法越写越写越好,是长江使他觉悟了书道。他说:“晚入峡,见长年荡浆,乃悟笔法”。白鹤梁,是长江中的一群黑色的石头,每到春天和冬天的枯水季节,它就像一条巨鲸的脊背那样露出来。它仿佛长江的灵魂,一现身,人们就要去祭祀膜拜,诚惶诚恐,看看大河之神在黑暗中又干了些什么。人们在上面刻字铭文,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民国、包括后来的地方官员,都在石头上留下痕迹,渴望着他们的名字能够依赖大河灵石而不朽。从唐代开始,白鹤梁就成为神话、传奇。一个传说是有道士于水落石出的时候在石头上修炼,水涨,石头消失,他羽化为白鹤飞去。人们还在石头的一处刻了两条鱼,相信石鱼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丰年吉兆。后来科学界发现,这两条石鱼标示的水位与涪陵地区的0点水位很接近,成为一个水位的标准尺度,那些题刻也可以视为一个古代的水文历史记录,一座记载了1000多年以来长江上游枯水水位表的“水文站”。

2003年,白鹤梁上的石鱼,重庆涪陵。 摄影/颜长江/FOTOE
库区蓄水之后,水落石出就不存在了,白鹤梁将永没水中。补救的办法是,在石梁周围建造一个玻璃罩子之类的东西,就可以随时参观了。但白鹤梁的神秘在于水落石出,它要整条大河在某一刻缓慢地落下去,才现真身,而且这大自然创造的伟大仪式通常每十年才出现一次,一个人就是一生住在涪陵守着,也就是几次机会而已。这水落石出的神秘仪式令人感受到的是时间,是比人的历史更长久的造物者的力量。我是幸运的人,癸未年的正月初三,白鹤梁再次水落石出,而且是最后一次,我是前往参观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员。明天,这里就要封闭施工,开始建筑水下展厅了。
我们乘着小船渡过长江的一段,驶向距江岸100米的白鹤梁,石梁长约1600米,宽约15米,并不是整石,而是许多石块组成的。那些石块上刻着各种字体的汉字,被江水打磨之后,像是刻在铁鼎上甲骨文。有的石头被雕刻成鱼,有的上面刻着白鹤。一位1963年在涪陵当专员的官员刻的文字对那些古代的题刻评论道:“尽管有唯心的观点,贵在四代文。”题刻内容大多是赞颂山水,祭祀神灵,到此一游。黄庭坚题刻没有单独用一块石头,而是随便题在另一幅石刻的一个角上,他题的是:“元符庚辰涪翁来”。果然不同凡响,什么也没有说,却字字珠玑,“来”已经足够。已经是造化,在着,如此,还说什么呢。石梁很滑,长江簇拥着它,像是要把它推走,它不动。以动着的河流观之,石头一直在动。以不动的石头观之,河流是不动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孔子说的是川流,也是石头。河流的灵魂是不动的,它现形于石头。我看见了那两条唐朝游过来的石鱼,水灵灵的,我慢慢靠近,蹲下来,摸了摸,它体温冰凉。

仿古的游轮穿行在长江三峡。 摄影/微光
那些食物的历史和长江一样古老,令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他们当然不会在一个叫做重庆的地方舍弃古老而伟大的火锅直奔麦当劳。
重庆是从宜昌开始的长达六百多公里的三峡大水库的终点。我们到达重庆的时候是公元2003年的2月4日,举国正在放假,大都会喜气洋洋。过春节与国庆节、五一节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大红大绿,大吃大喝,张灯结彩,红旗飘飘,标语挂起。重庆是长江流域的一个现代主义之梦,未来中国的样板之一。在出租汽车里,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听着相声,那相声在嘲笑重庆人的椒盐普通话。
古老的朝天门码头已经焕然一新,修得就像一艘水泥的航空母舰。三十年代的那个典型印象“雾都重庆”已经不大看得出来,高楼林立,大部分房间都装着空调,数千年来在炎热夏夜露宿街头的风俗终结了。由于高楼林立,城市感觉上似乎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高峻,几乎成了一个平台。摩天高楼的缝隙中,偶尔可以瞥见长江,它正经历着它最后的一个枯水季节。朝天门码头还可以看见原始的河床,江水在流动,一片巨大的沙滩裸露出来,它只是在冬天出现。许多市民领着孩子沿着水泥的台阶一直下到那河床上,在那里放风筝、玩沙。
解放碑因为有1949年解放重庆的纪念碑而闻名,这附近的街区是重庆市中心,已经率先进入现代行列,世界第一流的商业步行街、大商场、电梯、摩天大楼、玻璃幕墙和当代中国最时髦的红男绿女。春节期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购物或者走一走,满足一下。摩肩接踵,人头密集,洪流滚滚,空气令人窒息,它也许是世界上行人最密集的商业区了。二十多年前我在这个城市花20元钱买了一双黄色的皮鞋,但这次我什么也没有买,那些豪华的百货商场与昆明也差不多。
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名模广告、化妆品、各式各样的世界名牌,从那些时髦的大橱窗望进去,与在巴黎或者纽约的橱窗所见者并无二致。但人们一开口,你听到的就是古老的四川方言。解放碑的购物中心令我产生一种分裂的感觉,一方面是人们大大咧咧的举止动作,满街哗响的生动清脆的四川方言,令我这个四川籍的外省人听着亲切,颇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因为虽然身在云南,但我父亲一辈子都对我说的是四川话。对于我,这种语言来自我父亲,来自沱江边上一个叫做南津驿的小镇,可以上溯到于氏家族族谱的开头,上溯到古代的长江流域的巴人。另一方面,那些巨大的建筑物、玻璃、瓷砖、电梯似乎只是与英语或者普通话有关的某种生活。两种完全格格不入的东西拼贴在一起,一方面是与时俱进、日新月异的产物,一方面是古老时间以不变应万变的产物,是满大街的“乡音无改”。如果周围的人都不说话,这里看上去似乎就是纽约、香港的步行街或者斯德哥尔摩的皇后大道。但他们一张口,又仿佛是欧洲最时髦的商业步行街的行人都忽然被换了舌头,说起四川方言来,发音是从古老的长江流传下来的那种,是适合于传授榨菜与椒盐麻辣腊味烧卤的那种,是适合于李白苏轼这样的诗人吟风弄月、天马行空的那种,或者潭邦五那样的船老大在朝天门码头上喝五吆六的那种。

白帝城。重庆奉节。 摄影/王苗/CTPphoto/FOTOE
现代主义其实是一场英语领导的全球运动。在中国,它至少也是普通话领导的运动。四川方言无论怎么听与现代主义的标准都是别扭的,它完全不适合彬彬有礼地站在麦当劳的柜台前点炸鸡腿、热咖啡和汉堡包。在中国,普通话在四川最难推广,一讲普通话,四川人的舌头就硬掉。我父亲,四川资阳人,在政府里面工作一辈子,没有学会一句普通话,而是逼着同事听了一辈子他的四川话。所以,癸未立春这天的上午,在解放碑,在古老的四川话和日新月异的当代现实之间我有点感觉分裂,思维混乱。但转过一个街口,就看见无数人在小吃街上埋头猛吃麻辣烫,令人直咽口水的川味从一个接一个的小吃铺子里漫溢到街道上,这就对了,重庆真相毕露。什么西装领带,站在黄线外面等候,左手使叉,右手拿刀……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大家街边一站、一蹲,一靠、裤子一撸,领带撕开,埋头猛喝,凝神细品,汤泽汁液什么的把瓷砖地面弄得滑腻非常,一不当心就要滑倒。这些现代主义的瓷砖地面可不是为重庆小吃的卤泽汤水设计的。许多拎着竹篾扁担,衣服褴褛的挑夫,在人群间穿来走去,寻找活计,大家也不会白眼看他,怪他有辱现代化的斯文。那些食物的历史和长江一样古老,令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他们当然不会在一个叫做重庆的地方舍弃古老而伟大的火锅直奔麦当劳。
我在一家旅馆结束了长江之行,乘飞机返回昆明走之前,我走进昨天发现的一条即将拆除的旧街道,在这里,重庆的日常生活依然像榨菜那样缓慢地腌制着,人们在街道边上打扑克、敲麻将,补鞋匠靠在墙角落打盹,老人们坐在茶馆里聊天、下棋,老妈妈提着蔬菜篮子悠悠地往家去,找到活计的挑夫满头是汗坐在石坎上休息。这生活现场令人想起李劼人的小说。我钻进昨天吃过的那家小馆子,再要了一碗肥肠粉,老板依然像二十年前那样,朝着里面的伙计用乡音吆喝一声,“肥肠粉一碗……”。他把那个碗字唱得转了一个弯,那一刻,我感觉到时间并没有前进,就像永恒的长江。

重庆解放碑。 摄影/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