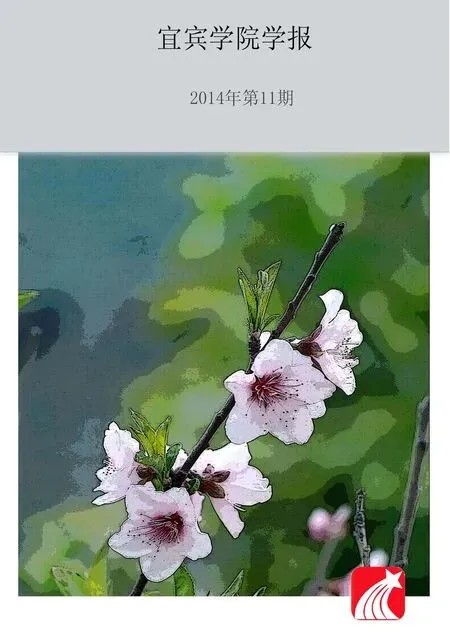进城农民工身份的焦虑与困惑——读孙惠芬《吉宽的马车》
2014-03-12庞倩薇
庞倩薇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我们是谁”这是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关于身份认同的命题,它是主体对自我身份的追问、确定与认同的开始。然而,随着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种种影响,“我们是谁”的问题不再是恒常不变的了,它会受到社会结构、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周宪认为,霍尔所指出的认同具有未完成性和总在过程性的深意在于,原来“过去时”的“我们是谁”的问题转变成“正在进行时”的“我们会成为谁?”的问题。因为,现代社会总体性的衰落、多元化的增长,流动性和碎片化的出现,使得原来确定的认同问题变得不确定了,这为身份的塑造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1]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由乡入城的跨区域流动成为当代中国最突出的社会景观。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却无法在异乡安身立命,进入城市却又无法成为城里人,返乡又有回不去的困惑,这种“边缘人”的状态引发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如何在城乡二元文化碰撞中以及多元价值、制度体系之间寻找到属于自我身份的归属地,摆脱身份的焦虑,完成身份的确认,是进城农民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一 “我们会成为谁”:无法摆脱的焦虑
鞠广大:“我每次回家过年,我发誓不回来了,不回城里了,可一到十五的时候就呆不住了,着急慌忙地往回赶。你说城里有啥呀,没老婆没孩子,没爹没妈,连块敞亮的地儿也没有。贱,我他妈就是贱勒。我贱我这样。”
民工:“打住,我知道。你想当城里人,你想当城里人了嘛……说实话,我也想当城里人。”
这段对话出自电视剧《民工》(由孙惠芬中篇小说《民工》和《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改编)。进城民工的意图在这番对话里表露无遗,问题是在偌大的城市里,是否有他们的容身之所,是否有一个适宜的身份?农民的“我想成为城里人”的愿望能否实现?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通过描写主人公申吉宽对“我是谁”和自己与城市关系的多次追问与思考,让我们看到进城民工在城市的边缘生存状态、无处安放的灵魂和面对“想成为城里人”及“我们能成为谁”的困惑。歇马山庄的懒汉申吉宽一开始并不向往城市,一次偶然的爱情冲动,唤起了他对城市的渴望,成为歇马山庄最后一个进城的中年男人。当他进城后目睹了城市的阴暗、浮华,回乡又发现与自己相互依存的老马死了后,他悲哀地发现“我已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了,是一个乡下的马车夫,还是一个进城闯荡的民工。要说是马车夫,我已经失去了老马,要说是进城闯荡的民工,我却没有自己的工地,没有属于自己的手艺。”申吉宽对自我身份的疑惑来源于城乡两种生活方式、文明在他身上的交织、撕扯。一方面,他没办法再像原来那样做个懒汉,恢复原来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尽管在林榕真的帮助下,他感觉到自己和城市的血管打通了,但他无法丢弃乡村记忆,全身心成为城里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歇马山庄饭店”是乡村记忆在城市的复现。它召唤着在城市中打工的民工,慰藉他们疲惫受伤的心灵。这种对故乡的思念与怀念切合费瑟斯通所谓的“刻意的乡愁”的说法,他认为乡愁乃是对一种无家可归感的反映,怀旧则是对传统失落的怀念,本真性的诱惑是因为当下生活变得越发短暂和趋向表层化。[2]作品中最为刻意的乡愁莫过于申吉宽在黑牡丹重新装修的饭店里挂乡村的苞米谷子、辣椒、大茧和装饰一幅马车在墙壁上飞奔的壁画,这种复现乡村经验的举动体现了申吉宽自身根深蒂固的乡土性。
实际上,这种对家园的依恋正是对某种失去东西的怀念,是对当下稀缺之物的需求。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说的,“记忆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题”。孟繁华也说过,“乡村的经验越多,在城里遭遇的问题就越多,从乡下到城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乡村文化来说,应该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3]。申吉宽越是深陷于过去的经验,这种和当前城市经验并不兼容的观念必然越会影响他对城市的认同。城乡两种文明在体内的交织、纠缠,上升到哲学层次就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我是谁?我将要成为谁?”的追问。这种追问使打工者遭遇了叶赛宁所言的“我走出了乡村,却走不进城市”的尴尬处境,造成了他们在身份认同上陷入重重桎梏。
二 人与城
贾平凹《高兴》中进城农民刘高兴以自认自己是西安人为开端,以自我构建的城市身份的失败为终,宣示了进城农民工自我身份确认的失败。而从进城第一天起,申吉宽就以一种好奇、进入又不沦陷的眼光打量着这座城市,他一直以《昆虫记》里的比喻来思考自己与城市的关系。如果说乡土记忆与城市经验的错综交织是申吉宽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将会成为谁?”的肇端,那么申吉宽与城市的关系就是他身份得不到确认、处于焦灼状态的生动证明。
(一)渴望拥抱的地方
作为一个懂得享受生活、追求另一种生活的懒汉,申吉宽并不向往城市。他进城完全是出于爱情的冲动,不过想向嫁作他人妇的情人许妹娜证明:我申吉宽也能像城里人那样有本事。为了追逐情人,申吉宽抛弃了属于自己的活法,背弃自己的生活,即便在城里无家可归的时候也丝毫不动回歇马山庄的念头。当他开始懂得在城市生活的价值、意义后,他不由自主地渴望与这个城市交融,渴望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的渴望与歇马山庄的男人们不同,他并不希望像他们那样通过做体力活、在工地上劳动来获取,直到他在拘留所遇到了林榕真,他才开始真正和城市共同呼吸。由于林榕真的帮助,申吉宽觉得“从酒店出来,再看这个城市,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路灯在我眼里再也不像死人时打起的经幡,一幢幢大楼在我眼里再也不是大楼而是一张张笑脸”。“他打通了我跟城市之间的血管”,使申吉宽在城里找到了立足之地,林榕真对申吉宽内心的介入就是城市生活对申吉宽生活的介入,这时,申吉宽才得以在身与心找到栖息地。
(二)城市与野兽
打通了与城市之间的血管是否真的就意味着申吉宽与城市水乳交融,从此成为身份确定的城里人呢?显然,作者的思考到此并未停止。作为一个出身农村,执著于书写农民的底层女性作家,孙惠芬对农民有切肤之感,能够理解与同情他们。作品中人物身份的焦虑一定程度上也是作家心理的投射,因而,作品中申吉宽的思索与追问也就代表了作家本人对此的思考。这与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有关,她从乡村一步步走出来,以为家园就在乡村之外的城市里,结果发现城市里并不存在自己想象的自然家园。她在自传式小说《街与道宗教》中说,“我把一颗扎进土壤的稻苗连根从小城里拔起,现在,我需要把这棵稻苗再一点一点安插到城市里去。而我在东奔西走手忙脚乱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唯有写作,才是我扎根城市土壤、让我获得身份和背景的途径……在我一程一程失去家园之后,我发现,只有虚构,才是我真正的家园”[4]。这番话说明作家本人也曾经有过身份认同的焦虑,文学创作作为舒缓焦虑的手段让她有更多的空间来追根溯源和确定自我身份。在作品中大量书写乡村,以农民为描写对象,探讨他们在城乡之间的精神困惑与身份焦虑自然成了作家在城市重塑自我身份的途径。通过了解作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申吉宽的困惑与焦虑了。
在申吉宽还没遇到林榕真之前,城市在他眼里“仿佛一座看不见方向的森林,穿行在森林里的我,犹如一只被猎人追逐的野兽。一天一天,我总是狂躁不安……站在高楼之间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或者走在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上,我的脑袋会自觉不自觉冒出这样的念头:我怎么能在这里?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这种空间感的断裂,带给吉宽的是惶恐与不安。在这里,他会不停地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林榕真的出现纾解了申吉宽的焦虑,他开始融入城市,和城市水乳交融。但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依赖他人才能得到确定身份从来不是可靠的途径。当林榕真在城市里陷入了与已婚妇女的情感纠葛,被她们玩弄于股掌之后,申吉宽深刻地发现“屋子不再是屋子,而是牢笼,人不再是人,而是困兽……实际上,不管是我,还是林榕真,还是李国平,还是黑牡丹,程水红,我们从来都不是人,只是一些冲进城市的困兽,一些爬到城市这棵树上的昆虫,我们被一种莫名的光亮吸引,情愿被困在城市这个森林里,我们无家可归,在没有一寸属于我们地盘上游动;我们不断地更换楼壳子住,睡水泥地,吃石膏粉、木屑、橡胶水;我们即使自己造了家,也是那种浮萍一样悬在半空,经不得任何一点风雨摇动……”城市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表面上风光无限底子里却摇摇欲坠的梦,注定要摔跟头。浮华一梦是大多数人阅尽丘壑的总结,申吉宽不忙于下结论,他还在经历。当他顶替林榕真成为装修公司老板成功揽下少年宫价值百万的装修工程和失去两个女人以后,他对自己与城市的看法却夹杂了憎恨之感,“最初,我只质疑为什么要有城市,城市为什么要吸引我,成为我们追逐的彼岸……难道除了城市,我们就不再有可去的地方?问题是,城市压根就不是我们的彼岸呵!”作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申吉宽内心深处的想法,不只是为了传达他对城市的看法,还通过他与城市的关系展示其中蕴含的自我定位和对身份的指认。将人与城的关系想象成野兽与森林的关系,充分体现了申吉宽对城市万恶之源角色的看法。问题是,人与城从来不是单一的主客体关系,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当城与人相处融洽、相得益彰的时候,就是主体自我身份确认的幸福时光,当然这个主体是外来的主体;当主客体关系发生变化,或者客体中的事物损伤了外来主体的时候,外来主体就容易陷入否定性思维里,以往确定的身份再度陷入焦灼、不确定的状态。
(三)对城市的理性反思
在作品中传递城乡二元对立、农村优于城市的观念并不是孙惠芬的初衷,她的目的在于通过书写来透析辽南乡村的广大农民在时代的变革中,在城乡文明碰撞的冲击下,在理想与现实的徘徊中心灵的骚动和精神的变迁。在孙惠芬所构建的“歇马山庄”系列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城市、乡村作为场域所显示的权力的力量,乡村人在城乡之间所寻求的身份定位与认同始终在迷茫之中行进,作家本人对此的思考也随着她的写作之路一步步深入。在孙惠芬多部小说中,《吉宽的马车》对城乡文明的反思、对进城民工身份认同的思考是目前所有作品里最为深邃的。她否弃了打工文学常常表现出来的单纯的城乡二元对立情绪,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审视城市与乡村深层的问题以及农民面对这一巨变的精神变迁。
孙惠芬对城市的反思是从人与城的关系入手的,前面提到,申吉宽对城市的感情经历了从疏离到亲密,再到破裂,憎恨的变化,最后,申吉宽从憎恨出发到达重新认识的和解彼岸。这种转变主要从他了解大家一直向往的在城里生活的大哥大嫂家真实的生活境遇开始,他才意识到“即使是城里人,也和我们一样,都是推粪球的屎壳郎”,都在为某种东西、某种目的努力生存着,只是大家努力的对象不一样而已。正是这种角度,不仅使他对城市的憎恨消失了,还把他从悲观中解救出来。尽管申吉宽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他仍然无法排解现实对他的打击——情人许妹娜沉迷毒品、抛弃了他。歇马山庄唱着歌、过着属于自己活法的懒汉抛弃了原先喜欢的生活来到城市为情人奋斗,结果除了饱受身与心的双重打击和账户多了些银子外,申吉宽什么都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带情人许妹娜回乡下的梦想始终不能实现。小说最后,申吉宽带着醉意寻找曾经的马车,恍惚中听到自己编的歌曲“林里的鸟儿,叫在梦中;吉宽的马车,跑在云空;早起,在日头的光芒里哟,看浩荡河水;晚归,在月亮的影子里哟,听原野来风。”曾经自由自在、舒适的生活荡然无存,跻身城市除了伤痕累累,一无所获,在别人艳羡的老板身份与马车夫身份之间,申吉宽的怅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民在城乡文明交错的时间里如何丧失自我、找不到归属感的悲哀。孙惠芬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说,她笔下的懒汉对乡村自然生活有深层次的思考,俨然一个乡村哲人。“但最后他不得不为了爱情而进城奋斗,但当他拥有了财富和爱情时,他想回但再也无法回到他的精神故乡。”其实懒汉吉宽的遭遇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而他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我们的悲剧,“我们远离了故乡,开弓便没有了回头箭,变成了身如浮萍的异乡人,生活永远在别处”[5]。《吉宽的马车》是一部典型文本,由此我们可以解读乡村人进入城市后的复杂心态和身份得不到确认的焦虑与困惑。在生活层面上,乡村人确实可以像城市人那样生活于城市空间之中,但是他们却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在得与失之间,作者让我们每一个人去反思这样的结果与意义。
三 无处安放的灵魂:危机与救赎
寻觅精神的归属已经成为孙惠芬等乡土小说家自觉追求的主题目标,孙惠芬说:“写民工,是因为我的乡下人身份,使我对乡村流浪者的心灵格外敏感。之所以称民工为乡村流浪者,是因为我把民工进城看作一种精神上的突围,这样的突围不仅仅属于民工,也属于社会上每一个或强大或弱小的个人。”[6]她也承认,“唯有写作,才是我扎根城市土壤、让我获得身份和背景的途径……在我一程一程失去家园之后,我发现,只有虚构,才是我真正的家园”[4]。对作者而言,写作是精神的归属,然而对于那些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农民来说,灵魂又该安放在哪里呢?申吉宽抛弃了马车,放下了扬起的马鞭,在城市多次碰撞之后,是否又能把灵魂留在城市呢?显然,作品最后告诉我们:身份认同的危机与焦虑无处不在,城市不是乡下人的家,乡下也已经没有进城农民的家。那么,如何安放这些在城乡之间承受双重漂泊的灵魂呢?孙惠芬在访谈中所说的:“我的身体看上去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远了,可是心灵离乡村却越来越近了。所不同的是,我身体远离的乡村是一个真实的乡村,贫穷、落后、天高地远、日月漫长,心灵走近的乡村却是一个虚化的乡村。”[7]作者这番话传达两层含义,一是救赎的必要,二是救赎的途径——将灵魂寄托于虚化的乡村,在作品中同样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不管是申吉宽,还是黑牡丹他们都存在身份焦虑的问题,乡村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在脑海里充满诗意的完美存在,真正回到现实乡村他们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适应,比如黑牡丹夫妇不愿意留在乡下过夜。如何在城乡之间找到自己的归属地,如何拯救在城乡之间漂泊的异乡人,作品最后作了深入的思考。“林里的鸟儿,叫在梦中;吉宽的马车,跑在云空;早起,在日头的光芒里哟,看浩荡河水;晚归,在月亮的影子里哟,听原野来风。”随歌而入的不仅是申吉宽对原有诗意生活一去不复返的忧伤,更是作者指出的一条或许可以救赎灵魂的大道——现实不可触摸,唯心灵的道路无限长。
结语
从本质上来看,进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并没有找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方式,孙惠芬试图对此作出解答,但她仅仅从精神的角度舒缓进城农民工的精神焦虑问题指出了一条理想之路,无法真正解决进城农民工双重漂泊的状态。进城农民工的身份问题依然如影随形,城市与乡村、理想与现实、文本与生活,依然泾渭分明。
[1]周宪.文学与认同[J].文学评论,2006(6):8.
[2]转引自周宪主编.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8.
[3]孟繁华.“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J].文艺争鸣,2006(6):47.
[4]孙惠芬.街与道的宗教[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61.
[5]卜昌伟.《吉宽的马车》写懒汉精神困境[N/OL].(2007-05 -28).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07 -05/28/content_4695.htm.
[6]姜小玲.孙惠芬《吉宽的马车》揭示民工心灵史[N/OL].(2007 - 05 - 10).http://read.eastday.com/renda/node5600/node5611/u1a1372859.html.
[7]张赟,孙惠芬.在城乡之间游动的心灵:孙惠芬访谈[J].小说评论,2007(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