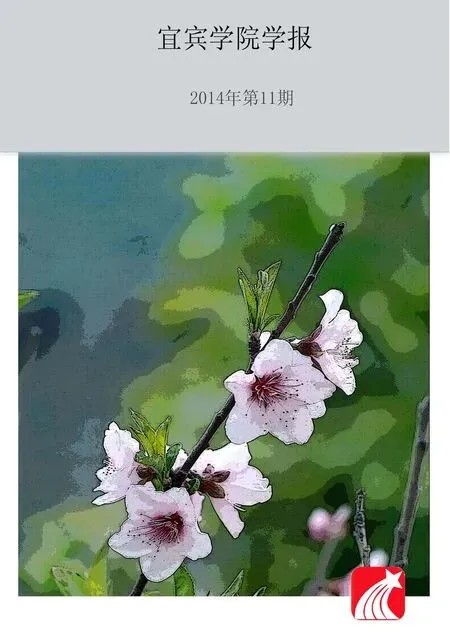从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探析学术研究的复杂性
2014-03-12张建伟
张建伟
(六盘水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六盘水553004)
从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探析学术研究的复杂性
张建伟
(六盘水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六盘水553004)
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观点引起其他学者的批评,这本属于学术领域的正常争论,但因毛泽东的介入,1954年文艺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使纯粹的学术争论演变成一场思想运动,呈现出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红楼梦研究》的出版和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都与俞平伯的生活状况、思想倾向密不可分,而批判运动在造成俞平伯等人伤害的同时也从客观上促进了红学的发展。
红学;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学术研究
俞平伯作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其对于新红学的发展有开创之功。从1921年与顾颉刚先生通信讨论红楼梦到临终前留下有关红楼梦的遗言,其研究红学近七十年。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俞平伯不断调整修正学术观点,如《红楼梦》的“著者”问题,对程伟元、高鹗续《红楼梦》的看法等,由于其学术观点的“善变”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当然,关于红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些争议,由于现存资料披露的不足与学者的个人学术趣味的不同,一时也难有定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其学术观点引起其他学者的批评,这本属于学术领域的正常争论,却因为1954年10月毛泽东同志的介入,文艺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学大批判”运动,批判运动很快就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进而演变成一件全国性的政治事件。
作为建国后学术史上的一场重大政治化运动,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考察也因此成了红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有关的重要论文有刘仓的《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研究述评》、杜敏的硕士论文《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①等,他们在论文中对于此次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运动的性质与目的、运动造成的影响、运动的经验教训与反思、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严谨的学术研究。而由于运动涉及面较广,对其某一方面研究的数量更是不可胜数,如俞国的《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看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心态》②等。作为一场学术批判运动,无论是对运动本身或其一方面的研究探讨,都是有其学术价值和意义的。笔者试图利用一些与此次事件有关的资料,对学术研究的复杂性做一点探讨。
一 《红楼梦研究》的出版动机
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并不是俞平伯的新作,而是其在1923年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的旧作《红楼梦辨》与一些新作的合成。建国初期的文艺政策虽然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来说还是较为宽松的,但与建国前相比,其对文艺界的控制已经逐步加强,写作与研究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前,沈从文为此被迫放弃了创作,转入了历史博物馆进行文物研究,并因为思想压力大而曾选择自杀。在1951年电影《武训传》已遭到全国性批判,1952年又进行了中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俞平伯,即使他作为一个较纯粹的学者,对政治缺乏的敏感性,根据现存的资料显示,其《红楼梦研究》的出版并不是其主动的行为,而是为了还欠的债务。据《红楼梦研究》的编辑文怀沙回忆:
大约是1951年,有一天俞平伯因父亲去世等原因找我借钱,我答应帮助他从上海棠棣书店预支稿费旧币二百万元(新币二百元)。开棠棣书店的徐氏兄弟是鲁迅的同乡,书店的名字还是鲁迅改的。他们请我主编一套古典文学丛刊,我就同俞平伯商量:把二十七年前出的《红楼梦辨》再加新作,再出一次怎么样?俞平伯在旧作的黄纸上用红墨水删改,用浆糊、剪刀贴贴剪剪,弄成一本十三万字的书稿。[1]10
俞平伯出身于名门之后,其曾祖父是清代大学问家俞樾,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是其门下弟子,其父亲俞阶青是清朝的探花,曾出任过四川副主考、浙江图书馆监督(馆长)等职务。到建国后的1951年,俞平伯作为北大教授,却因父亲去世等原因开口向好友文怀沙借钱,可见其家境的贫困。文怀沙当时属于供给制的干部,也无多少钱,凭借着在棠棣书店当编辑的机会,他帮俞平伯从棠棣书店预支了稿费,并借着主编丛刊的便利,把俞平伯在旧作加些新作重新出版了一次。如此看来,《红楼梦研究》的出版可以说是《红楼梦辨》的修订版,从内容上说并无过多的新意,出版的主导者是文怀沙,出版的动机也不是为了学术交流,更多的是为了偿还债务。
作品的观点涉及的是学术问题,而作品的出版动机涉及的却是复杂的现实问题。任何一位学术研究者都必须面对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学术问题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尽量做到客观、中立,而现实生活中的研究者面临的却是养家糊口这类非学术的关乎作者自身生存的问题,所以在非学术环境中生活着的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是否能够完全做到客观、中立便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总的说来,由于研究者从事研究的大背景来源于其现实生活,所以研究者在从事研究工作时难免会依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与经验。例如,钱钟书先生198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恳谈会上的讲稿《诗可以怨》,就其内容来说,可谓是一篇极其优秀的学术批判论文,但是,对于钱钟书先生为何选择这个题目而非其他,又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委屈和不满。回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出版问题上,如果俞平伯当时不欠债,也许就不会出版《红楼梦研究》,后来的批判运动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二 《红楼梦研究》背后的意识形态
根据现存的史料,毛泽东发起的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其本意并非是针对俞平伯,而是借批判俞平伯进而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据文怀沙的回忆,《红楼梦研究》出版后,“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1]10-11。《红楼梦研究》在最初还给俞平伯带来了一定政治光环。《红楼梦研究》是1952年出版的,“销路很好,印了六版”[1]10,一直没出什么问题,只是等到1954年,出于对意识形态整合的需要,毛泽东想借此批判运动“实现他多年来以马克思主义统一人们思想的宏大构想”[2]346。他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即提到:“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本主义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3]134。林默涵也明白批判运动的动机:“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老跟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很有意义”[1]11。
正因为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针对的并不是《红楼梦研究》本身,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所以,这次批判运动的发生,即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从对于思想领域的控制来说,运动的发生是必然的。而以《红楼梦研究》来作为运动的切入口,又有其偶然性,毕竟这次运动是在书出版两年以后才拿来批判的。事件的起因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两位学生李希凡、蓝翎在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中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批评,后又写了《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光明日报》副刊上,被毛泽东得知后扩大,从而在文艺界掀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由于运动已经由学术问题转变成政治性问题,俞平伯对于批判意见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批得厉害时,俞老情绪低落,压抑的厉害。”[1]13-14而“据俞平伯的外孙孙韦柰介绍,1954年大批判之后,外公外婆绝口不谈政治,不谈《红楼梦》”[1]17。可见运动对其造成的心理伤害。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1954年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其超出了学术的探讨范围。如果我们今天否定了那场错误的批判运动,也就否定了著名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与蓝翎。但是,作为接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初涉文艺研究领域的两位青年,其运用阶级观念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进行批判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在学术研究中,不同学者因不同的思想观念而形成不同的看法,在学术观点上有争议是在所难免的。可惜的是,在这场运动中,由于没有正常的学术探讨氛围,俞平伯与“两位小人物”就成了被批判者与被利用者,都成了运动中的牺牲品。
本来属于学术争论的问题,为何会逐渐演变成一场思想运动?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学术研究复杂的另一面。学术研究领域,是可以容忍不同思想观念的争论,但不同的思想观念背后,有着不同立场的人们。学术研究说到底,还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统治阶级在其建立之初,为了巩固其统治必然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统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其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思想,而这种思想又是以学术观点表现出来的。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含有某种思想的学术观点被打压也有其合理性。
三 学术研究政治化客观上促进了红学的发展
我们今天对1954年开展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持否定态度,但实事求是地说,那场运动在客观上促进红学的发展。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被批判,却因为批判的需要而被众多知识分子所阅读,从而扩大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就在运动中,俞先生他们校勘的《红楼梦》大量出版了,到了1962年《红楼梦》印数有十四万部,‘毛选’才五万部”[1]17。也正是由于这场运动,俞平伯的影响超出了红学界,从而更广泛地为人所知。我们不可否认批判运动对其心理造成了创伤,使其“以后三十年绝口不提红楼梦”[4]42,但“我们把当年对俞平伯先生的批判和俞先生为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写的信、1986年在香港的演讲,以及他逝世前不久的自省结合起来对比分析,不难看出俞平伯先生的自省与这些批判文章之间的关系”[5]2,那些批判文章从客观上促使了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研究的深入思考。
同样的,作为当年被毛泽东批注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与蓝翎,正是他们的文章引起了红学大批判的开展。由于毛泽东对其文章的肯定,“一时之间,李希凡与蓝翎由默默无闻的业余文艺爱好者,成为文坛瞩目的青年评论家。”[6]63之后不久,他们两人都进入了人民日报社当编辑,命运可谓是急剧改变。他们也由于是此次批判事件的参与者而被写入文学史,而研究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他们更是不可或缺的对象。当然,由于其文章是1954年批判事件的导火线,文中用政治与阶级的观念分析红楼梦,对俞平伯的观点进行批判,也使其在文革后学术界中的形象并不光彩,对他们对俞平伯的批判的评价也成了红学研究中的一部分。正因为其在运动中的作用和对俞平伯以及文艺界人士心理造成的伤害,二人在文革结束之后一直著文反思。我们可以推论:如果没有政治的原因参与其中,两人的批评论文仅是学术圈内的事,在红学的影响也不可能那么大。另外,两人最后都成为了红学专家,除了学术成果外,名声对其的发展也有推波助澜。
所以说,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复杂。政治如果介入到学术研究领域,肯定会导致学术研究的政治化,但这对学术研究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相反往往还会造成悲剧。不过,放宽视野,政治介入学术研究,虽然会造成学术研究一时的退步,但其也因有政治的参与,而形成一个考察学术研究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对象,丰富其研究的范围。政治会影响学术研究,但政治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方面。比如说,敦煌学能成为世界显学,与敦煌的文献、文物逸散在世界各地有关,而这些文献、文物是其他国家通过掠夺而来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谴责掠夺行为;但另一方面,也许正是这种掠夺行为,其他国家具备资料基础,才使敦煌学超出一国范围并在世界范围内兴盛。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也正是由于政治的参与,其在文学史、红学史上的地位才尤为特别。
结语
本文通过对《红楼梦研究》出版动机和对《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动机以及政治参与学术研究对于研究者正反两方面影响的考察,来认识作为一名研究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存在着的复杂性。学术研究者身份的二重性、学术观念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都是在我们进行学术研究中所无法逃避的问题,我们只能以一种理智、包容的态度去面对、去理解,才能更好地从事学术研究。
[1]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刘仓.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述评[C]//李文.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俞国.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看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心态[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1).
[5]张兴德.读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楼梦》研究反思[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3(3).
[6]陈辉.两个“小人物”的“红”与“黑”:李希凡与蓝翎的命运沉浮[J].百年潮,2006(8):63.
〔责任编辑:王 露〕
OntheComplexityofAcademicResearchBasedonthe1954CriticismofYuPingbo’sStudiesonADreamofRedMansions
ZHANG Jianwei
(ChineseDepartment,LiupanshuiNormalCollege,Liupanshui553004,Guizhou,China)
Criticisms on Yu Pingbo’s views onADreamofRedMansionsshould have been an ordinary sort of academic dispute, but the campaign of criticizing Yu Pingbo’sStudiesonADreamofRedMansionslaunched in 1954 took on a feature of political movement with the interference of Mao Zedong, revealing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tics.The publication ofStudiesonADreamofRedMansionsand the complex ideology hidden behind were closedly related to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ideology of Yu Pingbo.While having done harm to Yu Pingbo and his fellows, the campaign promoted to some degree the development of redology itself.
redology; Yu Pingbo;AdreamofRedMansions; academic research
2014-04-29
张建伟(1987-),男,河南舞钢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11
:A
:1671-5365(2014)11-002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