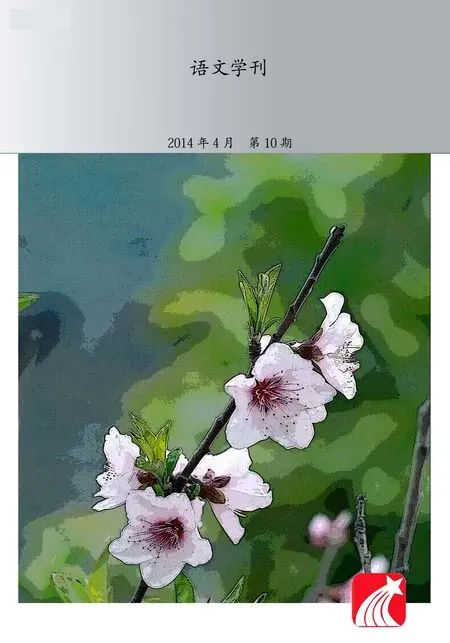“文学史”还是“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14-03-12崔荣
○ 崔荣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工作中,存在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讲授成“中国现代文学”课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其后果为何,亟待厘析。理清其来龙去脉关乎对教学内容的深层理解,更关系实际的教学效果。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和“中国现代文学”课在实际教学中有很大区别:前者更侧重对深长丰富的历史发生过程的描述,由此凸显文学运作的深在规律,并通过介绍文学思潮更迭、文学论争消长和流派浮沉、文体演变、代表性作家作品等内容促使学生了解较为全面的文学史框架,进而构建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令其获得观察定位文学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后者的落脚点在“文学”,又因为文学诸要素最终总要落实、反映在作品(文本)中,对文本(尤其是经典作家文本)文学性的准确体悟及文学价值的讲释是教学中心,其目的主要在于提升学生的文学体验和审美能力。
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这两个概念及其牵系的教学目标无疑又有相互联系的一面,首先,没有“文学”层面教学对学生审美感受和体验这一基本能力的训练、引导其从文学爱好者转变为专业读者,更高层面的能力培养,如历史认知和价值定位就会成为虚妄。毕竟,认知规律是观千剑而后识器。
那么,如何培养学生从名理层面“识器”的能力?必须将具体的文学作品放到历史的链条当中,这是两者更为深层的联系。譬如,判定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否具有超越性和伟大处,最终还是要将其放到文学历史的河流和时代的现场中,这时,“史”的线索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否则,学生会不断问出诸如“鲁迅的白话文佶屈聱牙从流畅度看远不如现在作家的文字,为何给他那么高地位?”等专业基本意识匮乏的问题。同样,缺乏对早期白话新诗质直理性的创作水准的感受,无法进入当时狂飙突进的时代氛围,学生在理解郭沫若《女神》的价值时,也就很容易苛评其诗歌语言,并对其中所表现出的历史青春期的狂喜和面向世界的宏大视界觉得不可理喻,当然也就无从体会其特殊的诗美和浪漫主义精神,进而无法对教师和教材关于郭沫若的历史评价有真正的认同。这时,缺乏“史”的介入就意味着不能唤起学生的美感。
另外,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产生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作品本身就是特定时代历史和文化的载体与映现,理解了那个时代才能最终回归对那个时代的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切实理解,反之则不然。譬如,现在的学生对鲁迅的杂文诟病颇多甚至不屑一顾,根本原因是今天的他们无法进入军阀割据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境,就无从理解蕴含在杂文中的沉郁与绝望。倘若学生只能从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理解问题,不具备将文本放回所从来自的历史文化语境的能力、无法建立它与历史事件的关联,那么,从价值意义上去科学定位文本根本无从谈起;如果再加上无从知晓从《新青年·随想录》开始,一代散文作者在杂文文体上的种种努力,以及杂文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与现代中国文学甚至是中国社会的复杂关系,恐怕也很难到位地理解鲁迅杂文的历史价值和审美蕴含。可以说,“史”和“文学”又是互证互识的关系。
当然,存在联系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混同:“史”的教学更“专”,是中文系专业的本科生必须接受的教育,更是成就研究生专业素质的必经之途;而“文学”教学更多侧重提升教学对象的美感,面向的是中文专科类学生包括新闻和编辑专业以及近年来针对海外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涉及的现代文学教学,因其审美愉悦性,这一层次的教学能吸引更多的学生走进中国现代文学。
二
那么又为何出现了 “文学”日益取代“文学史”的现象?
毋须讳言,首先当是课时的大规模缩减。由于课程结构的调整,中国现代文学的课时不断减少。另外,新的课程设置也要求缩短必修课课时而增加选修课种类,这更令本已捉襟见肘的现代文学课时雪上加霜地萎缩,“讲不完、展不开”是教师的普遍焦虑。如此外部环境和内心焦虑之下,就只能删削教学内容。
简化了哪些内容?历史文化语境的再现、文学思潮的更迭、文学论争的辨析、文体沿革的说明,等等。它们见弃因为,这些内容在脱离了历史语境后往往既显得抽象,同时牵涉的问题和历史要点又最多,要讲清楚极为耗时。例如,谈论1930年代的流派和文学格局,必要涉及“京海之争”。但要解析“京海之争”,恐怕得从新文学中心的南移说起,然后谈到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城乡冲突现实的中国作家的不同情感态度和文化价值选择,接着介绍京派作家和海派作家各自的文学观念和生存方式,继而回到论争,学生才可能对京海双方有到位理解。但因耗时,很多老师的处理方式可能就是略去此点而直接讲授两派作家。如此这般,在现代文学的每一个十年都会有类似的内容砍去,当然史的线索和链条就很难呈现,最后剩下的是重点作家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教学的立足点在转移:“文学史”成了“文学”。
比之教学时间的缩减,学生的变化也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安排:教学毕竟是一个发送——接收的双向过程。
其变化首先表现为文学素质的下降。目前很多大学的中文系都很难录取将中文作为第一志愿的高分学生,倘若出于种种原因学习了中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教学就必须针对现实,先从培养起学生的文学兴趣入手。另外,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复存在,文学读物阅读量下降是这些年媒体和大众关心的热点。自然地,受其影响,进入大学前就完整阅读过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学生几乎寥寥,更有甚者,名著就意味着由名著改编的漫画或影视剧,学生接受层面的速食化、肤浅化倾向十分严重。再加之扩招导致的就业艰难令考证、过级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学生的“专业”,复又导致其功利化倾向。因此现实是,布置下去的作品阅读作业几乎很少有人能完成——学生现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专业要求相差甚远。学生主动性不强及其接受层面的简单化倾向、功利化倾向令其对教师的课堂讲授有极大的依赖性,甚至可以说,教师在课堂上涉及文本越多,他们了解越多。面对如此教学实际,教师只能加强作品部分讲释;并且由于学生文学素养的降低,教学中首先还要激发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那么,更高层面的教学目标,或者也可以说其实是在本科专业教学阶段必须达到的教学目标,如建立文学史框架,形成历史感、分寸感和方向感以及具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等就很难达到,“文学史”教学变成“文学”教学。
其次,学生的期待视野、兴趣爱好也在让“文学史”变成“文学”。这个问题可从两方面考量。
其一,时代意识的转换导致学生的主观选择和接受视野在变化。如果说1980、90年代的大学生还有家国情怀,保持着对社会现实和文学发展的强烈关注;那么当下的学生更乐意接收、消化那些故事性强或是文字优美的教学内容,即,学生更易接受的是“文学”层面中感性、有趣的部分,一旦进入理性和哲思的层面,就显得兴趣不足。以沈从文和张爱玲的教学为例,介绍小说的故事层面时,学生往往听得津津有味,一旦向更深开掘,分析两个作家对文明的思虑、进而从思潮变迁角度介绍1930、1940年代作家对乡土文明和现代文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思考,学生就由不想进入而致不能进入。还有,学生一般对张扬个性意识的思潮、作者颇有好感,而一旦涉及家国、革命,包括文明之类严肃和沉重的课题,也会明显表示出排斥。比如,左翼文学关注社会重大历史问题,并给现代文学带来反映时代全貌的史诗性小说,在文学史意义上应着重强调,但因其主题倾向于社会剖析,学生也显得淡漠。故而,即使在教学中加入“文学史”的部分,学生最终到底能够接受多少,也是一个问题:学生的接受实际同样让“文学史”在变成“文学”。
其二是过分强调学生主体性有时也有消极影响。目前的大学教育正在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学校(教师)服务意识和学生消费意识都在增强。因此各高校现行的教学评估体系中,学生要评价老师。如此评价方式的初衷不言而喻。但问题是:教师为了求得学生心目中“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而迎合学生的需要和心理,忽视了学生人生体验并不丰富、阅读品味停留在较低层面以及接受过程中的肤浅化与简单化倾向等致命的问题。教师有意无意如此为之的后果往往就是“文学史”在变成“文学”,甚至还会有更恶劣的结果出现:“文学”教学又在变成“故事会”。
三
或者应该把问题向更深一层追问。“文学史”还是“文学”成为问题,其内在的症结在于:教师的主体性与教学的科学性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20世纪以来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中国现代化所具有的历史特点对现代文学的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1因而如果教学只关注作家作品,如此授课注定无法精彩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另外,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多舛和这个民族的艰难奋进让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以“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2]2,只有将作家面临的文化语境的沉重性揭示出来,才能精准解释中国现代文学文本苍凉沉郁的美感特征的成因。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学科特征决定了,教学中无法淡化“史”的线索,且必须帮助学生建立起必要的历史感,否则就无法呈现现代文学的学科特色。如此,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就必须理顺文学史和作品的互动关系,不可顾此失彼。
对策还应包括教师强化自身的主体性,首先是真正尊重教学内容的规定性,保证教学的科学性。“史”的线索的介入、具有思辨性和历史深度的内容的传授不仅会保证教学的严谨度,从更长的教学“视野”看,定会培养一批审美敏锐、头脑深邃的专业人员。而过于迁就学生较低层次的要求,不仅会在教学的完整性上丢了西瓜拣了芝麻,也不利于学生素质的培养与提升,这只会让教学陷入肤浅化、功利化的恶性循环。
其二,强化主体性也意味着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尊重教学内容自身特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尊重教学规律、把握学生接受实际,做一些必要的调试,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进入教学内容,比如,可以以对某一经典作家的讲授引带对某一思潮、某种文体的发展路向的呈现,这样处理既深入浅出,更以点带面、详略得当。
就客观方面和操作层面而言,按照新的课程设置要求,在本科阶段开设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课相补充的选修课恐怕是当前形势下的必然选择,而这些选修课应该有其特殊性:大部分还无法进入研究的更高层次,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在必修课教学内未来得及铺展的内容。这实际上是将基础教学进一步划分层次,在划分之后求得最终的完整性。例如,笔者在结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之后,曾实验过在接下来的学期开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的选修课,讲授“乡土小说派”时明确了鲁迅和这个流派的关系,深化了对于鲁迅的认识,而对此一流派其他代表作家的讲授则将文学史的丰富性呈现出来,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当然,必修课和选修课的科学设置和排课的连续性是保证实现教学完整性的重要前提。
出现“文学史”还是“文学”的问题,似乎给人以教学和研究在肤浅化、娱乐化的印象,但事实上,这也还是标志着学科观念、教学观念的进步,这说明,教学和研究也在不断回归文学本体——或许,强调“文学”这一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多年前把文学史等同于阶级斗争史的教学实际不得已而为之的对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学科在艰难回归自身。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舍弃历史发展和文学发展的链条就文学论文学,倘若在强调文学主体性的前提下完全将其孤立起来,反而可能离文学越来越远。也许,即使是在教学当中,我们必须摒弃的也是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这一点,才是解决教学中遇到的诸多问题的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C]//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