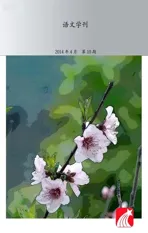民族化和全球化
——浅谈全球化语境下西部文学的发展
2014-03-12刘雪娥
○刘雪娥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眺望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技术一体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纳入到世界大工厂的体系之中。如此迅猛而广泛的经济大潮不仅影响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各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乃至文学的发展。在这样一个经济方面全球逐步趋向统一的时代大潮下,曾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地域文学,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强劲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何在宏大的全球化语境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亦或者说,西部文学是否会最终消解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浪潮中,成为历史记忆中多样性的表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西部文学应以怎样的姿态在一体化进程中保持自我,发展自我,如何在风驰电掣的全球化中保持西部文学鲜明的民族性,不迷失,不趋同?
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一直热度不减,相关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卷帙浩繁。那何为“全球化”呢?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笔者比较认同何为在《“全球化”概念的语义阐释》中的定义,他“从社会发展形式、时间、空间、人的实现方式、实践过程、认知方式等六个维度进行了辫证阐释,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多向度的综合概念’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一种全球多样一体化形式,是人类社会化为全球性的过程,是对人类的闭关自守状态的扬弃,是人类的本质力量以新的方式的对象化过程,是主体与客体对全球性社会的双向建构过程,是全球性社会的现实和理想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
由此可见,尽管全球化具有世界性,但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性,而是“多样一体化”的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的辩证统一。这就为民族性的存在留下了空间,也就是说,全球化并不否定和抹杀民族性,它与民族性的关系并不是要么你死,要么我亡的绝对对立,也不是历史性的承接关系,即认为全球化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相反,民族化和全球化是共时性的关系,民族化的发展是全球化发展的基础,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化能够促进全球化以生机勃勃的姿态呈现具有世界性的命题意义,也能使具有特色的民族性走向世界的广阔舞台。
因此,就西部文学这一具有民族性的地域文学而言,它在全球化语境之下的发展,也就不以抹杀其地域风情、民族特色为代价,而是在张扬和发展民族性的过程中,在多元文化的认同与吸纳中,逐渐汇入全球多样一体化的世界潮流,成为世界文化中独立的奇葩。
纵观西部文学的发展历程,经过许许多多西部文艺工作者不辞艰辛的耕耘,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以西部独特自然景色为底色,书写西部精神和人文底蕴的优秀作家,如贾平凹,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对家乡商州的风土人情进行深情的描绘,同时也将商州的发展放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召唤下进行审视和考察,在动态的发展中思考商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成就了其独具地域特色的“商州系列写作”。还有阿来以反思民族文化的视角对藏族土司制度逐步瓦解的回望,张承志以坚守理想的态度对回族哲合忍耶为守护心灵圣地而前仆后继誓死反抗精神的表现,郭文斌以空灵飘逸而又略带感伤的笔调对记忆中多情乡土的诗性阐释,董立勃在人道主义底色上,对现代性的平等、自由、尊严和人权意识的彰显等等。正是这些作家在自身生命体验之上对西部生存环境、生命遭际的深刻书写,使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包括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进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得以展现,也使西部文学独异于其他文学的美学特征和美学价值得以发现。在这些书写中,西部文学不仅主动关注、参与、呼应着文学主潮的发展,与中国文学的整体趋向基本同步,而且也依据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地域因素,不断抵近本土,发掘这一独特文化形态的潜在资源。也就是说,西部文学的发展,一直都得益于西部文化独特的民族性,这是西部文学得以自立自强的宝贵财富。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中,要使西部文学继续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不仅需要我们以全球化的眼光重新审视西部文学发展存在的问题,在自省中开拓创新,而且要正确认识西部文学对传统民族资源的利用和开掘,使西部文学以独立的审美姿态参与全球多样化审美形态的建构。
一、自省精神
人贵有自知之明,对本土文学的审视也一样,要想使西部文学得以长足发展,就必须以客观的自省精神认清文学发展的现状,包括认清它存在与发展的优势资源,存在的问题,及至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大的文学发展框架中它所处的地位和拥有的价值。西部文学发展至今,存在着一些影响西部文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问题,如话语建构的狭隘化、学术定位的模糊化、作品多精品少等等。因此,我们的自省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对于“西部文学”内涵的界定,我们知道,“西部”首先是地理的划分,这个地理性的修饰词限定了西部文学的地理范围,尽管这种限定是相对的,但也有其界定性,使我们不会把如山东、天津、上海这些东部地区的作家创作归于西部文学的范畴。同时,还得注意避免西部文学地域划分的狭隘化,如在《简明中国当代文学辞典》中,列有“西部文学”条,将其界定为“中国西北地区文学的统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西部文学进行了自我缩军,甚至有论者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例,认为“国内的‘西部文学’之名也被‘西北文学’甚至还需要加上缀语的‘西北大部文学’冒领,这构成了国内文学界中对‘西部文学’的后殖民理论想象的进一步狭隘化、边缘化”。这或许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看法,却也有其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警示我们如何为西部文学定界。另外,更为重要的是,西部文学也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包含着诸如宗教底蕴、民族互融、文明形态、精神内涵等诸多内容。因此,必须客观而准确地把握它的内涵,既要避免概念界定的狭隘化,又要避免泛化的倾向,正确地为西部文学定位。
其次,不能固化对西部的认识,这里既有对西部作家的要求,又有对西部评论家的要求。就西部乡土小说的创作来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涌现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如贾平凹的《高老庄》、雪漠的《大漠祭》、陈忠实的《白鹿原》等,这些作品不仅是西部乡土叙述中的精品,也是乡土中国想象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板块。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在西部乡土小说叙述中存在着模式化倾向,叙述的场景往往都是“传统文化积习深重,家庭血亲关系稳固,或是在现代文明和商品意识冲击下发生经济和文化震荡的西部村镇;而叙述的对象则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凡俗人生”。而且,由于西部长期的物质贫困、生存条件的艰难,苦难化就成为作家叙述的主要内容。如雪漠在《大漠祭》的前序中写道:“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这无疑是些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整个人生。我的无数农民父老就是这样活的,活得很艰辛,很无奈,也很坦然。”这样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典型性,将西部农民生存的痛苦体验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也有局限性。因为时代在发展变化,地域文化也在发展变化,我们对其的认识不能停滞,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贫困等外显的文化层次上,也不能停留在以奇特的地域风貌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表现层次上,更不能停留在由原始的惰性和凝重的习惯势力造就的西部人愚昧麻木的生存境况的书写上,而是要在动态发展中,试着去挖掘西部人的民族性格在时代变化中的新变化,表现文化的差异性和落差性,去寻找普世原则在西部生活的表现,包括普遍的人性、理性与逻辑思维法则等,建构西部文学的普世价值,提升西部文学的思想性。当然,必须明确的是,追求西部文学的普世价值并不是要丢掉我们的民族之根,一味跟上世界的步伐,迎合世界的潮流,而是在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探寻能够影响乃至引导世界文化潮流的精华。
另外,文学评价是文学生产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评论家对作品评价的角度和立场也影响着西部文学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因此西部文学评论家对西部文学的发展肩负着举足轻重的责任。对于西部文学创作的美学风格,丁帆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概括为“三画四彩”,即“呈现为外部审美要求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美学形态,以及作为内核的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的美学基调”。这是对西部现代文学美学特征高度而准确的概括,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对我们对西部文学美学特征的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概括性具有典型性和浓缩性,它在对事物的本质特征做出概括的同时,也可能使事物的丰富性丧失,西部文学因其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融合和碰撞,决定了它是一个丰富而多元的文学形态,仅仅用简单的概括难以将它的美学风貌一概而全。正如“新边塞诗”代表诗人、著名散文家周涛也对“新边塞诗”所做的反思,“对于‘诗美’,我不喜欢‘粗犷、豪放’的概念。美是丰富的,出于功利的目的去强化某种东西只能损害文学。西部诗给人的错觉与当时强调的表面现象有关,仿佛西部人就是能吃苦、耐劳。在这样的‘豪放’中,人的深层的感情未能在‘新边塞诗’中被发掘出来,发掘出来的内心世界只是一个层面的,不够丰富,诗人的美学追求应更深入地贴近自己的内心感受”。从这样的反思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边塞诗”因为过度强调其雄壮之美、阳刚之气,而使“新边塞诗”对美的描绘和阐释有所局限,破坏了它的多样性。而且,随着时代与社会的更替和演进,许多文化因子也会加速裂变,文学元素的变化也就在所难免。因此,这就需要西部文学批评家不断更新批评理论,与时俱进,尝试用新的理论方法,从多角度、多方位对西部文学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解读,挖掘西部文学中那些被遮蔽的话语,不断为西部文学塑造有内涵、有特色的新形象,扩大西部文学的影响力。
二、开拓意识
诚然,西部文学这些年来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这并不是我们故步自封、盲目自信的资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球化进程日益逼近,容不得丝毫的懈怠,怎样不断开拓和创新才是西部文学迎接全球化应有的姿态。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笔者认为西部文学应从对待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两方面入手求得生存之地。
首先,“拿来”西方文化。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学观念的发展速度一直领先于我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始,我们就开始广泛地向西方学习,借用其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建构我们自己的现代文学观。这些先进的文化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引入,也确实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想天空,为我们反观自身传统提供了绝妙的参照,才使我们在对西方文化的借用和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中形成了今天蔚为大观的中国现代文学观。井底之蛙止于井,天地大小限于井;天高海阔任鸟飞,乾坤无限览无余。这就是对比,也是实实在在的差别,对西方文化持什么样的态度,决定着我们的胸怀乃至视野是井中之天,还是域外之天。而且,没有交流和互动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一潭泛不起任何波澜的死水,是终究要消亡的静止的存在。只有多元文化之间的补充、质疑、对话、竞争才能产生让本土文化生机勃勃的引力,才是本土文学生命力之所在。因此,对待西方文化,我们依旧可以持有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既然已有车,何必闭门造车,拿来用之又何妨。不过,西方文化良莠不齐,鱼目混杂,不能全盘吞吃,“要占有,要挑选”,对其要批判性的吸收和接纳,即在辩证的认识中接受外来文化,增加知识容量,融会贯通,扩大视野,提升我们的思想深度,做有大气魄、大胸怀、大视野的学者、作家。同时,要善于捕捉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碰撞的新火花,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往往得益于这些新火花,它很有可能是本土文学新鲜血液滋生的契合点。
其次,要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每一个民族的职责是,保持自己心灵的永不熄灭的明灯,以作为世界光明的一个部分。熄灭任何一盏民族的灯,就意味着剥夺它在世界庆典里应有的位置”。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中,不能一味求同而不存异,只追求统一性而丧失民族性和多样性,保持民族自我,永不熄灭民族之灯,才能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纵观西部文学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它的发展受益于西部独特的地域风情和多样性的文化交融。神奇的天山、苍茫的草原、无垠的大漠、烈风中的经幡、烽火的残垣、荒凉的戈壁等意象和景观在西部文学创作中经常出现,给人色彩浓烈、风格奇诡多样的视觉效果,是西部文学赖以存在的背景底色。在这一背景之下,又有对西部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民族性格的关注,对西部普泛化的自然崇拜、隐秘的历史、虔诚的宗教信仰的追寻。这都是其他地域文学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学资源。文化的多样性则体现在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上,既有各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之间的冲撞与融合,游牧文化与内地农耕文化、现代都市文化的撞击和融合,还有异质文化的冲撞和融合,包括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中华民族之间的交流,这种文化的汇流,形成了西部多元文化混合的特色。而这些都是西部文学得以凭借的文学资源,过去是,将来更是。无根之木会枯萎,无源之水会断流,无基之房会坍塌,民族文化就是西部文学赖以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地基,它是曾经身处“边缘”的西部文学实现“文化突围”的珍贵财富,也将是西部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谋求更好更快发展取之不尽的宝藏。因此,西部文学也只有深深扎根于此,接受多元混合文化的熏陶,探索西部人民的精神脉向,发现广袤的西部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联系,才能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中为其找到恰当的位置。
纵观当今世界局势,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对话和交流在所难免。反思民族文化的优劣性,继承和坚守民族文化,挖掘民族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既是对全球化中多样性建构的贡献,也是对民族化中现代性建设的要求。因此,以对内自省、对外开放的态度兼容并蓄世界各种优秀文化,迎接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进程,才是西部文学发展应有的姿态。
[1]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M].人民出版社,2004.
[2]雪漠.大漠祭[M].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
[3]何为.“全球化”概念的语义阐释[J].西北人文科学评论,2009(10).
[4]田启波.矛盾与解析:全球化的哲学反思[J].广东社会科学,2003(06).
[5]黄祖桥.论全球化中的民族化[J].新视野,1999(03).
[6]王晓宏.关于普世价值的研究:问题与争鸣[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2).
[7]曹永萍.普世价值民族化与民族价值普世化[D].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8]白浩.西部文学想象中的理论后殖民与主体重铸[J].长江学术,2007(07).
[9]赵学勇.全球化时代的西部乡土小说[J].唐都学刊,2003(01).
[10]贺云.浅谈全球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J].理论与当代,20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