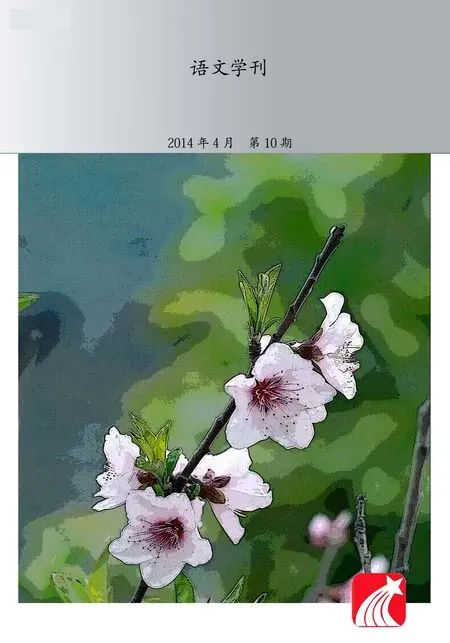再议汉字简化
2014-03-12刘昀
○刘昀
(天津师范大学 津沽学院,天津 300071)
一、源远流长
避难趋易是汉字演化的内在动力,因此简化汉字的现象古已有之。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隶书、楷书,汉字的象形意味逐渐淡出,符号性步步增强。
我国历史上首次自上而下的汉字简化运动是秦代的“书同文”。经过这次变革,小篆迅速推广开来,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初步得到了改善。二十世纪初,以陆费逵为代表的教育家借简化汉字探讨救国真理,后来,钱玄同、胡适、刘半农等学者纷纷响应。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先后组织了两次汉字简化工作。其中第一次简化方案在规范汉字、普及教育、提高效率等方面成效显著,虽有不足之处但深入人心,瑕不掩瑜。
由此可见,简化的趋势一直伴随着汉字流变的整个过程。吐故纳新,由繁至简是汉字系统新陈代谢的总体走向。
二、毁誉参半
汉字不是各种笔画的简单堆叠,而是由各个部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系统。“由繁至简”带来了方便,但也挪动了系统中的棋子,挑起了系统内部的矛盾,其中较突出的有两个。
一是“约定俗成”与“系统类推”的矛盾。现行的简化字,很多来自历代的“俗体”字,这些字并非造于一时,也非出自一人之手,造字者受时空所限,不能瞻前顾后,难免造出一些“编外分子”。
二是“化简为用”与“增繁为别”的矛盾。汉字的发展既要满足符号趋简避繁的要求,又要适应汉语日益精密化的演进,还要保证不同汉字形体的区别度。前者需简,后者需繁。“秧要日时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干。”既然无法面面俱到,简化的方案便难免听到反对的声音。如:
“破坏系统,因简害义”说:认为简化侵蚀了原有的表意系统,破坏了汉字的构形理据,并造成大量的信息流失。坊间有“亲(親)不见,产(產)不生,儿(兒)无首,飞(飛)单翼”的说法。又如,以“页”为意符的汉字“硕”、“颗”、“顾”、“颇”、“烦”等多与“头”义有关,而原本“从页豆声”的“头”(頭)简化后却成了系统中的害群之马,被拒之门外。很多学者还举到了“車”与“车”的例子,前者保留了车轴、车轮和两边木栓的形态,后者已被符号化,失去了“以形示义”的功能,进而丢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无法继续书写历史,传承文明。
“身兼数职,不堪重荷”说:简繁字体之间并非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对二,一对多的格局屡见不鲜。由此,个别汉字被委以重任,兼表多义。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很容易误导古文学习者,并给计算机处理带来了麻烦。例如:
一简对多繁的关系 误用举例
发——發、髮*一發千钧
历——歷、曆*日歷
复——複、復*回複
干——干、乾、幹、榦*幹燥
“扰乱书法,有碍观瞻”说:认为汉字简化生出的“不肖子孙”其貌不扬,严重影响了传统书法的艺术魅力,并使一部分手写字体的分辨率降低,带来了“风凤不分,厂广易混,阴阳难辨”的尴尬局面。
“隔断历史,阻碍交流”说:认为从时间角度看,简化字割断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联系,将大量古代典籍变成了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从空间上看,用字不统一,是大陆和港澳台文化沟通的瓶颈。
三、择善而从
鉴于上述问题,近年来“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呼声此起彼伏,不断冲击着文字改革者的耳膜。早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递交了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近日,香港演员黄秋生甚至用繁体字在微博上写道:“在中国内地写中文正体字(指繁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哎,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此言一出,众皆哗然。“废简复繁”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个人认为,“废简复繁”不合时宜。就好比着装,古人长袍大袖,今人西装革履,这是风尚发展的结果。至于唐装旗袍,偶尔一穿,尚可显示古老文明的魅力,如果为了继承传统而鼓励全体国民都穿回长袍大褂,那岂不是要穿越时空,重回唐宋?另外,推行简化字是国家政策,朝令夕改,也难以服众。许嘉璐先生在纪念推广普通话五十周年座谈会上曾提出“推行简化字,并不是要消灭繁体字,只是限制它的使用场合”。这样的意见比较中肯。
其实,简化汉字的遗憾未必全都是缺陷。首先,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形体的意义和字的意义本来就不能划等号,即使是象形如“日月山川”,字形也只能起提示作用,无法覆盖词义的全部内涵。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词义也会发生变化,比如现代意义的“车”已与古代有两个木栓的“車”大相径庭,再用繁体字,就画蛇添足了。繁体字是记录古代汉语的符号,语言发展了,文字形体有所变动亦不为过。
第二,计算机在处理“身兼数职”的简繁对应时,如能改良技术,将字体转换的基本单位由字延伸至词或词组,或许就能有效降低错误比例。如果仅为了计算机处理简便就大规模地改革文字系统,未免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
第三,情人眼里出西施。字体美丑是审美取向问题,见仁见智。美感只能影响却不能决定文字改革的方向。
第四,繁简字体虽有差异,但毕竟一脉相承,还不至“云泥已殊路”。因此,“用简识繁”对大多数学者来说并不困难。“用简”则效率提高,“识繁”则沟通无碍,简体字简约而不简单,简洁而不简陋,仍然可以记录和传播古老的华夏文明。
至于汉字改革将何去何从的问题,恐怕很难用“繁化”或“简化”一笔带过。有些汉字的优劣很难用繁简衡量。新造的会意字如灶(竃)、岩(巖)、众(衆)、灭(滅)基本都能兼顾形义关系,也算是传神之作,虽简而优。而像“燃”(古字“然”)这样的字,被假借后繁化,增加了形旁,使形义关系再度统一,是虽繁而优。因此我们不如说“择善而从”。
[1]苏培成.简化汉字60年[J].语言文字应用,2009(4).
[2]王宁.再论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J].语文建设,1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