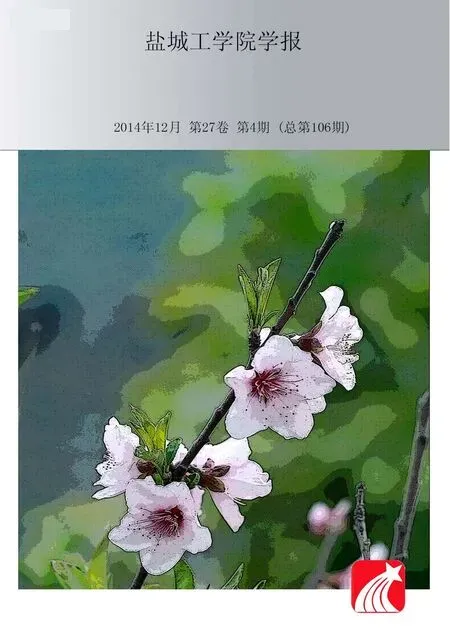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2014-03-12熊伟
熊 伟
(盐城工学院 社会科学部,江苏 盐城 224051; 香港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香港)
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熊 伟
(盐城工学院 社会科学部,江苏 盐城 224051; 香港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香港)
在祛魅的时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已无法诉诸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学说,而只能代之为全体公民所认同的公共理性。在通过公共理性来求得法律合法性的过程中,罗尔斯首先界分出具体法律规范与宪法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的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理论的核心。公共理性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证明,一方面为其奠定了一整套实质性正义原则,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程序性的指南。公共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作出证明,而且也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弘扬,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使得法律能够更具可接受性。
罗尔斯;法律合法性;公共理性
在法哲学的研究中,对合法性的探究既是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言其为重点,是因为合法性追问的是何为正义之法?法律的可接受性何在?这一法律合法性自身所带来的问题意识,决定了合法性乃是法哲学研究的生命线。而言其为难点,则是因为在“诸神争论”的现代世界,寻觅一个能够为所有公民都能接受的共识基础极为不易,同时法律的可接受性乃是法律合法性得以证成的核心。一般而言,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前现代社会,法律合法性的证明是通过为人们所共享的道德、宗教等整全性学说来完成的。而在现代社会,由于终极性的共同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式微,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前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合法性论证的范式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由此便给现代法律提出了一个难题,即现代法律的合法性何以依凭[1]?
合法性症结的聚焦之处,正是问题解决的关键支点。“合法性意味着为公民接受法律提供好的理由。法律合法性与法律的规范性质、集体性认同以及作为法律共同体基础的最终标准密切相关”[2]。所以,如何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为法律寻觅坚实的共识标准,成为了谋划现代法律合法性基础的要旨。而作为法律哲学家的罗尔斯,在该方面的有益探索,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理论世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起点是,“一个由自由而平等之公民——他们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了深刻的分化——所组成的稳定而正义的社会怎样才可能长治久安?”[3]13对于该问题的回答,罗尔斯认为,需要建立一整套的正义原则(自由原则、均等原则以及差别原则)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而正义的原则要能成为社会整合的基础并作为合法性的标准,就必须面对如何取得全体公民认同的问题,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建构有别于整全论的道德建构,它能够得到秉持不同整全论学说的公民基于公共理性的认同。质言之,作为公民理性的公共理性,可以解决正义原则的认同问题。因之,就本质而言,“政治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合法性,解决合法性问题要应用公共理性,而公共理性的对象是宪法实质和基本正义问题。”[4]
在罗尔斯看来,公共理性一方面为法律提供了实质性标准即两个正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为法律提供了程序性标准即公民推理和论辩的指南。正是公共理性被赋予了这两种特征,决定了其可以担当法律合法性的基础。运用公共理性来解决宪法实质和基本正义问题,构成了罗尔斯探究法律合法性的基本立论。宏观而言,罗尔斯的论证策略一方面接受了现代世界理性多元的现实,同时也肯定了法律合法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唯有诉诸启蒙的遗产——理性资源。问题是,公共理性是如何对现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加以解决的呢?罗尔斯大致上遵循了这样的思路:首先界分了两种合法性问题,即权力行使和宪法根本的合法性;在厘定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之后,将理论的重心投向了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此二者要获得合法性的证明就必须诉诸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在为现代法律提供理论论证的同时,也能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为合法性的实现提供论证资源。
一、两个层面的合法性
罗尔斯的学术抱负并非是为人类社会中的法律寻求一个超越时空的标准,而是立足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现实,试图解决社会整合以及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在罗尔斯合法性理论展开的画卷中,立宪政体是其分析问题的起点。他认为,在立宪政体当中,政治关系有两个典型特征:其一,它是社会基本结构或基本制度结构内的一种个人关系,个体与该基本制度结构的关系是因生而入其中,因死而出其外;其二,政治权力总是依靠政府使用制裁而形成强制性权力,因为政府在建立其法律时,才有使用强权的权威[3]143-144。第一个特征指向于与宪法相关联的社会基本架构;第二特征说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特征。政治统治中的权力,在得到理论确证的同时也要求在现实中加以实现,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权力的强制使用如何满足合法性的要求?合法性的追问,要求对权力何以被人们接受以及权力自身的可接受性作出回答。一般而言,在法治社会中,权力合法化的基本逻辑是来自具体法律规范的授权,而具体法律规范自身的合法性则来自上位法,经过层层上溯,具体规范的合法性被追溯至最高法——宪法。于是,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解,权力唯有在符合宪法的情况下才是合法的,所以,对具体权力的行使及法律的运用,其合法性最终会诉诸宪法。就此而言,该层面的合法性适用的范围是既定的法律秩序,通过上位法直至最高法律规范——宪法的保证,法律规则便获得合法性的证明。这一主张并非罗尔斯所独创,它与法律实证主义者所坚持的渊源命题(例如凯尔森的基础规范、哈特的承认规则)相去不远。在既定的法律秩序内,通过最终溯及宪法的方式来获得政治权力以及法律规范自身的合法性,说明了只要有宪法、法律的授权,那么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既定法律秩序内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并非法律合法性问题的全部,前述政治关系的第一个特征,还要求我们进一步追问宪法及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从何而来?这就涉及到合法性问题的第二个层面,相较前一层面而言,该层面合法性的证明更为根本,因为如果宪法的合法性得不到保证的话,又遑论立基之上的具体法律规则与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呢?
在既定的法律秩序内,宪法处于效力金字塔的顶端,是政治权力和法律规范的合法性源泉。罗尔斯继承了西方社会中审议民主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宪法的基本要素是可以合理期待被所有自由平等公民共同认可”[5],也就是说,宪法自身的合法性在于公民的共同认可。这样,我们可以界定罗尔斯的合法性理论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权力及法律规范的合法性;二是宪法的合法性。概括而言,“只有当我们履行政治权力的实践符合宪法——我们可以理性地期许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按照为他们的共同人类理性可以接受的那些原则和理想来认可该宪法的根本内容——时,我们履行政治权力的实践才是充分合适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原则。”[3]145
一如前文指出,第一层面的合法性只是一个包括立法与司法的技术问题,这在现代法治社会并非难题。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理性多元的情形下,正义的原则如何能成其为宪法乃至整个法律秩序的根基?同时人们又如何能够认同它?这便是宪法合法性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宪法合法性的公共理性证明
按照政治自由主义合法性原则的要求,“关于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问题,基本结构及其公共政策都可以向全体公民证明其正当合理性”[3]238,进言之,宪法合法性问题的证明需要诉诸全体公民,同时论证的根据应该是为公民广泛接受或具有普遍适用性。该主张的核心在于何种理由或证据具有普遍接受性。由于现代社会理性多元的现实,人们各自秉持着相互竞争的整全性学说,虽然这些学说都有其合理性,但任何一种学说并不能得到全体公民的认可,因此,宪法合法性的证明不能通过传统的形而上的信念获得。基于这一境地,罗尔斯认为需要引入一种能够为全体公民所接受的新的论证资源——公共理性。
与私人理性不同,公共理性包含了原则性和程序性两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是一套禁忌系统,它将“原初状态”下所选择的正义原则通过宪法的形式,对以立法程序所表达的人民主权有所限制。在这里,人民的意志不是最高的,在其之上必须有更高的公共理性(它通常以立法第一原理表现出来)来规约它,这样,才能切实保证民主社会不被自我颠覆、公共正义得以实现[6]。细而言之,公共理性是自由民主社会中一套有关正义的基本理念和规则,是政府官员行使公共事务的推理理性,也是公民们在对宪法和正义的基本原则进行表决的推理理性[3]405。其特征有三:其一,它是公民的理性;其二,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利益和基本正义;其三,它的本质和内容是公共的,是由社会的政治正义观念表达的理想和原则所给定的[3]226。
由是观之,公共理性的厘定植根于西方社会审议民主的传统,其目的则在于希冀建立其上的宪法根本及基本正义问题能获得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证明。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基本结构的实质性正义原则;二是各种探究指南即推理原则与证据规则(按照这些原则和规则,公民们便可决定能否恰当运用实质性原则,并确认那些最令他们满意的法律和政策)[3]237。公共理性在现实政治中是这样展开的:“第一,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所规导的;第二,这种政治观念是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达到重叠共识的核心;第三,当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发生危险时,公共讨论(即诉诸公共理性)是按照政治的正义观念来进行的”[3]45。具体说来,公共理性的核心在于,当公民对宪法及正义的原则进行讨论时,不能求助于他们所拥有的合理的整全论观念,而应代之以在正义原则指引下的相互共享的理性。宪法的实质问题指向于政府的结构、运行过程以及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其主题是公共的,自然它的证明也应向所有的公民开放。换言之,宪法应当是秉持不同整全论观念的公民们的一致共识,也即罗尔斯所谓的“重叠共识”,而这种共识能被人们所接受的理由则是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对宪法合法性证成有两层含义。一是宪法基本架构应该满足正义原则的要求,在罗尔斯看来,此处的正义原则主要是指平等自由的第一原则。何以如此?盖因实质性的正义原则内嵌在公共理性的内容之中。二是对宪法危机或进行解释时,应当诉诸公共理性,因为只有在正义原则的指引下,通过公民共享的公共理性的推理,而非借助个人整全性观念,于是,解决方案在符合正义的同时也能得到所有公民的支持。
三、司法实践中的合法性标准
经前文分析,罗尔斯合法性理论的关键之处就是通过公共理性来确证宪法的合法性,这一论证范式既不同于他在《正义论》中所主张的基于道德哲学的证明,同时也不与哈贝马斯式的单纯程序性证明相同,公共理性对宪法合法性的证明兼具了实质性和程序性两种维度。罗尔斯对公共理性所寄托的愿望并不简单地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他还将这一规划推向了具体的司法实践活动中。
公共理性所适用的范围包括官员、公民在涉及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讨论,还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在罗尔斯看来,在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的立宪政体中,公共理性乃是其最高法院的理性,而且是法院履行的唯一理性。最高法院是唯一可在政治体制上体现理性创造的政府分支,并且是理性的唯一的创造物[3]224-245。进一步来说,作为推理原则和证据规则的公共理性应当落实到司法领域中,唯有如此,司法行为才具有合法性。
需要注意的是,罗尔斯将公共理性运用于司法是有限定性的,它仅适用于具有司法审查制度的立宪政体。将公共理性视为最高法庭的理性,主要是针对法庭在履行较高法律(宪法或基本法)的司法解释职能而言的。在宪法需要解释之时,法官所论证的资源只能是公共理性,他们“不能求助于自己的个人道德,也不能求助于普遍的道德理想和道德美德……相反,他们必须诉求于他们所认为是属于有关公共观念及其政治正义价值和公共理性之最合乎理性的理解的那些政治价值”[3]250。罗尔斯将基于公共理性的司法解释视为最佳的解释,它是一种最适宜于表述宪法所规定的相关内容的解释;也是一种最能根据公共正义观念或该观念的一种理性变异观念来证明宪法内容之正当合理的解释。而司法解释为什么要诉诸公共理性呢?原因则在于,通过公共理性的解释,一方面使法官的行为能够得到具有同样公共理性的公民的认可,另一方面它为宪法和宪法解释之间建立起一种连贯性的关系。
除了对宪法进行司法解释时要使用公共理性之外,在疑难案件的判断中同样也需要公共理性。在司法过程中,法官经常会遇见现有的规则不足以裁决案件的情形,这该如何处理呢?基于解释主义的立场,德沃金认为,法官“不应该试图像立法机关会做的那样去进行立法,相反,应该试图辨识公平和正义原则,这些原则最好地论证了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法律,然后将这些原则适用于新案件”[7]。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法律秩序的基础是正义的原则和公共理性,为了保证这一规范性的要求,在疑难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不是在创设法律,而是将这一规范性要求延伸到法律的空白之处,唯有如此,方能保证整个法律体系的连贯性。简言之,法官在法律出现漏洞时,他诉诸的准则只能是正义原则,而获取的途径则是公共理性,这样在做到与基于正义原则的宪法保持连贯的同时,也能使适用于疑难案件的原则为公民所接受,从而满足了合法性的要求。
四、余论
将公共理性设定为法律合法性的基础,源于罗尔斯对西方现代社会理性多元现实的考量,其理论愿旨在于寻求一个能够为所有秉持着相互竞争的整全性学说的公民所认可的基础。在自由民主社会的国内政治中,公共理性认为所有公民都负有从一个共同的基础来论证其政治行动的特殊义务,这一共同的基础就是:通过法律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而可能共同拥有的理由和证据[8]。在法治主义的理念中,法律作为公器,它调整的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并应当反映公民的意志,因而,“法律是公共理性的表达形式……通过公共理性,法律所宣称的超越公民判断和行动之上的权威,必须最终基于公民们自己的理性之上”[9]。将法律合法性的最终标准溯及公共理性蕴含了对平等价值的关切。公共理性的观念预设着平等的、理性的现代人形象,他们被赋予了平等分享理性的能力,通过程序的设定保证他们平等对话的权利,将讨论的结果界定为所有参与者的共识以使人们能够平等的接受,所有这些都彰显罗尔斯对平等价值的坚守和弘扬,归根到底,是在现代性境况中对人之尊严的维护。
诚然,罗尔斯用公共理性来解决法律合法性的理论尝试并不是完美无瑕的,事实上,罗尔斯虽然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成功地摆脱了各种整全性学说的纠缠,依靠冷峻的公共理性的筛选,提出了一种关于基本正义以及法律合法性的重叠共识。但另一个事实同时出现,理性地推理时所摆脱的那些纷争,并没有离他而去,而是最终加倍地降临到他“赤裸裸”的正义理论上。人们纷纷指责,这种不追求更高意义的善的正义理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差别原则所体现出的权利对善的优先性究竟是不是合理?而哈贝马斯则将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斥之为一种“垄断式”方式,它仅是换了形式的“独断论”而已。
尽管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招致了诸多的诘难和批评,但是其理论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第一,公共理性观念并不满足于建构一整套的正义原则来作为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设计出程序性的探究指南来解决法律的可接受性问题;第二,在法律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现代世界,通过公共理性观念来证明法律合法性的主张,进一步拓展了合法性理论研究的空间;第三,它也提示我们在祛魅的时代,规范性的求得唯有诉诸人的理性,而对理性精神的弘扬,更是对人的平等尊严的维护。
综合而言,在现代性语境中,作为社会整合最基本手段的法律需要人们对其强制力的接受和服从,舍却法律的现代社会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对法律事实上的接受并不能自证法律的可接受性。法律合法性公共理性式的探究,旨在将法律的可接受性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其本质在于,“人的平等问题,是同样的人共同生活在共同的世界上,共同面对和解决公共的问题”[10]。事实上,法律在内容上体现着人们社会生活样态,在结构上它是为了调整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而选择的规范,如此,法律应当成为共同体当中所有成员的共同事业。一言以蔽之,罗尔斯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法律合法性理论唯有在重视公共性的资源时才能有广阔的延伸空间。
[1] 熊伟.现代法律合法性理论研究的三个视角——基于理想类型方法的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6(2):83-89.
[2] Stefanie Dierckxsens. Legitim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C]//Erik Wouter Devroe and Bert Keirsbilck. Facing the Limits of the Law. 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2009:194.
[3]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 姚大志.公共理性与合法性——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50(2):25-30.
[5] 林火旺.公共理性的功能及其限制[C]∥应奇,张培伦.厚薄之间的政治概念(卷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55.
[6] 熊伟.面向法律正当性基础重构的公共理性[J].河南社会科学,2008,6(98):49-52.
[7] 罗纳德·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义[M].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75.
[8] 史蒂文·马西多.公共理性的国内语境与全球视野:合法性、多样性与政治共同体[J].李石,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1):28-35.
[9] 大卫·高希尔.公共理性[C]∥谭安奎.公共理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45.
[10] 郭湛,王维国.公共性的样态与内涵[J].哲学研究,2009,43(8):3-7.
(责任编辑:沈建新)
Rawls’ Legitimacy of Modern Law
XIONG Wei
(1.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Jiangsu 224051,China2. Center for Chinese Law,HongKong University,HongKong, China)
In the era of disenchantment, the legitimacy of modern law has lost its way to resort to any kind of comprehensive theory. It has to be replaced by the public reason accepted by all citizens.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the legitimacy of modern law through the public reason, Rawls distinguishes two aspects of legitimacy of law: specific legal norms and the constitutio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 is regarded as the core of the theory of legitimacy. The proof of the public reason to the constitutional fundament has laid a complete set of principal for the basic justice and provided a procedural guidance as well.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has not only offered a proof of the legitimacy for the entire legal order in theory, but also put forward some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the judicial practice. The essence of public reason is to promote equality of human value. It is?the stick to this value that makes the law be more acceptable.
Rawls; legitimacy of law; public reason
2014-08-26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011SJD820023);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苏教师[2012]39号)
熊伟(1976-),男,江苏盐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D911
A
1671-5322(2014)04-0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