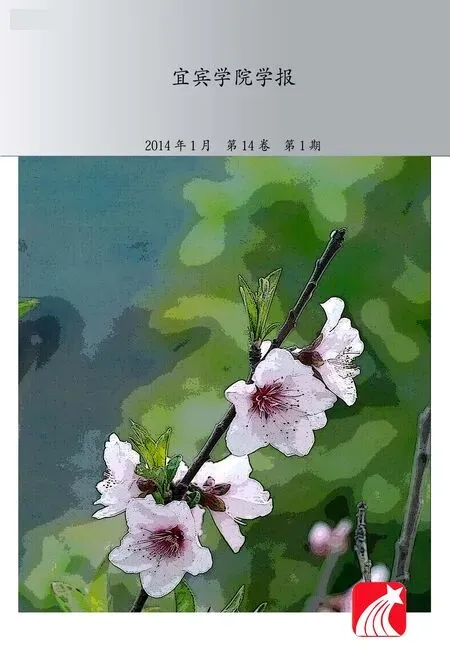茨维塔耶娃早期诗歌中的死亡主题
2014-03-12司俊琴
司俊琴,周 晶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俄罗斯著名女诗人,被誉为“20世纪的第一诗人”。爱情、死亡、生命与艺术是茨维塔耶娃诗歌创作的四个主要母题。在她49年的生命历程中,茨维塔耶娃不仅创作了大量回肠荡气的爱情诗篇,而且写过很多关于死亡的动人哀歌。一般人对死亡都怀着消极的态度,然而正是死亡放大了生命的意义,因此对死亡的激情也是对永恒的激情。从茨维塔耶娃诗歌的死亡主题中,我们感受到她对生命真正的爱与珍视。在她歌咏死亡的诗篇中,震撼我们的是亘古不变的爱的激情。茨维塔耶娃早期的诗集《黄昏纪念册》(1910年)、《神灯》(1912年)和《青春诗集》(1913~1914),都凝结着诗人对死亡的深入思考。
一 对死亡的渴望
《黄昏纪念册》收入了诗人15至17岁时写的诗,这些诗歌深受著名诗人沃洛申与古米廖夫的好评。其中许多诗篇是献给已故亲人的,诗人在诗歌中试图弄清彼岸世界的本质及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诗人早逝的母亲的形象贯穿于整部诗歌中。诗人写道:“妈妈,你给自己的孩子留下的只是忧愁”,诗人试图通过梦境与母亲交流:“小姑娘梦见了古老的菩提树与已故的面色苍白的妈妈”①。 诗人所描绘的彼岸世界对于在“此岸”受苦的人来说是绝好的归宿,如“一天又结束了,我已无力活下去。/……/不要忧伤!死亡对她来说更轻松:/死亡是对妇女最好的馈赠”。其中许多诗歌都是献给天才的艺术家玛利亚·巴士凯尔采娃的,其作品与创作个性给茨维塔耶娃很大影响。诗人在十四行诗《会面》中写道:“在梦的幽谷,我多次遇见这位站在漆黑窗口的姑娘/——这是俗世中天堂的幻影。/可她为什么如此忧伤?/这透明的身影在寻找什么?/或许,天堂里也没有幸福……”
茨维塔耶娃早期的一些诗歌表达了她对自杀的思考和不可理解:
弃绝生命者是否正确?
死后面对的是否是永远的黑暗?
只有后人才能知道,
而我们无法得知。
茨维塔耶娃早期的诗歌死亡充满了光明,在阴阳两界之间没有冲突,死亡只是阳世生命合乎规律的终结。“在写死亡的同时,她常常抒发对生、对爱的渴望,并借助与前人对话的机会,了解彼岸世界。她敢向死神挑战,更敢诅咒它。受罗斯托夫、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她认为,彼岸世界比此岸世界更完美,人只有在灵魂离开肉体时,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1]但是从茨维塔耶娃所钟爱的早逝的主人公身上逐渐显示出她对死亡的对抗性:诗歌《叛乱》中体现出诗人对抗死亡的观点日趋成熟,《纪念妮娜》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与此岸生活处于不和谐状态。尽管生者面对死亡时有消除痛苦的解脱感,但死亡还是作为生的对立者而出现:
死亡——这只是个故事的终结,
棺材里才有真正的快乐。
……
我们的快乐是多么有限,
心灵,被痛苦所吞噬!
这一主题同样出现在《谢廖莎》这首诗中,该诗是献给女友夭折的儿子谢廖莎的。阳世生活的忧伤、荒唐与阴间的快乐、幸福、宁静相对照:“你走了……谢廖莎,/你是多聪明的孩子!/在这个世上,只有忧愁。/在上帝那儿不会有忧愁!”
对年轻的茨维塔耶娃来说,死亡是神秘的,她竭力探究死亡的本质。她在自己17岁生日那天,写了著名的《祈祷》一诗,宣布了对死亡的渴望:
啊,请让我马上去死,
整个生命就像我的一本书。
……
你给过我童年,更给过我童话,
请再赐我死亡,——就在十七岁!
但让人难以捉摸的是:为什么如此热爱生活的女主人公会呼唤死亡?为什么在度过神话般的童年之后,她像等待奇迹一样等待死亡?俄罗斯评论家认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优美的童年画卷未必不是被理想化了的,在她眼里,死亡集狂热、神秘、冒险和自由于一身……死亡的这种二律背反的语义,源于贯穿她的整个童年的恐惧与忧伤的记忆。她之所以向往死亡,是因为她幻想在另一个世界能与母亲相见。”[2]因此我们认为,女主人公渴望死亡,就是幻想把昨天变成神话,也就是让自己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变成永恒。
诗歌《在天国》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并在勃留索夫所组织的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这是有“成群的天使”与美妙音乐的天堂,也就是一个充满和谐与平静的世界,但女主人公仍然无法弃绝尘世的情感,她意识到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并公开与之相对抗:
独处于纯洁严肃的少女之中,
我含笑告别天国的幻影,
尘俗而外来的我,
将永远唱着尘世的旋律。
“尘世”与“天国”的主题贯穿在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这是她认为两个世界不和谐、不完善的注解。她认为生死两界不相容表现在死亡破坏了生命,因为生命是“闪光的双眼”,抒情主人公则是“玫瑰色的”、“火焰般的”;而死亡则是“暗淡的时刻”,“嘈杂的海洋”,“清晨的迷雾”。生命的火焰“消失”在了死亡的“黑暗”之中。一方面,死亡的恐惧加剧了彼岸世界的神秘性与不可知性;另一方面,主人公与尘世的不相容性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与死亡的对抗关系:
在尘世没有遇到王子的公主,
给我们只留下了鲜花与秘密,
我们的世界还比不上
你那长着纤细指甲的小指头!
在讨论茨维塔耶娃作品中关于死亡的主题时,俄罗斯批评家斯特努维认为:“茨维塔耶娃少年时代对自己与别人的死亡持认同的态度,但是在1912年左右,她突然一反而为完全的不接受。从那时起,她不再认为死亡是‘解开所有链条的’钥匙,而是生命的消失”[3]。 在论证这个论题时,用如下的逻辑来推论:面对死亡感到恐惧,因此,不相信永生不死,这本身证明了不相信上帝。在我们看来,清晰地界定对待死亡态度的转变是复杂的,因为她对死亡的不接受是逐渐表现出来的,潜在于她早期的作品中。
二 对死亡的抗拒
茨维塔耶娃逐渐地意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永远地死去》、《受谴责的心》),这导致了无法忍受的痛苦(《痛得发抖》)感受的产生。如果说以前诗人思考的是别人的死亡,那么现在诗人开始把它放在自己身上来设身处地地加以思考(《理解一切并为所有人受难》)。这些诗歌的基本主题为——死亡不是让主人公成为永恒,而是空虚与忘却的(《人们忘了》、《融化的雪与蜡烛》):
藏起一切,为了让人们忘却,
就像忘记融化的雪和蜡烛。
将来仅化作一杯尘土
埋在坟头十字架下?我不愿意!
每个瞬间,因疼痛而战栗,
我再次面临一个问题:
永远死去!命中是否注定
让我去理解这一切?
茨维塔耶娃的诗集《青春诗集》(1913~1914)中收集了诗人刚出嫁时的诗,当时的她幸福、自信,并获得了别人的认同。1913年,她的个人生活幸福、顺利(出嫁的第二年,生了女儿阿利娅),她对死亡的理解也进入了另一个层次。死亡与生机勃勃、充满乐观生命力的她格格不入:
听着:我不同意!
这是陷阱!
不要把我埋进土里,
不要。
同年五月,诗人写下了《你走来,步态和我相似……》这首诗:
你走来,步态和我相似,
低垂着眼帘。
在东北方言词汇系统当中,重叠式构词方式极具优势。和普通话类似,东北方言词汇的重叠式主要以动词和形容词为主。
我也曾低垂着双眸!
过路人,请在这儿停一停!
你先采上一束五虎草,
和罂粟花,再把碑文读一读:
我叫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我曾活过几多岁数。
……
你先摘一些野草的茎,
然后再采上一些野果,
墓地上长的这种草莓,
既大又甜,最为可口。
这种来自“地下”的呼声令人难以忘怀。过路人与抒情主人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她曾经“存在”,过路人对抒情主人公的认识要通过联系两个世界的特殊客体——罂粟花、五虎草及碑文——来认识。这两种花实际上是亲本植物,它们在神话中同梦与死亡紧密相连,作为死亡之花象征着彼岸世界的宁静。在诗人心目中,过路人与自己在精神上息息相通,因此过路人的形象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草莓是联系两个世界的又一个客体:从词源上讲它是由“土地”构成的,同时表明既是居住地,又是埋葬地。尤其是“墓地里的草莓”吸足了墓地中始祖的营养之后,变得又大又甜。借助于植物中介,活人与死者进行交流与对话,从而使阴阳两界互相渗透,这种渗透实际上表现为诗人尘世感情的完全消失与彻底平静。
有研究者指出,这个诗集中流露出诗人的自我中心主义:“既放肆,又天真感人。”[4]在谈到玛利亚·巴士凯尔采娃对《青春诗集》的影响时,评论家安·萨基扬茨指出:“同《黄昏纪念册》与《神灯》相比,《青春诗集》中的诗歌展现出女主人公注定的特殊使命感”[5]。
终有一天,我会从地球上消失,
所有歌唱过、斗争过、发过光、挣扎过的
这一切,都会凝滞:
我的绿色的双眼,温柔的声音和金色的头发。
面对“消失”,主人公还是不能容忍这个事实,她不止一次地要求不要把她遗忘:
听着,请再爱我一次
因为,我将要死去。
在茨维塔耶娃的创作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因素,充满冲突与对抗:她一方面拒抗死亡,同时,又在不断地呼唤死亡。诗歌中,要求被记住及被爱的想法逐渐被生命终结的预感所代替,但是在《致一百年以后的你》(1919年)中,诗人坚信,百年过后,她虽死犹生,因为她的读者将会去追寻她的足迹。
1913年,诗人在最著名的一首诗《献给我早期的诗》里,表达了青春与死亡平等的观点,由此确立了她早期及全部创作的基本主题。1914年诗人给罗扎诺夫的信中写道:“请听着,我要告诉您一件事,大概对您来说这是件可怕的事:我完全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及阴间生活。”从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无助及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无能为力导致了祈祷、顺从及对生命疯狂的爱。该年十月在纪念丈夫谢尔盖·艾伏隆的献词中她写道:“我嘲笑阴间的黑暗!我不相信死亡!我从火车站接你回家。”爱终究战胜了死亡。
1915年诗人在诗歌中开始广泛讨论死亡这个主题。这时她不再把生与死对立起来,以对死亡的不可避免地确认来代替对死亡的反叛。诗人这时的诗歌失去了年轻时的极端,诗歌的基调显得平和多了。
结语
总之,年轻时的茨维塔耶娃对死亡思考了很多,这个主题成了她早期创作及全部创作的中心母题。从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待死亡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最初由思念引发的对死亡的渴望:无法追回的过去在她的诗歌中表现为对逝去的亲人的追忆及浓厚的思乡之情。过去的时光变成了她永远渴望然而无法实现的对象,她希望死亡使童年的幸福生活凝固而成为永恒。接着她产生了由对生命的热爱而引发的对死亡的抗拒:特别是在体验了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如此渴望活着,从而延续了“爱比死亡更有力”这一主题。她对死亡的不接受多半是由于热爱生活及对生命无法割舍的爱而决定的。最后是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而以平和的态度对待死亡:死亡作为尘世苦难的摆脱,对尘世痛苦的忘却及尘世情感的彻底平静。
斯特鲁维指出:“宗教的东西只有用宗教才能认识,茨维塔耶娃试图用情感来认识上帝,因此她的碰壁是在所难免的。”[6]套用斯特鲁维的话,可以说茨维塔耶娃借助于情感来认识死亡,因此她很担心自己作为生命与尘世情感的独特化身将来会被忽视、被遗忘。但是精神的产物——诗歌——会代替肉体,因为它是诗人思想、情感与经验的结晶,它作为精神财富会被保留下来并与未来的读者见面:“终有一天,我的诗会像贵重的红酒一样被世人欣赏。”
注释:
①Каверин В. Собр. Соч В 8 т. [M]. М.:Худож. лит. ,1982.(本文所引用的诗歌全出自该诗集,由文章作者翻译)
参考文献:
[1] 荣洁.走近茨维塔耶娃[J].俄罗斯文艺,2001(2):22.
[2] Флоря А.В. Заметки о некотор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художест венного мироощущения и лингвоэстетики ранних стихот ворений М.И.Цветаевой[C]//Борисоглебье Марины Цветаевой.Шестая цветаев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о-тематиче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борник докладов. М.:Дом-музей Марины Цветаевой,1999:185.
[3] Струве Н.А. Трагическое неверие[J].Вестник РХД. 1981(135):167.
[4] Коркина Е.Б. Поэтический мир Марины Цветаевой[C]// Цветаева М.И.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Л.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90:10.
[5] Саакянц А.А. 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M]. M. :Эллис Лак,1997:43.
[6] Струве Н.А. Трагическое неверие[J]. Вестник РХД,1981(13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