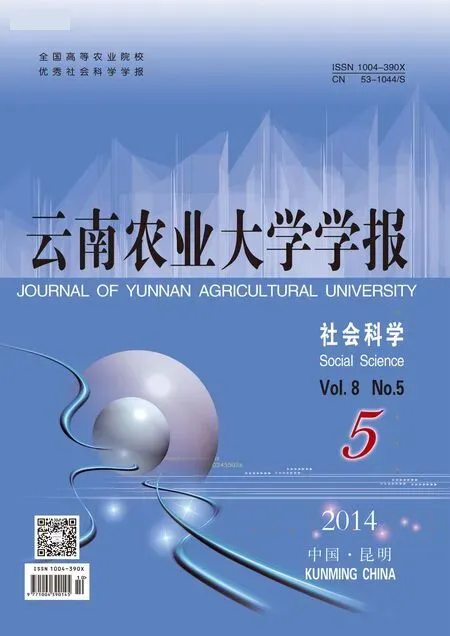留住传统民族村寨守护都市记忆
——以贵阳城市建设为例
2014-03-09王炳忠吴晓梅
王炳忠, 吴晓梅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都市里的民族村寨记忆
贵州省会贵阳已经建设成“高速环线”有效通达东西南北的西南大都市,然而,在环线内,不难发现有很多苗族村寨和布依族村寨。很显然,远古的贵阳曾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如今,在贵阳城中心区的云岩区黔灵镇三桥村还保存着二桥苗寨,地处黔灵山公园后门,与黔灵湖相连,生态环境良好。据了解,这是贵阳城市中心仅存的一个苗族聚居村落,居住着以唐、鲁、朱、王等姓氏为主的227户467位苗族村民,有26.7多hm2土地。二桥苗寨历史文化悠久,村民只知道先人在远古时代就定居在这里。这些村民还能说苗话,节日期间还穿苗装,会酿制苗家特别喜好饮用的米酒,会唱苗族古歌,依然传承着刺绣、蜡染、传统乐器制作等苗族民间技艺。保留着农历“二月十五”、“三月三”、“四月八”等传统节日,盛大闻名的“圣泉三月三”活动场址就在二桥。
二桥苗寨是在众多贵阳苗族村寨中唯一保存下来的,是贵阳都市的历史见证。贵阳历来都有苗族居住,村寨不少,文献有零星记载,人们保存着难以淡忘的记忆。“现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原是一个苗族大寨,名曰白岩脚,清代光绪年间,住有七、八十户,全是苗族。民国初年,当局要在这里开办畜牧场,将苗族强行迁走,只剩二、三十户。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当局在这里修建‘贵州日报’社的房舍,不久毁于大火,改办农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杨森任贵州省主席,把现今省政府大礼堂所在的大片土地辟为跑马场,供他跑马娱乐。”[1]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贵阳工作的很多专家学者见证了苗寨在贵阳的存在,并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研究贵州历史文化取得成果颇多的贵州大学历史系苗族教授田玉隆进行了记忆性的记载:民国年间,省政府片区辟为“贵州农业试验场”,此区苗族被迁走(详见《贵州农业改进所》档案)。建国初,田玉隆作过见证性的关注调查:贵阳汽车客站(延安西路的原贵阳客车站)到黔灵公园,到省政府一带,有苗族连片居住。1954—1958年,建贵阳汽车客站,贵阳铁路局、贵州省地质局等地带的苗族被迁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贵阳火车站片区,有许多连片居住的苗族,每当春耕、夏耘和秋收,苗寨周围苗歌此起彼伏,热闹非凡。1958年贵阳建火车站,这一带的苗族被迁走[2]。经历沧桑历史,解放初期,苗族还坚守在祖国的西南小省城贵阳,过着面土背天的欢乐耕耘生活,还保存着群居的苗族村寨。
二、从村寨到都市的贵阳
综上所述,贵阳曾经有许多村寨,而且是苗寨。苗语称贵阳为“格桑”(kai31tshɑ43)。苗语的“格”对应于汉语的“场”,指商贸集市。“桑”是地名,代指贵阳。苗语中用“格”来称谓的,大多为苗族的社会活动中心,是交流交往的重要场所。如“格巴”( kai31npɑ43)指花溪高坡;“格羊白”(kai31ɑ55p31)指青岩;“格哈阿洛”(kai31hɑ33qɑ24lo31),习惯简称为“格洛”,指花溪;“格壤后”(kai31rɑ55hou13)指惠水。除此之外,在苗语中还以“格”来称谓冠名的,是起到娱乐祭祀等集中展示苗族文化功用的斗牛场。如,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甲定斗牛场叫“格党阿定”(kai31nɑ31qɑ24ti24),龙里县湾潭河镇果里斗牛场叫“格壤莫肚”(kai31rɑ55mhon33tlu13),惠水县大坝乡批弓狗场叫“格旦迈欧”(kai31tl13mplhai33qou33),等等。由此可见,在苗族古代社会里,贵阳已经由村寨发展成为“格”,即商贸交易市场、人际交流中心、娱乐活动场所。
苗语常把龙里县城与贵阳并列称为“鲁立格桑”,把花溪与贵阳并列称“格洛格桑”,把青岩与贵阳并列称为“格羊格桑”。史书记载:“贵阳府为省会首郡。禹贡梁州荒裔。汉为牂牁郡地。”[3]“隋开皇初置牂州,大业初改为牂柯郡。唐初复置牂州,隶黔州都督府……”[3]“牂牁”与“牂州”之“牂”与“格桑”之“桑”,语音都与苗语里的tshɑ43相近,都是对贵阳的称谓。这不是历史记载中的巧合,完全可能,在历史上,人们把苗语的kai31tshɑ43之tshɑ43记载为“牂”;把kai31tshɑ43之“kai31”记为“牁”。现当代以来,学者们从苗语世界中去研究贵阳及范围内的苗族历史文化时,在田野调查中把苗语的tshɑ43谐音记为“桑”。“格桑”是苗语中名为“桑”的市场(“格”)。汉语的语法顺序与苗语不同,在汉语中的“牂牁”,是名为“牂”的市场(“牁”),“牁”对应于苗语的“格”,指市场,“牁”与“格”都是谐音记录。如今,在广大农村,还有“狗场”、“猫场”、“羊场”、“猪场”等称谓,而在苗语中,对这些市场的语音表述顺序则是“场狗”、“场猫”、“场羊”、“场猪”等。很显然,我们可以看到“牂牁”与“格桑”的语音关系和语序关系之密切。“格桑”的意义给我们作了交代,贵阳已经从村寨变成了市场,而且与周边的龙里、花溪、青岩同时只是市场而已,是苗族人交往、交流、交易的场所。贵阳城就是从这样的场所发展为城的。以致成为兵争之地,随后成为省之中心:省城。
关于贵州省城贵阳,在宋代时是“八番”的管辖之地。元代时改“八番”与“鬼国”为“顺元路”。史书有记载:“八番”人改称“苗人”,“顺元多苗人”。元明至清初,贵阳地区的居住着的“苗人”不是泛称,而是指今天苗族的先民[2]。以上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证,那就是贵阳已经从苗族社会的集贸市场、交流中心发展为国家体制行政区划下兵家争战的城池。据清顺康人许缯赞《滇纪程摘钞》载:“贵州省城……(贵阳)故府城西一带称老苗城”[1]。贵阳被称“老苗城”,这样的称谓前后约计400年历史,并得到官方的认可,这是官方沿袭历史,又感、观居民服饰异彩、语言交流相殊而得“老苗城”。民国末期,任可澄、杨恩元编《贵州通志》(1948年版)仍然把贵阳称为“老苗城”。今天,贵阳被称为“老苗城”,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记忆,人们容易记起的是“多彩贵州”的“爽爽”省会。贵阳城市在迅速扩建,成为西南地区很有发展潜力的大都市。
三、“四月八”活态记载贵阳历史
一座城市的重要历史记忆,可以说是这座城市的重要文化名片,约定俗成的贵阳苗族“四月八”,记载着贵阳的历史,也留给贵阳一个不可多得的节日和一张表达着文化厚重的名片。“格桑”(贵阳)不仅是古代苗族世界里的一个集贸市场、交流中心,还是苗族有历史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王城。英雄史诗《亚鲁王》作为苗族历史的重要载体,记载“格桑”(贵阳)是最大的城市。史诗记载苗族先民开辟贵阳,并在那里勤劳生产、幸福生活、吹笙欢舞。智慧聪明的亚鲁在贵阳被尊为王。传说苗族先民在贵阳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后来外族前来攻占,亚鲁率领苗族先民顽强抵抗,不幸于农历四月初八战死,被埋葬古苗语称此地为“嘉西坝”[1]的阳贵喷水池。铭记英雄,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亚鲁的祭日,苗族人总是聚集到贵阳市喷水池吹芦笙祭奠。苗族传统节日“四月八”又叫“亚鲁节”。
苗族纪念英雄亚鲁的“四月八”习俗经历上千年,经久不忘。“四月八”记载着一场战争,也记载着贵阳这座城市的历史。贵阳及其周边的苗族一直惦记着“四月八”节日,没有文字记载,他们以唱诵的形式记忆历史,成为久唱不衰的史诗,印入心中,成为人生仪式必须念诵的“经典”。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来临,贵阳市周边的苗族,自觉地按照传统习惯,上山采摘一种特殊树叶取汁浸米,把糯米蒸熟成黑色的“乌米饭”。四月初八,吃过早饭后,苗族男女青年身着民族盛装,成群结队赶赴贵阳喷水池吹芦笙,或吹笛子,或吹箫筒,围圈起舞,纪念在他们心目中永远的英雄亚鲁王。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叶圣陶途经贵阳,恰好遇上“四月八”盛况,提笔记下所见所闻作了有力见证:“其女子或系多褶之裙,佩用织花之带;或腰围织物,如日本女子”;“其男子服装与汉人无殊,往往三五成群,来回路上”。“看热闹之人,拥挤不堪”[4]。
四、在城市化建设中留住根性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每天平均有几十个传统村落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中消失,与之相应的大量各民族农民群体在“消亡”——零碎分散杂居。冯骥才先生说:“2000年以来,我国在十几年间消失了几十万个自然村,很多都湮没于城镇化的浪潮中。”“我们民族的文化痕迹,比如节日、民俗、音乐、舞蹈、美术、曲艺、杂技等等,大部分都活态地保存在各地的村落里。”一个传统村落在现代化机械下是很容易推翻,也是也很容易新建的,但是,要重建一个村寨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道理就像“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一样。
“非遗的载体——也就是中华民族根性文化的载体是一个个村落。它不仅有精美和独特的建筑与大量珍贵的物质遗产,还有那一方水土独自创造的口头的和无形的文化遗存,如民间的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手艺等,还有种种独特的民俗。它们最直接地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民间情感、民族气质及其文化的多样性”[5]。然而,城市化又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生活的必然要求,全国如此,贵阳也如此。但是,历史文化的消失也是很沉痛的,无法复制的根本性要求我们在城市化建设中,留住一些民族村寨,守护文化,记载历史。这是完全可能的,对历史负责,也对人类及文化负责。在贵阳城市高速环线以内,据统计,有近百个苗族、布依族村寨;在环线以外10 km内有近千个民族村寨。可见在贵阳城市建设中,在期中心区保留两三个苗族、布依族村寨,对守住贵阳历史的民族性具有长远的意义。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各民族农民变成了城市新民工,以城市新人去融入城市生产、生活和发展。从农民到城市新人的主体转换中,他们既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有田土的农民,也还没有真正地融入现实意义中的城市人,徘徊在两种人之间,他们有向往也有困惑,他们寻求新的生活,也回望过去的“生活”。过去的生活是一个广泛性的生活,包括宗教、风俗、习惯、信仰、伦理、道德等根深蒂固的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在文化生活层面上的融入面临着两难的境地,要么丢弃自己的民族文化,完全融入主流文化或现代文化中,实现与城市社会的全面融合;要么,固守自己的民族文化,与城市文化“隔绝”,而又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心理上一方面希望与城市真正融合在一起,获得城市身份的认同,而另一方面也害怕或是担心自己无法与城市融为一体,从而导致他们的潜意识里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疑虑[6]。还有,婚丧嫁娶按照传统仪式进行还是按照城市方式进行,尤其是丧葬仪式经过的那么一套繁复的通过仪式,如果简化了,死者亡灵能够通关到达祖灵世界吗?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留住城市历史,或是留住城市文化,贵阳在推进大都市建设进程中,应该在城市里保留一些或者两三个传统的苗族、布依族村落。同时,也让离去家园的人们找到一条回归文化的路,有一个回望家园的地方。
可以把保留下来的这两三个苗族、布依族传统村落打造成为升级版的文化传承载体,树立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在融入城市化建设中相统筹相结合的典型,树立创新型的文化保护传承样板,对全省建设100个示范小城镇、500个特色民族文化村寨和 1 000 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特别是贵阳市城市中心区二桥苗寨,可以打造成为都市特色苗族风情古村落,暨守住贵阳曾经是苗寨的历史,保存为苗族“四月八”传统节日的活动场,还为贵阳留住一张文化名片。在城市建设中留住民族传统村落,也为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增加新的亮点,从而提升贵阳市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生产力,增强贵州原生态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
[参考文献]
[1]贵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苗族四月八[M].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136.
[2]王炳忠.亚鲁王城——“格桑”初探[J].贵州文史丛刊,2014(1):74-80.
[3]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21.
[4]冯骥才:城镇化浪潮中如何保护古村落[N].大众日报,2014-03-03.
[5]曹津生,高丽. 专访冯骥才:古村落保护工作迫在眉睫[EB/OL].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tianjin/2011-09-09/content_3744494.html
[6]刘吉昌,武娜,刘勇.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研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