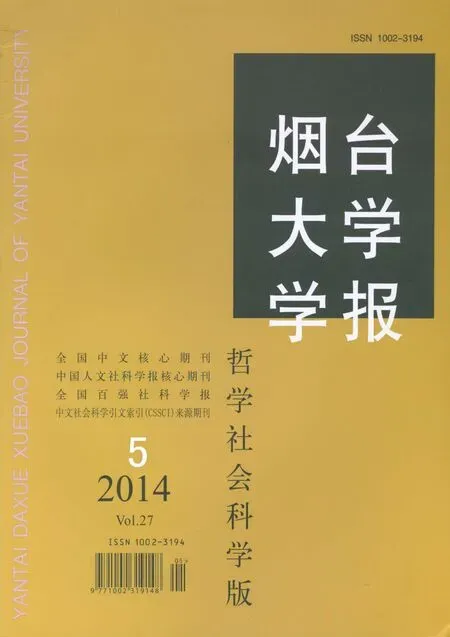游牧行国的内涵及其特点
——多民族国家视角下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研究
2014-03-06李大龙
李大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北京 100005)
一
民国时期的学者胡焕庸以黑龙江瑷珲(今黑河)、云南腾冲为两极由东北向西南画出了一条线,将中华大地分为东西两半区域,并指出:“此东南、西北两人口区域之分垒,与全国种族之分布,亦殊相合,东南半壁为纯粹汉人之世界,惟西南山地,有少数异族杂居其间;西北半壁则汉人殊少,除‘甘肃孔道’及新疆境内有少数汉人以外,其余均为满蒙回藏各族之领域,此区以内,面积虽广,人口则少,境内各地,盖大部为不毛之沙漠,与积雪之寒漠,仅极少数之水草地,可供畜牧或耕种之用。”①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此即是人口地理学上著名的胡焕庸线。这条线大体上也是中华大地上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分界线,所谓东南半壁“纯粹汉人之世界”基本是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族群,西北半壁生活的族群则以牧业尤其是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
在人类历史上,农耕和游牧曾经是人类社会两种主要的但形式既有联系又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世界历史上具有不同特点的众多人类文明。关于游牧和农耕的分离时间,尽管学者们还有不同的认识,但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长期左右着人类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游牧族群*我国学界一般习惯用“民族”来称呼这些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但建国后“民族”的称呼被赋予了很多非学术的因素,笔者以为用“政治体”或“族群”称呼它们似乎更恰当,而相比较“族群”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有学者使用,故笔者虽然认为“政治体”更准确,但有时为了方便理解会使用“族群”。和农耕族群长期持续不断的冲突和融合,一直在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近现代之前世界文明格局演变、族群分化、聚合乃至融合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即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我国史书虽然很早就依据生产生活方式划分不同的人群,但用现代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探索则以西方的学者为先。相关研究情况的介绍,可参见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一定程度上能够概括分别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生业的两大族群。司马迁在其《史记》中用“行国”和“城国”来区分两种具有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行国”一词用于指称草原帝国相对形象准确,指出了草原游牧政权的构成特点,但“城国”的指称范围相对狭小了些,并没有包括中原地区。中原地区政权的构成特点不仅有“城国”,在其外围还有“藩属”,共同构成了一个“政治体”,古人称为“藩属”。“藩属”一词虽然晚在清代才开始出现,但“藩”和“属”却一直是用来指称中原王朝的边疆统治体制。由此,笔者认为用“游牧行国体制”和“王朝藩属”可以概括推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生业的两大族群“政治体”的特点。
贾敬颜先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个将“行国”列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贾敬颜先生在其所著《释“行国”——游牧国家的一些特征》*贾敬颜:《释“行国”——游牧国家的一些特征》,《历史教学》1980年第1期。中认为用“行国随蓄”可以“概括了他们的一切”,并进而对“行国”主要经济方式、结构特点等做了概要的探讨,最后归结为六点:“第一,行国与城国对立,它是经济上完全不同于农业生产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第二,行国由于生活上、生产上特殊原因所造成的行政上、军事上的独特风格和方式,必然为城国所不具备,或者根本无法办到;有它进步的一面和成功的一面,有它独到的优越性。第三,行国政治上不稳定,往往是经济上不稳定的反映。游牧民族骤兴骤衰,暴起暴落,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和生产力的影响,有它本身难以克服的弱点。第四,行国的民族溶化以及它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不像城国农业民族那样显著,那样持续,那样原委分明。因为‘人’和‘地’不那么结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深远。第五,行国与城国相结合,不但长治久安,而且互相补充,变不足为有余。牧业和农业、手工业、商业,一方面有矛盾,一方面又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彼此之间是一个完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第六,一点多余的题外话。以古鉴今,以今律古。必须注意农牧业结合,农、牧、林业互相补充,必须把饲养业与种植业并重起来。坚决克服‘牧业落后论’,反对滥开荒,须知牧区是无所谓荒地的。”由此看,贾先生对“行国”的探讨也是将其置于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互动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着眼点和笔者从多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看两大族群的互动略有差异,而且笔者也并未完全认同其所有上述观点,但其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为本文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以下,笔者试图对游牧行国的内涵、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二
“行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此贾敬颜先生已经指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多处使用到“行国”一词: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闲,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对于司马迁所用“行国”一词的具体含义,中华书局本《史记》引《集解》曰:“徐广曰:‘不土著。’”贾敬颜先生据此认为“‘不土著’的行国与‘土著耕田’、‘有城屋’、‘有市民商贾’的安息、条支、大夏、身毒这些城国绝对不相同,即是说,他们都是以畜牧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贾敬颜:《释“行国”——游牧国家的一些特征》,《历史教学》1980年第1期。贾先生的这一认识十分准确,从《史记》的具体使用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所谓“行国”是相对于“城国”而提出的。司马迁的着眼点是西域众多族群或政权在生产、生活方面的明显差异,不过从上述记载中有“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的表述,可知司马迁虽然没有明确说匈奴也属于“行国”,但其确定是否是“行国”的标准则是依据匈奴的“风俗”,即所谓“与匈奴同俗”。
对于匈奴的习俗,《史记·匈奴列传》有如下概要记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从这一记载分析,所谓“行”应该是指“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而之所以称其为“行国”则因为匈奴虽然“逐水草迁徙”但却是以“政治体”的形式存在于草原之上的。由上述记述,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司马迁认定“行国”的要素做如下归纳:
首先应该是“国”,即是有一定规模的拥有“君王”的“政治体”。“行国”最典型的特征是“政治体”也即政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放牧的需要几“落”乃至十几“落”游牧民聚居在一起似乎构不成“行国”。从《史记》中司马迁对“行国”的使用看,乌孙、大月氏、康居、奄蔡等规模从“控弦者数万”到“一二十万”差别很大,但都属于“行国”。而从《汉书》对“行国”的使用看,其《西域传》有:“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东北到都护治所五千四十六里,东与皮山、西南与乌秅、北与莎车、西与蒲犁接。蒲犁(反)[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2-3883页。如此小的西夜国也被称为“行国”,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其已经是一个“政治体”,有“王”为首的管理体系。
其次是以“行”为生存特征,即以游牧为生业,“逐水草迁徙”。司马迁《史记》中所指出的几个“行国”都是或“随畜”或“随畜迁徙”,而对匈奴习俗的解释中更加突出了这一点,并特别强调“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以示与农耕族群之间的差别,不过从“然亦各有分地”以及结合有“王治”来分析,其“行”也有一定的范围,而且内部包括游牧民、草场似乎也有了明确的划分。
再次是拥有军队,即“控弦者”,或称为“甲骑”、“胜兵”。上引《史记》的记载已经清晰地表明了“行国”的这一要素,不过“控弦者”或“甲骑”似乎更能显示其军队的特征,即“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这是一支游牧生活培养出来的军队,弓箭、马匹、甲是其主要的装备。
最后是有独特的风俗和价值体系。由于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行国”也有着与农耕族群不同的习俗和文化价值体系。司马迁虽然没有明确描述乌孙、康居等“行国”的习俗,但指出其与匈奴同俗,而对匈奴习俗和价值体系的记述则如上引,不仅包括了语言文字、衣着等生活习俗,而更重要的是归纳了其社会价值体系,即所谓“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些构成了“行国”社会价值体系的鲜明特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特征的归纳是通过和农耕族群社会的对比得出的结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农耕族群处理与游牧族群关系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它也体现了农耕族群对游牧族群价值体系的一般认识,从其后史书的大量记载看,这些认识不仅成为了农耕族群观的重要内容,而且也由此影响到了农耕“政治体”的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
三
司马迁对“行国”一词的使用,从草原地区众多游牧行国的兴废历史看,只是揭示了游牧行国建立初期,也即行国形成初期凝聚核心(或称之为“行国内核”)形成后的一些特征,而对于强盛起来的行国,如此简单的概述是难以让人了解其全貌的。实际上,随着行国凝聚内核的完成,为了保护其利益,它会将更多的其他“行国”或“半行国”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进而构建起更大规模的游牧行国。以匈奴为例,“匈奴”之称虽然早已出现,而且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也将其形成历史追溯到夏代,但其核心族群的凝聚,由史书记载看,一直到秦汉时期才完成,头曼单于向冒顿单于过度应该是其标志。核心族群凝聚完成后,匈奴游牧行国开始了对草原地区其他族群的整合,在冒顿时期就已经构建起了以单于为中心、以匈奴族群为核心,南起河套,东至兴安岭,西包括西域在内的庞大游牧行国。对于匈奴构建起来的以匈奴族群为核心的“政治体”,我国史书多以“匈奴”称之,而勒内·格鲁塞和狄宇宙都称之为“匈奴帝国”,*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第43-68页;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第195页。美国学者托马斯·巴费尔德则称之为“匈奴帝国联盟”。*托马斯·巴费尔德著,邱克摘译:《匈奴帝国联盟:其社会组织与对外交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笔者认为不管是“匈奴”,还是 “帝国”、“帝国联盟”似乎都没有充分反映出其特点。从草原地区族群发展的历史来看,匈奴“政治体”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草原地区出现的这些“政治体”虽然具有明显差异,共同点也很多,冠以核心族群的名称、用“游牧行国”称呼这些“政治体”似乎更为恰当,更能反映其主要特征。
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将斯基泰人、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喀喇契丹、花剌子模以及蒙古各部建立的众多“政治体”列为阐述的对象,称为“草原帝国”。应该说,这些“政治体”从史书的记载看多有“游牧行国”的特征,但由于笔者考察的主旨是“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上述这些“政治体”有些和“王朝藩属”之间并没有发生密切的互动关系,或是作为一些大的“政治体”的组成部分而和“王朝藩属”发生互动关系,因而笔者只将在北部草原地区建立过相对完善的“行国体制”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以及蒙古列为重点考察的对象。从秦汉至元朝,以游牧族群为核心构筑起相对完善的“游牧行国”体制的这些“政治体”,从史书的记载看,大致呈现以下主要特征:
(一)都有一个以游牧为生业的族群作为行国凝聚的核心力量。
匈奴虽然不是第一个在北方草原地区出现的游牧行国,但从史书的记载看它却是第一个实现草原较大范围统一的游牧行国,由此开创了游牧行国辉煌的历史。从匈奴到蒙古汗国,虽然每个游牧行国存续的时间不同,但都有一个构成游牧行国核心力量的游牧族群。核心族群的出现是游牧行国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在游牧行国存续期间不断凝聚着其他游牧族群,随着游牧行国力量的膨胀而壮大。诸如匈奴游牧行国因为匈奴族群的形成而出现,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为我们勾画出了构成匈奴游牧行国核心族群的发展脉络。《隋书·北狄传·突厥》对构成突厥游牧行国核心族群的形成则是如下描述的:“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儿,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歘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记述中虽然有传说的成分,且真实性有待考证,但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清晰地形成轨迹。如匈奴、突厥游牧行国一样,构成其他游牧行国的核心族群也大致都有一个凝聚形成的过程。核心族群的形成为匈奴、突厥等游牧行国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族群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就是游牧行国的形成和发展。游牧行国的出现和长期存在,一方面将草原地区众多的游牧族群纳入到游牧行国体制之下,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政治体”,另一方面,游牧行国的长期存在又为族群之间的融合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中原地区族群融合为汉族的过程大体一样,在经过匈奴、北魏、突厥、回鹘、辽、金对草原地区众多族群的凝聚、融合之后,最终大蒙古国的出现实现了草原地区众多族群的蒙古化,今天的蒙古民族就是大蒙古国(包括元朝)在草原地区长期存在下众多游牧族群不断凝聚的结果。
(二)都拥有一个被称为单于或可汗,类似于中原农耕王朝皇帝的行国权力核心。
游牧行国和中原地区出现的“政治体”一样,无论大小,都有一个权力核心,最早见于汉文史书记载且用自己的语言称呼的权力核心是匈奴的“单于”。《汉书·匈奴传》有对“单于”的解释:“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这一记载从具体表述上分析存在一定矛盾。因为按照“撑犁孤涂”是“天子”的解释,“单于”是“广大之貌”,加在一起并不能得出“象天单于然”的含义,如果其意是“象天子然”相对更容易理解。由此笔者认为《汉书》对“撑犁孤涂单于”的解释明显有附会汉语“天子”的嫌疑,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和农耕族群接触后受到了汉语“天子”的影响。不过,上述记载尽管存在一些疑问,但它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明确的:匈奴游牧行国权力的核心与中原“王朝藩属”的权力核心称呼不同,一称为“单于”,一称为“天子”。虽然称呼不同,辖众不同,但在游牧族群的心目中“单于”和“天子”一样并没有差别。
游牧行国的权力核心在经过了匈奴游牧行国对草原地区的长期统治之后,被“可汗”的称呼所取代。《旧唐书·音乐二》有“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的记载,但是对于“可汗”出现于何时?含义是什么?学界历来有鲜卑、柔然两种不同的解释。《通典·北狄》载:“蠕蠕自拓跋初徙云中,即有种落,后魏太武神中强盛,又尽有匈奴故地。其主社仑始号可汗,犹言皇帝,以后常与后魏为敌国”。而《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则有:“四部服其雄武,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似乎乞伏国仁称可汗在前。对此,薛宗正认为:“鲜卑、柔然皆乃兴起于公元三、四世纪之交的漠北民族,何以不约而同地采用此一尊号呢?迄今仍无令人满意的解释,可见二说皆非学术定论。我以为‘可汗’……大贤王之意也。突厥又为柔然属部,布民放弃土门(万人长)旧称,同柔然主一样上建可汗尊号,自称伊利可汗,意味着正式宣布同柔然脱离传统的宗藩关系,并进一步取而代之。”*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7页。罗新则认为:“吐谷浑时期的慕答鲜卑和力微以前的拓跋鲜卑,其政治体(polities)都处于较低级别的发展阶段,尚未进入原始国家,甚至还只是处于酋邦的初始阶段。而柔然社仑称可汗,是与北魏天子相对抗的一种政治形态,其政治体已经具备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因此,依据现存史料,认为可汗作为原始国家或酋邦这一级政治体(supratribal polities)的首脑(supremeuler)的称谓最早见于柔然,也是可以成立的。……无论可汗一词最早出现于哪一部族、哪一语言,在柔然之后,经嚈哒、吐谷浑,特别是突厥等民族的传布,作为高级政治体首脑、取代匈奴单于的可汗称谓,遂广泛流行于内亚各语系、各人种的民族中。”*罗新:《可汗号研究——兼论中国古代“生称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笔者则认为,于游牧行国形成和发展而言,是称“单于”还是称“可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类似于农耕族群“天子”一样的核心权力的出现。草原地区游牧行国的历史已经表明,核心权力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游牧行国已经形成,而且也是游牧族群实现局部或更大范围统一的开始,这一点与中原农耕族群历史的发展轨迹是相同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汉文史书的记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汉文史书基本上都是以核心权力的出现为开端来记述游牧行国的发展轨迹。《史记·匈奴列传》虽然将匈奴游牧行国发展史追溯到传说中的夏,但游牧行国的历史是从单于的出现开始的,即:“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旧唐书·突厥上》开头言:“突厥之始,启民之前,隋书载之备矣”,然《隋书·突厥传》如上所引也是以记述可汗家族的兴起为开端的。《新唐书·突厥上》则载:“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臣于蠕蠕,种裔繁衍。至吐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旧唐书·回纥传》对回纥游牧行国形成和发展的记述相对比较典型:“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其众微小,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隋开皇末,晋王广北征突厥,大破步迦可汗,特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击特勒诸部,厚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为变,遂集其渠帅数百人尽诛之,特勒由是叛。特勒始有仆骨、同罗、回纥、拔野古、覆罗,并号俟斤,后称回纥焉。在薛延陀北境,居娑陵水侧,去长安六千九百里,随逐水草,胜兵五万,人口十万人。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菩萨劲勇,有胆气,善筹策,每对敌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少制众,常以战阵射猎为务。其母乌罗浑主知争讼之事,平反严明,部内齐肃。回纥之盛,由菩萨之兴焉。”从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权力核心的出现对游牧行国形成和壮大的重要作用或称之为关键作用。应该说,从史书的记载看,草原地区游牧行国的形成和发展都遵循着这一规律,有着大体类似的发展轨迹。
(三)都拥有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维持和发展着行国体制的运转。
以游牧为生业构成了游牧行国的最大特征,而由此也导致了游牧行国的军队构成也是以骑兵为主,甲骑、“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是其最显著的基本特征。在冷兵器时代,游牧行国的骑兵和“弓矢”的结合给农耕族群带来了很大威胁,以致于我们在汉文史书中见到的记载,不仅如上所引司马迁《史记》对西域各国的记载大多以“控弦”的多少来记述游牧行国的军事力量,在农耕族群有识之士议论军事力量尤其是游牧行国强弱的时候也经常见到用同样的例子。如《后汉书·班超列传》载:班超“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这种状况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按照上述《史记·匈奴列传》对匈奴习惯的记载,骑马和射箭是游牧族群必备的技能,即“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也正因为如此,骑兵不仅成为游牧行国维持内部稳定的主要力量,也是对外战争的保障。赵武灵王引入“胡服骑射”虽然带给农耕族群的多是惊讶,但游牧行国的“甲骑”真正带给中原农耕族群的震撼似乎应该是史家笔下对匈奴甲骑兵围白登的描述:“是时,汉初定,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阳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信将王黄、赵利期,而兵久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开围一角。于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得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去。汉亦引兵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53-3754页。“三十余万骑”且分为白、駹(青色)、骊(深黑)、骍(红)四种不同的颜色,这是《史记》和《汉书》作者笔下对汉初匈奴游牧行国军力的记述,而这支强大的“甲骑”也是匈奴构筑起东起大兴安岭,西到中亚,将众多草原游牧族群囊括其中的庞大游牧行国,并维持其正常运转的重要力量。
从史书的记载看,能够构建起涵盖整个草原地区,或实现草原大部分地区统一的游牧行国基本都有一支和匈奴一样规模强大的“甲骑”。《隋书·突厥传》载“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为步离可汗,居西方。时佗钵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至隋文帝立国时,沙钵略为汗,“控弦之士四十万”,沙钵略上书隋朝皇帝,自言:“突厥自天置以来,五十余载,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过万里,士马亿数,恒力兼戎夷,抗礼华夏,在于北狄,莫与为大。”回纥汗国的形成和发展从《旧唐书·回纥传》的记载看也是依赖于强大的“甲骑”。据该传记载:“贞观初,菩萨与薛延陀侵突厥北边,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十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因逐北至于天山,又进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回纥之盛,由菩萨之兴焉。”其后的契丹建立辽、女真建立金,乃至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等,也都是依靠游牧族群强大的“甲骑”。也就是说,保持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不仅是维持游牧行国存在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游牧行国实现草原“一统”的牢固基础。
(四)都拥有一套维持行国体制运转的以十、百、千等数量为单位设置的管理体系。
“不土著”、“毋城郭”、“随水草迁徙”是草原游牧族群和中原农耕族群具有明显不同的居住特点,因而在内部管理体系的构成上游牧行国也形成了独特的以数量为单位的管理体制。《史记·匈奴列传》是如此记述匈奴游牧行国管理体制的:“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随水草迁徙、不定居,导致游牧行国难以像农耕政权那样以村寨为基础单位的管理体系,但也出现了以什长、百长、千长,乃至“万骑”以数量为特点的政权管理体系。
游牧行国的这一独特的内部结构,是适应游牧行国的发展需要而出现的,其形成的时间是在匈奴时期,与中原地区秦汉大一统王朝同时,甚至略早。这一结构在经过鲜卑、突厥、薛延陀、回纥、契丹、女真等游牧行国的不断实践之后,至辽金后期被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发挥到了极致。《元史·百官一》载:“元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似乎《元史》的作者对蒙古汗国的内部结构并没有做出太高的评价,其记载的视角是从农耕族群的角度出发的,和农耕王朝的官职相比游牧行国的管理体系虽然简单,但确是适应游牧行国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在继承和发展游牧行国组织体制的基础上,蒙古汗国建立了更加完备的千户体制,《蒙古秘史》第191节载,面对乃蛮的威胁,成吉思汗停止了围猎,“点数自己的人马。每一千人,组成一个千户(千人队),委派了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成吉思汗打乱了草原原有的部落组织,按照地域划分为左右两个万户,万户之下以十进制分设千户、百户、十户,功臣为千户长,“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到惩罚”。*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页。千户制将分布在草原地区的众多游牧族群凝聚到了一起,不仅为蒙古汗国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也为蒙古构建融游牧和农耕族群为一体的大一统的元王朝提供了重要保障,更为草原游牧族群的蒙古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
(五)拥有具有以一定继承关系的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游牧文化。
游牧族群不仅有着独特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和农耕族群不同的组织和政治结构,也有着维持其社会稳定的价值体系,进而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独特的游牧文化。
对于游牧族群的价值体系,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开端,汉文史书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多有记述并大加诟病,其关注点从《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且“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所谓“宽”,一般理解为平常时期,但似乎更应该是指生活稳定,能够维持生计,而“急”虽然可以理解为紧急,但更多则应该指生活处于窘迫的状态,故有“随畜”、“侵伐”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如此理解这一记述,和“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的评价也能够形成呼应,因为“侵伐”的目的是解决生活遇到的困难,是为“利”而去,自然“不利则退”。至于“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评价,则完全是站在农耕族群的视角做出的,丝毫没有考虑到游牧族群的文化特点。
二是“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作为游牧族群,“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是由牧业这一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是“君王以下”似乎是试图说明“君王”和一般百姓不同,但不同不可能是表现在“食畜肉”上,而应该是指穿着。也就是说,君王的穿着已经不限于畜产品,也有了与农耕族群交换来的衣服,这也是等级观念出现的表现之一。而更能显示游牧族群价值观念的则是“贵壮健,贱老弱”一语,这一观念和农耕族群的“尊老爱幼”形成巨大反差,因而也是被农耕族群强烈否定的价值观念之一。
三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父亲和兄弟死后纳后母和兄弟的妻子为妻,是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在婚俗方面最显著的不同,尤其是“妻其后母”的习俗显示了不同经济形态所导致的巨大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差异随着农耕王朝边疆政策中和亲政策的实施遭到了农耕族群的广泛质疑。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的上述这些习俗虽然在游牧族群中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但“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大体上反映出了游牧行国存在的基本特征。《汉书·匈奴传》记载了一例西汉降匈奴者中行说和西汉使臣辩论的大段对话,从中很容易就看出游牧行国的文化特点:
初,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卬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 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
……
汉使或言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亲岂不自夺温厚肥美赍送饮食行者乎?”汉使曰:“然。”说曰:“匈奴明以攻战为事,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以自卫,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庐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父兄死,则妻其妻,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阳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到易姓,皆从此类也。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喋喋占占,冠固何当!” ……
以往学者很少对上述记载给予特别关注,但仔细分析中行说的言行,实际上反映着早在汉代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游牧和农耕给族群文化带来的差异,并利用这些差异制定出了相关政策,以维系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草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游牧族群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是牛羊等牲畜,而牲畜及游牧的生产方式很难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其生产、生活保障远不如农耕族群那么稳定,因而在生产、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进行狩猎或“侵伐”是维持其存在的唯一出路,具有普遍性。游牧生产方式的这一特性也决定了游牧文化的其他特征,而这种差异也早已为农耕族群所认识,并成为其针对游牧族群实施同化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恰如中行说所言,如果游牧行国改变习俗,那么游牧行国的立国基础就会被削弱,没有了立国的基础,其归宿就只剩下了被农耕族群融合一途,两汉时期的南匈奴、南北朝时期的鲜卑,以及建立辽金的契丹、女真等最终融合为“汉人”都是例证,或多或少都起始于游牧习俗的改变。这也是中行说代表匈奴游牧行国和汉朝使者力争的原因之一。
四
限于篇幅,本文难以对草原游牧行国做更加具体细致的描述,不过从东亚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草原地区游牧行国的发展历史看,游牧行国或称为政治体的聚合过程大体上和中原地区一样,遵循着以下发展轨迹:最初分布着星罗棋布的众多小的族群,之后不断凝聚、壮大,发展成为一些规模不等的,以某一族群为核心的游牧行国。匈奴、鲜卑诸政权、突厥、回纥等都是例证。在不同时期,草原上的游牧行国存在数量取决于游牧行国实力的对比。一般情况下游牧行国的存在状态是势力较大的游牧行国和周围的实力相对较小的游牧行国构成某种依附关系,但这种依附关系也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一旦对比发生变化,旧有的依附关系就会为新的依附关系所取代。突厥之前是柔然的锻奴,但隋唐时期却臣服了柔然。所以,草原地区游牧行国的数量和规模是在不断变动中的,变化是其常态。和农耕地区政治体的运行轨迹一样,在经过长期的凝聚后,有一定规模的游牧行国会出现在草原地区,不仅会带动更大范围内游牧族群的凝聚,也会改变游牧行国之间的依附关系,进而使游牧行国涵盖的范围更大,所体现出的政治格局演变即是实现局部乃至整个草原地区统一的游牧行国的形成,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藩属一样,由之达到了最大化,其形态即是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所称之的“草原帝国”。但是,和农耕王朝藩属体系呈现的样态不同的是,支撑游牧行国的如果单纯的是游牧经济,往往难以抵御持续的天灾和人祸,盛极一时的游牧行国持续的时间不如农耕王朝藩属体系那样持久,会很快分裂为几个行国,甚至瓦解,其后草原地区游牧行国呈现的状态又是一个个涵盖某一区域的政治体。在不断聚散的过程中,游牧族群的凝聚却是一直在进行着,经过数次聚散,至成吉思汗时期终于构建起庞大的蒙古汗国,游牧行国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蒙古汗国及其后继者元王朝的长期存在,草原地区的游牧族群终于如中原地区农耕族群随着汉王朝的出现而凝聚为汉人一样,也实现了蒙古化,不仅《南村辍耕录·氏族》所载 “阿剌剌、札剌儿歹、忽神忙兀歹、瓮吉剌歹、晃忽摊、……八怜、察里吉歹、八鲁忽歹、哈答歹、外剌”等72部落都被称为“蒙古”,而且以前存在草原之上的众多游牧族群也多消失在史书记载之中,游牧族群也完成了自己的凝聚。
值得说明的是,如果将匈奴游牧行国实现对草原游牧族群凝聚看成是第一次,那么到蒙元时期草原游牧族群逐渐蒙古化,游牧族群的凝聚似乎远远晚于农耕族群的凝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游牧族群凝聚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将凝聚成果带入与农耕族群的互动中,并为农耕族群的凝聚和壮大提供了新的来源,或称之为新鲜血液和凝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