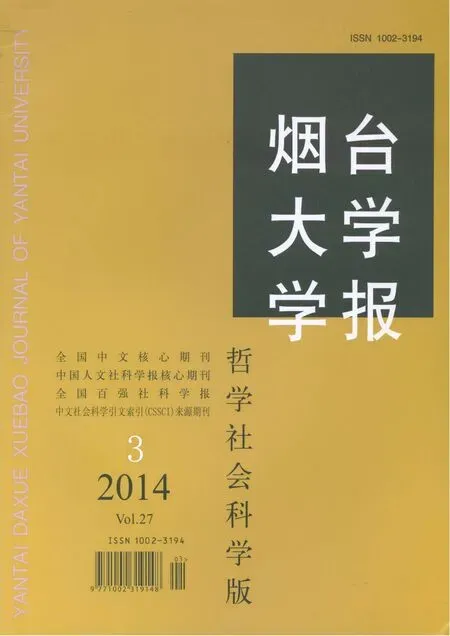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
2014-03-06闫晓昀
闫晓昀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现代文学史上,《边城》因其诗情画意的文学世界、和谐静远的桃源氛围和缓慢悠长的叙事节奏而独秀于现代小说之林,被称作“诗化小说”的典范作品。这一独特的文体形式使《边城》呈现出弱情节化特征,一般来说,紧张的情节与激烈的冲突是推进叙事的两架引擎,如何在几乎没有对立矛盾的情节设置下调用各种元素参与叙事,使情节得以推动、细节得以展现,便成为检验创作主体创作技能的试金石,而沈从文在《边城》中对文学意象这一叙事元素的处理方法,即体现了作者对这种创作技能的追求。文学意象是重要的诗学范畴,也是文学批评经常选取的切入点。杨义曾指出“研究中国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①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7页。,颇有见解地点明了意象对于理解中国文学内涵、意蕴及其诗学建构的意义。本文即试图以意象为入口品评《边城》,以期能呈显作者的叙事技巧,揭示沈从文蕴藏于意象之中的深层创作理念和美学追求。
在描摹边城社会风貌、呈示翠翠情爱发展的过程中,水、烟雾、动物及植物等意象被反复选用,贯穿作品始终,作者将客观意象纳入叙事行列,使其成为参与情节建构的重要元素、组成因果链条的主要环节以及推进情节前行的核心力量,进而使“意象”超越了“寓意于象”的浅层意义,上升为一组具备叙事价值的“情节化”意象,“是叙述中的将能开花结果的种子”②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以意象为切入点,可以探知作者在“讲故事”层面所体现出来的别出心裁,以及这一“别出心裁”之于《边城》的意义。
一
水意象是进入《边城》深层结构的第一把钥匙。《边城》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水气氤氲的世界,“水”蜿蜒流淌在《边城》的文学版图中,是其故事的背景和源头,具有奠定作品基色、串联故事发展、参与构建人性道德的深层功能,是作家礼赞生命和思索人生的载体。水意象在《边城》中的首要作用是充当了一条隐形线索连结起故事始末。水是《边城》得以存在的基础,串联着边城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茶峒小城依山傍水,“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茶峒民众的生活也与水密切相关,“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倍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对“边城人”而言,水是其根基与主宰,有水才有后续传奇,依水而生、傍水而逝是其既定宿命,无论幸福或苦难唯有顺意接受,“某一年水若来的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水意象在此俨然已具有了掌控命运的神性特征,在“水”这一自然神祇的引领下,茶峒小城仿佛是跳出现实之外的独立存在,不与时代回应,不受外界干预,人性纯洁自然,生活模式亘古未变,《边城》的乌托邦模式正是基于此而得以建构,可谓无水则无如此之边城。在情节推进方面,《边城》同样与水密不可分,翠翠与爷爷靠水度日,翠翠与傩送的相识相恋因水而起,天保溺水而亡导致傩送顺水而下不知何时回乡,爷爷在一个洪水之夜故去,留下年少的孤女独守河边靠渡船过日……“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摆弄着故事发展,每次情节的转折都有水参与,水意象也从而成为推动情节前行的关键,承担起举足轻重的叙事意义。同时,水意象还兼具激发作者创作欲求、反映作品创作主旨之功能。湘西地处辰河沅水流域,对水以及水边人事与情景的记忆,使生长于斯的沈从文在远离故乡的日子里也“苦苦怀念我家乡的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①沈从文:《无法驯服的斑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14页。。作者曾深情表述“水”之于他的重要影响:“我感情流动而不凝滞,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的关系。”②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九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09页。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一特定的地理条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童年经验决定了沈从文的创作方向与数路,作者从“水”中获得了创作源泉和审美体验,因此,在沈从文笔下,水意象已不再是单一扁平的自然意象,而是与其完成了情感体验的深层交互,“与其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③沈从文:《沈从文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页。,先天性地暗含着丰富的内涵,于主客体交融中实现了双向建构,因此,它也成为探幽沈从文文学世界的起点。在作者的观念中,“水”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元素,它的清明与灵秀更是表征了边城世界内蕴的品格与情操,作者凭借清澈明透的“水”来作为描述小城祥和宁静、赞美茶峒人事美好的参照,借以纯化茶峒自然景观、反衬村民的质朴真纯。水意象俨然已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为一个象征性存在,在其背后,一个理想世界正在悄然构建,作者的“爱恋激情”也在“水”的干预下得以激发。“爱恋激情”是创作激情的来源,它在对某一具体对象的强烈眷恋中获得情感的满足,从而达到生存的诗意、自由与和谐,具有高洁的形而上特性以及超逸的内在旨趣。在对“水”的爱恋中,沅水流域的风土人物升华为沈从文的理想与寄托,被赋予了由“水”所表征的至真至纯的人性和至善至美的人生形式,边城也因之而呈现出理想社会图式——景观明丽净美、百姓质朴纯粹、社会安定有序,一幅人性伊甸园的和美画卷。可以说,《边城》的灵性和情感张力正是以“水”为根基,“水”因而亦堪称《边城》的叙事原点与目的,正因作者予以水意象如此重要的叙事功能,《边城》才得以启动情节并奠定下整篇作品的情感基调和艺术风貌,《边城》中文学意象的叙事意义从中也可窥见一二。
与“水”类似,“烟雾”也是《边城》中承载着独特语义的意象。烟雾意象“出场”五次,其中三次出现在翠翠的视线中,两次由老船夫引出。正像翠翠的世界单一恬淡而祖父的世界复杂忧愁一样,出现在二人眼中的烟雾也有不同的内蕴。小说第五节,天保与翠翠初遇,老船夫看中天保,而翠翠的心思却早已暗许傩送,在主观错位与客观偶然的交汇中,爱情与命运的走向皆显得捉摸不定。“祖父把手攀引着横缆,注目溪面的薄雾,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轻轻的吁了一口气”。祖父看到了什么?他又在叹息什么?从这片“空雾”中,老船夫俨然“望见了十五年前翠翠的母亲”。烟雾意象在此以其“茫然混沌”的内在寓意凸现了深存于祖父意识之中的天命思想,传达出其对多舛命运的哀伤与忧虑,隐约地昭示了一个悲剧结局——翠翠对爱情的固执正像她的母亲,而这种执著终将使翠翠像他可怜的女儿那样滑入不幸的泥沼。与祖父不同,少女翠翠的世界单纯明了,因此,同样是烟雾,翠翠寄予烟雾的情绪则轻盈了许多。“细雨还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翠翠回想着两个端午节上的际遇,像烟雾一样难以琢磨的爱情使翠翠负上了甜蜜的负担,“好象目前有一个东西,同早间在床上闭了眼睛所看到那种捉摸不定的黄葵花一样,这东西仿佛很明朗的在眼前,却看不准,抓不住”——情窦初开的翠翠在“一片烟”中回味与吸收初恋的美好,这片似有似无的轻烟,恰如其分地衬托出少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烦恼模样,而少女的情爱意识正是在“烟雾”的干预下逐渐强化。“雨还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在故事情节的缓慢推进中,烟雾意象适时地出现在每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时刻,以诗性的方式反照出少女对于爱情的体味与把握,在省却了长篇累牍的心理描述的同时,也在“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阅读体验中为作品制造出“留白”的余韵。不同于“水”的单纯通透,混沌迷蒙的“烟雾”交替出现于翠翠和爷爷眼中,带着相悖的语义交结在一起,将“美丽总是愁人的”这一难于言表的矛盾情绪轻轻笼上《边城》——“美丽”是烟雾在翠翠眼中的投影,表达着作者对茶峒人生命形态及情感世界的赞赏,而“美丽”的结局却像老船夫在烟雾中看到的那般,是“愁人”无比的。“美丽”与“愁人”在翠翠与傩送的初遇中即发生了正面冲突,在赞美理想人生之余,作者也借此为作品暗置了悲剧伏笔。傩送因“捉鸭子”出现在少女面前,作者为两人的相遇设置了一个美丽的前景——“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薄雾”,这诗情画意的场景本应带给人物以美的体验,然而“翠翠望到这个景致,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她想:‘假若爷爷死了?’”——如此诗性美好的景观,却指向了死亡隐喻,这里的“薄雾”已远不止是诗化外在景致或衬托人物诗性品格那么简单,它直接参与了情节的建构,与结尾的布设潜在地对接起来,并以另一种形式言说着作者的创作主旨。从人物的视角而言,此处的“薄雾”引发了翠翠对失去精神依靠的忧惧,从沈从文的角度来看,它表达了作者对由祖父所表征的理想世界行将逝去的悲愁。作为一曲悠扬的现代牧歌,《边城》极力避免残酷的现实主义摹写,可“避免”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边城乌托邦正在外来文化势力的蚕食下日渐消失,《边城》也始终迷蒙着一层烟雾一般的忧伤情绪,为确保《边城》整体风貌的统一,沈从文尽量淡化了对不和谐因素的描述,他独辟蹊径,借由“烟雾”的多重指涉及由之而来的相互冲突婉转地表达了其拒绝直言的事实与情绪,既巧妙回避了直面现实的悲痛,又将作品主旨完整体现,虽途径曲折,却比直白地表达更多一分含蓄的朦胧之美,而烟雾意象在承担抒情表意重任的同时,也成为作者叙事技巧的标签,折射出沈从文在诗化小说诗学构建上的深厚功底。
二
除上述自然意象外,动植物意象也是《边城》中写心传意的介质。在翠翠与天保、傩送的情爱纠葛中,虎耳草、鸭子、鱼等意象反复出现于情节关键处,沈从文发挥其“文字魔术师”的叙事技巧,使这些意象与人物的情爱表达建立起联系。在早期作品中,作者的情爱描绘大多自然野性,作者宣扬狂放的、契合于原始人性的情欲,歌颂冲破伦理道德、世俗规范的男女欢爱,正像沈从文本人所言,“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①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九卷),第179页。。与这些作品不同,《边城》表征了沈从文全新的情爱观念,此一转变与作者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与张兆和(翠翠的原型之一)的恋爱以及在国立青岛大学为时三年的执教经历促进了沈从文审美情趣的转型,作品中的情爱描写逐渐内敛克制,恋爱双方恪守礼节、遵从古训,追求矜持平缓的情爱过程。这种天真而不造作、活泼而不轻佻、期待而不强求的全新情爱观念决定了作品中不会出现热烈直白的情爱描述,这便要求沈从文在向读者展示情爱细节、传递情绪信息时必须采取一种“隐晦”但有效的方式,上述动植物意象的介入对此可谓“功不可没”。
虎耳草是《边城》中最常出现的植物意象。虎耳草总计出现六次,交替出现在现实与梦境之间的虎耳草,图现出少女情爱意识的深化及其对初恋少年爱恋之情的增进。虎耳草意象在初次出场时即创造性地获得了在特定情境中表征翠翠情爱意识的功能。父母因唱情歌而产生爱情的故事深印在翠翠心中,“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祖父所讲的陈年往事激发了少女对于爱情的渴望,翠翠陷入期待的梦境,而“摘虎耳草”这一看似突兀的行为在此具有了情爱暗示意味,隐晦地表达出她对傩送的期待。在后续情节中,“虎耳草”作为少女情爱意识的象征,不断地出现少女情爱进展的关节之处,将翠翠微妙复杂的心理世界展示出来。如在第十五节里,祖父为翠翠唱了十支傩送唱给翠翠的情歌后,翠翠“文不对题”地说道“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从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可知,“虎耳草”已经从先前的梦境走到现实,被翠翠主动认可为情爱符码,而到故事推进至第十七节,当清晨去山后挖鞭笋的翠翠却将一大把虎耳草带回家时,沈从文终于将翠翠对傩送的相思与爱恋之情在“挖虎耳草”的辅助下明确地呈现给读者。虎耳草这一意象的选取与使用例证了文学意象是间接彰示人物内心活动的有效手段,对《边城》中虎耳草的理解正如瑞恰慈所说的那样,“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一个意象的生动性,而是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②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93页。,“虎耳草”同“翠翠的爱情”在正是在这种相互映照的过程中实现了双向建构,在“恰到好处”的出现中,虎耳草具备了超越审美价值的语义阐释功能,仅着六处笔墨,便已能替代繁琐的描述,将翠翠复杂的情爱心理变化凝练地呈显。
与虎耳草功能相似的还有“鸭子”意象。动物意象向来是传情达意的重要意象,在诗人笔下,特定的动物往往成为凝结相思、表达爱恋的重要手段,《诗经》中的白鹭与雎鸠可谓其最典型的代表。因此,《边城》中的“鸭子”意象在出场之初便先天性地内蕴了情爱指涉的可能。“捉鸭子”是湘西民众在端午佳节进行的一种民俗游戏,是其欢庆端午的独特方式,对《边城》而言,“捉鸭子”还是启动小说情节的外部动机之一。端午、中秋与春节是湘西社会中最重要的节日,也是边城世界里最热闹的三个时节,其中端午尤甚如此。与中秋和过年这两个以家族意识为核心的节日不同,端午追求“与众乐”,是小城参与人数最多的节日,关涉到家族之外的人际交流和往来。民间传统节日是长期苦于生计的人民苦中作乐、释放情感的重要时刻,其时人们的心理和情感活动都异常活跃,在《边城》诞生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传统的湘西社会还保留着古老的礼制,“欢庆端午”这一民俗活动的存在为当地男女青年提供了结识的机缘与环境,作为重头戏的“捉鸭子”是青年男子参与的竞赛项目,年轻女性借此可以近距离地感受男子的异性魅力,而其情爱意识正是在此异性魅力的激发下萌生。在这种男女欢会的时节与场所,“鸭子”对于边城青年来说具有情爱启蒙的功能,包孕着的两情相悦的情爱指涉,而边城男子的本领与力量,也可通过“捉鸭子”的行为得以直接显现。如作为当地码头掌事人的船总顺顺在“青年时节便是一个泅水的高手,入水中去追逐鸭子,在任何情形下总不落空”,而当他发现“次子傩送过十二岁时,已能入水闭气汆着到鸭子身边,再忽然从水中冒水而出,把鸭子捉到”时,便说道“这种事情有你们来作,我不必再下水了”。由此可见,在茶峒人看来,捉鸭子的能力与男子的本领直接关联,一个会捉鸭子的男子,已经成熟到可以承担起社会、家庭与婚恋的多重责任,而同伴对傩送的调侃更是明确地凸显了由“捉鸭子”所表征的情爱能力——“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在翠翠看来,“捉鸭子”本领极高的傩送释放着迷人的异性吸引力,鸭子意象从而也成为翠翠与傩送爱情的诱发因素,亦是其婚姻归属的象征,因此,当爷爷暗许了天保以“送鸭子”为象征的求婚时,翠翠即嗔怪道“谁也不稀罕那只鸭子”。作为一个心有所系的少女,翠翠正是以拒绝天保所赠的鸭子来表达其情爱意识的觉醒,而爷爷也以“谁送那只白鸭子”的自问来表达对翠翠婚姻去向的担忧。作者赋予“鸭子”以独特的婚恋指涉能力,通过对鸭子意象的加工来简化对主人公情爱细节的表述,从而制造出简约明快的阅读体验和内敛含蓄的审美品格。
同样作此处理的还有小说中的“鱼”。《边城》中涉及鱼的对话频繁出现,几乎每段有关主人公情爱发展的场景都有鱼意象的参与。由于鱼产卵数量多,繁殖能力强,因此,“鱼”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文化中均不同程度地暗涵繁殖意蕴。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鲤鱼撒子、童子抱鱼、鲤鱼戏莲等图景,往往被直接用以喻示性爱和生殖。《边城》自觉沿用了这一传统文化符号,使“鱼”与少男少女的恋情取得了相互关联。翠翠与傩送在初次相遇时便引发了有关鱼的对话,在码头边等待爷爷归来的翠翠误会了傩送对她的邀请,由此也将了鱼意象引入情节。傩送对翠翠玩笑道“你不愿意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翠翠回答说“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待到随后翠翠生气老船夫的“迟到”时,少女嗔怪地说道“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在此可见,同虎耳草一样,“鱼”在初次出现时便已被少女认同为情爱符码,在“鱼咬人”、“鱼吃人”的表述中,对傩送的爱恋情怀已悄然植根于少女心中,自此,“鱼”意象便负担起独特的表意责任,多次出现在作品涉及翠翠婚恋进展之处,无论是在翠翠对“大鱼吃掉你”的自我回味中,还是在爷爷以“大鱼咬你”来暗指“傩送喜欢你”的说笑里,鱼均作为承载着情爱意识的特定符码而出现,鱼意象从而也成为维系翠翠与傩送关系的内力,委婉地表达着少男少女朦胧情愫的发生与发展,“翠翠的情爱意识正是在鸭子、鱼等意象的综合作用下,在傩送、老船夫和傩送的伙计等人的不断暗示下,在自己反复的咀嚼和品味中自然萌生的”①姜峰:《情爱意象:沈从文的民俗审美发现》,《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沈从文也凭靠这些语义独特的意象组群完成了其全新情爱观念的表达,在经由意象传递情爱信息的过程中,浓郁的古典情韵款款而来,萦绕于茶峒的山水角落间。
三
在此可以看到,《边城》的表现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学中常用的艺术手段极为相似,它通过选用具有丰富象征和暗示意义的具体物象来代替复杂的叙事过程,带领读者进入感悟式的审美世界,继而实现诗人孜孜以求的“写意”与“传神”。作为一个崇尚传统抒情主义的作家,沈从文从古典诗词中吸取了叙事手法上的含蓄,将中国诗歌艺术中借由意象表达精神世界的方式引入小说,取道水、雾、动物、植物等意象途径代替对紧张情节的精心营构,柔和地释放出内心深处爱与美互相交融的情感,提供读者以舒缓诗意的阅读感受。从这些意象上沈从文体会了生命与自然的宽博与伟大,以及它们对其创作思路和叙事手法的启示。作者以繁密的意象群组,打破了一般小说中以风景点缀人物、以人物构建故事的叙事模式,在作品“弱情节化”的前提下,它们有效地传情达意,参与叙事过程,推进情节发展,并于情节叙述之外传递出作者深蕴内心的复杂情绪,在阐释作者叙事意图、凸显作品叙事技巧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帮辅作用。评论界常以“诗化小说”这一指称来称谓《边城》这类富于诗性的作品,以此来概括由某一整体性情绪引导的、以非线性叙事方式结构的一种弱情节化的小说类型,但小说究竟是如何被“诗化”的,则常常语焉不详,而大都从阅读体验入手,给出一个模糊的印象式阐释。实际上,“意象叙事”(或称作意象的叙事化)正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诗化小说创作者实现小说诗化的关键。它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传统诗歌创作手段移至现代小说创作中去,为《边城》营造了一个诗情画意的特别氛围,不仅“诗化”了阅读方法,同时也“诗化”了阅读体验,《边城》也在意象这一叙事元素的参与下弥散出浓郁典雅的中国意味。意象向来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组成,“所谓意象就是点睛艺术在叙事文学中的运用,它成为叙事过程中极为精彩、极有关键价值的笔墨。诗有诗眼,意象就是叙事文学的文眼了。”①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第317页语言表达总有“言不及义”的困扰,而意象以及由之而生的象征与想象的介入,则能于意义的“不确定”中传递出“确定”的意义,中国艺术的留白精髓,其目的与价值均在于此。在此有必要围绕意象与象征的关系问题略作讨论。此两者虽常以相伴相生的姿态出现,也均以符号建构为己任,但却内蕴着不同的思维方法与艺术精神。意象是中国艺术精髓,象征则属于西方文化范畴。民族意味浓郁的意象叙事有其独特的理论渊源,与西方象征主义似而不同,它讲求整体化,含蓄内敛,注重抒情,而西方文学的象征叙事则讲求条理明确,立意清晰,重于表意,简言之,象征基于理性逻辑,而意象则立足整体性的顿悟感知。从这一角度来讲,解读《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功能,实际上也是挖掘其内蕴的民族性的过程。意象的特性为《边城》提供了“诗化”的可能性以及东方式的“诗化”思维:感知客观之“象”,附之以“意”,由意生“境”,在“境”中完成客观事物与人之情感或记忆的“再现”。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汲取了来自民族文学传统的养料,然而《边城》仍在这一过程中赋予意象叙事以现代色彩。实际上,小说的“诗化”,本身即是小说“现代化”的表现之一。对意象这一传统诗学核心要素的“叙事化”处理使《边城》突破了古典小说以情节推进作为叙事动力的传统模式,《边城》也因其独特的叙述策略而具备了意识流特征,使作品呈现非逻辑性、流动性和跳跃性特征,与现代创作手法完成了对接。这也解答了为何以《边城》为代表的“诗化”小说总是漠视情节的线性逻辑,而更注重统摄性情绪或意境的营造,毕竟,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混沌笼统,并无逻辑可言。在《边城》中我们可见作者显然更希望传递一种和谐恬美的桃源风情,而非为读者讲述一个复杂跌宕的情爱故事,无论在人物内部还是外部,都缺少推动情节有序前行的动力(意象的叙事功能正根植于此)。因此,虽故事中心为翠翠的婚恋纠葛,但作者仍有极大的笔墨用于其他事物以及整体生活情境的描述,以致最终留给读者的是一种“边城情绪”,而非一段“边城情节”。同时,作为一部颇具传统意味的作品,《边城》又不像现代意识流小说一般仅注目意识的流动,毕竟对“意识流”过分依赖极易使作品掉入单纯的形式创新的陷阱而忽略了文学创作中“内容”的本体意义,对此,沈从文似乎有着自觉的认识。他在凭借意象来跳跃意识之余,始终将“意识流”引向一个明确的中心,即,他要以意识的流动表明其创作并非基于理性逻辑,而是基于一个抽象的观念世界,其意识流动的动力与结果均在于对这一观念世界形神品貌的再现。这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古典文学在现代的演化,换言之,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在现代视阈下理解传统的结果。作为叙事核心要素的“意象”在此兼具了传承传统、确立民族叙事特征的文化价值,其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意象叙事作为中华民族极有光彩和特色的叙事方式和谋略,从历史深处走出来,接受了时代的考验和询问,在融合外来的现代思潮和叙事经验中,丰富了自己的形态,从而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神采了。意象叙事在其历史进化中,已经具备民族思维的优势和时代思维的优势,它使叙事作品诗化和精致化的生命力是难以磨灭的。”①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第329页。《边城》对意象的叙事化处理反映了现代作家在现代语境下接纳传统话语的努力,是以古韵承新意、把古典元素重新纳入现代文本使之重新焕发生命力与魅力的过程,它不仅协助沈从文打造出兼具中国气度与现代魅力的《边城》,同时也为思考中国小说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如何在现代中留存传统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