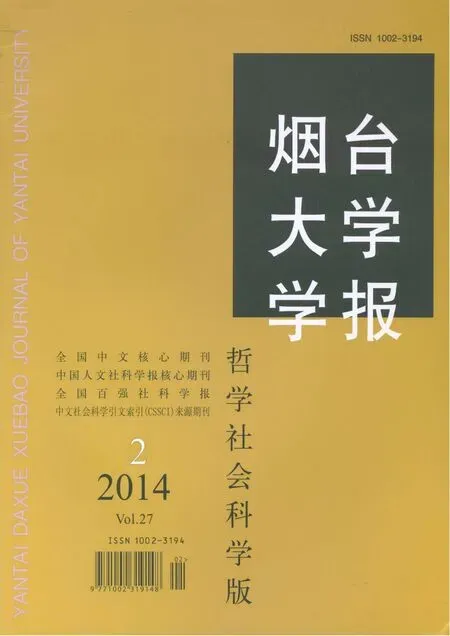从“羊人为美”看中国审美文化假扮基因的传承
2014-03-06刘心恬
刘心恬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 250100)
从“羊人为美”看中国审美文化假扮基因的传承
刘心恬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 250100)
假扮的本质是基于想象的精神模仿行为,其源头可追溯至先民在原始巫术仪式中装扮为祖先或图腾以祈福的活动。从民间游戏到工艺制作再到艺术鉴赏,“羊人为美”所携带的假扮基因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得到广泛传承,涵盖民间游戏、诗文艺术及工艺赏玩等五个分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审美文化史重精神模仿而轻形式模仿、重意境而轻形似的审美习性以及借神思作忘的方式通达心与物游境界的审美追求是历经传承的假扮基因所造就的。
羊人为美;审美文化;假扮;游戏;精神模仿
一、以“羊人为美”为模型的假扮基因
关于“美”字起源的字源学考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逾三十载,各派论争尚未尘埃落定,仍不断有年轻学人加入“羊人为美”(“象人头戴羽饰”、“象人头戴冠笄”、“象人头戴羊头羊角”)、“羊大则美”、“羊女为美”、“羊火为美”、“色好为美”、“美善同义”、“巫王为美”、“从羊大声”、“从大芋声”等派系的阵营,为各自的观点找寻历史依据与美学、文化人类学及哲学支撑。一方面,各派对所持历史依据的阐释均具有逻辑合理性,且从技术层面证实文字学路径与文化学路径哪一方更有说服力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又各有偏颇不实或过度阐释之弊,既有研究路径面临瓶颈,亟须创新思路予以突破。徐复观认为,“对于艺术起源的问题,最妥当的办法,是采取多元论的态度”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这一方法论对“美”字起源的阐释同样适用。回溯本源的思路造成各执一端、众说纷纭的局面;立足字源而考察其基因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史上的传承方能统合把握其在现象与实践层面的民族特色。在考察中国审美文化基因传承的问题上,既要“求本”,又要“逐末”,“求本”于“逐末”,“逐末”以“求本”。所谓“本”是指作为基因播撒于后世的“美”的字源根据,所谓“末”是指传承携带这一基因的子嗣。二者恰似树根与枝叶,若要窥得中国审美文化史这株大树的全貌,须得缘根求叶,“求本”与“逐末”得兼。在此,以最具代表性的“羊人为美”与“羊大则美”二说为分析对象,通过考察其作为文化基因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史上的传承,得知论的阐释与史的表征在何程度上彼此契合。
首先来看“羊大则美”说。李泽厚指出,“‘羊大则美’,认为羊长得很肥大就‘美’。……美与感性存在,与满足人的感性需要和享受(好吃)有直接关系”,说明“‘美’是物质的感性存在,与人的感性需要、享受、感官直接相关”。①李泽厚:《美学四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61-62页。陈望衡指出“羊大则美”的阐释“应该说是根本的”,因为“对于原始人类来说,首要的是活着,而活着必须要有食物。个体生存无疑是第一义的”②陈望衡:《华夏审美意识基因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皮朝纲将“羊大为美”与饮食文化相关联,指出“‘羊大为美’说比较接近‘美’字的最初含义”,因其“符合上古先民重视生命与现实、崇拜种的繁衍和渴求物的丰产的原初心志,符合当时的物质生产状况和饮食文化发展水平”③皮朝纲:《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的“羊大为美”思想》,《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但是,这一基因在审美文化史上的表征不明,或有将之与“味”相联者,难免牵强附会之嫌。殷杰指出,“美所包含的原初的审美意识决不是‘以味为美’”④殷杰:《中华古典美学三题》,《文艺研究》1993年第5期。。口腹之欲即生理快感是“羊大则美”说所强调的,而作为审美范畴的“味”与这一维度关联不大,即便表面字义关联,在深层意义上也是断裂的两端。二者并非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指涉口腹之欲的“味”不曾退场,仍作为字义被广泛使用。司空图、苏轼等人论诗味是以隐喻手法表述的,作为审美感知的“味”与之构成的是隐喻关联,而非前后相继的关系。“味”作为审美习性,根植于与其他范畴协同相通的基础上。若非背道而驰,重生理快感及重功利目的也远不是本民族审美的基本路数,因而将饮食等同于审美、将饮食文化等同于审美文化以维系“羊大则美”的基因在审美文化史上的血脉实在是牵强。再者,口腹之欲的满足无法涵盖审美感知的丰富多维,且在社会性及精神性上与审美无关。古人的审美活动遍及诗文艺术创作、工艺制作赏鉴、山水之乐乃至民间游戏,远非“味”所能涵盖,以之作为美论生长点实属鸡肋。此外,有学者指出“羊大则美”说的最权威来源即《说文解字》对“美”的字义解释“甘也。从羊从大。……羊大则美,故从大”,所依据的是“美”的小篆形体,而非“美”的最原始甲骨文字形。⑤申焕:《“美”的原始意义探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可见,“羊大则美”说作为中国审美文化史的分支之一是可能而合理的,但作为源头不妥。它的基因被直接传承至饮食文化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与作为审美感知范畴的“味”的字面义并不直接相关,与该范畴在中国审美范畴史语境下的内涵及外延亦不通达。
再来看“羊人为美”说。李泽厚指出,“从原始艺术、图腾舞蹈的材料看,人戴着羊头跳舞才是‘美’字的起源。”⑥李泽厚:《美学四讲》,第61页。林君桓认为“把‘羊人为美’看成是化了装的人的形象,显然是能够说明美的最早来源之一的”⑦林君桓:《“羊大则美”与“羊人为美”孰先孰后》,《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年第3期。。“羊人为美”说强调“美”字的甲骨文字样象征“佩戴头饰、手舞足蹈作法礼神的巫师形象”,形象化地描述了“原始巫师从事巫术活动时的状态”,因而“羊人为美”是“汉字‘美’的最初含义”,其产生“直接导源于巫术活动”。⑧万书辉:《“美”的文化人类学阐释》,《重庆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羊人为美”说将“美”的甲骨文字形视为会意性的完整体,但从上下两部分加以阐释——下部代表某种身份的人形,上部代表装饰人形的某种器物。此派内部论争的焦点在于上部装饰物的属性及下部人形的身份,大致分为三种观点:萧兵、李泽厚、刘纲纪等学者是“美”像人戴羊头羊角说的支持者,认为“美”的甲骨文字形“象一个‘大人’头上戴着羊头或羊角”,其下部的“大”在原始社会里是“有权力有地位的巫师或酋长,他执掌种种巫术仪式,把羊头或羊角戴在头上以显示其神秘和权威”⑨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0-81页。;王献堂、康殷等学者是“美”象人戴羽饰说的支持者;高建平则认为“把‘美’字看成是象人头戴冠、笄等头饰似乎证据更充分一些”。①高建平:《“美”字探源》,《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此外,朱良志等学者在赞同“‘美’是经过装饰的人形”的基础上又提出“舞人为美”说,认为“‘美’是一种跳舞的人形,是一种艺术造型。这里所含有的意念不是‘羊人为美’,而是‘舞人为美’”。②朱良志,詹绪佐:《中国美学研究的独特视境——汉字》,《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羊人为美”与“舞人为美”分别侧重原始社会的巫术祭祀仪式和舞蹈艺术形式,虽然李泽厚“‘美’字与‘舞’字与‘巫’字最早是同一个字”的观点未必有据可考,至少说明“巫”、“舞”在上古不分家,巫术仪式以舞蹈艺术的形式表现,舞蹈艺术的目的在于巫术祭祀,可知“羊人为美”与“舞人为美”的基本思路相差不大。二者的共同点不仅在于形式上的假扮,更在于通过假扮行为沟通天地神人以求庇佑、以示膜拜、以表崇敬的思维模式。借助装饰物装扮自身以获取有别于现实身份的虚构身份,或者借助道具以生发出与仪式有关的虚构事实的假扮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游戏。“羊人为美”作为基因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的传承正是以这种假扮游戏的样貌表征为巫舞仪式、民间游戏、诗文艺术、工艺赏玩乃至山水之乐的诸多方面。从本末传承的基因脉络上看,“羊人为美”更为直接、广泛、深入、多样,家族谱系的丰富完善性及成熟程度更高。
因此,在假扮的意义上使用“羊人为美”更为妥帖:淡化“羊人为美”与“舞人为美”在载体上的差别,有利于挖掘其在深层内涵上的互相联通之处。“美”象人头戴羊角、羽饰还是冠笄只在文字学的意义上才有分歧,在假扮意义上却是一致的。与其争辩“美”在形式上象人头戴羊角、羽饰还是冠笄,不若思考“羊人为美”在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深层本质,从中国审美文化的基底与载体入手考察其假扮基因在后世艺术文化现象的蓬勃衍生。事实上,原始社会的巫舞仪式只是携带了假扮基因的一个模型,中国审美文化的假扮性特征远比巫舞更为丰富。“羊人为美”的精神滥觞之后,中国审美文化史掀开了假扮游戏的新篇章。
二、“羊人为美”假扮基因的滥觞、繁衍与成熟
“羊人为美”的假扮基因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的传承分为滥觞期、繁衍期与成熟期三个阶段,历经功利性渐弱、游戏性增强的变化,假扮基因由形式上的表征转变为心理上的表征。
首先,“羊人为美”的假扮基因滥觞于原始社会的巫舞仪式。原始巫舞仪式具有典型的假扮性,“崇拜羊图腾祖先的氏族,要举行播种、祈丰、狩猎、诞生等等巫术伴舞的时候,就要由表演人物(一般是酋长兼巫师)扮演为羊祖先的样子,要扮演羊,或者头插羊角,或者戴着羊头;有时候仅仅以人工制造的羊头来代替,然后大蹦大跳,大唱大念,甚至随着乐奏”③黄杨:《巫、舞、美三位一体新证》,《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富有象征意义的装扮(“羊人为美”的“羊”)赋予巫舞者(“羊人为美”的“人”)以通灵者的身份,通过表演特定的巫舞动作与天地神明沟通对话以表达本部族的祈福要求。哈登指出原始部族成员“用图腾的名称作为自称”并相信自己是该图腾的后代,通过“穿戴图腾动物的皮肤或身体的某一部分,……让自己与图腾更为相似”,以使自己“受到图腾更多的庇护”,因而“巫术行为通常主要是一种与原始象征主义结合的模仿表现”④哈登:《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3页。。巫舞者在仪式之外的氏族生活中担任酋长等权威角色,在仪式之中则是本氏族图腾的“化身”。氏族成员相信酋长是图腾化身的事实为真,并随他的舞蹈作出俯跪叩首等祭拜动作。然而,原始巫舞毕竟是出于功利目的宗教仪式,假扮停留在装扮自身以获得虚构身份的形式层面,氏族成员在心理上仍对仪式及舞者抱持信仰膜拜的态度,滥觞期的假扮基因主要表征为装扮与装饰。除仪式装扮外,生活器具及装饰品的纹样图案也寄托辟邪祈福的愿望。譬如商代青铜面具与傩戏面具,佩戴者被面具临时赋予了有别于真实自我的虚构身份,在巫舞仪式中扮演的“他者”角色遮蔽了佩戴者的本来面目,观看者也假装忘记他的真实身份,而以敬神的态度膜拜他。此外,在丧葬仪礼中以陶俑陶马代替活人活马殉葬的习俗也是一种假扮,贡布里希认为这种替代物的使用与“偶像代替神”的做法遵循同一思路,这些制品“只有在作为替代物的意义上才‘再现’了什么”①贡布里希:《木马沉思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页。。仪式的流程秩序及纹样装饰的祈福意义在部落群体中形成约定俗成的契约,要求成员以虔诚待之。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时代,原始宗教及其规则不仅是精神寄托,更是求生必备。滥觞期的假扮行为尚停留在形式模仿的初级阶段,巫舞仪式的参与者期待长老能与神明祖先真正实现沟通,真实的宗教信仰与浓厚的敬神氛围不容许质疑,心理层面的假扮因而受到抑制。
其次,“羊人为美”的假扮基因繁衍于民间游戏。随生产力的提高及对自然认知的增加,先民不再倚赖巫术求生存,形式化的巫术假扮仍旧存在,但已不占据主导地位,假扮基因转入民间游戏并得到广泛繁衍。相较于原始巫舞,民间游戏的功利性减弱而娱乐性加强,但维系一致的是玩家须遵守规则,以煞有其事的严肃态度对待游戏。加达默尔认为游戏行为“具有一种独特的、甚而是神圣的严肃”,只有当玩家全神贯注于游戏时,游戏才能实现本身,因而“使得游戏完全成为游戏”的因素正是“在游戏时的严肃”②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30-131页。。民间游戏的道具与服饰实现了玩家在真实自我与虚构自我之间的身份转换,生发出关于虚构自我的游戏事实。官打捉贼、网鱼、黄鹞吃鸡的游戏者扮演了“官”、“贼”、“鱼”、“网”、“黄鹞”和“鸡”;“二龙戏珠”、“双跳龙门”、“金龙蟠玉柱”对龙的姿态的描述实为假扮龙的表演者的动作;踩高跷与跑旱船的表演者装扮为民间传说的虚构人物,借助道具以表现骑驴坐船的虚拟场景。繁衍期的假扮基因实现了从形式到心理的进化,以纸鸢与竹马为例。纸鸢有燕形鹰形,是仿照被再现对象的样貌制作的道具,但竹马却不模仿真马的样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描述了骑竹马的假扮游戏,一根青竹竿与真马毫无形似之处,儿童以竹马为真马,并非因其形似于真马,而是遵照游戏规则假装竹竿是真马,在骑竹马的游戏世界中,全部玩家都要假装相信竹竿是真马的虚构事实为真。可见,假扮基因在民间游戏的繁衍过程中发生了从形式到心理的变异,形式上的相似性不再占据主导,心理上的假扮开始萌芽、发展。
再次,从假扮基因理论审视中国审美文化史,“羊人为美”的假扮基因成熟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大致可分五类。其一是以各派戏曲为代表的表演性假扮。戏曲的假扮性表现在脸谱、装束、舞美、道具、动作程式及虚构时空上。譬如,脸谱是表演者最贴身的道具,生发出关于角色性格命运的虚构事实:红脸关公忠义正直、白脸曹操奸诈多疑、黑脸包公铁面无私。男扮女装唱旦角也是典型的假扮行为。又如,舞美布景和道具也多靠假扮,以布帘代城门、挥鞭代骑马、摇橹代撑船。白鞭代表所骑为白龙马,挥黑鞭代表坐骑是乌骓马,看到表演者手中的红鞭的观众假装看到关羽骑乘赤兔马。再者,动作程式也具有假扮性,即使舞台上没有一扇门,观众看到表演者假装左手按住门板,右手拉开门闩,再双手向外拉门的动作便知其在“开门”。此外,三五插旗扮作千军万马,绕场几周便是行军千里,幕幕间寒暑交替,前后脚屋里屋外,都是虚拟时空的假扮表现。其二是以写意画为代表的视觉性假扮。写意画重意境而轻形似,尤以大写意形态最为夸张。国画视觉假扮表现有四:一则不求形似,譬如水墨一支以浓淡相宜的水墨代缤纷的五彩,梅菊竹兰本各有原色,以水墨绘之自有无限韵味,比鲜艳重彩更受文人墨客喜爱;二则以无扮有,譬如表现鱼戏水中之趣,只需点几尾鱼而不必画水,至多以涟漪代之,比绘上水纹更逼真醒目;三则以虚扮实,譬如以飞白作枯藤瘦石比湿墨更显凹凸有致;四则点到为止,譬如描绘兰芯,三点成形却也摇曳多姿,又如山水卷幅中的人物,三五笔粗粗勾勒身形衣褶,不画五官表情倒也生动鲜活。画中本无山水树石,赏画之人却看到群峦起伏、碧波荡漾,而其实不过是寥寥墨线、点点缀缀。在国画审美欣赏的视觉假扮游戏中,观者借助审美想象假装立于秋菊丛簇之前而不问其为何墨色,想象看到潭中鱼戏而不问为何无水,移情于江雪垂钓翁而不问其为何缺失五官。稀疏几笔落于纸上便为假扮游戏提供了道具,写意的抽象是假扮的抽象,注入想象的画面总是丰富可感的,画中才有了水墨世界,假扮视角之外的画作只剩气势灵动的勾勒和洇透纸背的色块所呈现的形式美。可见,由追求形似到摒弃形似,假扮基因须借助想象方能实现转型,观者才能于画作中看到“看不到”的时空与实体。其三是以诗文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性假扮。宋词婉约派男性词人常以女子口吻作词,这与京剧男性演员饰演旦角一样具有假扮性,词人假装自己是女子,体其心悟其情、模仿得。小说借笔者或叙事人之口陈述关于作品世界的虚构事实。虚构事实建构起作品的虚构世界,角色作为虚构个体存在其中。读者被虚构故事所吸引,想象自己也在西天取经路上,并为窦娥与黛玉落泪,想象自己透过诸葛亮之眼看到赤壁之战的壮观景象。虽然作品世界与虚构个体与现实不同,不具有物质实在性,但读者却乐于假装相信这些人物及其虚构事实都为真,因而金陵、大观园、天庭、西天等虚构世界具有心理实在性和独立自足性。所谓“相信”只是“煞有其事”地“信以为真”,读者清楚知晓孙悟空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乐于旁观三打白骨精的精彩场面并绘声绘色地向旁人转述的行为具有典型假扮性,说话人与听话人在“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体验中共同参与了以《西游记》为道具的假扮游戏。其四是以盆景为代表的器物类假扮。古人将山水之乐凝聚在盆景中,在壶中天地收藏了名山大川。盆中泥塑的三五知己,或端坐庭中,赋诗品茗、闲敲棋子,或斜倚枯松、共赏雪景,把酒言欢。盆景佳作不仅缩微了空间,还沉淀了时间,绿植随四季变换样貌,春华秋实凋零复青葱,盆景世界中的人们也历经雨雪风霜、昼夜往复,别有一番意境:沐雪江中垂钓者披蓑又戴笠还是染白了须发,赤脚水中摸鱼者蹑手蹑脚怕惊了鱼,打湿裤腿而浑然不觉。盆中树下有邀月赏花畅饮者,眼神迷离,仰面高歌。把玩盆景的主人想象自己便是座中嘉客,嗅闻酒香四溢,尽享对诗墨戏之趣。盆中世界的虚拟构造依照主人的审美理想被摆置成聚友赏花、溪钓田耕、寻隐小酌的可触可碰、可观可闻的白日梦。其五是以音乐为代表的听觉性假扮。欣赏《高山流水》的听众想象指拨琴弦所发出的不是和缓波动的纯粹乐音,而是汩汩流水声;聆听《金蛇狂舞》的听众不仅用“曲风活泼”、“节奏感强”、“令人亢奋”来描述欣赏体验,更假装想象自己听到了狂舞的韵律、看到了金蛇的姿态。
三、结 语
“羊人为美”的假扮基因自滥觞期发展至成熟期,以想象与移情为途径的心理假扮基本取代了通过模仿匹配追求相似性的形式假扮,审美旨趣在文化心理的深层携带假扮基因,在文艺作品样式的表层却呈现多元化的表征。值得深思的是,“羊人为美”的假扮基因的心理根基何在?沃尔顿认为,人们对“假扮活动的参与本身就是精神模仿的一种形式”①Kendall L.Walton,quot;Spelunking,Simulation,and Slime:On Being Moved by Fictionquot;,in Emotion and the Arts,ed.Mette Hjort and Sue Lav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37-49.,这有助于理解假扮的本质。假扮借助想象,而想象通常以“第一人称”模式展开,是由之内心、关乎自我的②Kendall L.Walton,Mimesis as Make-Believe:On the Foundation of Representational Art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8.,因而精神模仿是以自我作为想象情境主人公的虚拟体验。庄周梦蝶化而为一者便是精神模仿的隐喻,在梦的语境下,庄周感受到蝴蝶“栩栩然”如真如实;但与此同时,庄周并未丧失真实自我,只是在梦境无意识状态下假装自己是蝴蝶。“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蝴蝶只是被梦境临时赋予的虚构身份,庄子将这一体验称作“物化”,其实质是精神模仿。假扮无关认知亦无关现实,它所要求的“严肃”是主体遵守游戏规则以守住虚构性的真实不被现实真实所打扰。在假扮的意义上,即便子非鱼亦能知鱼之乐。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与假扮和精神模仿相关的范畴有“游”、“心斋”、“作忘”、“无我”、“虚静”、“神思”等,都是借助想象暂时摆脱现实自我的束缚向虚构自我寻求庇护的体验。无论是梦是醒,庄周都可戴着蝴蝶的面具,假装忘却自我的身份,假装相信自己是蝴蝶的事实为真,想象关于他这只蝴蝶的无限虚构事实,在白日梦的乌托邦里借着假扮获得审美愉悦。中国古代审美文化是重“意境”的文化,但“意境”并不是虚无缥缈、深不可参的,假扮式的精神模仿就是意境所由生的具体途径。正如观看写意画的欣赏者假装自己便是画中那尾灵动游水、自由吐纳的鱼,正如赏玩盆景的文人假装自己正是树荫下品茗对弈的隐士,正如聆赏《高山流水》的听众假装自己正与知音端坐凉亭之中欣然汲取峭壁飞瀑送来的清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审美习性所携带的是千年以降传承自“羊人为美”的假扮基因,中国古代审美文化所推崇的“心与物游”的体验实质上是作为精神模仿的假扮游戏。
[责任编辑:刘春雷]
“Yang Ren Wei Mei”and the Prosperity of Make-Believe in Chinese Aesthetic Culture
LIU Xin-tian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The essence of make-believe is an imagination-based mental simulation,which stems from ancestors wearing decoration on head pretending to be gods in ancient religious ceremony as shaman,in order to pray for living,health and winning in conquest.The make-believe factors inside ancient religious ceremony had been brought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from ceremony to literature and arts,as well as games and artifacts.According to the paradigm of make-believe,Chinese artists prefers aesthetic atmosphere to resemblance to represented objects.Thus,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rts shows similar qualities with the game of make-believe,which pursues freedom as aesthetic pleasure.
“Yang Ren Wei Mei”;aesthetic culture;make-believe;play;mental simulation
B 83-092
A
1002-3194(2014)02-0058-06
2013-02-27
刘心恬(1983- ),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密歇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