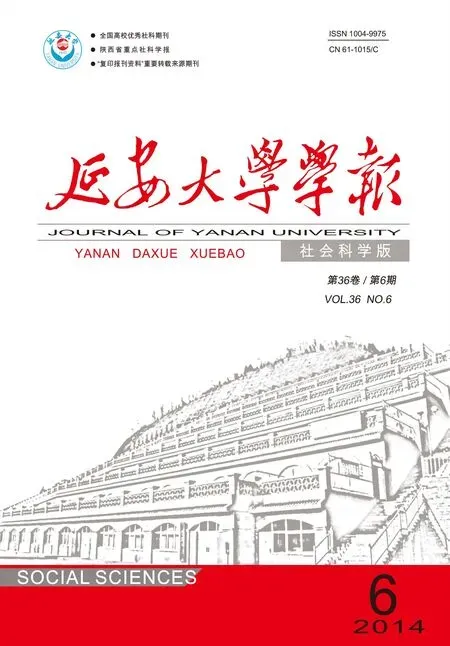从“文学风格”到“审美体验”
——基于朗加纳斯、柏克、康德崇高理论文本的分析
2014-03-06李惠
李 惠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在西方文论史上,最早探讨崇高理论的是古罗马的朗加纳斯,由此,人们通常认为西方崇高理论源于朗加纳斯的《论崇高》。其实,只要我们深入朗加纳斯、柏克、康德等人的崇高理论文本,梳理一下他们各自的崇高理论就会发现,后世美学家柏克、康德等人关于崇高的论述与朗加纳斯《论崇高》中所说的崇高有着很大的差异,一为文学风格,一为审美体验。虽都是心灵之产物,一个在创作者之心,一个在欣赏者之心。
一、朗加纳斯:主体心灵创造的文学风格
在《论崇高》中,朗加纳斯多次直接称崇高为文章风格,他说,“修辞格如果使用得当,会为文章的崇高风格增色不少”[1]34。“修辞格具有一些特殊的天然品质,可以增强文章崇高的风格”。[1]37“崇高的风格有五个源泉”。[1]12“崇高、强烈的风格更应该适用于有着夸张和热烈感情的文章中”。[1]22这众多关于崇高的表述表明,朗加纳斯把崇高看作是一种文学风格进行论述的。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之上,朗加纳斯运用了大量篇幅,从修辞学、雄辩术的角度探讨作家如何创造出具有崇高风格的作品,以及如何运用各种修辞格增强文章崇高风格,以增强雄辩气势与说服力。譬如,他认为,铺张这种修辞格就能创造出崇高风格,增强雄辩的气势,他说,“将老生常谈的东西重新加以修辞,或是故意夸大要论述的事实或论点,或是铺陈事实,或是激发感情”就可以达到铺张的效果,当“崇高的词句一个个滚滚而来,气势随之不断增加。”[1]24同时,设问也能增强文章或论辩的崇高感,从而使文章更具说服力,因为“这种一问一答的转换,加上对自己问题的回答就好像是面对别人的质疑一般,使得他的语言显得更为崇高,并且更有说服力。”[1]38而且,“这种设问并回答的方式也会让听众误认为,每一个事先思量过的问题都是一时间脱口而出的。”[1]39使观众折服。
此外,倒装法、叠叙法(单复数互变、复数变单数、时态的互换、人和人称的转化)、隐喻、俗语、迂回、夸张、接续词省略、对比与明喻等修辞格都可以产生崇高的效果,增强雄辩的气势,产生无可辩驳的说服效果。因为“崇高的语言对听众的效果不是说服,而是狂喜。一切使人惊叹的东西无往而不使仅仅讲得有理、说得悦耳的东西黯然失色。相信或不相信,惯常可以自己做主;崇高却起着横扫千军、不可抗拒的作用:它会操纵—切读者,不论其愿从与否。”[2]122不仅如此,朗加纳斯甚至认为句子成分的合适搭配往往会弥补诗人先天的不足,即使是“那些没有崇高的天赋”、“没有雄浑的才华,在大部分时候只是使用些普通的流行词汇,缺乏非凡的联想”的散文作家或诗人,只要“他们尽力将这些词汇按照合适的顺序组合,也会获得成功与卓越的反响。”[1]68-69这就是说,崇高的效果就是行文材料的组织、句子成分的合适搭配、铺张、设问等各种因素的有机统一。因为“当崇高的文章中各个部分被分解开,文章的崇高也会随之各散东西”。[1]68当然,“不合时宜的冗长”、“肤浅的表达”等也会降低崇高的效果,有损文章崇高的风格。
不过,在朗加纳斯看来,导致文章崇高风格最主要的源泉不是修辞技巧的运用,而是主体心灵的创造。在《论崇高》中,朗加纳斯论述了崇高风格的五个来源:即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情感、运用藻饰的技巧、高雅的措辞、完整的结构。五个要素尽管都可以导致崇高,但最重要的还是作家伟大的思想、高尚的人格。在《论崇高》一开篇,朗加纳斯就指出:“所谓崇高,不论它在何处出现,总是体现于一种措辞的高妙之中,而最伟大的诗人和散文家之得以高出倚辈并获得不朽的盛誉,总是因为有这一点,而且也只是因为有这一点。”[2]122这就是说,伟大的诗人和散文家,他们之所以获得不朽的盛誉就在于他们文辞的高妙,而这文辞的高妙乃是源自伟大诗人和散文家伟大的思想、旷达的胸襟。因为“一个毫无装饰、简单朴素的崇高思想,即使没有明说出来,也每每会单凭它那崇高的力量而使人叹服。”[2]125而且,“真正的思辨只有胸襟不卑鄙的人才有”。那些“把整个生活浪费在琐屑的、狭窄的思想和习惯中的人是决不能产生什么值得人类永久尊敬的作品的。……卓越的语言,自然属于卓越的心灵。”[2]126因此,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2]122从朗加纳斯关于崇高的诸多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论崇高》通篇都是从文学风格的角度来论述作家怎样凭借伟大的心灵品格,借助修辞格、行文材料的组织等技巧创作出具有崇高风格的文学作品。整个一部《论崇高》,我们似乎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部修辞学、风格论专著来读,崇高实在就是一种文学风格,是作家伟大思想借助诸多修辞表达在文学中的显现。
据波兰美学家塔达基维奇的《西方美学概念史》载,在西方,“崇高的概念形成于古代的修辞学之中”,“被认为是雄辩术三种风格之中最高雅的一种”,“这种风格也被称作是雄浑(grandis)和庄重(gravis)”。[3]所以,西方古代的修辞学、诗学中经常讨论到雄浑的风格,也即崇高。很显然,朗加纳斯沿袭了西方古代修辞学、诗学中关于崇高风格的传统观点与古罗马修辞学“以修辞助雄辩”的传统,深刻论述了创作主体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激动的情感、修辞技巧等对文章崇高风格的贡献,崇高乃雄浑的文章风格。
二、柏克:立足于感性经验的审美体验
18世纪,柏克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中以其经验派美学的一贯传统,从人性、生理、心理角度,以感觉、情感和情绪为出发点对崇高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探究。在论及崇高时,柏克首先阐述了崇高的来源,他说:“凡是能够以某种方式激发我们的痛苦和危险观念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以某种表现令人恐惧的,或者那些与恐怖的事物相关的,又或者以类似恐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事物,都是崇高的来源。”[4]36这表明,在柏克看来,崇高并非是主体心灵自然生发的,而是由外在于人的客体对象的某些特征的激发而产生的。譬如色彩的晦暗、力量的巨大、体积的庞大、数量的无限等等,繁星闪烁的夜空、巨大的瀑布、猛烈的风暴、隆隆的雷声之所以能让人产生崇高感,原因即在于其数量上的无限与力量上的无穷令人大惊失色,不仅如此,柏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沉寂、困难、孤独、黑暗、空虚、寂静、声音、间隔性、突然性等都可以产生崇高。用柏克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是能够见到的恐怖事物,无论是否尺寸上巨大,都会令人产生崇高感。”[4]51所以,他认为,“无论任何情形之下,或隐或现,恐怖都是崇高的主导原则。”[4]50正是基于此,柏克认为,就产生崇高的效果来看,“一座漫坡皆绿的大山在这方面完全不如某座昏暗、阴沉的山;乌云密布的天空比碧空万里要更令人感觉震撼;黑夜比白天要更为崇高和庄严”[4]71。
恐怖感何以会令人产生崇高?柏克认为,客体事物的恐怖性给人的感官和心灵以强烈刺激与震撼,使得我们心中只剩下所面对的对象,而不会注意到其他事物。客体对象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迅速裹挟着我们,容不得你进行任何理性分析便在心灵中唤起一个伟大和畏惧的感觉,一种欣喜的恐惧感,也即崇高感。当然,恐怖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转化为崇高感。“如果危险或者痛苦太过迫近我们,那他就不能给我们任何愉悦,而只是恐惧;但是如果保持一定的距离,再加上一些变化,他们或许就会令人愉悦。”[4]36也就是说,崇高源自本身可怕而使人产生恐惧感的对象,但这些恐怖的对象要成为崇高,必须不对人构成真正的危险,从而能使人走出惊惧,即人要处于安全地带,似乎要受到危险而其实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危险。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中,恐怖情绪才会转化为一种类似于瞬间转危为安的欢愉之情。这种感觉源于恐惧,但又超然于恐惧,唤起人们的惊赞与敬畏。
虽然柏克未能就崇高范畴给出特定的美学定义,但从其著作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柏克是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来谈论崇高。因为,柏克认为,崇高不具有功利性,在他看来,实用而不具危险性的事物是不能产生崇高感的。他以被阉割的公牛为例,认为一头被阉割的公牛虽具有巨大的力量,且非常实用,但因其不具有任何危险性而丧失了崇高。而一头未被阉割的公牛的力量有着强大的破坏性,且在实际工作中几乎没有任何实用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公牛效用的观念完全消失了。此时,“关于一头公牛的观念是伟大的,在对崇高的描述中占有一席之地,比较起来更令人精神振奋。”[4]57同理,当马被当作有用的牲畜用于耕地、拉车时,并无崇高感可言,但是,当“它的喷气之威使人惊慌,它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马的有用性一面不见了,而恐怖感与崇高感一起涌现。”[4]57也就是说,当把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对人所具有的现实伤害力消除掉,使它变得实用时,也就破坏了它原本所具有的崇高。由此,柏克指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力量仅仅是实用性的,用来为我们的安逸或者愉悦服务,那么它就不会是崇高的。”[4]57这看似较为极端、绝对的表述凸显的正是崇高在美学意义上的非功利性与自由性。
此外,与朗加纳斯推崇创造崇高技巧不同的是,柏克强调的是源于自然特性而非人工雕琢的崇高。在柏克看来,过多人为的修饰加工不但对崇高效果无益,反而会损害崇高。譬如,巨大的石头随随便便堆砌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粗糙感,就常常能给人以崇高的印象,而这种崇高的印象恰恰是因为其自然而然的天然性所导致。倘若对其进行一番人工造作和特意安排,非但不能产生崇高,反而会削弱其原本应有的崇高感。所以,柏克认为,在艺术中,诸如庙宇、宫殿等建筑的宏大规模,修饰和装帧的朴素自然、甚至粗糙最能引起崇高感。如果对其进行过分的人工加工,用雕刻、镶嵌、壁画等过分地装饰,反而有碍于崇高感。
总之,柏克以欣赏者惊惧的心理感受为出发点,从客体恐怖性的角度探讨了导致崇高的各种因素,指出崇高乃是由事物的恐怖性所激发的欣赏者惊赞的心理感觉,具有无功利性的特征,使崇高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审美体验。
三、康德:理性超越感性理念的审美体验
康德在吸纳、借鉴柏克崇高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了人类感性经验的有限性,因为,“在我们的想象力里具有一个进展到无限的企图,而我们的理性里却要求着绝对的整体作为一个现实的观念,于是我们对感官世界诸物的量的估计能力的不适性恰正在我们内部唤醒一个超感性能力的感觉”。[5]89所以“真正的崇高不能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里,而只涉及理性的观念。”[5]84由此将崇高提升到超越感性理念的理性层面。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将崇高区分为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并认为数学的崇高是人的想象力与认识能力相联系而产生的,是那种“绝对大的”东西所引发的。“崇高是一切和它较量的东西都比它小的东西”,[5]89也即当一个客体对象在数量上、体积上无比巨大,远远超出我们感官所把握的范围时,人们仅凭感官无法把握客体对象的整体性,譬如浩淼的星空、无边的大海,辽阔的宇宙。面对这些无形式的客体对象,我们的感性能力无能为力,无法对其进行整体直观。但是由于想象力具有进展到无限的企图,于是主体的超感性能力——理性能力被唤醒,正是这种被唤醒的理性能力使人们的认识具有了进展到无限的可能,似乎感觉到自己把握了感性能力无法把握的客体对象,从而产生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感。力学的崇高则是想象力与欲求能力相联系而产生的,是由对象无比的威力所导致的。诸如闪电雷鸣、飓风怒涛之类,当我们面对此种完全超出我们感官感知力与想象力的无比巨大的力量时,固然可以“发现我们的局限性、但是仍然在我们的理性能力里同时见到另一种非感性的尺度,这尺度把那无限自身作为单位来包括在它的下面,对于它,自然界中的一切是渺小的,”自然“威力之不可抵拒性虽然使我们作为自然物来看,认识到我们物理上的无力,但却同时发现一种能力,判定我们不屈属于它,并且有一种对自然的优越性”。[5]101换句话说,自然威力的不可抗拒性虽然使我们认识到自我物理上的局限性,但同时却唤醒了我们内心的理性能力,超越了感性理念,使人感觉到自我独立于自然之外、超越了自然,认识到我们不屈从于它,从而产生一种超越自然的优越感。
显然,无论是对数学的崇高分析还是对力学的崇高的论述,康德的崇高理论都超越了柏克立足于感性经验描述的崇高,已经上升到了哲学上的规定。认为是我们的“思想样式把崇高性带进自然的表象里去”,[5]85自然在我们的审美判断里被认定为崇高不是由于它引发了我们内心的恐惧,而是因为它唤醒了我们内心超感官的力量——理性能力。
在此基础上,康德对崇高感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康德认为,美的对象因为其外在形式的有限性与合目的性,是直接令人愉快的。而崇高的对象因其外在形式上的无限性或是内在力量的无穷性远远超出了主体感官把握的范围,人们在面对这些对象时,起初内心会产生一种力所不能及的挫败感或是令人恐惧的恐怖感,但因其并未真正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继而,人在理性能力的作用下会产生一种超越自然物之上的优越感,也即崇高感。它“是一种仅能间接产生的愉快”,需要“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加强烈的喷射”。[5]84康德指出,崇高感不同于美感,它不是一种直接的愉悦感,而是经由感官震荡的痛感转化而生的间接快感,先带给人一种不快,之后再让人产生愉悦感。只不过这之前的不快和之后的愉悦感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是由于感官受到震荡,似乎生命力受到威胁而又并没有受到真正威胁时由痛感转化而来间接快感,显现出对柏克感性经验崇高的继承与超越。
可以说,康德很好地继承了柏克美学意义上非功利性的崇高理论,并将其由感性经验的广度引向了超越感性理念的理性深度,为后世美学家研究崇高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世美学家席勒、叔本华等人所论及的崇高实质上就是柏克、康德审美体验的崇高。譬如,席勒在其《论崇高》里认为,崇高是人的理性本质的胜利,既使人超越外在的自然,又使人超越自身的感性,可以说是对康德所谓“超感性能力”的进一步发挥。叔本华则直接继承了康德的崇高理论,认为崇高乃是观赏者意志受到无法抗拒的优势力量的威胁时极力地脱离它们,进而对那些使意志感到可怕的对象进行静静地沉思时对自己意志的超越。
总之,通过对朗加纳斯、柏克、康德崇高理论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崇高理论从文学风格到审美体验的发展演变。古罗马朗加纳斯的崇高是文学风格论意义上的崇高,其论述是基于作家如何借助伟大的思想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或创造出具有崇高风格的文学作品而展开的,他看重的是艺术家伟大的思想与导致崇高风格的技巧。而柏克、康德等人是从美学意义上审美体验的层面展开对崇高的探讨,他们抓住了明确的崇高观念,指出了崇高的无功利性,认为令人恐惧而又不对人的安全构成真正威胁的自然对象是崇高形成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崇高本质上是由对象的宏大或力量无穷的气象激发的欣赏者的惊赞或是自我肯定。这一界说也成为后世美学家探讨崇高理论的核心所在。可以说,后世美学家关于崇高的论述实际上是柏克、康德美学意义上的崇高,而非朗加纳斯文学风格意义上的崇高。
参考文献:
[1][古罗马]朗吉努斯,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美学三论:论崇高、论诗学、论诗艺[M].马文婷,宫雪,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2]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3][波兰]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M].褚朔维,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231.
[4][英]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M].郭飞,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