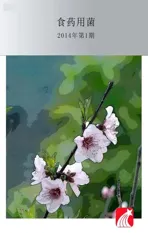对明代《菽园杂记》所引香菇栽培史料的研究回顾和补充
2014-03-05芦笛
芦 笛
对明代《菽园杂记》所引香菇栽培史料的研究回顾和补充
芦 笛
(伦敦大学学院)
明陆容《菽园杂记》引用了一则关于香菇栽培技术的资料,注明出自《龙泉县志》。前贤对于究竟是那一时期的《龙泉县志》产生过两种不同的意见。本文首先对相关史料加以回顾,然后引述前贤的观点,同时补充必要的资料,认为张寿橙先生的观点扎实可靠,即陆容所引用的《龙泉县志》是南宋何澹于1209年修纂的嘉定《龙泉县志》。
菽园杂记;龙泉县志;香菇;陆容;何澹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引用了一段注明出自《龙泉县志》中关于香菇栽培的文字,是中国食用菌栽培技术史上极其重要的史料。然而关于该引文的具体出处和年代,学界有不同意见。本文试在相关的史料基础上,对过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加以回顾,并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评论。
1 陆容、《菽园杂记》和香菇栽培史料
陆容(1436—1494),字文量,号式斋,江苏太仓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官至南京主事、兵部职方郎中、浙江参政等,著有《菽园杂记》15卷和《式斋集》38卷[1~3]。关于《菽园杂记》的成书年代,因书中卷15提及“甲寅六月六日”(1494年7月6日),而该年即陆容之卒年,可知此书最后之写定即1494年[4]。《菽园杂记》卷14录有一段香菇栽培史料,如下:
“香蕈,惟深山至阴之处有之。其法,用干心木、橄榄木,名曰‘蕈樼’。先就深山下斫倒仆地,用斧班驳剉木皮上,候淹湿,经二年始间出,至第三年蕈乃遍出。每经立春后,地气发泄,雷雨震动,则交出木上,始採取。以竹蔑穿挂,焙干。至秋冬之交,再用工遍木敲击,其蕈间出,名曰‘惊蕈’。惟经雨则出多,所制亦如春法,但不若春蕈之厚耳。大率厚而小者,香味俱胜。又有一种,适当清明向日处,间出小蕈,就木上自干,名曰‘日蕈’。此蕈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蕈用日晒干,同谓之‘日蕈’,香味亦佳。”
对于腕表而言,同轴擒纵系统可减少机心内部的摩擦,提高机械效率,保证腕表的长期耐用性。对于消费者而言,同轴擒纵系统可保证腕表在更长周期内的精准走时,延长了腕表的保养周期。
在这段文字之前,陆容还引了4则分别关于“五金之矿”、“青瓷”、“韶粉”和“采铜法”的资料,并注明“已上五条,出《龙泉县志》。银铜、青瓷,皆切民用,而青瓷尤易视之,盖不知其成之之难耳。苟知之,其忍暴殄之哉!‘蕈’字原作‘葚’,土音之讹,今正之。又尝见《本心斋蔬食谱》作‘荨’,尤无据。盖《说文》、《韵会》皆无‘蕈’字,《广韵》有之。”[5]事实上,《说文解字》中是有“蕈”字的[6]。根据注文,可知在《龙泉县志》原文中,香蕈的“蕈”字写作“葚”。引文中所述香菇栽培技术,前人已有详析[7],兹不赘述。那么,陆容《菽园杂记》所引用的《龙泉县志》,究竟是历史上哪一种《龙泉县志》呢?
2 宋、明两朝之《龙泉县志》

3 对前人研究的回顾和补充
“今山中种香蕈,亦如此法。但取向阴地,择其所宜木(枫、楮、栲等树),伐倒,用斧碎斫成坎,以土覆压之。经年树朽,以蕈碎剉,匀布坎内,以蒿叶及土覆之,时用泔浇灌,越数时,则以槌棒击树,谓之‘惊蕈’。雨雪之余,天气蒸暖,则蕈生矣。虽踰年而获利,利则甚博。采讫,遗种在内,来岁仍发复。相地之宜,易岁代种。新采趁生煑食,香美;曝干则为干香蕈。今深山穷谷之民,以此代耕;殆天茁此品,以遗其利也。”[23]
类似的观点亦见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食用菌百科》[21]。其中提到了《菌谱》佚文,以其所记栽培技术简陋,而引文却述之较详,否定了出自南宋嘉定《龙泉志》的可能。但是该《菌谱》佚文现已被证明并非佚文,而是出自明方以智的《通雅》(约刊行于康熙七年[1668])[22],从时间上看,自然不能再作为早期资料和《菽园杂记》之引文作比较。另外,古人信息交流不如现在便捷,知识的积累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层累模式,加之技术的保密和多地区起源,以及古代作者并不都是食用菌栽培技术专家等因素,这就是为什么《通雅》中对食用菌栽培的记述反而不及《菽园杂记》详细的主要原因。文字记载中信息的详略程度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主证。事实上,在元人王祯(1271—1368)所著《农书》中,虽采用的栽培技术有所不同,但也较为成熟和细致,且注重惊蕈:
“《菽园杂记》引据的《龙泉县志》,从时间上推断,当然不可能是嘉靖志或万历志;再从栽培方法和技术发展水平来推断,《菌谱》佚文所述台州栽培方法,虽然具备了砍花法的雏形,但仍不够成熟,而《菽园杂记》中的栽培方法,已臻至成熟,直到晚近,其法仍为菇民所沿袭,少有更新。因此,《菽园杂记》所据也不可能是嘉定志,而只能是正统志,这一推断若能成立,我们将龙泉香菇栽培业的形成,系于明代初年,大体上是接近事实的。”[20]
陈士瑜先生认为陆容的引文出自那部不知撰人的明前期的《龙泉县志》:
总而言之,肌理作为一种新的绘画语言,就应该在绘画作品中体现的恰如其分,不多不少,不偏不倚,这样才能使肌理在工笔花鸟画中得以继续发展和创新。
无独有偶,王菱菱在研究宋代铜矿开采冶炼技术时,也曾对《菽园杂记》中引自《龙泉县志》的资料进行过独立的考证。虽然王文只提及南宋嘉定《龙泉县志》和明嘉靖《龙泉县志》,且弄错了前者的作者(误作“陈百鹏”撰),但同样给出了论证:
张寿橙先生则主张《菽园杂记》之引文出自南宋嘉定《龙泉县志》[25,26],并给出了证据:
宋、明两朝,题名《龙泉县志》的共有4部,均已亡佚:嘉定《龙泉志》(6卷,南宋龙泉何澹纂,修于1209年)、嘉靖《龙泉县志》(20卷,明龙泉叶溥、李溥纂,修于1525年)、万历《龙泉县志》(明怀远夏舜臣纂,修于1598年),以及一部不知作者的《龙泉县志》(9卷)[8-13]。其中,嘉定《龙泉志》或题“《龙泉县志》”,增“县”字,作者何澹(1146—1219),字自然,浙江龙泉人,乾道二年(1166)进士,所在何氏家族系宋代龙泉乃至浙东地区的名门望族,除《龙泉志》外,还著有《小山集》[14,15];最后一种《龙泉县志》则录于明人杨士奇等人编定于1441年的《文渊阁书目》之“新志”类[16],而该书目“新志”类收录之地方志书除《安南志略》修于元代外,余皆修于永乐(1403—1424)至正统六年(1441)年间[17~19]。从成书时间上看,只有这两部《龙泉(县)志》是陆容所能得见的。那么到底是其中哪一部呢?
采用动力学求解器进行仿真,总仿真时长为0.000 2 s。计算结束后分析导线仿真模型对于方案2设定的外部加载的响应,提取芯棒中心单元绘制应力时程曲线,如图10所示。由图10可以看出:在加载过程开始后,芯棒、外层铝股的应力快速上升,很快达到最大值,即达到最大应力状态;而后随着时间推移,铝股间出现相互作用,应力出现震荡并逐渐达到稳定。
大海子水库新建涵洞、闸井工程总投资284.92万元,其中建筑工程、临时工程、独立费用所占比重较大。经过经济评价,本工程在经济上合理可行,且项目投入使用后各受益方需要分摊费用,农业灌溉作为最大的受益方完全可以承受新水价,因此该项目实施有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元朝国祚短暂,去宋不远;据其描述,该技术已较成熟,必定是经过了较长时期的实践发展而来。陈士瑜先生也认为《农书》中的种香菇法是对“唐末或五代初(9世纪中期至10世纪初)中原地区种香菇方法的继续和发展”[24],可备一说。
除了林下作物,麻类产品还被应用到主粮的生产之中。据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副所长王朝云介绍,目前,全国水稻产区的水稻种植普遍采用机插秧,而机插水稻要成功,育秧是关键。在传统育秧中,由于育秧盘运输不便、散秧多,机插秧过后,需要人工补插秧,十分影响劳动效率。
“处州原名括州,唐大历十四年(779年)‘以括州犯太子名,改为处州,’两宋时期一直沿袭此名;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即宋端宗景炎元年)攻克南宋两浙路地区,遂改称处州为‘处州路’;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部攻克处州路,先改名为安南府,‘寻曰处州府’。上述材料证明,符合《龙泉县志》所述‘处州’称呼的不是元、明时期,而是唐大历以后至南宋端宗景炎元年的近500年时期。因此,《龙泉县志》的写作时间必定在元代以前。
……
据《宋史》卷192《兵志六·建炎后砦兵》记载:‘处州二砦(砦是‘寨’的异体字):管界、梓亭。’这一记载证明,梓亭寨始设于南宋建炎时期,是驻扎军队的营寨。另外,明代的《嘉靖建宁府志》卷20《古迹》中也明确提到:‘梓亭寨,在(松溪)县北七十里,即处州龙泉县松源乡之地,宋时建,兼管龙泉、遂昌、松溪、政和四县境。’依据梓亭寨的设置时间,我们最后可以确定《龙泉县志》撰于南宋。”[4]
如果说引文中“处州”一词还可能是元代“处州路”和明初“处州府”的省称的话,那么关于“梓亭寨”的设置和行政区划的情况就成了论证的焦点。按,明黄仲昭《八闽通志》(成书于1486年)卷80《古迹》篇载有“梓亭寨”,云:“梓亭寨,在县北七十里,即处州龙泉县松源乡之地,界龙泉、遂昌、松溪、政和四县境。宋时建,元改隶龙泉县,后废。”[28]可见在1486年时,“梓亭寨”已是古迹;而且“梓亭寨”是属于松源的。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4在“庆元县”条下载:“梓亭寨,在县西,宋置梓亭巡司,元因之,后废。”[29]其中“巡司”即“巡检司”之简称,属于一种主要在武装和治安方面发挥作用的基层组织;而“梓亭寨”之所以被列在庆元县内,是因为松源是庆元县的治所。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44《处州府》篇载:“庆元县,……本唐龙泉县地,宋置庆元县,治松源乡,因纪年为名,属处州;元因之入龙泉县;十四年复置。”[30]《明史•地理志》在“庆元”县条下注云:“洪武三年三月省,十三年十一月复置。”[31]。又光绪《庆元县志》卷1载:“宋宁宗庆元三年,吏部侍郎胡紘请于朝,以所居松源乡置县治,因以纪年为名。”可知,庆元县建县于庆元三年(1197)[32],以年号得名,其后虽在洪武三年(1370)并入龙泉县,但又于洪武十三年(1380;按,《大明一统志》谓“十四年”复置,不确)复置。因此,“梓亭寨”在1380年以后是属于庆元县的,也就不会出现在永乐(1403—1424)至正统六年(1441)年间修纂的《龙泉县志》中。这一点,张寿橙先生已经指出。此外,《明史•地理志》在“处州府”之“龙泉”县条下注云:“南有庆元巡检司”[33]。可知在明代(至少1380年以后),龙泉已经没有“巡检司”的设置了。而据《八闽通志》,即使是庆元梓亭寨的巡检司,在1486年时也是久已废弃的情形,俨然成了“古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陆容《菽园杂记》所引《龙泉县志》当即南宋何澹所撰的《龙泉县志》。在吴学谦和陈士瑜先生合撰于2002年的《中国香菇栽培技术的变革与发展》一文中,也开始接受南宋《龙泉县志》之说。
4 小 结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引用了5段出自《龙泉县志》的文字,最后1则涉及香菇栽培技术,前人或认为其出自南宋嘉定《龙泉县志》,或认为出自明正统《龙泉县志》,且各自都作出推断和论证。在前人论证的基础上,笔者经过核查引文其余部分中的地名“梓亭寨”的行政区划变迁,以及龙泉和庆元县的建县过程,方知“梓亭寨”早在1197年就随着松源乡被划入庆元县;其后庆元县虽在洪武三年(1370)又并入了龙泉县,但自1380年以后即再次置县,终明之世未复变动。而且至少在1380年以后,龙泉就没有了“巡检司”的设置,而庆元县梓亭寨的巡检司到了1486年也因久废而成古迹。因此,陆容所引的《龙泉县志》,只能是南宋何澹撰的嘉定《龙泉县志》(或称《龙泉志》)。
[1] (清)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433, 2469, 7343.
[2] 昌彼得, 等. 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78: 567.
[3] 伍跃. 谈《菽园杂记》十五卷本[J]. 文献, 1987, (4): 240-246.
[4] 王菱菱.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所引《龙泉县志》的作者及时代——兼论宋代铜矿的开采冶炼技术[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 (4): 96-101.
[5] (明)陆容. 菽园杂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78-179.
[6] (清)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36.
[7] 张寿橙, 赖敏男. 中国香菇栽培历史与文化[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115-120.
[8] 洪焕椿. 浙江方志考[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448-449.
[9] 林平, 张纪亮. 明代方志考[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167.
[10] 顾宏义. 宋朝方志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02.
[11] (明)薛应旂, 等. 嘉靖浙江通志[M]. 见: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第26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468.
[12] (清)顾国诏. 光绪龙泉县志[M]. 见: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665.
[13] 宋晞. 方志学研究论丛[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0: 54.
[14] 昌彼得, 等.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M]. 台北: 鼎文书局, 1984: 1265.
[15] 邓小南. 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50(2): 113-130.
[16] (明)杨士奇, 等. 文苑阁书目[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260.
[17] 李艳秋. 明文渊阁地方志收藏述略[J]. 图书与情报, 1998, (2): 11, 28-30.
[18] 张升. 明代方志数质疑[J]. 中国地方志, 2000, (3): 64-67.
[19] 巴兆祥. 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J]. 中国地方志, 2004, (4): 45-51.
[20] 陈士瑜. 中国方志中所见古代菌类栽培史料[J]. 中国科技史料, 1992, 13(3): 71-82.
[21] 黄年来主编. 中国食用菌百科[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7: 3-4.
[22] 芦笛. 关于日本《惊蕈录》所引南宋陈仁玉《菌谱》文字的考证[J]. 食用菌, 2013, (3): 75-77.
[23] (元)王祯著, 王毓瑚校. 王祯农书[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1: 110.
[24] 陈士瑜. 中国方志中所见古代菌类栽培史料[J]. 中国科技史料, 1992, 13(3): 71-82.
[25] 张寿橙. 中国香菇的砍花法栽培(连载)[J]. 中国食用菌, 1993, 12(2): 5-7.
[26] 张寿橙. 浙闽赣粤等省、区的香菇发展史(一)——浙江在香菇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J]. 浙江食用菌, 2010, 18(2): 50-52.
[27] 张寿橙, 赖敏男. 中国香菇栽培历史与文化[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80.
[28] (明)黄仲昭. 八闽通志(下册)[M]. 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891.
[29] (清)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4333.
[30] (明)李贤等. 大明一统志[M]. 台北: 台联国风出版社, 1965: 2957.
[31] (清)张廷玉, 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115.
[32] (清)林步瀛, 等. 光绪庆元县志[M]. 见: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574.
[33] (清)张廷玉, 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114.
S646.1
A
2095-0934(2014)01-0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