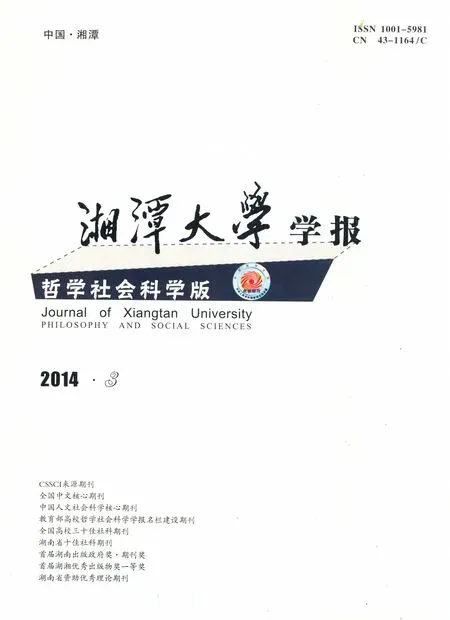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异国形象研究*
2014-03-04曹顺庆张莉莉
曹顺庆,张莉莉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它脱胎于影响研究,长期隶属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然而,形象学学科归属是否得当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1999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形象学归于追求实证性研究的法国学派是否得当的问题,[1]142出席会议的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谢弗莱尔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这一问题。这种困惑同样体现在比较文学教材的编写体例上。杨乃乔主编的教材虽然将形象学纳入影响研究,但却认为形象学包括了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即‘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所以,它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2]235陈惇等主编的教材则干脆将形象学归为平行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的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3]51同样,叶绪民主编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也将其划为平行研究:“形象学主要探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成因。”[4]35却又强调影响研究的实证性对于形象学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种模棱两可的困惑与尴尬,实际上折射出形象学学科属性的不明确性。在国外,长期处于影响研究名目下的形象学,使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异国形象,为什么在中国却遭遇了如此的尴尬与困惑?显然,此中大有深意。
我们认为,形象学应当重新归类为变异学,因为在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语境下,异国形象的塑造会受到诸如历史、审美、心理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此与真实的异国大相径庭,于是将形象学纳入影响研究的合理性不可避免地遭到诸多质疑,只有归类为变异学,才能得其所归焉。
2005年,在出版的《比较文学学》一书中,我们就将形象学从影响研究的体系下剥离开来,首次将它纳入变异学的研究范畴,这样做的学理依据是基于变异学理论的提出,“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将变异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5]30与追求可实证的影响研究不同,变异学追求的是同源中的变异性,异国形象属于对他国的文化或社会的想象,积聚着深刻的文化沉淀,是无法按图索骥去实证的,必然会产生偏离异国原型的裂变。我们从变异学的视角来审视异国形象,立足“异”的形象研究,便会发现形象研究早就涉及了当时尚未被察觉的变异,无论是与之相关的集体想象物还是套话都能从中找到异国形象的变异因子。因此运用变异学理论恰当地解决了形象学学科归属不当的问题,使得形象研究从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中突围,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比较文学新视野。
一、被遮蔽的变异:形象研究的缺失
早在19世纪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和科学主义精神盛行的法国,主张文学比较研究的学者就发现两国文学研究必然会涉及文学中的他国。在法国文学的先驱者斯达尔夫人看来,形象问题应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等层面糅合在一起加以关照,她特别推崇异国风光与异国情调便是例证。而师承斯达尔夫人文学思想的泰纳注重民族意志、心理以及性格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对后来的形象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被公认为形象学奠基人的卡雷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谈到他国形象就是“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6]19异国形象蕴含着一定的想象力,标示着个体或集体强烈的主观印记,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很难予以证实,因而这种影响关系不完全具有实证性。而基亚进一步阐明了卡雷的观点,他的《比较文学》专设一章“人民眼中的异国”来探讨异国形象。他沿袭影响研究的传统思路来研究异国形象,坚持准确地描述异国形象的流传需要依靠确凿的文学事实,事实罗列和对比是研究异国形象的根基,这种形象必须是明晰和确定的。但他也意识到了形象研究应转向,“不再追踪研究使人产生错觉的一般影响,而是力求更好地理解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的民族神话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的。”[6]19“个人和集体意识”混合着情感和主观的色彩,事实联系无法轻易获知,影响的边界并非明晰可辨,而民族神话的产生和发展却是仍然试图追踪溯源。卡雷隐隐约约察觉出形象研究的缺失,却无法找到最终的突破口。
由此可见,在最早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影响研究就已经涉及文学作品中的他国形象问题。影响研究往往会从异国的层面入手进行渊源考证,他国态度和评论必定会涉及集体想象,这明显超出了实证研究的领域。从变异学的观点出发,其实这就是一种异国形象的变异。遗憾的是,法国学派虽然意识到了异国形象与真实的异国不同,却拘泥于实证研究的一隅,没有站在理论的高度探究变异现象,而把全部的心思花在求同上,即这个异国形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真实的异国,一味地用实证的方法去研究非实证的异国形象,自然走入死胡同,以至于韦勒克批判形象研究已经从文学研究滑落至思想史研究。法国学派的形象研究在犹豫迟疑中向前缓慢发展,无法获得与同时期萌发的其他分支如流传学、渊源学等同等匹配的地位,最终错失了用形象研究为自己理论不足修正的机会,以致后来被美国学派击中要害,失去了在比较文学领域一度领先的文学研究地位。
早期的形象研究一度陷入实证性的漩涡,而后莫哈和巴柔将形象研究从实证的牢笼解救出来,他们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使形象学从20世纪的比较文学危机中及时脱身,在比较文学领域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充分利用形象学跨学科的优势,把接受美学、符号学、当代心理学以及哲学中的想象理论借鉴到研究中,极大地拓展了形象学的研究领域。
不同于将异国形象当作现实复制品的法国学派,后期的形象研究几乎抛弃完全实证的方法,从实证性的影响关系转向“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从复制式的形象到创造式的形象,非实证性色彩愈加浓烈,用文明的差异性否定异国形象的客观基础,企图建立一种可操作性的、程式化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生成模式,“但若因此而忽视了文学形象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忽视了每个作家的独创性,那就是忽视了一个形象最动人的部分,扼杀了其生命。这就有使形象学研究陷入到教条和僵化境地中去的危险。”[6]10我们再回到巴柔的理论里:“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6]155不妨将这里的“差距”理解为一种变异的表现形态,“他者”形象经过主体的自动筛选,将不符合自我意识的形象过滤掉,这个过滤过程正是一种变异过程。例如法国作家伏尔泰的学生塞南古,他从未去过中国,书本是他了解中国的惟一途径,所以他根据自己的体悟创造了想象的中国形象:一个理想化的对宗教极为宽容的国度,自然神论和美德的故乡。塞南古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儒教思想和自然神论有相通之处,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他不满国内的教士与政权相互勾结的现状,寄希望在中国找到一片人间净土,启发人们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中国作为被注视者一方,塞南古作为注视者一方,他所构筑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与现实的中国相差很远,殊不知,基于文化过滤与误读的异国形象,通过社会集体想象物而发生了变异。
二、异国形象通过社会集体想象物实现变异
形象学是一部关于异国的幻象史,我们按照本国社会需要重塑了异国现实,它是一种变异性的集体幻象,是对真实的异国的变异。莫哈认为,形象学研究的形象包含三重意义:“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6]25我们关注第一层含义,“异国”意味着存在一个参照系,即现实存在的他国,如果轻易地将异国形象视作对现实的复制,就容易朝着实证研究的方向偏执地走下去。而第三层则强调形象所展现的文学性,但文学却无法跟社会语境割裂开来,异国形象是由身处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家只是形象制作的媒介,不起决定性作用。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第二层的含义,真正创造了形象的是与民族、社会或文化相关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社会集体想象物”一词借鉴于法国年鉴学派,它包含的是整个社会对异国的看法,蕴含着相对于真实异国的偏离和变异,是不可实证的,它使异国形象研究的重心从辨别形象的真伪转移到形象的生成过程上,从而观察异国形象的变异是如何发生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异国形象属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而集体想象物是塑造异国形象的关键。如果将形象还原为社会集体想象物,我们可将社会集体想象物分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类形象。这里的意识形态形象指的是按照本国社会群体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本国社会群体将自我的社会价值观主观地投射到异国的身上,并整合想象的相异性的他者形象,以此来强化本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例如清代的很多诗文将日本人称为“倭寇”,大量作品描绘了倭患频发带来的灾难,此时小说里的日本人形象与灾难、可怕紧密相连,作家注重描绘日本人外貌的兽类化或妖魔化,以此来反衬其道德品质的丑陋,塑造了一种奇淫无比的倭寇形象。在中国人的集体想象中,倭人不论男女老少皆淫荡无比,这种认识在清代小说中通过模式化的情节表现了出来,并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形象是与倭寇两字密不可分的。作家对异国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集体想象物的制约,因而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象的投射物。又如英国作家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对中国充满敌意,借鲁滨逊之口对中国进行长篇谩骂,批评中国人懒惰愚蠢,跟英国人相比一文不值,利用中国负面的例子赞美他的祖国英国,这种结果是真实和想象脱节使然。这种有关中国的意识形态形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待中国态度的影响,注视者带着一副西方文化高高在上的有色眼镜,去审视中国人和一切有关中国的想象,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在笛福笔下悄然发生了变异。
与此相反的则是乌托邦形象,形象制作者们用与本国社会群体模式完全不同的社会话语塑造出来的异国形象,这是一种与其自身所处的现实根本不同的理想的他者社会,这种异国形象也总是表现出相异性。例如晚清外交家黎庶昌的海外游记《卜来敦记》,描述的是代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作者眼里的英国人悠闲惬意,逍遥快活,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繁华和悠闲的生活景象。这是作者所理解的英国,这样的英国并不是真实的英国,他没有看到此时底层的工人们正为自己的生计忙碌奔波,巨大的贫富差距隐藏在生活的表象之下,他将这种表象和自己先入为主的有关英国的文化想象相互重叠,构成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异国想象。这种西方的乌托邦形象对作者来说是一个他者,他将在中国难以实现的圣人理想投射在他者的身上,也暗含了对晚晴社会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反观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1907年中国纪行》中塑造的中国形象,[7]37-46作家以一种亲善与平等的心态观察和评价中国,他所描述的20世纪初的中国,与传统的西方人观察和描述的中国截然不同,既不是充满异域情调的神秘东方,也不是愚昧落后的东亚病夫。在他的眼里,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中国人民热情好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他的这种对中国形象的描写背离了其所在社会群体的既有模式,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起到了颠覆群体价值观的作用。
在为《关于“异”的研究》一书写的序中,乐黛云谈到:“如果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联成一道光谱,那么,可以说所有‘异域’和‘他者’的研究都存在于这一光谱的某一层面。”[8]2这说明经由社会集体想象物参与创造的异国形象,作家们总是赋予意识形态或乌托邦色彩,有意或无意维护或颠覆自我文化,体现出与真实异国的背离。异国形象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过度迷恋异国或过度诋毁憎恶,都是一种偏见和盲目。例如德国19世纪末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卡尔·迈对中国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和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在他的笔下里,中国是一个最落后、最肮脏、最没有意义的国家,中国人比印第安人还要落后,中国人衣服又破又脏,天生不爱干净,中国文化古老死板,中国人的思想是僵硬和干枯的。由此可见,社会集体想象物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已经经历了一个生产与制作的过程,是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在注视方的自我文化观念下发生的变异的过程”。[9]6形象的生成过程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无论是意识形态形象还是乌托邦形象,与作为形象之“原型”的异国本身相比,蕴含着某种相异性的特质,这二者之间必定存在相应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对异域历史文化现实的变异的结果,所以将形象学纳入变异学这一范畴来论述是妥当的。
三、误读——异国形象变异的深层原因
纵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不同国家以及民族的相互交流传递了多样的文化讯息,透过广阔的文化视野来审视异国形象便会发现,异国形象通常建立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体察和观照的基础上,形象接受国并非全盘接收,而是自动架设一道天然的文化屏障,将自身文化的特性融入到异国形象的塑造中,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是无法抹去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面,异国形象是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注视下塑造完成的,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和沟通,逐渐打破了原有文化的封闭状态,也带来了异国形象的变异,这是文学误读的产物。
所以,我们把形象的变异研究归入文化层面的变异。形象的变异归根结底源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经过文化想象中的过滤机制,异国形象在创造过程中产生了扭曲与变形,乃是异国形象误读的产物。所谓“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误读终究是难免的。但是误读并不是随意发生的,我们总会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选择符合自身需要的异国形象,对它进行改造与变形。以中西方文学和艺术中的狮子形象为例,[10]65-76西方文学和艺术中的狮子形象,大都象征着凶猛和高贵,《圣经》中便有大量此类形象的描述。而在中国的狮子,不管是装饰门庭的石雕狮子,亦或是过年渲染气氛舞弄的狮子,大都失去凶猛的本性,变成玩物之“犬”,完全是一副温驯可爱的狗的形象。李白的《上云乐》便有对狮子的描述“五色狮子,九葆凤凰,是老胡鸡犬,鸣舞飞帝乡”。那么,中国原本是没有狮子的,为何中国的狮子形象会偏离了狮子的生物本性,而最终成为有异于西方文化中的狮子形象呢?原来,狮子最早出现在中国是因为它是西域献给皇帝的贡品,专为皇帝献媚逗乐的玩物。狮子作为臣服归化的象征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君临天下的优越感,这注定了狮子会远离凶猛的天性。中国作为狮子形象的接受国,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出发,一步步改造成了温驯可爱的中国化的狮子形象。
按照莫哈的说法,“形象一词已被用滥了,它语义模糊,到处都通行无阻。所以思考一下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又大量存在的形式——套话——不无裨益。”[6]158套话是形象学中描述异国形象的一个术语,原指印刷用的铅版,引申为人们认识一个事物时的先在之见,后来被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指的是人们大脑中先入为主的观念。而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的套话则代表了人们对异国形象相对稳固的看法,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反复使用、用来指异国异族的约定俗成的词语。
套话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异国形象,高度浓缩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体察,文化误读是套话产生的基础,套话的生成及推广过程离不开它的积极参与。研究套话是形象研究中最基本、最有效的部分。所以我们通过套话来审视异国形象的变形和意义重构,探讨异国形象误读背后的文化心理蕴含。中国人对外国人形象的误读,以“洋鬼子”的套话最为典型;同样,西方也有类似的套话。以套话付满楚(Fu Manchu)为例。[11]281他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来源于英国作家罗默发表的小说《付满楚博士的秘密》,后成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角色。在此篇小说中作家塑造了一个邪恶、凶残、令人恐惧而又充满诱惑的中国人形象。单看他的外貌便是令人害怕的,他高瘦而狡猾,长着一张撒旦的脸和精光的脑袋,一双细长闪着猫一样绿光的眼睛,高耸的双肩,莎士比亚般的眉毛。付满楚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19世纪下半叶,欧洲文化中出现了黄祸论,说人类将被黄种人毁灭,一种既轻蔑又恐惧担忧的复杂情绪弥漫于其中,有关付满楚的套话便是欧洲自我对异国形象妖魔化、丑化的表现,也是体现了黄祸论思想的最彻底的典型。他曾在西方许多作家笔下反复出现过,20世纪30年代以后更被好莱坞搬上大银幕,成为邪恶和妖魔的化身。付满楚所代表的就是相对于西方的中国这个异域国家的形象,也是19世纪以后西方关于中国的典型的负面套话。
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是一面镜子,通过套话,既可审视他者,也可透视自我。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自我的双重功能,当强势文化凌驾于弱势文化之上时,此时的文化处于不对等状态,蕴含着异国形象的套话自然是负面的、消极的。强势文化试图借处于弱势地位的他者,塑造敌对的异国形象,来反衬自身文化的优越感。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跨文化对话,加强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去逐渐消解这些负面的套话形象,如中国佬约翰、异教徒中国佬、查理陈,这些或多或少不平等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套话。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套话的有效性以及文化的不对等性在逐渐减弱。不过,厚重的文化壁垒始终需要我们有效而耐心的文化对话才能得以实现。
总之,异国形象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创造,它的生成过程就是一种文化对异域文化的接受与变形的过程。把形象学纳入变异学的研究范畴,以异国形象的变异为立足点,既能弥补法国学派由于致力于可实证的同源性影响研究而忽视形象研究变异的缺憾,又能避免后期形象学一味追求固定化的研究模式,沉迷于文化研究探索之不足。纵观国内形象学研究,侧重点在于异国人物形象的研究,研究范围狭窄,可是形象本身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风物、景物描写、观念和言词等都可以成为关注的对象。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关注对象,将文本中的异国形象与客观的异国进行对比,通过其中的变异再去审视自我的价值观,去探求形象变异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内涵,加深和拓宽形象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彰显变异学普世、总体性的独特价值。
[1]张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2]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陈惇,孙景尧.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叶绪民,朱宝荣,王锡明.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5]曹顺庆.比较文学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6]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刘燕.中国之镜:《1907年中国纪行》中的中国形象[J].国外文学,2008(6).
[8]乐黛云.序[M]//顾彬.关于“异”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曹顺庆.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1).
[10]傅存良.李白《上云乐》中的狮子形象[J].中国比较文学,1996(2).
[11]姜智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M].济南:齐鲁书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