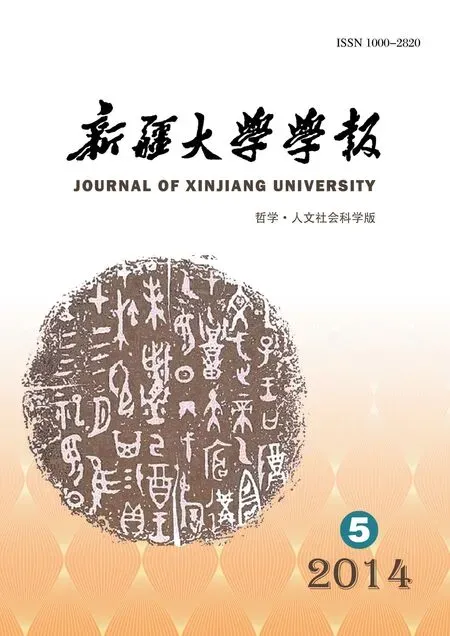扭捏作态的都市爱情—论李健吾戏剧改译本《说谎集》∗
2014-03-03安凌
安凌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在五四时期被热情推荐给中国的现实主义剧作家有两位,一位是易卜生,另外一位则是在英国大力介绍易卜生戏剧并被认为是英国的易卜生的萧伯纳。不过,“英国的易卜生并不是一位英国人,而是一位爱尔兰人。他也不是一位冷静的社会改革家,而是一位喜欢炫耀、妙语横生的社会批评家,一位一流的喜剧大师”[1]。他曾经努力像易卜生那样创作戏剧,但是并没有因此不顾戏剧的规律,因为他不相信任何抽象的戏剧,他知道戏剧性冲突必须是情感上的和活生生的。对于中国的改译者来说,从关注萧伯纳戏剧中的社会因素到关注其戏剧冲突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种过程揭示了改译者立场的变化以及改译剧目演出的成败。
一、萧伯纳的“新派娱乐喜剧”
改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在异质文化的跨文化交际中,误解和误读是不可避免的。误解也许更多是无意的,是源于两种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误读则可能更多是有意的,在接受美学看来,所有的阅读都是不同程度的误读,这些误读共同组成了对于作品内涵的无限靠近。而在文化的推介和引进中,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带有非常明确的目的,这种目的往往会造成以下两种结果:其一,传播者意欲传递给接受者的意义和接受者向传播物寻求的意义有差异,因而后者拒绝接受这种推介和引进;其二,对于同一个作家,在某个时期人们更多地认识他的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又往往突出了这位作家的某种形象特征,等这个时期过去之后,我们可能又会更多地认识他的另外一类作品,这类“新”作品则可能让他的形象大为改观、甚至让我们难以接受。这里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只是说明了时代的位移改变着我们接受的方式,当然也改变了我们对于一些作家的认识,所以,熟悉的大作家们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了,这种陌生的感觉带给我们好奇。以上这两种结果我们都能在萧伯纳戏剧在现代中国的改译和演出活动中看到。
“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十年间,萧伯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其竞争对手,成为跻身商业领域的唯一一位‘新剧作家’,因此对观众的影响是知识精英阶层所无法企及的,但是从他的第一部戏剧公演到获得如此成功,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期间他为了建立起商业演出的平台,做了许多有意识的宣传——更不用说冒险冲破当时可接受的界限了”[2]189−190。这里的界限就是指近似闹剧的喜剧。“自1904年至1907年,格兰维尔·巴克与J.E.韦德雷纳合作管理宫廷剧院期间,萧伯纳的作品开始走红,至少有11部戏剧上演,从而奠定了其‘新派’娱乐喜剧作家的坚实地位。”[2]190独幕剧How He Lies to Her Husband就是一部成功的娱乐喜剧,这种成功不仅体现于当时的舞台演出中,而且也体现在日后的传播方式变更中:它是第一部被录制成广播剧的萧伯纳戏剧,也是第一部被拍成电视剧的萧伯纳戏剧①Robert G.Everding,Shaw and the polular context,fro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orge Bernard Shaw,edited by Christopher Inn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
1935年,在《文学》第四卷第5号上刊登了由萧伯纳的How He Lies to Her Husband改译的剧本,名为《说谎者》。改译者李健吾在剧本之前登出了一篇类似于序言的短文,短文的写作日期是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八日,这段文字讲述了改译的缘起。其中有很多对于我们理解改译这一现象本身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实,20世纪30年代之后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剧本都大量增多,尤其是“难剧运动”的发展对于剧本的需求给翻译剧本的演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根据我的统计,英语独幕剧的翻译在整个现代阶段总数达到了73部,可是李健吾为什么不直接演出这些翻译的喜剧独幕剧,而要对剧本进行改编呢?他自己说之所以不能采用翻译本,是因为它会在演出中造成实际困难,就是观众对地名和人名的不熟悉会影响他们看戏。这里其实已经说清了剧本作为读物时不构成阅读障碍的因素,而在剧场演出时,也许就会成为障碍了!由于李健吾特殊的身份,即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戏剧评论家和改译者多重身份,他对于改译问题就有了独特的精到的看法。他首先说明,改译是因为剧本荒;剧本荒并不是没有剧本,而是指没有合适搬演的剧本,尤其是独幕剧;适合搬演的剧本条件有三:一是适于本剧团演员的角色分配;二是适合当天晚上演出的节目搭配和时间调度;三是没有人演过。李健吾特别说明,这只是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条件,其他条件没有一一说起。至于这个剧本的改译则是因为适于剧团演出的剧本一个也没有,所以众人讨论的结果是由他改译这出戏。考虑的出发点与上文对应,也有三:一是只需要两男一女三个演员;二是当时正在演出的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三幕悲剧《梁允达》,《说谎者》以“猗丽的城市生活景象”搭配《梁允达》“粗旷而单纯的情调”;三是萧伯纳此剧从未在中国演出过。他认为“一出戏的生命正好建筑在好些细小的过节上”,“独幕剧尤其如此”,“删去一点点动作,会失去无限的韵味”。但是他同时又忍不住说,他的这个“改动不大”的剧本《说谎集》已经“近似一篇创作”了。这里看上去有些自我矛盾。按照李健吾说的,他在尽量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改动了人名、地名、典故和“语气的自然”,我认为这里后两者的改动就是大改动。所以虽然这个剧的情节、人物身份、布景都没有改变,但是由于添加了属于中国文化的典故,又加之人物语气的自然,舞台上演出的已经是道地的“上海故事”了!
二、中国化的都市闹剧
《说谎集》是结局出人意料的一部独幕剧。一对情人的诗稿落在了丈夫的手里,为了让丈夫相信他们之间没有感情纠葛,“她”恳求“他”否认诗是献给“她”的。丈夫相信了这一点,但随即大怒,认为这是对于“她”的侮辱乃至于对于他们夫妻俩的轻视。当“他”最终忍不住说出真相时,丈夫转怒为喜,恳请出资出版这些诗稿。这部剧的喜剧性来自于一个天真的但是“成长的太快”的年轻诗人、一个虚荣心强烈得足以忘却自己的丈夫,和一个玩感伤的感情游戏的女骗子。在萧伯纳的喜剧世界中,女主角比起男主角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她们在与男性的较量中往往棋高一筹。在这部剧中,“她”既不漂亮也不聪明,甚至也不再年轻了,除去自以为是的美貌和优雅,所剩的其实就是做作。但是她却能使她的丈夫认为自己娶到的是最漂亮的女人中最漂亮的,认为所有上流社会的男人们见到了她都会把持不住;她还能使一个十八岁的美貌少年为她发狂,不仅写诗歌颂她的“美丽”、“崇高”,而且盼望着同她私奔。最终她不必自己出面,就使两个男人为她大打出手,而且又在瞬间为她握手言和。这样的人物关系和这样的结局真有些让人莫名其妙、啼笑皆非。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女人把两个男人玩于掌上,其实,让两个男人尤其是丈夫成为滑稽的笑料的,正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人们给虚荣心效的劳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然而却博得永恒的感激。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都围绕虚荣心而生,都不过是满足虚荣心的手段。虚荣心是以想象中别人对他的欣赏为基础的自我欣赏,所以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从而是比自私更自然、更普遍的先天的缺点······”[3]16所以,丈夫不能容忍其他人破坏他对于自己的想象:他娶了最漂亮的女人,他被其他男人所艳羡和妒忌,同时他们之所以不追求他的美人,是为了尊重他所以强自克制;少年不能容忍女人说出真相:他没有被“爱上”,他“爱上”的根本不是美女更不是女神!甚至,他写的诗歌“她”也从未读过一遍!“一个滑稽人物的滑稽程度一般地正好和他忘掉自己的程度相等。滑稽是无意识的”[3]11,当这种滑稽被剧作家有意识地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于舞台,却获得了动人的艺术魅力。因为在剧中不管人物的一言一行是多么有意识,“他之所以滑稽,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他自己所不认识的一面,有他自己所忽略的一面。只是因为有这一面,所以他才可笑。高度滑稽的话语是赤裸裸地显示某一缺点的天真的话语”[3]98。而我们作为观众去认识他那被自己所忽略的一面,我们既可以说看清了剧中人,也自然联想到自身,对自己进行反省。在我们和剧中人人性的相通之处,我们能够发现平时在日常生活中被我们忽略了的意义,这其实正是喜剧所具有的社会批判的力量!
戏剧情境由时(时间、时代)、空(场景)、事(故事情节)三者组合而成。其中,时空的转换能很好地突出改译本的地域性特征,再现民族生活的现实场景,为观众对“事”的接受提供了有效的物质前提。中国现代英语戏剧的改译多把大都市作为故事的发生地,例如上海。一则因为那里在战前是中国演剧活动的中心地区。二则因为上海有租界。抗日战争爆发后,租界成为文化荒漠中仅存的一点绿地。著名的改译本中,例如《少奶奶的扇子》、《梅萝香》、《荒岛英雄》等均把故事的发生地选在上海,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改译者对于洋场文化的批判,《说谎集》也不例外。
接下来,李健吾通过剧中人名的改动使戏剧情景与民族文化传统发生一定的联系。
在《说谎集》中人物出场顺序为:蔡惜红、邵罗茜(剧中说其英文名为Rose)、邵玉诚。
这里“惜红”作为年轻诗人的名字最令人叫绝!可以说这个名字引起了我们很多的联想,尤其才子佳人小说、鸳蝴派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都会因为这个名字浮上我们的脑海;而这位才子爱恋的对象却是一位如此平庸做作、比他年龄大一倍都不止的中年妇女,这就是喜剧效果的来源!人名的改动有时也与民族文化传统发生一定的联系。体现在剧本的台词中,两剧都有这样一段,当女主角发现诗稿丢失了,她觉得别人一定会根据她在此地独一无二的名字猜到诗是写给她的时,她自怨自艾。原剧:
She.How will they know!Why,my name is all over them:my silly,unhappy name.Oh,if I had only been christened MaryJane,or Gladys Muriel,or Beatrice,or Francesca,or Guinevere,of something quite common!But Aurora!Aurora!I’m the only Aurora in London;and everybody knows it.(下略)①此处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改译本:
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子(原文如此)不全在诗上写的好好的吗?倒楣的名子!我为什么不叫春兰,不叫秋香,不叫黛玉,不叫宝钗,不叫二丫头,哪怕再俗也好,却偏巧叫个罗茜!罗茜!上海就是我一个人叫罗茜,是人全知道。(下略)
这里的名字实际上有两类, 一类是Mary、Jane、Gladys、Muriel、Francesca,是英语中女性常用的名字,即类似于过去普通人家的春兰秋香二丫头;另外一类是Beatrice和Guinevere,前者即但丁《神曲》中的比阿特丽斯,后者是《亚瑟王传奇》中的王后奎尼薇,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专有名词,就如《红楼梦》中的黛玉和宝钗,提到这些名字会引起某个民族对于女性形象的特定想象。
此外,典故在这部剧的改译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说谎集》中关于《西厢记》一段对话是原剧中没有的,完全是李健吾的独创。原剧中诗人慷慨激昂地劝说“她”和自己私奔,拿起自己送她的花和戏票,说是问她丈夫借马车去看戏,然后就回到他的住处了。之后紧接着的是“她”问是否就告诉她丈夫他们要私奔了。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改译本插入了一段对于独幕剧来说比较长的对话,即“她”立刻问戏票是什么戏,回答是他们俩就看《霸王别姬》与《西厢记》,这次是《西厢记》。首先这出戏暗合了他们之间的偷情关系,其次诗人自况是张生(结尾处又出现了一次这种自况),把对方一个37岁无貌无德的已婚妇女比作莺莺!这种巨大的反差也带来了喜剧的效果。而“她”关于莺莺如果有个小姑子,《西厢记》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剧的奇谈怪论,以及之后对于姑嫂关系的恶毒语词不仅对于诗人的想象是一种反讽,而且也更鲜明体现了中国家庭关系特色。至于语气的自然,不仅体现在李健吾的翻译中,也体现在他添加的某些感叹句中②例:源语本:She’ll understand more harm than ever was in them:nasty vulgar-minded cat!改译本:她会把白的看成是黑的。天生的贱痞子!又如添加源语本没有的语句,当发现诗稿丢失,“她”非常紧张时,他:我还当什么了不得的事发生了呢!源语本没有这句。。
在李健吾作为序言的短文最后,改译者以近乎俏皮的语气自问自答,在上海能否有这样一出戏?尤其是有这样怪异的丈夫?他说他不准备告诉观众答案,让他们自己从戏中看出各自的答案。但是他又说:“在畸形发展的大都市里面,什么也是可能的”,即丈夫这样怪异的人性是畸形的大都市的产物。这与萧伯纳对中产阶级虚伪的仇视和冷嘲热讽达成了共识,在萧氏的“喜剧中任何类型的爱情都具有扭捏之态”[2]190,这是因为“我们对喜剧新的鉴赏源于现代意识的混乱”,现代意识迫使我们承认,“荒诞”正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角落中。
改译对于源语本的选择是改译本能否成功演出的关键所在。如果要成功改译并演出一个具有思想深度的剧本,改译者应该认识到,由于观众的缘故,他在选择源语本时就不能依凭他自身的审美喜好和理解能力,而要充分考虑本民族观众的审美习惯和接受愿望,所以他的工作不是简单地追逐名人名作,照搬西方的现成作品,而是需要对本民族戏剧接受传统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分析,需要从观众容易懂的和乐于理解的方式出发去考察源语本。当他考虑改译时,他还应置“剧”的艺术形式于“思想”内容之上;否则,当观众看不到真正的“剧”时,任何高深的思想、任何尖锐的社会批判对于他们都是无意义的,不但不能引起他们的思考,反而会破坏他们观看话剧的兴趣。
萧伯纳剧作的改译本在现代中国演出的失败和成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改译者由于过分重视原作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却忽略了这种关系必须通过演出与观众的接受来实现,因此既不能在深层意义上领悟原作的精神实质,也不能通过技巧实现审美原则的转换,改译出来的必然是一个不中不西的怪胎。而任何强加于观众的抽象的社会意识都会在演出中被观众所唾弃。反之,当改译者有了对本民族社会现实的深切体验,有了自身对于戏剧艺术的审美追求,原作所给予他的是一种启悟,这种启悟激发的是他的创作冲动。这样的改译本不仅能够贴近现实生活,而且能够感染观众,打动观众。惟其如此,戏剧的效果才成为可能,戏剧艺术也才能够成立。
注:本文作品版本:Bernard Shaw,How He Lies to Her Husband,from The Complete Plays of Bernard Shaw,London:Published By Constable&Company Limited London W.C.2,1931,Pp452-460.
李健吾:《说谎集》,《文学》 第四卷第五期,1935年,第761-772页。
[1]J.H.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M].邵牧君,齐宙,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81.
[2]西蒙·特拉斯勒.剑桥插图英国戏剧史[M].刘振前,李毅,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3] 柏格森.笑[M].徐继曾,译.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