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冰雪奇缘》看迪斯尼公主题材动画片的传承与创新
2014-03-02王晓彤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电影学硕士研究生
□文/王晓彤,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电影学硕士研究生
王璁,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学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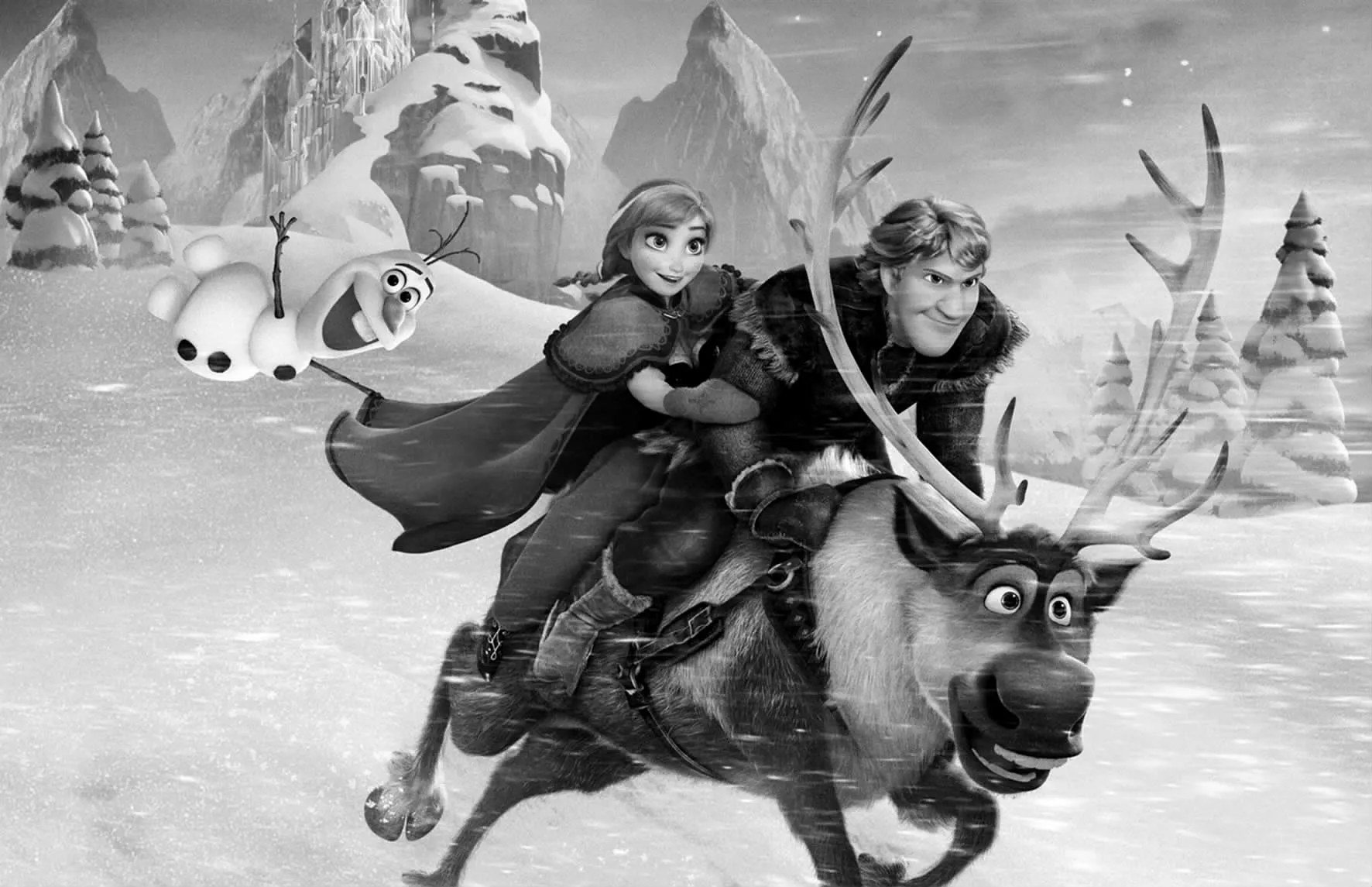
冰雪奇缘剧照
2013年11月底,迪斯尼推出了根据安徒生童话《冰雪女王》(The Snow Queen)改编的动画电影《冰雪奇缘》(Frozen)。这部动画片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在获得高达10亿美元全球票房的同时又拿下了奥斯卡与金球奖最佳动画电影奖项。与以往迪斯尼推出的公主系列动画片有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体现出了较多的性别与阶级意味,在传承迪斯尼电影创作传统的同时,又对顺应观众潮流进行了创新。
早在1943年,迪斯尼公司就考虑将这部安徒生童话作品改编成动画片,然而在故事设计上屡屡遇到困难,使得这部作品的推出计划一再被搁置。首次发表于1845年的安徒生童话《冰雪女王》(又名《白雪皇后》)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恶魔打破了一块魔镜,使得碎片散落各地。魔镜的碎片割入人体后会使人变得邪恶无情。名叫凯伊(Kay)的男孩被一块魔镜的碎片刺入了心脏,使得他的心肠变得十分冷酷。凯伊在与朋友乘雪橇时遇到了暴风雪,冰雪女王趁机将他带走,并以她的吻使他完全忘记了他的青梅竹马恋人吉尔达(Gerda)。吉尔达为了得到凯伊的消息,踏上了寻找凯伊的路程,在历经艰险之后,凯伊终于在冰雪女王的宫殿找到了凯伊,她以爱融化了凯伊的心。这对青梅竹马得以再次团聚,随着季节的变暖,他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1]然而由于安徒生对冰雪女王的描写太少,加上她与恶魔和魔镜的关系交待得并不清楚,因而读者在解读冰雪女王时常会发生两极化的见解:冰雪女王到底是恶魔还是一个被人误解的“好人”?这个版本的故事中,行动性最强的女主角吉尔达与冰雪女王之间也缺少互动和直接冲突。除了迪斯尼公司创始人沃特·迪斯尼本人以外,历任迪斯尼公司主管都试图将这个有潜力的题材搬上大银幕,然而他们均未取得成功。解决冰雪女王这个角色在故事中的定位,成为影片创作成败的关键。经过编剧组的反复讨论之后,安娜与艾莎之间的姐妹情成为了故事的主线,而故事主要冲突也由原本设定的正邪对决,变成了爱与恐惧之间的角力。
对经典童话故事进行改编是迪斯尼的传统,公主系列动画片大多取材于世界各地的民间文学、童话故事,虽然沿用了源文本的框架结构,迪斯尼的改编却没有简单遵循原著。在《青蛙王子》中,王子受到诅咒变成青蛙,只有得到公主的亲吻才能解除魔咒。但在动画片《公主与青蛙》中,黑人女孩亲吻了变成青蛙的王子,不仅没有让王子恢复人形,自己倒一起变成了青蛙。随后两只青蛙开始了解咒之旅——情节的丰满让故事更具波折,而《冰雪奇缘》的改编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一、姐妹情取代王子与公主的爱情
在早期的迪斯尼公主题材动画中,公主形象通常是美丽、善良却受到陷害的女性形象,她们在历经艰难之后最终得到王子的拯救。如1937年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以及1950年的《仙履奇缘》,1959年的《睡美人》。女性由于其自身的美丽遭人嫉恨,陷害公主的角色恰恰是女性——女巫、后母、坏心肠的仙女等。女性之间的嫉妒和仇恨成为了故事冲突的直接来源,而道德上占优势的女性必将在男性的拯救下获得胜利。女性自身的行动通常是消极被动的等待,而占据行动上的主动和道德上的优越通常是男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意识的兴起,迪斯尼顺应潮流先后推出了《小美人鱼》、《美女与野兽》、《风中奇缘》、《花木兰》、《公主与青蛙》、《长发公主》等以女性角色为主要人物的动画电影,这些动画片在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塑造了带有现代价值观的女性角色,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女性寻找自我和爱情,摆脱压抑与束缚的觉醒意识,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性。脱胎于《海的女儿》的《小美人鱼》由纯真善良的美人鱼变成了勇敢冒险追爱的女孩;《风中奇缘》则将宝嘉康蒂塑造成环保主义与和平主义者;《花木兰》直指女性的自我价值、勇敢打退外敌入侵,连皇帝都不得不向她鞠躬。这些角色摆脱了前女权时代的“被拯救”标签,不但可以寻找自己的生活目标,甚至可以充当英雄去拯救男性。这种凸显女性主体价值的动画片也赢得了不少成人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青睐和关注。
迪斯尼动画片中常常出现“落难”与“拯救”的故事模式,在本片中成为安娜拯救艾莎。公主的爱情生活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甚至第一次出现了反派王子汉斯的形象。影片强调了女性的自我成长,男女之情不过是路途当中的额外收获。选择这种叙事策略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公主动画片的一脉相承,无论是《花木兰》还是《公主与青蛙》,或者是《长发公主》,在这些作品中,男性角色常常陷入困境,需要女性角色予以帮助和拯救。如《风中奇缘》中约翰·史密斯被宝嘉康蒂拯救;《花木兰》中花木兰拯救校尉李翔和皇帝;《公主与青蛙》中黑人女孩蒂亚娜拯救青蛙王子马文(虽然失败了);《长发公主》中Rapunzel用长发拯救窃贼Flynn。相较于以往的迪斯尼公主系列动画片,《冰雪奇缘》这部影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第一次设置了双女主角,并以姐妹情作为情节的主线,妹妹安娜的爱拯救了姐姐艾莎,女性的落难通过女性的解救得以完成。
对比安徒生的原著不难发现,吉尔达——凯伊的青梅竹马的异性恋爱情关系变成了安娜——艾莎的姐妹关系,吉尔达冒着风雪寻找凯伊也直接变成了安娜不顾一切寻找艾莎。故事保留了部分核心元素,如安娜用爱感化对方,化恶为善;艾莎的性格特点则重新塑造成自我逃避、恐惧的形象。影片一开始,艾莎不小心用魔力伤害到了妹妹安娜,从此陷入自责当中。父亲给了她一副手套,并对她说“别去想它,别去施展它”,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艾莎的心魔越来越严重。当安娜去找艾莎一起搭雪人玩的时候,艾莎孤僻地把门关上,躲在密闭的房间内。寂寥的王宫、幽闭的王国显得无比压抑,让艾莎喘不过气来。
迪斯尼动画中常常着重刻画父女之间的感情,宽厚慈爱如基督般的父亲对女儿的疼爱、帮助和成全:如《小美人鱼》中爱丽儿的父亲用魔力让女儿长出了双腿,成全了爱丽儿与王子的爱情;《风中奇缘》中宝嘉康蒂劝说父亲放走了约翰·史密斯;或者是女儿对父亲的孝顺、思念和报答:如花木兰替父出征、《公主与青蛙》蒂亚娜对已故父亲的思念。但本片中父亲对女儿的影响有限,父亲的力量显得十分无能为力。艾莎发现自己的魔力无法控制,父亲和母亲给她的解决之道只有躲避、掩盖。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其中含蓄传达出的同性恋意味:手套和紧闭的房门是这种恐惧同性恋心态的具体象征。艾莎继承王位后不慎暴露魔力,她跑到山上建造了一座冰宫将自己封锁起来,唱词中“let it go”的表白也恰似同性恋人群表明性取向之后的内心宣言。最后在故事的高潮中,妹妹安娜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拯救艾莎,成功地化解了姐姐的心魔,使阿伦黛尔王国重回夏天,打开了这扇“门”。姐妹情取代了公主与王子的爱情,童话中俗套的“真爱之吻”在这个故事里也失去了作用。虽然这样的解读只是一种揣测,然而这部影片体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情调却是不可否认的。就像本片作曲家克里斯汀·安德森-洛佩兹所言:“我觉得《冰雪奇缘》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传达的理念:真爱不一定要从英俊的王子那里才能找到,有可能就在你的家人中触手可及。”
二、配角的设置和含义
迪斯尼动画的另一特色是配角的设置和再创造。《花木兰》中絮絮叨叨的木须龙,《王子与青蛙》中酷爱音乐的短嘴鳄,《长发公主》中爱耍宝的马,都是原著中不存在的角色。[2]这些新塑造的配角大多形象憨态可掬,性格活泼,带有喜剧色彩,并且会在主角陷入困境时挺身而出,帮助主角解决问题,推动情节发展,同时其背后隐含的意义也值得思考。《冰雪奇缘》中的典型形象便是雪宝(Olaf)。雪宝是冰雪女王艾莎创造出的雪人,本片编剧、导演珍妮弗·李指出:“她开始释放她隐藏了一生的魔法。她创造的这个雪人来自她和安娜小时候度过的美好时光。雪宝代表了纯粹的天真和童年快乐。我们一开始这么想他,雪宝就活灵活现的蹦了出来。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好玩,完全不受尘世的玷污。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恐惧对决真爱’影响的角色。他就是爱的化身。”雪宝由五个雪球组成,能够以不同的形式解体和组合。在雪宝刚出场不久,创作者就安排了一段歌唱场面,表现雪宝对夏天的向往:
小蜜蜂嗡嗡叫,孩子们吹着蒲公英,而我就去做雪人在夏天都会做的事儿;
酒杯在我手中,雪做的皮肤躺在火热的沙滩上,被晒成漂亮的古铜色;
我终于见到夏天的暖风,吹散了冬天的暴风,也看见了天气变暖时凝固的水会变成怎样;
迫不及待想看见自己,暴晒之后我的美丽身体,幻想着夏天我会变得有多酷!
寒冷与炎热是多么的刺激,要放在一起才更加合理!
冬天是适合睡觉的好时机,但要把我放在夏天,我就会是个——幸福的雪人!
当生活不如意时,我喜欢经常温故我的梦想,在夏日的阳光下休闲,就那样放松下来;
天会是湛蓝的,你们两位也在那里,终于也能和其他雪人一样去享受夏天的滋味!
在这个段落中,雪宝畅想自己在夏天中的种种感受。画面和唱词中体现的阶级意味是很明显的——冬天象征着贫苦(冰天雪地,山区,物质的贫乏),夏天象征着富裕(阳光、沙滩、美酒、蓝天);穷人向往富裕的生活,其中的代价可能是遭遇毁灭(雪人被融化),而自己却不自知;唱段结束后,山民克里斯托夫立刻说“我要告诉它事实。”而安娜劝阻了他——可以理解为:处于同一阶级的平民想戳穿“跨越阶级的神话”,而富人阶级则努力维护这个神话。克里斯托夫与雪宝这两个同属一个阶级的人物对梦想的理解是截然相反的。克里斯托夫从不奢望与公主的爱情,甚至连雪橇损坏了都不期望能得到补偿。雪宝则充满了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创作者设置的这两个人物恰好形成了对比,表达了平民阶层对梦想神话的不同态度,故事的结局自然是两人双双实现了梦想,以神话实现为告终。
迪斯尼动画片在改编中加入的配角除了带有喜剧色彩、帮助主人公实现目标以外,它们自身也有着各自的理想。《公主与青蛙》中短嘴鳄的梦想是去新奥尔良演奏爵士乐,《长发公主》中的匪徒则梦想成为演奏家。《花木兰》中的木须龙像是花木兰的一个缩小版的化身,它与它的主人一样担负着捍卫家族荣誉、实现自我价值的使命。这些角色都在一定程度上力图通过自己的才能、技艺来实现梦想,暗示了跨越阶级的神话中所需付出的代价是“出售才艺”。而雪宝的志向更加明确——盼望夏天,意即向往美好的生活,实现从穷人到富人的转变。这样的角色设定取消了俗套的温情励志元素,反而呈现出一种悲剧感与宿命感——跨越阶级即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富裕之时即是死亡之日。这种强烈的阶级暗示是以往作品中不曾有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神话——当然最终又以实现神话来缝合叙事。
由此可见,迪斯尼动画在对经典童话故事文本进行吸收和改编的同时,也充分加入了标志性的类型元素,《冰雪奇缘》在继承迪斯尼改编传统的同时又对安徒生童话进行了新的解读和涵义挖掘,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多重文化图景。
[1]安徒生.白雪皇后[M].叶君健,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10.
[2]闫兰.迪斯尼经典动画电影配角形象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