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外的村庄
2014-02-13孙焱莉
孙焱莉
边外的村庄
BIAN WAI DE CUN ZHUANG
孙焱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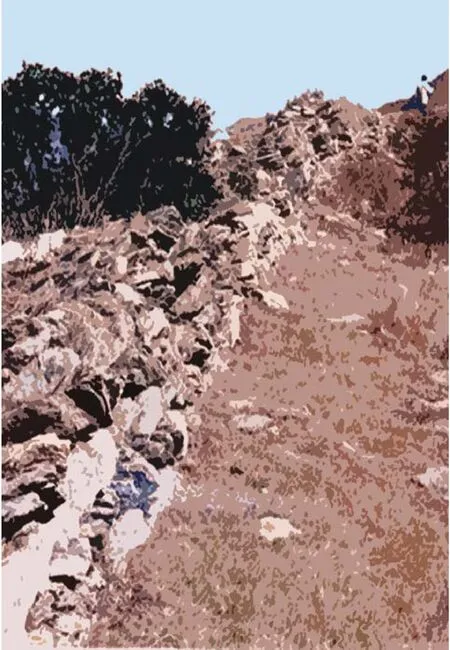
老边口
我对村子以外的记忆从那里开始。
父亲第一次送我和母亲及妹妹去姥姥家,就停在那儿。他目送我们登上高高的壕坝,顺着那排老柳树走上一段,再下去。上午的太阳,亮、薄、透彻,如站在刀刃上一般,内心有微小的稍纵即逝的惊惧。父亲是自动停下的,那儿似乎是他的边界。

孙焱莉,70后,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第九届签约作家。有中短篇小说发表于《清明》《星火》《山东文学》等。短篇小说《扫尘》《满绣》被《小说选刊》选载,其中《扫尘》被《小说选刊》选入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12短篇小说》。获辽宁文学奖。
懵懂的我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只是奇怪那些高大的柳树和一眼望不到边、高低不平的壕坝,它们怎么能在那里横空出现?
剩下的一段由母亲带着我走。下了坝,走上一条土路,再拐上一个弯儿,不远处就是母亲原来的家。其实算起来,是一段并不近的路,可父亲只送到那儿就停了下来,而母亲也认同父亲的做法,说你回去吧!然后抱着妹妹扯上我向前走。
母亲的神情自下坝后与先前有所不同。
至于不同在哪里;而那种令人不易觉察的细致变化,我一个才记事的小孩子是怎么轻而易举地就捕捉到的?抑或这些本就是我的臆想呢?都不得而知,我只是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穷尽我所认知的词汇,仍然找不到一些准确的句子描述她的神情。
一道壕,一排老迈的柳树,使一条路有了两条分岔,一条通向昨天,一条通向明天。在人的心底插上鲜明的标志。
那个地方就是老边口。那是满清皇帝的聪明之作,起壕为墙,插柳为界,垦田打猎,休养生息,就这样一统江山近三百载。
这些都是后来通过读一些地方志了解的。
而当时,那些故人往事,以及从陈年里走出来的旧景物,不能影响年幼的我半丝情绪,我新奇而羞涩地跟在母亲身后。
很快就到了边里姥姥家。这儿也是一个村庄,甚至是一个拥挤的村子。在我看来这种挤并不是院落小、人家多、道路窄,而是另一种情形,比如柳树老得垂垂欲卧睡去的枝条,井里石壁上长满的青苔,石头底座的土墙上泡得绿一圈黑一圈的泥裙子……一切都散发着陌生而陈腐的气息,仿佛老边里的村子是从远古里走来的。不光外面的景物是,屋子也同样旧。姥姥家的老板柜和黑色立柜正面那几块闪闪发光的黄铜锁孔里生着一丝别人无法注意的绿锈;柜子上面坐卧着的那两个长长的老梳妆匣边沿镂空的花边;姥爷四四方方的硬枕头;左邻二姥脑后的圆发髻及发髻的罩网上面插着的吊珠银簪子,还有她的小尖脚儿,包在一双滚口的鞋里面,她稍稍外八字的走路姿势和细碎尖嫩的南城话……这些构成了我对边里姥姥家的一种疏离和迷茫,这种感觉使我备感拘谨。越看周围越使我惶恐不安,甚至忘记了依靠母亲。
后来院子里聚了很多人。
姥姥和姥爷、三姥与二姥他们与母亲说长论短,逗着妹妹。母亲的一些姐妹也来家里,她们说笑得极热闹,仿佛在吵架,间或有一个姨低下头摸着我的脑袋与我说话,我坚持紧闭着嘴,生怕走漏什么。她们便不再理会我,从母亲怀里接过小妹,后来又挽起母亲到院子外面的树荫下说话去了。母亲对这里如此熟悉,她表现得如鱼得水。她能准确找到水缸后的一把小铲子,找出“搁灯窑儿”里的一根针给姥姥缝被子。
她因高兴而放任我,不过多管束我,在我看来这就是对我的一种疏忽。
自我到姥姥家后,没人再和我说什么,母亲也不似在家里,这里总有她好多事要做,可我却想找人说话,我想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呢,我怎么也无法理清。踌躇了好久,我才问母亲:咱们好像忘了点什么?母亲从忙碌的事情里抬起头说:什么?
这样,辗转了一下午,吃过晚饭,到了黄昏,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站在壕坝向上眺望的神情。他那时看上去和我一样小,仰着头,看我们高高地在坝上走,他凝神时脸上的汗水悄然落下。我终于想起来了,突然大哭起来,我对母亲说,我们回家吧,我爸还在那儿等着我们呢!母亲说,他送我们,送到老边口就回去了。我不信,依然声嘶力竭地哭。母亲很生气地打了我一巴掌。后来姥爷套着毛驴车拉着我和母亲、妹妹往回走。两个人一路上都在数落我,说,这个小孩子怎么一个心眼儿,长大了可咋办。
当姥爷把车赶上大坝,说:看,哪有你爸?
迎着夕阳,壕坝另侧一地灿烂。
父亲真的不在那儿!
一片广袤的碱草甸子在夕阳的照耀下,在微风的吹拂下,涌起一波又一波的橘色的浪。远处,隐约有一个村落的影子罩在朦胧的雾气之中,它显得那样遥远,却瞬时让我无比温暖、安宁。
那就是我家的位置,一个坐落在边外的村庄。
天 土
太阳如此羞涩,红了脸。云,似额前的长发绕在唇边。偶来的风一吹,墨赤的云便丝缕着散尽,黄昏已至。父亲在这样的时间与气氛里仍没回来。
每天,父亲在太阳坠落的这个时刻都没有回来,我这样说是因母亲马上就要临产了。
我结结实实地被关在了那扇门的外面。
里面很嘈杂,但我清晰地记得里面只有母亲、四娘和姑姑三人。但记忆里的声音依然让我感觉心里有少有的凌乱与破碎。
天在这时慢慢暗下来,我爬上高高的灶台,挪开笨重的木锅盖,里面露出了金黄的玉米面蒸饺。在黄昏没有到来时,母亲曾坐在灶前烧火,我蹲在她身边看一膛红艳艳的火,听豆秆在火里“噼噼啪啪”地吵闹。锅里是我们热气腾腾的晚饭,它们胖胖地、温暖地挤在一起,它们的气味舔舐我辘辘的饥肠,让我小小的心里藏匿着莫名的悲伤而舌根儿快乐的唾液则一波又一波,延绵不绝。
可当我移开锅盖看到它们的那一刻,却一点也不饿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时常被前面一些未知的东西所左右:比如关着的一扇门。可后来,我还是忍着烫捡了一个。只因母亲在把门关上之前说过“一会儿,你自己吃吧!”
母亲忙她的事,我自己管自己,我自己捡饺子吃,在那个黄昏过去之后。
有一种土,是被风刮来的,据说叫“天土”。
它们来了之后,就聚集在一起,虽然是被风带来的,却不愿意总和风去流浪,在土壕的下面、土崖的底下、一些被取走了树根的土坑的侧壁上到处都藏匿着。它们细细、软软、柔柔地集在一起,绵软而洁净,一动便顺着坡势如水一样流淌,一直流到平如水面为止。四季里,只要是有阳光的时候,沙土便如母亲温热的手心,哪怕是冬天。
我经常看见爱干净的鸟们用它洗濯羽翅,有时竟用去半日的时光。天空上染着的尘埃有时要用落在地上的土来掸净。
此前,在一个暖和的天气里,记得应该是秋末,地里除了裸露的土地,真的再没有什么了。土地是最真的面目。父亲曾领着我收集了许多这样的土。我在他全神贯注做此事时,问:“要这做什么?”他一笑说:“有用!”
天真正暗下来,我看见房子外的树都摇曳成了黑影。
父亲在这时才风风火火地进来,他进来时没有和我说话,没有看我。那时,我在哪里?是站在灶前、门口,还是躲在了水缸后面?我为什么会想不起来呢?或者那时我根本就不存在,正游移于母亲的体内!人的记忆如此脆弱,不能细细琢磨,不然就会迷失!
上古的女娲用泥捏成我们祖先的血肉,从此人与土系在了一起。人去世后,埋进土里就成了土。这土多年后会不会被风带到土地的另一隅,成为那里的一捧天土?
我是怎样走进屋子的,谁给我开了门,我忘记了,其实这并不重要。
屋子里亮堂堂的。
我看见了母亲的第三个孩子——我的弟弟,他降生于天土上面,他红嫩的皮肤闪闪发光,是土让他看起来生动无比!
“真是个男孩!”父亲说!姑姑笑得更加灿烂。
我终于明白了天土的用处。

我,我的妹妹、弟弟;我的父母与祖先都降临在上面,并且这些土还会睡在身下一段时日,直到能够坐起来、站起来,它才悄然退到角落。这是一个风俗,也成为了一个仪式。许许多多人都是从这沙土上站起来的,走向自己的生命。
生于斯,殁于斯,土是我们永远的家园,先人是睿智的,用盛载着无数祈福与灵性的土养育亲近的人,生即永恒,有着某种神性预示。
在弟弟的第一声啼哭完结之后,我觉得一阵风刮过,似乎有什么飞进了我的眼里,我声嘶力竭地哭起来。屋里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我,我说我被沙子迷了眼睛,“是那里的沙子!”我指着火炕上已焐热了的一堆绵绵沙土,母亲眼含热泪,姑姑和父亲给我吹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发现。
那个时刻,我知道:我就是一粒沙,是自己眼里的沙,从天土上衍生出的一粒沙。
责任编辑 叶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