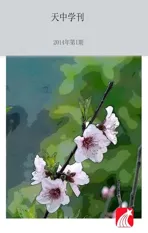温太真玉镜台故事的演变及文化意蕴
2014-02-12董艳玲
董艳玲
温太真玉镜台故事的演变及文化意蕴
董艳玲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温太真玉镜台故事经历了魏晋志人小说、唐宋诗词典故、元代杂剧、明代传奇等多种表现样式,人物形象不断发生变化,故事情节也越来越复杂,这些文本形态变化的背后是不同时代文化内涵的折射。
温太真;玉镜台;演变;文化意蕴
温太真,实有其人。《晋书·温峤传》:
温峤,字太真,司徒羡弟之子也。父憺,河东太守。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风仪秀整,美于谈论,见者皆爱悦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隶命为都官从事。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奏之,京都振肃。后举秀才、灼然。司徒辟东阁祭酒,补上党潞令。[1]1785
正史中温太真是为国为民、谋略过人的士大夫,史传中记载了他抗胡斗争、绝裾、击楫、平定王敦和苏竣之乱、燃犀的事迹,却没有关于玉镜台的记载。
魏晋时期是温太真玉镜台故事的形成期。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温太真玉镜台故事短小精练,情节简单,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性格描写不够细致。这一时期的温太真玉镜台故事受人关注较少,可以说是当时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笑料。
隋唐至宋是温太真玉镜台故事的流传期。这一时期玉镜台故事多应用于诗词中,通俗文学没有涉及。温太真玉镜台故事最早出现在诗歌这一文学样式中是南朝萧纲的《咏雪》:“思妇流黄素, 温姬玉镜台”[2]296。这一典故应用于诗歌,引申为婚娶聘礼之称或表达相思爱恋之情,例如唐代诗人张纮《行路难》、李白《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常浩《寄远》、李商隐《中元作》都属此类。另,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和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都有此故事的记载,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温太真玉镜台故事沿袭前代,没有大的变化。
元明是温太真玉镜台故事的繁盛期。以温太真为主角的作品共有5部,其中改编玉镜台故事的有3部,分别是关汉卿杂剧《温太真玉镜台》、朱鼎传奇《玉镜台记》、范文若传奇《花筵赚》,其他2部是元代佚名南戏《温太真》和明杨潮观的杂剧《温太真》。《温太真玉镜台》《玉镜台记》和《花筵赚》对这一故事进行了不同的改编,故事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刻画、语言描写等都有很大差异。和前代相比,它被演绎得越来越复杂,故事也更加完整。
清代是温太真玉镜台故事的回落期,有清一代没有以此故事为蓝本的作品。《合锦回文传》《美人判》《巧联珠》《五色石》等多部小说中有章节引用此故事,多沿袭前代描绘才子佳人的风流爱情故事。
自晋至清,温太真玉镜台故事主要以“骗婚与老少配”的文学内涵而存在,但经过历代文人的改编与再创作,文本体裁和文本内容都有了很大变化。文本体裁上,最初是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唐宋时期多是吟诵婚姻爱情的诗词典故,元代演变成底层民众喜闻乐见的杂剧形式,明代以文人传奇的样式呈现。文本内容上,《世说新语·假谲》简略叙温峤骗娶自己表妹;关剧演变成老夫追少妻的风月爱情故事;朱剧一改关剧的幽默、调侃风格,把婚姻爱情和时政历史结合起来,增加了历史沉重感;范文若的传奇,插入另一人物,此故事发展成三角恋式的才子佳人故事。
狂狷任诞,彰显魏晋士人风度精神
温太真玉镜台故事最早载于《世说新语·假谲》: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3]857
在魏晋那个个性张扬的时代,士人以放浪形骸而自我标榜,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尊崇自我内心的想法,以一颗赤子之心生活在俗世之中。《世说新语》这样的描述也与当时的人物品藻活动有关。汤用彤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指出:
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明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壑。朝廷以名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竟以名相高;声明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认为,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为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4]203
魏晋时,人物品藻从社会评价发展为人物审美。从《世说新语》中的多则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时代对仪容之美有着狂热的追求,魏晋时期士人对仪容之美的追求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封建道德“德”的评价,而上升到了独立的对“美”的审视。如:
奉倩曰:“妇人徳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味昧此语。”[3]918
可见,温峤看到自己表妹仪容之美而心动之追求之,并骗娶之。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他的行为摆脱了传统封建道德的樊笼,是对独立个体审美的追求。另外,我们翻阅正史等相关资料,则发现历史上真实的温峤却没有这段佳话。关于温峤娶妻的材料,有以下记载:
骠骑将军温峤前妻李氏,在峤微时便卒。又娶王氏、何氏,并在峤前死。[1]1795……其后峤后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载丧还都。诏葬建平陵北,并赠峤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绶。[1]1796……峤初娶高平李暅女,中娶琅琊王诩女,后娶庐江何邃女。[3]857
2001年发现的温峤墓志如是记载:
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始安忠武公并州太原祁县都乡仁义里温峤,字泰真,年四二,夫人高平李氏,夫人琅琊王氏,夫人庐江何氏。息放之,字弘祖。息式之,字穆祖。息女膽。息女光。[5]11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温峤先后三娶,却没有表妹刘氏。另外,刘氏笑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但据本传“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时年四十二”和墓志记载,温峤卒时年龄42岁,温太真玉镜台故事中温峤怎么能是“老奴”呢?这样看来,《世说新语》中关于温太真玉镜台的故事虚构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世说新语》记载了温太真的多则轶事:
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蒱,与辄不竞。尝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数四。温公喜慢语,卞令礼法自居。至庾公许,大相剖击。温发口鄙秽,庾公徐曰:“太真终日无鄙言。”卫君长为温公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3]744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温太真任性放纵,凭禀性行事,他用这种任诞狂狷的行为来表达超越名教、皈依自然的自由人格精神。温太真是如此洒脱、不羁之人,在《世说新语》中,作者杜撰玉镜台故事,让他老少配、让他骗婚有何不可呢!他的这种狂狷行为彰显的是魏晋时代士人的风度精神。
风流老少配,底层市民文化的迎合
元代,大量的文人开始改写或引用温太真玉镜台这一故事。在杂剧、南戏、散曲和诗歌中以这一故事为典故或者楔子更是不少,例如关汉卿的《温太真玉镜台》、郑光祖的《梅香骗翰林风月》、乔吉的《玉箫女两世姻缘》、南戏《荆钗记》、任昱的散曲《中吕·朝天子》、汤舜民的《友人客寄南闽情缘眷恋代书此适意云》等。作品中温峤多以“风流温峤”“羞杀晋温峤”等风流才子的形象出现。
关汉卿的《温太真玉镜台》,共四折,较于《世说新语》中的玉镜台故事,做了很大的改动,故事内容、人物形象和语言刻画更加生动细致。剧中的温峤对刘倩英一见钟情,恰好姑母让其教刘姑娘诗书并为刘找婿,经过一系列的曲折,温峤终于将表妹娶回家,但刘却不让温峤进洞房,直到王府尹设水墨宴,温峤的才情赢得刘的芳心,故事才得以圆满结局。在人物形象上,杂剧中的温峤脱离了魏晋时期狂狷任诞的士人形象,变成了风流滑稽、幽默谐趣的风流文人。刘倩英这个人物形象,由于杂剧体制的限制,她没有较多的出场,但通过她不让新郎入洞房,还说“兀那老子,若近前来,我抓了你那脸”[6]248的语言行为来看,她的性格豪放泼辣,比《世说新语》中的形象更加逼真。关剧语言通俗,用了不少的俚俗语言,接近底层市民的生活。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7]自序而文学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者对汉民族文化既向往又恐惧,科举制度几乎处于荒废状态,汉族文人无法通过科举走向仕途。其次,森严的民族等级制度,使汉族文人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对统治者有着恐惧心理,对仕途望而却步。这些因素使汉族文人开始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扩大了他们的创作视野。随着杂剧这一文学样式逐渐深入人心,剧作家通过作品来反映现实、映射历史或者抒发自我的愤懑,他们创作爱情风月剧、神仙道化剧、历史剧等,来排遣内心的压抑与郁闷。正如丹纳所说:“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8]26关汉卿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的创作无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不管是文学语言、文学内容、还是文学形象都是从普通百姓日常中汲取营养,迎合市民阶层和观众的审美趣味。《温太真玉镜台》剧中的温太真油滑、幽默、调侃的语言特色,无疑受到底层市民语言风格的影响,女主人公的不拘小节、泼辣豪放显然是典型底层妇女的写照。关汉卿正是用这种接近市民底层的人物形象、人物语言和故事情节来构造风流老少配的故事,来迎合底层民众的需要。
因而,从晋至元,温太真玉镜台故事由最初的在士人阶层中流传,彰显士人放荡不羁,超越名教的人格精神,演变成为底层大众津津乐道的风流老少配的故事。玉镜台故事的风格基调也发生了变化,《世说新语》和唐宋诗词中是雅正的,关汉卿杂剧《温太真玉镜台》则是俚俗幽默的。
雅俗相结合,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交融
明代,温太真玉镜台的故事发展到了顶峰,以此故事为底本的传奇作品就有朱鼎的《玉镜台记》和范文若的《花筵赚》。小说《二刻拍案惊奇·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剪灯馀话·贾云华还魂记》,笔记《夜航船》《余冬叙录》都借温太真玉镜台故事作为开场诗或者引用这一典故。
朱鼎的《玉镜台记》中,温峤不再是一老头儿,而被塑造为一翩翩美少年,由温峤丧妇改写为温未娶,剧中的温峤既有关剧《温太真玉镜台》中的影子,还借鉴了《晋书·温峤传》中的记载。温峤建功立业大多依据正史,婚姻爱情故事虚构成分较多,这部剧将爱情和家国结合在一起,脱离了简单的风花雪月般的戏剧模式。对此剧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明代的戏曲理论家吕天成和祁彪佳对此剧都评价不高,现代学者郑振铎却给出了较高评价,他认为:“朱鼎《玉镜台记》虽亦为写悲欢离合的剧本,却全异于一般的恋爱剧。在这里,国家大事,占据了家庭变故的全部。虽本关汉卿《温太真玉镜台》,却比原剧面目全殊。其间《新亭流涕》、《闻鸡起舞》、《渡江击楫》、《击帻》诸出,至今读之,犹为之感兴。”[9]893从文本内容来看,该剧男女双方是两情相悦的,改变了温峤骗婚这一故事情节。从人物形象来看,温峤一改关剧诙谐幽默,不再是风流成性的老头儿,而成为一温润如玉的文人,感情专一,敢于承担自己肩上的担子,他的身上体现的是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继承——修身治国平天下。正如郭英德所说:“在明清文人传奇中,我们感觉到对古代文化思想传统的强大向心力,古代文化思想传统的浓重阴影笼罩着几乎全部文人传奇作家作品。”[10]前言女主人公则由最初的大胆泼辣转变为温柔贤惠、通情达理,为了丈夫的壮志而甘愿受苦的传统女性形象。本剧借定情信物玉镜台歌颂了两人纯洁的爱情和温峤为国为民的一颗鞠躬尽瘁的心。这则故事反映了中国封建士大夫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抛家弃子来承担起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为了国家利益而放弃自我利益,为大家舍弃小家的儒家士文化精神。另外,考虑到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严嵩专权的时期,它无疑也告诫世人“忠”的道理;再者,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在思想领域心学流行,情欲不断开放,对正统的道德观念和婚姻观念带来了重大冲击,面对这些新的挑战与质疑,文人士子无疑感到责任重大,不管是剧中的温太真还是作者朱鼎,都是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和婚姻观念的。
范文若的《花筵赚》不再是温太真和表妹刘氏两个人的故事,插入了第三者谢鲲,演变成了一个三角恋的故事。范文若传奇中的温太真成了一个丑陋的才子,其情敌谢鲲则才貌双全。郭英德称这两种人物形象为“外表丑而内心美的滑稽性喜剧形象”和“外表不丑而内心极丑的讽刺性喜剧形象”[10]75。整个剧中则反复演绎这两人对表妹刘碧玉的争夺,最终温峤俘获了表妹刘碧玉的芳心。剧中的温太真不仅要战胜自己的情敌谢鲲,而且还要让表妹接受自己,在成婚当日他想出了“新郎盖头”的方法,偷天换日进入洞房。剧中这种滑稽性的喜剧性描写还有多处,如为了接近美人,他和谢鲲扮作乞儿在刘家门前打花鼓,来表达爱意。这些故事的改编和喜剧性的描写符合了明代中后期市民的审美趣味,三角恋的故事情节和滑稽行为的描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相统一。晚明的思潮解放推崇解放人的天性,反对理学“禁欲”的道学观念,提出要解放人的七情六欲。因此,作家和市民阶层都热衷于才子佳人缠绵旖旎的爱情故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家为了演出的需要和作品的影响力,必然加大对世态人情的描写,宣扬自我情欲,歌颂世俗的感官享受和欢乐。
明代关于温太真玉镜台的故事演变是复杂的,在文本内容上,对《世说新语》和《温太真玉镜台》有继承,但更突出的是改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文章基调等的改变,隐含了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首先,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眼光投向了金钱,在思想领域受心学的影响,市民自由化达到了封建时代高峰,他们不仅注重物质享受,而且追求感官刺激,范文若的《花筵赚》就是这种文化产物的一代表。其次,当一种思想产生时,总会有不同的意见,而明代的这两部传奇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一部分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们能感觉到经济的发展、思潮的涌动带给人们的后果,在他们的作品中会有潜在的反映,如朱鼎的《玉镜台记》,作者似乎看到了多年以后晚明士人的堕落、癫狂,因此在这部剧中他既有对当时时政的映射,又有劝导士大夫要向温太真那样不仅有担当国家的重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而且在婚姻上也应该有所担当,感情专一。较之《玉镜台记》,范文若的《花筵赚》体现的更多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和文化思潮下底层群众的需要,它反映的是市民文化——通俗文化。站在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这两部作品,它代表了明代中后期正统的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交叉。
要之,温太真玉镜台故事以婚姻爱情为主题,从晋宋到明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世说新语》中虚构了温峤骗婚下玉镜台为定情之物的故事,元代则演绎成风流温峤老少配的喜剧,到了明代则出现了分叉:一则上升到了爱情和历史相结合的时事剧,二则是符合下层民众心理的三角恋爱情故事。从文化内涵来看,此故事的缘起是映射魏晋士人风度精神,是士人文化的代表;隋、唐、宋三代,通过玉镜台这一典故借代男女联姻或者悲欢离合的文人情感;元代,杂剧、南戏等文学作品反应的则是底层民众的通俗文化;明代,这一故事体现了雅正的士文化和通俗的市民文化交融。
[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穆克宏.玉台新咏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法]丹纳.艺术哲学(图文本)[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9]郑振铎.中国文学史(插图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0]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刘小兵〕
The Evolu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Wen Taizhen Jade Mirror’ Story
DONG Yan-l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In the paper, we detailed analyze this evolution of Wen Taizhen Jade Mirror’ story by Narrative Culturology. The story has implicated varieties of forms which include: tales of human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y, Tang and Song poetry allusions, Yuan drama and the legend of Ming Dynasty. In the texts, characters constantly change and the plots are increasingly complex. All thes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story implicat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refraction by different times.
WenTaizhen; Jade Mirror; evolution; cultural connotation
董艳玲(1985―),女,山东菏泽人,博士研究生。
2013-12-05
I206
A
1006−5261(2014)01−0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