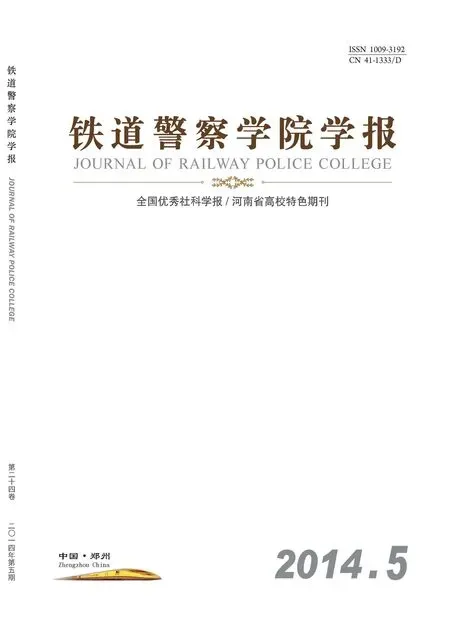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2014-02-11闻志强
闻志强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闻志强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得更少;二是“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目前,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它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它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但书;司法适用;实体和程序
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第13条确立了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即“什么是犯罪”。细究之,这一有关犯罪概念的规定实际上包含了两部分内容:前半段主要阐明“什么是犯罪”,后半段主要阐明“什么不是犯罪”,其中后半段的内容,学理上一般称为“但书”或曰“但书”规定①。针对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笔者结合刑事司法实践,针对“但书”的司法适用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在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来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一、“但书”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但书”作为我国《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唯一可以作为出罪渠道的法定依据。但是认真考察“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却发现其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得更少。“但书”理论定位不明,即在犯罪构成中的位置不明确,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时有逃避和畏惧心理。据统计,仅有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和《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个别地区的醉驾案件和盗窃案件等极少数司法判决引用《刑法》第13条“但书”作为出罪理由和无罪判决引文依据,“但书”的司法适用局限在较窄的范围内。
二是“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但书”内容过于简洁、抽象和原则,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细则可供依循,导致各级各地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在司法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标准不统一、不协调,这不仅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也不利于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基于此,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值得思考并应给予明确解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看,“但书”需要而且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运用。
二、“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分析
(一)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
基于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立法规定的犯罪概念应与司法适用中的犯罪构成在内容上保持完全一致,以确保立法划定的犯罪圈与司法认定形成的犯罪圈相一致,这就需要犯罪构成在构成要件的设定上完全满足和实现犯罪概念的全部内容,即必须把《刑法》第13条的前半段所初步划定的犯罪行为和后半段的“但书”划定的不是犯罪的行为两部分内容完整地体现在犯罪构成中,亦即最终认定的属于犯罪的行为中必须排除其中包含的符合“但书”情形的不属于犯罪的行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定犯罪圈。前半段规定属于宏观的入罪机制,对应于微观层面的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中的四要件;后半段规定属于宏观上的出罪机制,但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中却没有体现。这表明我国传统的四要件平面式犯罪构成无法全部实现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概念的所有内容,二者存在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即出罪机制在犯罪构成中有缺失。
从实际角度看,我国现有犯罪构成理论过于注重入罪机制的建立,即在司法理念上和司法实践中过于集中于关注某一行为成立犯罪各要件的满足上,而对行为人及其行为所具备的不成立犯罪的各种要素和可能性则漠然视之,甚至视而不见。这就导致通过适用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考察评价行为人及其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方面很下力气、下功夫,但在面对行为人及其行为存在不成立犯罪的否定性要件时则非常“纠结”,秉着“宁错勿纵”的观念,对一些行为人及其行为在形式上满足犯罪成立要件时,一味认定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而作为犯罪予以惩办,最终导致适用现有犯罪构成理论只能得出某一行为人及其行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结果,而这与《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划定的犯罪圈不完全吻合,甚至背离了刑法设置“但书”的初衷。因此,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没有出罪的有效机制,这不仅有违刑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机能,也与我国立法规定的犯罪圈存在偏差。因此,无论是理论研究中还是司法实践中都需要建立出罪机制,在关注行为人及其行为入罪以保护社会的同时,兼顾注重人权保障的出罪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防止重打击轻保护、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障,以切实实现犯罪概念的全部内容,保证刑法的两大机能平衡、协调,特别是人权保障机能发挥实效。
(二)“但书”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了犯罪概念,该条后半段即是“但书”。与此实体法规定相对应,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被排除在犯罪圈外,在第15条作了如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判,或者宣告无罪:(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先贤有言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和活力在于正确理解和实施,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于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一部法律,无论法条书写得多么完美,制度设计得如何细致缜密,如果不能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那也只不过是“纸面上的法律”而已。既然我国刑法已经规定了“但书”,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对于符合“但书”情形的处理程序,那么“但书”也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才能使两大法律规定具备真正的法律效力和权威。将这一规定认为是不能或不便适用的,都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也将损害相关法律规定的尊严和权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之一即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而这一规定的具体适用只有得到刑事实体法的进一步明确,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如果“但书”不能在刑事实体法即刑法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得到司法适用,则这一诉讼程序的规定也将无法切实践行,必将束之高阁,形同虚设。
此外,根据前述对于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的分析,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出罪机制以弥补现在的漏洞,而“但书”作为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实际上即是法定的出罪依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也将使得符合“但书”的情形,通过司法程序获致“不认为是犯罪”的结论,从而可将一部分案件进行司法分流处理,有利于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保证诉讼质量。故而,从《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司法适用前提和我国犯罪构成出罪机制落实的角度看,“但书”的司法适用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程序法明文规定的支持和依托。
三、“但书”司法适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
我国刑法典分为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两部分,二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的具体内容和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我国刑法立法规定的整体和全部。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的前提是必须全面、深刻把握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关系,即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刑法分则,刑法分则的适用必须遵循刑法总则的规定,二者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刑法总论阐述的是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刑法总则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性,可以发挥概括、指导、制约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构成特征和刑法适用的功能。应当说,总则原则对分则具体罪名的制约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因此,在认定行为人及其行为构成某一个罪时不能脱离刑法总则规定而仅以刑法分则为据。如果认为刑法分则已经明文规定的各种犯罪排除了非犯罪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则刑法总则中的“但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将导致其“名存实亡”。故而,刑法总则规定的“但书”内在地制约了刑法分则中的个罪认定,即刑法分则总计十类犯罪都必须受刑法总则“但书”的制约。从理论上讲,即是任何个罪都有适用刑法总则“但书”的可能性和内在必然性,否则将会破坏刑法体系的统一和稳定,有违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界定。
(二)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根据法理,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当包括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个基本要素,但是也存在不少法律规范特别是法律规则缺少这三个要素中的一个甚或两个。考察“但书”,其完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本构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属于假定条件,“但书”前的内容属于行为模式,“不认为是犯罪”属于法律后果,三个要素完全满足法律规范适用的前提。
法律规范的基本内容必须经由司法适用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效用,从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否则便形同虚设,丧失法律的效力和权威。迄今为止,自我国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首例“安乐死”案件第一次明确适用“但书”开始,各级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明确使用“但书”的无罪刑事判决少之又少,这使得学界对“但书”在刑法总则中的去留展开激烈讨论。笔者认为,在满足法律规范基本构造三大要素的基础上,只有通过“但书”的司法适用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保持其生命力。因此,“但书”的司法适用符合对于法律规范基本构造的判断,也是其延续法律规范生命力的现实需要。
(三)是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
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能否和应当如何适用“但书”,最高司法机关已经通过司法解释这一准立法行为给予了回答。迄今为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但书”的司法适用已经通过相关司法解释作出了选择,即最高司法机关认可司法实践适用“但书”。与此同时,还针对个罪认定中适用“但书”可能出现的问题,明确规定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具体情形,以最大限度地明确个罪适用中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判断标准,从而准确出入人罪。这实际上不仅肯定了“但书”司法适用的可行性,而且已经在法律规定层面进行了局部的完善,以指导司法适用。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1)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2)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或者被胁迫;(3)具有其他轻微情节的。再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1款规定,本解释施行以前,确因生产、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饵料自用,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可以依照《刑法》第13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但书”,将其作为刑事判决不构成犯罪的法律依据得到了最高司法机关的首肯,具备合法性基础。同时,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发布司法解释针对刑法分则个罪认定适用“但书”进行细化规定,表明最高司法机关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必须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但书”司法适用的具体标准和操作细则,改变目前司法实践中“但书”适用少、适用不统一等现状,保障“但书”在司法适用中保持旺盛生命力。
四、“但书”司法适用路径的建构
如何在具体操作层面真正将“但书”运用于司法实践成为我们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当务之急是通过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层面来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
(一)程序法层面的适用分析
1.侦查机关
刑事案件的办理一般需要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涉及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刑事司法机关,在这三个阶段都存在适用“但书”的可能性。因此,公安机关等也可能会适用“但书”认定某一行为人及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我国,公安机关是主要负责刑事案件侦办的刑事司法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它和其他侦查机关都享有刑事立案权和撤销权。所谓立案,对于公安机关一般而言是指其对于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等材料,依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以判明是否确有犯罪事实存在和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并依法决定是否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的一种诉讼活动[2]。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侦查机关决定立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存在犯罪事实,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在刑事诉讼的第一个环节——侦查阶段,如果侦查机关发现存在“但书”适用的情形,可根据具体情形作出不予立案或撤销立案的决定,从而终止刑事诉讼程序。
2.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扮演两种角色:一是办理法定自侦案件的侦查机关,二是侦查机关办结移送案件和自侦案件的公诉机关。在办理法定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职权相同,享有刑事立案权和撤销权,其在侦查阶段适用“但书”与侦查机关相同,在此不再赘述。下面着重讨论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但书”的具体程序,这主要体现在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三个方面。
在对公安机关行使立案监督权方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具体案件是否符合“但书”适用情形,作出维持或撤销原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或撤销立案决定。在审查逮捕方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逮捕决定时,如果发现存在适用“但书”情形时,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后,可以同时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方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的公诉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对公安机关提请公诉案件的审查权,并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5条、173条规定,在符合“但书”适用的情形下,该类案件属于绝对不起诉。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如果发现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可以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自侦案件则可以退回侦查部门建议撤销案件,从而终结刑事诉讼程序。
3.审判机关
审判机关在我国指称人民法院,它是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的最后一道防线,享有案件的终局处理权,尤其是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案件的审判权。此外,人民法院还受理公民或法人自行提起的自诉案件。无论是自诉案件还是公诉案件,人民法院作为案件的审理者都有权根据具体情形,在符合“但书”规定两个条件时适用“但书”,认定某一行为人及其行为不是犯罪。
(二)实体法层面的适用分析
1.明确司法适用效力,确立法律引用依据
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有言:“立法者可以大笔一挥,取消某种制度,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同宗教信仰相连的习惯和看法。”[3]“但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顾忌。立法总是滞后于社会实践,而立法与社会实际存在脱节,司法工作人员观念保守、陈旧更是不可避免,这在“但书”的司法适用中暴露无遗。应当看到,新旧两部刑法都有“但书”规定,而且最高司法机关相继针对一些个罪认定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以明确“但书”的具体适用情形,并发布指导性案例肯定了“但书”的司法适用效力,但其在司法实践中的使用率,特别是作为审判机关作出无罪刑事判决的引文依据则屈指可数。自1987年发生于陕西汉中市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4],人民法院首次采用“但书”作为判决依据,认定行为人不构成犯罪以来,很难再见到法院的司法判决径行通过“但书”认定行为人无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变成一纸空文。由此可见,观念的转变对于发挥“但书”司法适用效力是多么重要。
与此同时,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的法官们对于“但书”规定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存在误区,还存在盲区。误区在于认为“但书”规定不能用,不可以用,不能作为支持无罪司法判决的理由和依据;盲区在于不少司法工作人员甚至都不知道、不清楚、不理解“但书”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应有内涵。许多法官都认为“但书”不可以用,也没有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明确可以适用,因而出于保险起见,基本不用,实际上是不敢用。此外,法官们过于依赖和信任前面刑事诉讼程序机制的过滤作用,认为已经有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两道关口的把关和判断,因而觉得没有必要适用“但书”出罪或者内心存在畏惧心理,害怕挑战乃至推翻前面的公安、检察的入罪判断得罪“兄弟单位”。对此,笔者深感忧虑。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两个维度看待“但书”,它是唯一能够通过刑法明文规定认定某一行为人及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法定依据,在经由诉讼程序的运作中,使得这一规定形同虚设、空置高阁,恐怕与立法意旨相去甚远。
笔者认为,前述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但书”司法适用的观念存在问题。究其实质是司法机关特别是作为终局审判机关的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在观念深处秉持的仍然是有罪推定的法律思维和反诉讼程序、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逻辑,还没有真正建立无罪推定、罪刑法定、保障人权的法律思维和过滤筛选的诉讼程序逻辑。“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理念无疑是先行的。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有与之匹配的理念,都可能异化为最坏的制度;相反,一个不健全的制度(一定意义上说,每种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分健全的),如果有良好的理念作为精神基石,也可能得到良好的运行”[5]。
因此,从观念层面改变现行“但书”司法适用现状是治本之法,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等有效法律规定,赋予“但书”作为司法判决引文依据的效力,规定其可以作为认定行为人及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判决依据,保障“但书”司法适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同时也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官们的职业风险等后顾之忧。
二是破解“但书”司法适用中的理论难题和实践疑问,不断总结经验,积累理论基础,牢固树立无罪推定思维,践行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各刑事司法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诉讼程序逻辑推进司法程序,真正实现相互制约和前后一体联动监督,确保“但书”司法适用的准确性、统一性。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法院审判作为诉讼程序最后一道过滤机制,是对“但书”适用具有决定权的终局处理机会,更是对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适用“但书”正确与否的终局审查。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始终牢记自身的终审决定职责,防止敷衍塞责,避免过度依赖审前过滤机制,从而真正“敢用”并“用好”“但书”。
2.明确司法适用原则和规则,消减模糊性
理论上一般认为我国立法规定的犯罪概念是形式与实质混合、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犯罪定义,这在我国刑法分则的个罪规定中也多有体现。作为犯罪概念必要组成部分的“但书”实际上也是定性与定量因素结合的统一,如何在定性与定量中把握一个“度”成为当务之急。基于此,笔者认为“但书”在司法适用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在操作上要“能用”,即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决定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但书”。如果各个刑事司法机关在不同诉讼程序阶段认定某一情形是否适用“但书”存有分歧,则“但书”适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会引人置疑。为避免上述问题发生,进一步明确“但书”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明确“但书”的司法适用原则和规则,以消减其内在的模糊性,增加明确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改革现行司法解释体制。根据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享有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具体适用的司法解释权,如果二者意见一致,则对法律理解和适用无甚影响,如果二者意见相左,则会导致司法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影响法律的统一、稳定、权威和司法适用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刑法分则个罪的认定存在不同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可觅踪影。最新的例证是《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对于酒驾行为是否一概予以追诉,是否存在“但书”适用的合理空间,两家意见截然对立,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参见张伟刚、谢晓曦:《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要求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达到醉驾标准的不一定构成犯罪》,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5月11日;王秋实:《醉驾危害轻微慎重追究刑责》,载《京华时报》2011年5月11日;邢世伟:《公安部:警方对醉驾一律刑事立案》,载《新京报》2011年5月18日;邢世伟:《最高检:醉驾案证据充分一律起诉》,载《新京报》2011年5月24日。。如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但书”司法适用的具体情形规定不同,则会导致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分歧,不仅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而且会导致司法诉讼效率和质量下降。笔者认为,应当将司法解释权完全归于最高人民法院,理由在于它是最终的司法审判机关,享有对案件的终决权,由其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汇总个罪认定中适用“但书”的具体情形,总结考量和评价因素,制定可行的统一标准以明确“但书”适用的具体情形,将可以有效避免分歧和冲突。
二是“但书”在刑法分则个罪认定中应当把握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根据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这一前提,原则上“但书”作为刑法总则的条文之一,而且是立法规定的犯罪概念的重要和必要组成部分,应当具有对刑法分则的普遍适用性。但基于我国犯罪概念定性与定量因素结合的特点,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现行刑法同西方各国刑法相比较,有一非常鲜明之特点即立法对大多数犯罪行为既定性又定量,而西方各国为立法定性、司法定量”[6],而且我国刑法分则不少个罪规定中已经存在对诸如情节严重程度、危害后果、犯罪数额等要素的考量和评价,因此,在坚持“但书”普遍适用于刑法分则时,还需灵活把握具体的适用方法。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适用情形:其一,对于刑法分则已经明文使用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相同或类似入罪情节规定的(这里不包括情节特别严重、特别恶劣等相同或类似表述的条文,因为这类规定属于量刑情节,不属于“但书”规定适用考量的犯罪情节),则不再重复适用“但书”,否则存在罪量因素的重复评价;其二,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入罪情节的,但规定了入罪的其他评价因素,如犯罪数额、危害结果包括危险状态实际发生与否或达到一定程度等,则可以将其归入定量因素的范围,根据个案决定是否适用“但书”;其三,对于既没有入罪情节程度的规定,也没有数额、结果等其他定量限制的,则一律可以适用“但书”;其四,对于最高司法机关各自或联合发布的立案追诉标准、司法解释等具有法定效力和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定等,如果对某一个罪原有立法规定进行细化或解释,从而对刑法分则相关入罪情节有详细规定或明确表述排除“但书”适用余地的,则一般也不再适用“但书”。原因在于这类规定已经细化或者实质上改变了相关个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已经与“但书”规定考量的因素重合,如若再适用“但书”存在重复评价的嫌疑,有违刑法公平正义。
三是立法与司法良性互动共促“但书”司法适用的发展和完善。从立法方面讲,立法机关应当严密刑事法网,准确使用文字词语,特别是对刑法分则规定的个罪条文要尽可能地采用明确的完全罪状描述,对于入罪情节或者存在其他定量限制因素规定的文字表述要更加严谨细致,保障刑法的理解和适用准确、统一。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但书’规定也存在不合理性,如‘但书’规定与罪状定量要素无疑给予了司法者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权力存在就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在不‘因噎废食’前提下,立法者应通过制度安排或设置来尽量降低不合理性,例如,为防止司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可以借鉴意大利在刑法总则对‘情节严重’、‘情节较轻’等需要作出判断的综合性要件作出统一规定,或者如俄罗斯在刑法分则对‘情节严重’、‘情节较轻’等需要作出判断的综合性要件作出具体、细化规定,或者在坚持成文法的前提下吸收判例法的援引先例制度等等”[7]。从司法上看,则应当坚持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相结合,要结合各级各地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适用“但书”的具体情况,提炼经典判例,归纳、总结审判经验,以逐步完善对于个罪认定中出现的可能适用“但书”规定情形或因素的认识和把握,并通过理论抽象和概括,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或其他规定,使其具备可操作性,以确保司法适用的统一、协调。条件成熟时,可上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但书”理解和适用的立法解释,从而保障全国法制统一、稳定和权威。立法的完善和司法实践的积累、成熟及其二者的良性互动将促进“但书”司法适用的深入发展。
3.赋予司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个案正义
在理论研究方面,已有学者针对刑法分则个罪中适用“但书”进行了研究,并归纳、总结了一些适用情形,可以为司法实践所借鉴和参考①如《法学》2011年第7期关于“危险驾驶罪与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的适用”板块的讨论;刘宪权、周舟:《〈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司法适用相关问题研究——兼论醉驾应否一律入罪》,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6期。。然而“但书”要真正持久地发挥效用,成为现行理论体系和司法实践中的唯一顺畅的出罪渠道,最重要的还是在实践中的使用率及其准确率。正如哈罗德·伯曼所言:“人类的深谋远虑程度和文字论理能力不足以替一个广大社会的错综复杂情形作详尽的规定。”[8]因此,我们要在实践中“善用”“但书”,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自觉性,健全和完善适用规则,丰富适用情形,并最终促使立法的积极回应,形成立法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推动刑法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司法适用机制的健全,给予“但书”规定旺盛的生命力。因此,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有必要赋予各级各地法院及其法官在适用“但书”时一定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从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现个案正义。
[1]赵绘宇,纪翔虎.对于危险驾驶行为适用“但书”条款并无不当[J].法学,2011,(7).
[2]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67.
[3][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467.
[4]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27.
[5]童德华.规范刑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2.
[6]冯亚东.犯罪概念与犯罪客体之功能辨析——以司法客观过程为视角的分析[J].中外法学,2008,(4).
[7]刘树德.论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A].游伟.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7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8.
[8][美]哈罗德·伯曼.美国法律讲话[M].陈若桓,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20.
责任编辑:赵新彬
O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Proviso”in Article 13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Wen Zhiqiang
(Graduate School,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Some worrying problems have been exposed in the present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proviso”.In general,they show in two aspects:first,there’s a littl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proviso”and less application as legal basis supporting acquittals;second,the“proviso”does not have unified and coordinated judicial application.Thus,to demonstrate and clarify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roviso’s judicial application is the top priority.To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cessity,the improvement of traditional theory system of crime constitution needs to set up impunity mechanism,which is the internal need and entity premise of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al law.To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asibility,it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and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specific instructions of criminal law;it is the embodiment that the fundamental construction of legal norm function and keep vitality;also it has legal assurance and recognition from judicial interpretation.Accordingly,we can build the path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the proviso from two dimensions of procedure and entity to maintain its effectivenes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proviso;judicial application;entity and procedure
D924
A
1009-3192(2014)05-0064-07
2014-08-10
闻志强,男,河南信阳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①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中的“但书”、“但书”规定皆指我国《刑法》第13条中的“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