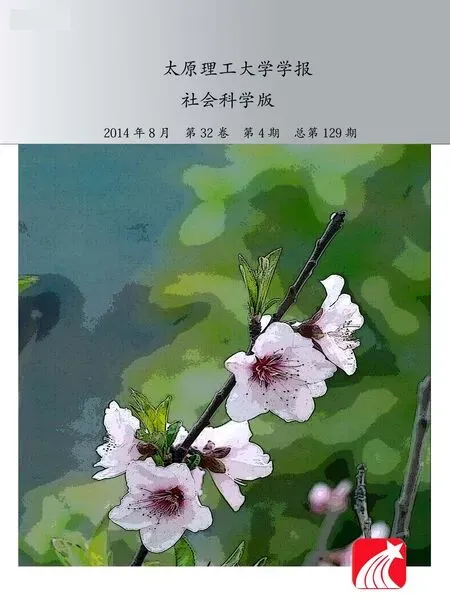《群书治要》修身治国、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探析
2014-02-11韩丽华
韩丽华
(泰山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群书治要》取材于经、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1]。《群书治要》汇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如魏征所言,此书可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2]。《群书治要》包含了丰富的德治思想,对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构筑民族中国梦,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一、 以德配天,正己修身
《群书治要·尚书》中西周的敬德保民思想是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发展起源。西周统治者认为德治与天道息息相关。西周盛行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天命无常,惟德是辅”、“明德慎刑,为仁以德”、“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德治思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之于人。”[3]《群书治要·尚书》把人民的德行与天相统一,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重民、民本思想。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将天的意志服从于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与天意相合。人民可以接近之,但不可以轻视之。民众是国家之本,人民团结、服从国家才能安宁、政治才能稳固。周王强调德治和仁政思想,重视人民的利益,对人民施以德政,以惠民为本。为善则治,为恶则乱。仁政爱民则国家有治,四邻友好,王室巩固,家和国兴。周文王吸取商王灭亡的教训,注意仁政德治,谨慎刑罚。“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弗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3]周王认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只有“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才能使周朝的统治稳固。所以他很注重施行德治,重视民心。周王制礼作乐也是以“敬德保民”为前提。他认为以公欲灭私欲,老百姓则归顺之。圣王明君要学习古训以治政,则其政不迷误。“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弗迷。其尔典常作师,无以利口乱厥官。”[3]贤明君主懂得以古代典籍为依据以治政,这样其治政才不会出错。其恭敬勤俭以树立道德威望,不存在狡诈奸伪。唯有为政以德的君主才会心情旷达而不烦忧。
德治,首先表现为执政者修身正心,正身律己。《群书治要·管子》讲,“政者,正也,圣人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4]。执政者从政就意味着必须先正自己,使自己做到正而不邪。正,就要保持不偏不倚,公正不阿。英勇而讲仁义,仁义而讲法度。执政者发言必须合乎规矩,行为必须体现善良意志。仁义智慧可以参比天地。《群书治要·尸子》认为,“仁义圣智参天地,天若不覆,民将何恃何望?地若不载,民将安居安行?圣人若弗治,民将安率安将?是故天覆之,地载之,圣人治之。圣人之身犹日也,夫日圆尺,光盈天地。圣人之身小,其所烛远。圣人正己,而四方治矣”[5]。 执政者就要做圣人,圣人的行为如同日月,为民众指明方向。如果圣人能够正己,那么国家不治而治,不用刻意去治理也可政通人和。“上纲苟直,百目皆开。德行苟直,群物皆正。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则人不从。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诸心而彼正,谓之至政。”[5]执政者正自己就是正人。如《群书治要·论语》所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6]。
治理国家在于德治,德治的根本在于治国者自己正身修心。《群书治要·傅子》提到,“治人之谓治,正己之谓正。人不能自治,故设法以一之。身不正,虽有明法,即民或不从,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明法者,所以齐众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7]。执政者行为若不正,即使有严刑峻法,百姓也很难服从。所以执政者必须先正己而后正人。严刑峻法是道德的底线,执政者的德行才是民众要学习的。
要做到德治,国君必须先自我修行,做到修身齐家。德治与国家的治理息息相关,身不正则国不治。《群书治要·礼记·大学》中以尧舜对人民仁爱而民服从、桀纣对人民残暴而民反叛作对比,以说明治国在齐家,齐家在于仁民爱物,善待天下百姓,不能把不好的政令强加于人民,主张把仁爱之心推广扩充至天下百姓,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家。”[8]治国在齐家,齐家在仁爱。安土敦仁、乐天知命的仁爱思想对个人来说实为仁爱的修养,对国家来说实为仁政的施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正是把个人的仁爱推及天下,施以仁政。
二、 修身治国,以德教民
德治思想还包含以德教民,教育人民修德向善。实行德治,就要以德性伦理教化人民,教育人民向善修行。君王以身作则,以身示范,便成为老百姓言行的榜样。《群书治要·管子·形势解》中提到,“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礼。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4]。执政者的言行举止对老百姓都有深刻的影响,上行下效。唯有执政者行得正,坐得直,才能使老百姓正面效仿。君王自己修德,独善其身,并兼济天下,以德教化人民,使人民也修德向善,这是德治的基本要求。《群书治要·论语》曰:“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尤病诸?’” 执政者当为君子,真正的君子懂得修己,使自己做到诚敬仁爱,修己修德则民众信服[6]。
若要施行德治就要教育人民遵循尧舜先王之道,以先王之道为修行的标准。如《群书治要·孟子·离娄》所言,“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9]。孟子认为尧舜制定的先王之道,给后世提供了仁政的榜样。无规矩,不成方圆。“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只有仁善不足以为政,只有法度不足以治国,要遵循先人之道,以此为施行德治的依据。因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9]。
治理天下在于治心,在于通过道德教化使老百姓懂得怎样做人,国君治国主要不在于治理百姓之琐事,在于以道德治民心,教人民懂得礼义廉耻。如《群书治要·袁子政书·礼政》所讲,“是故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耻;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苟免。是治之贵贱者也。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10]。以礼义教化人民,使人民知道自觉遵守道德,避免犯法。先教礼义而后行刑罚,是明君之教。《群书治要·潜夫论》讲,“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 以道德礼仪教化百姓,则老百姓心志向善,不生奸邪之心,社会安定,民心淳朴,这不是严刑峻法导致的,是教化导致的民心思善。“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11]治理百姓,重在治心,使老百姓心悦诚服,此为治本。 “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11]真正的圣王明君治世懂得从治心上治本,老百姓心性正当向善,则奸邪无所生。
真正的圣王明君懂得以身作则,实行德教,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重礼仪教化。《群书治要·孙卿子》提到:“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12]。君王讲究礼义,重贤能之人,清正廉洁,则人民懂得礼义廉耻,忠信节义。《群书治要·昌言》讲到,“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亲百姓,训五品,和万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应,降鬼神之吉灵者,实德是为,而非刑之攸致也”[13]。虽有刑罚,但仅在平定治国大业,降服奸宄同党的时候用。“至于革命之期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业。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13]所以,制度要周全才能有所依据,礼义有差等才能有所依据。法律不固定就会法网密布使老百姓难以逃避。礼制不明则百姓无所取信,这都是关于德与法关系的治国之道。“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所不可得而易者也。”[13]圣王明君依靠典籍制定礼仪,建章立制,使之成为恒常不变的道理。礼仪制度不周全,法律教化不明朗,则人民行为无所依据,这样社会难以稳定。
三、推己及人,仁政爱民
圣人要将自己的不忍之心推己及人,将自己的仁爱、孝敬之心推至天下,则老百姓都懂得孝敬、贤达,懂得以仁爱之心待人,则天下无冻馁之忧。《群书治要·傅子》讲,“昔者,圣人之崇仁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仁以济。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于沟壑。然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人”[7]。君王先做到“己所不欲,无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而后做到“达则兼济天下”。“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推己心有乐于妻子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欢矣。推己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无冻馁之忧矣。”[7]这种仁民思想就是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想的推广扩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世之道。有的用于要求自己以务本,有的用于要求别人以逐末。圣王君子懂得务本,所以能够建功立业而很少招致怨言。小人不懂得务本,因逐末不能建功立业且招致怨恨。《群书治要·中论》主张,“民心莫不有治道,至于用之,则异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己。用乎己者谓之务本,用乎人者谓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务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废而雠多”[14]。真正为民着想的君主在内致力于务本,从事农耕,充实粮仓,在外为保卫国家安全尽心尽力。老百姓逐利就如水就下一样,有利则来,不利则去。所以懂得如何赢得民心的国君必定为人民谋福利。《群书治要·管子》讲,“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可来也。莅民如父母,则民亲爱之,导民纯厚,遇之有实”[4]。对人民有利,人民则不召自来。对人民有害,则人民不会接近。真正爱民的国君对人民厚爱,也会得到老百姓的爱戴。
真正能赢得老百姓亲近爱戴的国君必定是为天下兴利除害,恩德施与天下,使百姓生活安宁,万物得以养育。如《群书治要·管子》中所言,“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4]。为政之本就在于治理人心,仁政爱民,得到人民的拥护。“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旁无择也。”[4]圣贤明君治理国家懂得以仁义对待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以忠信引导百信,为老百姓消除灾殃,为人民带来福分。《群书治要·吕氏春秋》认为,“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15]。唯有对待百姓像对待印玺与封泥一样重视,才能够无敌于天下。
粮食为百姓之本,人民为国家之本,国家为国君之本。真正懂得治国之术的国君知道顺应天道使百姓衣食丰足。《群书治要·淮南子》讲道,“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16]。真正懂得治国之术的国君知道顺应天时、地利、人力,顺应自然之道,使万物各因其宜。“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各因其宜。所以应时修备,富利国民,实旷来远者,其道备矣。”[16]这样,福国利民,国库丰足,老百姓自然归顺。唯有真正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
圣明君主收税必定考虑人民的收成和生活情况,考虑人民的负担,根据人民的收入拟定收税的多少,绝不横征暴敛,至百姓死活于不顾。如《群书治要·淮南子》所言:“人主之赋敛于人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民饶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16]圣明君王必定考虑人民的生活情况来收取赋税。若百姓生活困窘,则国君不会征收重税,一定会考虑人民的负重能力。“高台层榭,非不丽也。然民无窟室狭庐,窟室,土室,则明主不乐也。肥醲甘脆,非不香也,然民无糟糠菽粟,则明主不甘也。匡床衽席,非不宁也。然而民有处边城,犯危难,泽死暴骸者,则明主不安也。”[16]若百姓有饥馑、无住处、缺衣少食,无安全保障,则圣明君主必定寝食不安。只有百姓生活富足安乐,国君才能与人民同乐。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政情怀。
四、 德治为主,明德慎罚
《群书治要》的德治思想还体现在赏罚分明、“明德慎罚”的思想上。圣贤明君,对法律执行严明,因而群臣不敢徇私枉法,国家有治。《群书治要·管子·明法解》认为,“明主者,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职。此之谓治国。故曰: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4]。圣贤明君明悉法律,故无人敢违反法令。圣贤明君详查百官的职分使群臣遵守职分而不至于混乱。由于君王执法严明,所以群臣不敢营私,不敢蔽塞地位低的人。所以国家老弱孤寡都得到供养,国家太平安定。“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其当赏者,群臣不得辞也;其当罚者,群臣弗敢避也。夫赏功诛罪者,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4]法律要严明且清楚明白。圣人制定法律,必定使法律明白易懂,使老百姓都懂得守法而避祸就福,因此天下得治。《群书治要·商君子》讲,“圣人为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知之,万民无陷于险危也”[17]。由于圣君使法律明白易知,老百姓都因明法而不去触犯法律,所以天下大治。“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民皆知所以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17]这比起那些不制定明确的法律而滥杀无辜的统治者强多了。
古代圣明君主用圣贤教育教化人民,教育人民修养向善,虽然国家也明确设定法律,但是法律是对人民的约束,其目的并不在于刑罚。刑法虽严厉,但只是用于对人民的警示和惩戒。《群书治要·盐铁论》认为,“古者笃教以导民,明辟以正刑。刑之于治,犹策之于御也,良工不能无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圣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厉而不杀,刑设而不犯”[18]。圣明君主借助威严的刑罚以对人民加以惩戒,但不会滥施刑罚。当人民做到自我约束而不触犯法律,则刑罚就只是一种警示而不会被滥用。国君若不懂得仁政爱民,德治教民,则国家混乱。“故民乱反之政,政乱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润穷夫,施惠悦尔,行刑不乐也。”[18]所以人民背叛、朝政混乱,国君要反思自身,国君身正则天下自然安定。真正的贤明国君赞美善良之士,对不善之人抱以同情,对受刑之人、对贫穷之人都施以恩惠和同情。
真正的圣贤明君懂得明德慎罚,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法律只是作为以德治国的辅助,而绝不是以法律作为主,德治为辅。 因为他知道,法律只是对人的外在规范,法律可以惩罚人的犯罪而不能从思想上使人懂得自律和仁爱。《群书治要·盐铁论》认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者,贵其絶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18]。所以,实施法律重在以法律作为使人守法向善的动力,不在于以刑法惩罚罪人。这正如良医的可贵在于他能去除人的病痛而不在于他会针灸;官吏的清廉在于他能教育百姓不作恶而不在于他的严刑峻法。
防止偷盗之类的不义之事发生,靠门户的严闭不如靠严厉的刑罚,靠严厉的刑罚不如教化老百姓提升其道德水平。《群书治要·袁子正书·厚德》讲,“恃门户之闭以禁盗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圣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无过行也。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10]。道德教化和严刑峻法兼而用之。道德教化使老百姓知道羞耻而不犯过。如果仅靠严厉的刑法,即使每日都惩罚很多犯法者,也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明者知制之在于本。故退而修德,为男女之礼,妃匹之合,则不淫矣。为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则不盗矣。以贤制爵,令民德厚矣。故圣人贵恒,恒者德之固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恒而可以成德,无德而可以持久者也。”[10]所以要从治本上下功夫,教育老百姓修德,使老百姓有廉耻之心,则民心归善,回归淳朴境界,则国得以治理。
《群书治要》的德治思想以执政者正己修身为本,并把个人修身齐家的修行实践与治国平天下的大业联系起来,而治国平天下要从自我修养做起。执政者个人修身正己,而后把个人的修养德性向外推广扩充至国家,教育人民修德,仁政爱民,以民为本,明德慎罚。这种以德性为治国之道的政治就是德治。《群书治要》的德治思想有利于圣王明君个人的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国家政治相结合,有利于国家的妥善治理和长治久安,有利于社会和谐。《群书治要》的德治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治国安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唐)魏 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第一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4.
[2](唐)魏 征,褚 亮,虞世南,等.群书治要译注:第一册[M].《群书治要》学习小组,译注.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3:2.
[3](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二·尚书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16-29.
[4](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三十二·管子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409-416.
[5](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尸子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482.
[6](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129-131.
[7](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663-654.
[8](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七·礼记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97.
[9](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三十七·孟子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487.
[10](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五十·袁子正书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664-668.
[11](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四十四·潜夫论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594.
[12](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三十八·孙卿子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511.
[13](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四十五·昌言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601.
[14](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四十六·中论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612.
[15](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三十九·吕氏春秋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527.
[16](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四十一·淮南子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550-551.
[17](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商君子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473.
[18](唐)魏 征,褚遂良.群书治要卷四十二·盐铁论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561-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