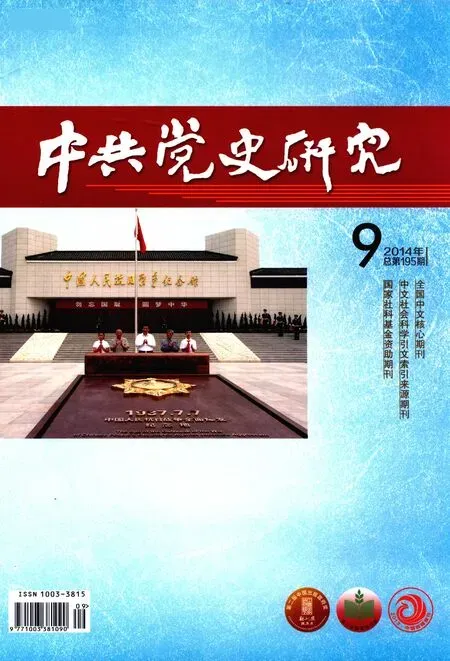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以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
2014-02-05田毅鹏李珮瑶
中共党史研究 2014年9期
田毅鹏 李珮瑶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兴起的对计划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父爱主义长期被视为计划时期体制僵化和关系主义的最主要表现而备受诟病,但研究者很少对父爱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走向制度化的具体历史过程展开研究,对其运行所面临的诸多复杂制约因素亦关注不够。而通过对单位子女就业政策阶段性演进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五六十年代的子女接班顶替主要是出于对因工死亡、致残或年老体衰职工的社会保障而颁布的一种补偿性和照顾性的福利政策,此后又陆续扩大到一些艰苦行业和特殊工种,但涉及面仍较窄,在实行条件和执行标准等方面有明确限定,社会影响不大,并始终未提升到制度层面,是一种有条件、有原则的父爱主义。70年代末,为解决“文革”时期积累的就业重压,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的子女顶替政策被逐步大幅度放宽,厂办大集体制度得到全面扩张,为解决企业子女就业问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父爱主义的制度设计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和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征,它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较强封闭性和自给性的单位共同体为制度性前提,也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但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企业在落实这一政策之际,往往采用“化大公为小公”的各种变通手段,导致子女顶替和内招制度弊端丛生,证明国企父爱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吴志军摘自《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全文约1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