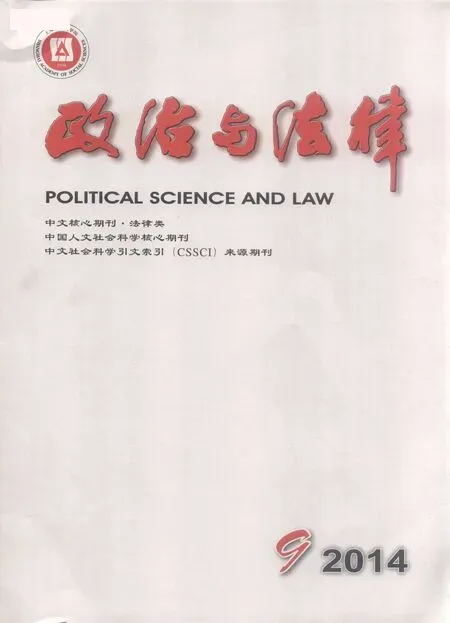论我国条约解释主体制度的完善——以修订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为视角
2014-02-03冯寿波
冯寿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44)
一、条约国内有权解释主体问题的提出
关于条约解释,中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导致人们不清楚在条约适用过程中谁有权解释条约以及解释的规则。①李鸣:《应从立法上考虑条约在我国的效力问题》,《中外法学》2006年第3 期。条约效力包括国际法上的效力与国内法上的效力。条约解释包括谁有权解释和解释方法问题。条约国内有权解释主体问题并非一个孤立问题,该问题的明确需以条约的国内法位阶以及国内法对条约/法律解释主体的明确规定为前提,涉及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间条约解释权力分配。因此,条约国内位阶问题是探讨条约国内解释主体问题的“先决问题”,否则,解释国内法律的制度安排就难以与条约国内解释主体问题明晰合理对接。在我国,条约国内法位阶因我国《宪法》规定缺失而存疑。例如,国务院(部委)签订的行政协定与基本法律间冲突问题就与条约国内法位阶在我国法上并不明确有关。
条约国内解释主体问题涉及法律解释权同立法权关系。“从现今各国实际情况看,有的国家的法律解释权包含于立法权之中;有的从属于立法权;有的同立法权平行存在;而在法治偏于落后的国家,则没有比较明确的制度,实践中则呈现比较杂乱的状况。”②周旺生:《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现代法学》2003年第2 期。根据我国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是最主要的法律解释机关,但“实际生活中,最主要最经常的法律解释主体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是最高司法机关”。③同上注,周旺生文。我国条约解释主体制度仍存诸多缺陷。
“国际法规则鲜少能获得精确表达”,④郑斌:《国际法院与法庭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韩秀丽、蔡从燕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4 页,脚注97。国际法体系的日益丰富使条约解释主体问题日趋复杂。不同法系国家的国内解释条约主体对待《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称:VCLT)第31 条、第32 条的习惯国际法解释规则的实践可能不同。“对条约解释规则的恰当适用需要正确程序和对达致正确解释的最佳保障。”⑤Richard K Garadiner, Treaty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t 29.而我国尚缺乏明确的包括条约解释主体在内的国内法制度保障。条约在我国的解释主体问题无论在立法、行政还是在司法领域都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条约国内解释涉及条约解释主体、解释方法、解释程序、解释效力、双语翻译等问题,而条约解释主体直接与条约制定主体问题相关。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尚未就我国批准或参加的条约在国内的解释主体及权限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一般可从诸多渠道发现条约的国内解释主体。⑥Asif H. Qureshi, Interpreting WTO Agreements: Problems and Persspectives, Cambridge,2006, at 75.必须根据其历史、文化、法律和经济背景来考虑国内措施,正如国内法院通常会考虑该背景一样。⑦US-Anti-Dumping Act of 1916 (Panel), paras 6.59, 6.41, 6.60.条约国内解释与国际解释间存在关联性,⑧例如在WTO 争端中,成员既可对争议的《WTO 协定》条款进行国内解释,也可寻求国外解释。DSU 第3.2 条仅规定了解释《WTO 协定》应遵循的规则,其第9 条仅规定成员有“寻求对一适用协定规定的权威性解释的权利”,其均未明确有权解释的主体范围。对《WTO 协定》的有权解释问题,该协定第9.2 条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对本协议和多边贸易协议有专属解释权。”“这表明解释条约的权力不会隐含着或不经意地存在别处。此外,DSB 通过专家组报告与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解释条约,两者不同。例如,DSU 第3.9 条规定:本谅解的规定不影响成员根据《WTO 协定》的决策程序寻求对协定条款进行权威解释的权利。上诉机构还指出,《国际法院规约》第59 条也有类似规定:‘法院之裁判除对于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但这并没有妨碍该法院发展出一套先例,并且这些先例的价值显而易见。……‘引用’和‘遵循’除名义上的区别外,事实上很难区分。事实上,WTO 是‘遵循先例’的。”杨国华:《事实上的遵循先例》,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 ArticleID =82306&Type=mod,2014年4月9日访问。条约国内解释主体及权限问题都关涉条约义务的履行、国内法与条约的一致性。本文主要研究条约国内有权解释主体。
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仅在第13 条规定不同文字文本在涉及条约解释中的作准问题。这涉及VCLT 第33 条。但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对条约国内法位阶、解释主体、解释效力、解释规则、解释的权力制约及程序等相关内容并无规定。国家主权决定了条约国内、国际解释于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谁制定的法律谁就有权解释”是罗马法原则之一。该原则表明法律解释主体与立法主体间的密切关系。假如条约国内解释会影响条约国内实施,那么,条约国内解释之国际法意义如何?例如,该解释结果会否导致GATT1994 第23 条规定的成员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换言之,条约国内解释在国内法、国际法上的效力如何?深入研究条约国内有权解释主体问题,对修订《缔结条约程序法》等国内法条约解释条款,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特别是还需从法律解释在法制整体中的位置角度来观察问题,才能完整认知并进而完整实现法律解释的意义和价值”。⑨同前注②,周旺生文。Wladock 认为“解释”是适用条约的一个根本要素。⑩Supra note 5, at 29.
因此,研究条约国内有权解释主体问题不仅涉及相关国内法修订及国内法位阶体系的完善,还有重要的国际法层面意义。
二、《缔结条约程序法》等国内法在条约解释主体方面的缺陷及原因
我国法律对条约解释主体的规定仍存诸多缺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制定历史不长,在规范缔结条约程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缔结的条约数量、内容等越来越多、复杂,其局限性渐显。该法实施已20年,其间我国外交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缔结条约问题依照现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程序进行处理,不仅缺乏必要的灵活性,而且有时面临实践突破立法的问题。外交部采取了很多临时性措施来弥补漏洞。该法的局限性包括条文过于原则,影响了可实施性;缔约权限及制约机制不够清晰;“条约”概念与分类使用较混乱;国家主席缔约权限缺失;未明确规定条约解释主体、解释程序、解释监督等。
有媒体指出:“一是该法仅有21 条,只对条约的谈判签署、国内审批以及公布和备案等程序问题作出了原则规定。一些条约主管部门反映,缔约程序法的内容过于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充分发挥该法作为工具法的指导作用;二是该法对国务院各部门办理缔约工作的事权规定不清晰,造成缔约工作的混乱。由于缔约程序法对国务院各部门在缔约工作的各个环节中需要承担什么职责、怎样承担职责缺乏清晰的规定,导致这些部门无所适从,办理的缔约工作出现混乱,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信誉;三是近年来,由于该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条约的权力与国务院核准条约的权力界限不清,影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审议批准一些国际条约和重要协定;四是对外缔约的工作实践产生新问题。条约主管部门在办理与港澳有关的条约时缺乏法律依据。”⑪谭丽琳、陈成智:《尽快修改缔结条约程序法》,《海南日报》2008年3月14日,第5 版。该法对各类条约的界定并不明确,导致运用缔约程序的不一致。该法中重要协定的范围偏窄,投资、税收等经贸类条约关涉国家经济主权,其地位和影响均非常重要,却不在重要协定之列。这些局限性都可能会妨碍条约国内解释主体及权限的明确确定。
《缔结条约程序法》存在的条约解释主体方面的立法缺陷,其原因还包括上位法立法缺失、自身存在缔约权限及制约机制方面的缺陷。通过国内立法和政策措施来理解条约在国内的实施离不开对条约国内解释主体制度的依赖。
除明确规定特定实施模式的条约外,只要缔约方遵守VCLT 相关习惯国际法条款,缔约方可自由适用其国内宪法规定的方法来履行条约义务。在立法方面,我国现行法并未厘清条约外延,这也会影响缔约主体、条约国内解释主体及权限划分。很多非条约性的国际文件如示范法、指南、宣言等往往成为正式条约的前身,即使最终没有形成正式条约,也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参与国家的立场和观点。因此,这些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但是,《缔结条约程序法》仅规定了正式条约的缔结程序,对于这些同样重要的文件却没有涉及。由此,在这些文件的国内解释主体等问题上缺乏国内法规范。
“一国法律解释制度通常由宪法、法律解释法和其他有关宪法性法律所建置。中国迄今尚无专门的法律解释法。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主要存在于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定中。”⑫同前注②,周旺生文。根据现行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在不同程度上共享缔结条约的职权”,⑬江国青:《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几个问题》,《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2 期。缔约权和条约的国内效力是两个有关联但又彼此独立的问题,各国宪法大多是将它们区别对待的。如美国宪法第2.2 条规定缔约权,第6 条规定条约的国内效力。我国宪法在条约国内效力这个问题上是沉默的。⑭同前注①,李鸣文。《立法法》只字未提条约,它既没有谈及条约的国内适用,也没有给予条约在国内法上任何地位或名分,更没有涉及条约的解释问题。关于条约的国内效力,《立法法》上也是一片空白。而条约的性质是法律,国务院及政府部门无权解释法律,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与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法律意义。
《宪法》、《立法法》等都存在相关规定的缺失,使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不明,造成法律体系的紊乱,令条约解释主体等事项难以在《缔结条约程序法》中明确。《立法法》第42 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其第43 条的规定,国务院及政府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无法律解释权,仅有请求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建议权。而上述规定与尚未被废止的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 决议”)存在一定冲突,因为根据该决议,法律解释权并非仅属全国人大常委会,包括国务院(部委)、最高司法机关等也有一定范围法律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运作制度,立法法已有若干规定,但不具体,需要进一步细化,使其既周全又可以操作。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运作制度,尚无法律作出哪怕是框架性的规定,因而其建置和完善的任务更显突出。”⑮同前注②,周旺生文。“我国宪法对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的适用及效力问题没有做出直接和具体的规定。我国缺少宪法性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导致国际条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⑯侯连琦:《论我国宪法中有关国际条约适用的缺失》,《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 期。条约与我国宪法、法律的位阶问题缺乏根本法依据,从而导致下位法对条约解释等事项出现明确的困难,由此亦导致学者对条约位阶的不同主张。该问题的答案明晰与否直接涉及条约国内解释的有权主体的确定。⑰在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目前学者关于条约国内法位阶的主要观点有五种。参见王勇:《条约在中国适用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20 页。大多数国家国内宪法都规定了条约在国内法的地位及效力。⑱同上注,王勇书,第68-69 页。此外,如果采用纳入或转化方式确定条约国内法位阶,对条约国内解释方法会产生影响。⑲Supra note 5, at 127.
该问题也涉及国内法和国际法在解释主体上的差异与联系。条约解释与国内法解释存在联系与差异。从国内法有权解释主体看,条约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不同解释主体对条约解释的效力产生直接影响。⑳相关论述可见万鄂湘、石磊、杨成铭、邓洪武:《国际条约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 页。条约国内解释主体之解释具有对内对外不同意义。从条约国内解释对其他缔约国的影响来说,一般认为,一个/少数缔约国对条约的解释对全体缔约方无拘束力,至多形成嗣后协定,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形成嗣后惯例。从条约解释主体看,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条约国内解释机关的解释是有权解释;而条约有权解释主体主要包括缔约国全体、一定条件下的国际司法机关和某些国际组织。有学者认为:“具有不同法律效力的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应处于不同地位。”㉑刘永伟:《国际条约在中国适用新论》,《法学家》2007年第2 期。从VCLT 规定的条约效力角度说,我国缔结的所有条约在我国的效力位阶是相同的;但从条约国内解释层面说,不同国内缔约主体缔结/批准/核准的条约在国内似乎有事实上的不同法律位阶,从而影响解释主体的确定。尽管其解释在国内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条约法意义上,这些国内不同主体的有权解释对其他缔约国通常不具有约束力。
此外,《宪法》对条约位阶及适用问题的规定尚付之阙如,则难以明确其制定主体和解释主体。原因还可能有,“如果人民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允许人民代表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予以解释,这种解释又具有法律效力,则人民代表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权威在逻辑上便不复存在,‘议行合一’便不复存在;所存在的,便是立法、司法、行政三者分权制衡的体制。而这种体制,许多人认为是不合中国国情的。”㉒同前注②,周旺生文。《缔结条约程序法》存在条约于国内法位阶不清从而造成我国条约解释主体不明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协调处理好宪法与条约的关系、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对法律规则的有权解释的权利仅属于有权力修改或废止该规则的人或机构,这是一个已确立的原则。㉓Delimitation of the Polish-Czechoslovakian Frontier (Questions of Jaworzina)PCIJ Advisory Opinion, Series B,No 8, at 37.换言之,条约缔约方全体最终控制条约解释的效力。实践中,诸缔约方之间协定并非获得有权解释的唯一途径。在条约法层面,条约解释主体通常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院和法庭以及国内法制中的条约解释者。在国家为条约缔约方情形下,条约解释者事实上指“政府、政府法律顾问和官员、国家立法机关、律师和非政府机构”。㉔I Johnstone, Treaty Interpretation: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Michigan JIL (1990-1991)12, at 371.《立法法》和“1981年决议”分别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法律解释权限范围所作的规定,形式上似乎划清了界限,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划清界限,因而不可避免会出现此类问题: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事项,往往由最高司法机关解释了;应由最高司法机关解释的事项,在少数情况下,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了。这种法定制度界限不清的状况,实际上也就是以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数量很少的主要原因之所在。㉕同前注②,周旺生文。
三、条约国内有权解释主体的理论分析
条约解释和适用并非完全是一个机械过程。条约在我国的解释主体实践中是多元的,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个人、研究机构等,而条约国内有权解释主体主要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当对条约条款存在几个不同国内解释时,例如有管辖权的国内法院适用不同解释而作出不同的、相冲突的裁决时,就有必要在国内法法理和国内法律制度框架下权衡这些不同解释。此外,条约国内解释主体及权限不明,会妨碍条约在国内的施行。
(一)国内司法机构的条约解释
我国《宪法》、《立法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都未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立法主体。实践中,最高司法机关已成为法律解释主要主体,其所作的法律解释具备事实上的“法律”效力。“两高相当多数量的以‘通知’、‘规定’为形式的司法解释就是一种规范性的解释,尤其是以‘规定’命名的司法文件,大多是对诉讼程序、证据、法庭规则等做出的规定,并不以解释相关法律文件为目的,甚至是没有可供‘解释’的相关立法。”㉖袁明圣:《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法商研究》2003年第2 期;汪全胜:《司法解释正当性的困境及出路》,《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3 期。“现今绝大多数国家法律解释权一般都主要由司法机关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确难以有效享有和行使主要的法律解释权,难以胜任主要的法律解释的角色。”㉗同前注②,周旺生文。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的数量达上千件。㉘同前注㉖,汪全胜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条约的司法解释对我国司法机关有一体遵循的效力。“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1981年决议”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2 条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法律解释权之法律根据。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2 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31 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备案。”然而,“具体应用法律”的含义及标准并不清楚,有学者认为:“司法解释应严格限制在个案解释的范围,不能超越一个个案而进行规范性的解释,即‘立法化解释’,司法机关‘具体应用’法律的理解,应严格限制于司法机关处理的个案中,严格限制于‘个别性解释’。”㉛同前注㉖,汪全胜文。这样,是有利于减少或避免司法解释的立法化现象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无法律解释主体及权限方面的规定。有学者提出,“1981年决议”的内容并没有被《宪法》、《立法法》所吸纳,致使其合法性没有得到更高层次的认可。《立法法》第五章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却未明确规定司法机关能独立进行法律解释。这里可能存在的争议是,比如说,《宪法》、《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的法律范围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其他属于“法律”的法规范性文件该由谁来解释没有得到明确,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可行使法律解释权。㉜同前注㉖,汪全胜文。笔者认为,该主张实际上试图通过对“法律”的广义或狭义界定来协调实践中法律解释的法理困境。
法院对条约的适用会涉及条约国内解释主体问题,并且国内外的(准)司法机构在解释条约时的考量和要求存在差异,其解释的效力也存在差异。对国内法院作出的不同、存在冲突的条约解释,国际争端裁决机构会面临选择问题。在“1916年美国反倾销法案”中,专家组提及国际法院做法,并引用了“巴西贷款案”:“如果在案件中确定国内法的一个问题对国际法院的裁决来说有根本性作用,则国际法院将不得不对国内诸法院所依据的法理进行权衡,且如果这并不确定或是割裂的,法院将选择其认为与法律最相一致的解释。”专家组认为,DSU 条款以及上诉机构实践都未禁止专家组“对(美国)国内法院的法理进行权衡,如果它是不确定的或是割裂的话”。这并不要求对美国法律进行独立解释,而仅是在诸相关判决中选择最符合美国法律的解释,以解决争端。专家组还列出了选择正确裁决时要考虑的因素。㉝Case Concerning Elettronica Sicula S.P.A[ELSI] (US v. Italy) ICJ (1989), see WT/DS162/R/Add.1, note 389 ; WT/DS136/R,para 6.53, 6.57, 6.58.在国际层面,如果条约国内解释与条约不一致,则该国可能需对此进行解释,在WTO 中,则可能会被其他成员提起诉讼。“国内法院的解释在WTO 争端解决过程中可能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其特点,尤其是被诉讼的诸当事方用以支持论证。确实,WTO 诸协定越是被纳入成员的国内法律体系,诸当事方在WTO 层面就越能获得更多这样的次级规范(second-generation norms)。”㉞Supra note 10, at 81.可见,不同国内司法机构对条约的直接或间接适用的结果并非仅有国内法意义,国内不同司法机构的相关判决可能被作为证据适用于WTO 争端程序中。
作为条约国内解释主体之一的国内法院适用(经转化为国内法的)条约而作出的判决还可能具有条约法意义,构成“缔约情形”,从而影响其他条约解释。当国内法院涉及国内措施的判决构成VCLT 第32 条“缔约情形”之基础时,这些判决就会变得很重要了。对成员国内法院判决原则上能否作为VCLT 第32 条的补充方法来予以考虑的问题,“欧共体无骨分割冻鸡关税分类案”的专家组认为,就第32 条而言,欧共体立法与欧共体判决间并不存在有效的差异。上诉机构同意该看法,并认为:“就第32 条下的解释目的而言,如果国内法院判决能有助于确定诸当事方的共同意图,我们同意专家组的一般不应将国内法院判决排除于作为条约‘缔约情形’的考虑。尽管如此,有必要指出,判决一般处理具体事项的争端,就判决性质而言,其与通常适用的立法行为(尽管在某些法律体系中判决可能具有先例的效力)相比不具有什么相关性。”㉟WT/DS269/AB/R,WT/DS286/AB/R, para 309.该案专家组认为,就第32 条目的而言,“缔约情形”可能有助于对《欧共体减让表》当时谈判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这一历史背景由代表欧共体主要形势的事件、行为和其他文件构成。该案专家组还引用了学者Mustafa Yasseen 和Ian Sinclair 的观点予以佐证。㊱WT/DS269/R , para 7.392; WT/DS269/R, para 289, 291 and 297.可见,该案上诉机构专家认为,国内司法判决可作为“缔约情形”而在条约解释中起到一定作用。作为条约解释的“缔约情形”之国内法院解释需具备下列条件:“只要与阐明条约文本含义是‘相关的’,没有时间限制;对该‘相关性’的确定要根据国内判决对条约文本的影响——特别是判决是如何有助于识别条约当事方的共同意图;需要依据诸客观因素来确定‘相关性’;国内法院解释已被官方出版且可公开获得。”㊲WT/DS269/AB/R,WT/DS286/AB/R, para 309.
此外,国家对条约的国内适用采不同形式,这可能会影响该国法院如何对待VCLT 解释规则。㊳Supra note 5, at 127.一些国家的国内法院在解释条约时重视VCLT 解释规则。我国国内法并未明确法院作为事实上的条约解释主体之一,在解释(经转化的)条约时是否应遵守VCLT 解释规则。
(二)行政机关的条约国内解释
“1981年决议”规定:“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有学者指出:“在法律解释权归属问题上,中国采行的制度是二元化的体制。一方面确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法律解释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另一方面,又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和其他方面也是法律解释主体,也行使法律解释权。这种二元化法律解释体制,在目前各国法律解释体制中殊为少见。”㊴同前注②,周旺生文。尽管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都会涉及条约解释,但政府涉及条约解释的机会最多,因为政府是条约谈判的主要机构。尽管通常会受到最高权力机关的制约,处理对外各领域的国际关系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条约的谈判、缔结和实施中,政府及其官员都必须解释条约。不同宪法安排下政府实施条约的方法存在差异。条约往往需要借助国内法措施来有效实施,因此,国内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在履行各自职能时都会涉及条约解释,㊵Supra note 5, at 127.但参加条约谈判和缔结的行政机关最了解所缔结的条约内容。
行政机构以行政立法或其他方式对条约所进行的国内解释也具有域外影响。政府措施表明其对条约的国内解释。这些行政措施或行政法规反过来对理解条约会产生影响。“成熟的国内贸易政策的内在一致性会形成对条约的国内解释结果。由于这个理由,国内贸易政策视角是理解影响国内层面上条约解释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㊶Supra note 6, at 73.政府机构拥有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力,不同行政机关拥有不同行政管理权力。政府机关通过其管理行为和执行活动制定与条约有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政策等,从而实际上参与了条约国内解释过程。例如,国务院发布的《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和《保障措施条例》的性质是行政法规,这些行政法规是以行政立法形式对《WTO 协定》之《关于执行GATT 第6 条的协定(1994)》、《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保障措施协定》的转化。这些国内立法形成的过程包含了最高行政机关对条约的国内理解和解释。“中国——影响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案也与条约的国内行政机关解释相关。中国政府出台的三部部门规章加强了对进口具有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关税征收的规制,反映了发改委、财政部、海关总署、商务部对WTO 规则以国内部门规章形式进行的解释或理解。“作为申诉方,欧、美、加等国认为系争措施以违反GATT1994 第3.2 条第1 句话的方式征收了‘国内费用’,而中国则抗辩认为征收的是符合GATT1994 第2.1 条(b)的‘普通关税’。”㊷朱榄叶编:《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7 页。该案经过专家组程序和上诉程序后以中国败诉结案,上述部委遂联合宣布取消实施4年多的《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这表明作为条约国内解释主体的国务院部委对条约的解释或理解并非任意,而要受制于条约。“中国稀土案”2014年专家组报告涉及中国《进出口关税条例》、《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等法规。可见,政府行政立法体现了其对条约的理解和解释,具有国内法效力,但通常不具有条约法上的效力。条约国内解释通常对其他缔约方无约束力,在国际争端解决中,其往往成为引发争端的系争措施。如果被WTO 争端解决机构确认违反了《WTO 协定》,败诉的成员就不得不废止或修改相关国内法措施。我国政府在WTO 中作为申诉方、被申诉方或第三方涉诉,相关权利主张往往体现国内条约解释主体(尤其是商务部)对条约的解释和理解——无论通过国内行政法形式,还是通过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对条约含义或国内法合法性的解释与论证。“申诉方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启动反映了一缔约方对《WTO 协定》解释的看法是如何相异于另一方的看法;当条约的一缔约方作为被告参与了争端,则反映一成员对被规定在其国内法中的《WTO 协定》的最初解释;通常作为第三方参与争端的成员往往会涉及对《WTO 协定》的解释过程的参与以及该国国内对诸体系问题的关注。”㊸Supra note 6, at 73.WTO 成员以不同身份参与争端解决,往往会从追求胜诉的策略性目的解释《WTO 协定》和本国国内法。国家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对同一条约条款用语的含义的理解或解释会发生变化。
(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条约国内解释主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与法律有同等效力。我国《立法法》第42 条至第47 条专门规定了法律解释权限与程序。这些解释程序中仍存缺陷。“研究和回答谁有权规定中国法律解释制度问题,便需要选择下限,也就是确定一个起码规则:有权规定法律解释制度的,至少应当是有权制定法律的机关;无权制定法律的机关,也同样无权规定法律解释制度。”㊹同前注②,周旺生文。与国内立法有关的事项在WTO中被认为是事实问题,对事实的确定会受制于与翻译有关的某些不确定性。
条约国内解释并非任意。在WTO 法框架中,全体成员依贸易审查机制对成员国/域内全部贸易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及对多边贸易的影响、与《WTO 协定》的一致性、对承诺的履行等进行定期监督。条约如何被一般性地或具体地进行国内解释,也是与完善我国条约解释制度相关的问题。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对条约在国内应如何被解释的主张往往存在差异。此外,国际法作为国内法的一个直接或间接渊源,国际法法理或WTO 法理何时以及如何在国内条约解释中被考虑,也会对解释结果是否会与该条约保持一致性产生影响。
在国际海洋法领域,作为“一揽子交易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未解决或明确所有海洋法问题,该公约仅规定了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文物、历史性所有权对划定领海界限的影响(第15条),其中尚未见到适用于中国南海“九段线”的条款。在中国国内层面上,对南海“九段线”以内的海域享有历史性权利或类似领土主权(权利)的理念一直贯穿于我国海洋政策、立法与实践中。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 条规定:“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该条规定的历史性权利之含义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历史性权利的含义有所不同。该差异与我国人大常委会如何在国内法层面理解公约条款相关。为实施条约而进行的国内立法之起草历史、方式,可体现国内相关政策。但是,对为了在国内实施条约而制定的国内法进行的解释往往应遵守关于法律解释的国内法原则和规则,这些原则和规则能展现国内解释条约的过程。同样,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是结合中国的法律、具体情况和外交实践,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转化为国内法的结果”。㊺黄德明:《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 页。该条例“不仅澄清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不明确的条款,而且对公约未作规定的地方也加以了补充和完善”。㊻朱奇武:《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 页。该条例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以国内立法形式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进行的转化和解释。
在直接适用条约的一些国家,在同意成为条约缔约国时向立法机构或其他机构提交的材料中常包括对条约义务的解释性备忘录或其他指南,虽然这样的指南包括了对条约条款的指导性解释,但从根本上说,该解释是对条约用语含义的单边理解。尽管如此,在源于对条约含义分歧而对条约的解释过程中,有时会提及相关指南。在采“转化”方式的国家中,与条约文本在措辞上的任何差异可能被当作立法者对条约用语的理解。㊼Supra note 5, at 128.全国人大在批准我国加入条约时,其批准文件中时常载有对条约的立法解释。如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对1965年《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之文件中,在公约正文之前,有一段说明(解释或对法官适用该条约的指导),其中还包括对第10 条的保留。不过,《立法法》在法律解释草案说明方面的缺陷是,该法“没有规定列入审议议程的法律解释草案是否应当同时提出关于草案的说明”。㊽同前注②,周旺生文。
在WTO 争端中,国内有权解释成为案件事实。因此,国内立法机关应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做好条约国内解释工作。“国家(National)解释和国内(domestic)解释过程都会与WTO 争端解决过程和《WTO 协定》的实施间相互影响。一旦缔结了国际协定,就必须在国际层面对之进行解释并涉及到国内立法,并以该方式实施。由于同样原因,为得到实施,必须在国内层面解释国际协定。”㊾Supra note 6, at 70.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TRIPS 第1 条体现了国际法与国内法间的相互协作和制约关系。㊿在“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310 节”案中,专家组认为,当根据《WTO 协定》第26.4 条对国内法与WTO 义务的一致性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诸成员法律制度中范围广泛的多样性。在不同法律制度中可以不同方式保证相符性。有价值的是最终结果,而非获得最终结果的方式。只有通过理解和尊重每个成员的法律制度的方法,才能确立对相符性的准确评估。即使授予政府机构具体权力的制定法用语可能在表面上与WTO 规则相符,但该负责机构在其被授予的自由裁量权限内可能会采取与WTO 义务不符的国内标准或行政程序,结果使全部法律违反了WTO 法。相反情形可能同样正确:尽管制定法用语可能构成表面不一致,但在对该相同法律的其他行政的或机构的因素审查后,可合法解除该不一致性。WT/DS152/R, para 7.24,7.27.如前所述,如果成员域内法规定被其他成员视为不符WTO 协定,就可能涉诉,如2000年“加拿大——药品专利保护案”(WT/DS114/R)中,欧共体对《加拿大专利法》第55.2 条的合TRIPS 性提出申诉。条约国内解释应与缔约方在约文中体现的共同意图一致,对条约任意、非善意甚至扭曲的解释是对“有约必守原则”的违反。[51]冯寿波:《论条约的“善意”解释》,《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5 期。“并不存在普遍可适用的制度,每个国家的(条约国内解释)程序受其宪法和法律制度的支配。尽管如此,单边解释必须诚实反映缔约方间协定下义务。国内法中的缺陷并不构成缔约方违反条约义务的抗辩。”[52]Supra note 5, at 110.VCLT 第26 条、第27 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在确定国内法与WTO 协定相符性方面,“印度专利案”的上诉机构认为,为此目的的国内法律是一个事实问题:“在国际公法中,国际裁决机构可能会以几种方式来看待国内法。国内法可起到对事实的证据作用,并提供国家实践的证据。尽管如此,国内法也可构成与国际义务相符或不相符的证据。”[53]WT/DS50/AB/R, para 65.因此,作为我国法定条约解释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转化方式解释条约时,其所制定的国内法是对条约的国内理解和解释,具有一定国际法意义。
(四)条约名称、位阶、解释效力与条约国内解释主体
根据VCLT 第2.1 条甲项,条约可采取其他特定名称,但VCLT 并未明确不同条约名称在法律意义上是否存在差异。从条约法律效力角度而言,这些不同条约名称并不影响其对缔约方的拘束力。“条约的效力不取决于它的名称。因此,国际条约不论采取什么名称,都具有国际法上的法律效力。”[54]徐杰:《论条约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4 期。从其他国家的视角看,中国的缔约权是统一行使的,不管是由《缔结条约程序法》等国内法规定的哪个机构或个人来行使。尽管如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条约的不同名称间无任何差异。从国内视角看,不同国家国内法对缔约程序、权限、条约形式(名称)、国内解释主体等的规定往往具有国内法上不同的意义或效果。“在国际法领域中,有一种普遍意见,认为文件名称具有法律意义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难于接受的。”[55][美]小约翰·金·甘布尔:《多边条约各种名称的不同意义》,卢莹辉译,《环球法律评论》1983年第1 期。就《缔结条约程序法》而言,不同机构或个人有不同缔约/批准/审查权限。实际上,使用不同名称的条约往往与该条约的内容、批准程序等问题存在一定相关性,例如,造法性条约常使用“公约”这个名称。不同性质或重要性不同的条约,是造法性条约还是契约性条约,与缔结/批准条约的机构/个人的权力层级直接相关。由不同国家机构签订/缔结/批准/核准的条约,尽管对其他缔约国来说,对中国都有同样法律效力,但从中国国内层面说,则意味着条约缔结、解释权力在不同国内机构间的配置。对国内缔结条约权限的严重违反可能会影响条约效力。条约国内位阶似乎仅具国内法意义。从国际法理看,“有约必守原则”、“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已成习惯国际法规则,VCLT 第27 条、第46 条明确规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效力关系。VCLT 第46条规定国内法对缔约权限的规定通常并不构成其撤销同意的法律依据,VCLT 第47 条是第46 条的例外,表明国内法对缔约权限的规定对条约效力的影响。缔约权限直接与条约国内解释主体的确定问题相关,且国内法对缔约权限的配置并非仅有国内法意义。从确定条约国内解释主体而言,“国内法位阶比照论”似有一定价值,因为我国国内法对不同机构规定了不同的解释法律的权限。“国内机构或个人对《WTO 协定》的解释会受到其所处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的制约。该国内框架可能会清楚地规定在实施WTO 的立法中。就解释者的环境而言,这会对解释产生影响。尽管这严格来说更是一个法律渊源的事项,但该背景因素可能会对解释过程产生影响,特别是对解释方法产生影响。”[56]Supra note 6, at 74,75.就我国来说,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具有不同的法定职责,作为条约国内解释主体在解释中受到的制约因素存在差异。例如,“解释履行WTO 承诺的国内立法之目的解释方法可能不一定与WTO 争端解决机制层面上对WTO 义务的严格解释相一致。为了在国内解释中既不出现对WTO 义务的扩大解释,也不出现与国际承诺不一致的解释,需要使国内对WTO 层面上解释WTO 诸协定的方法的认识保持一致”。[57]Id. , at 72.
可见,条约名称与国内法规定的缔约主体、权限及国内解释主体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不同名称的条约在国内的不同位阶可能会影响条约国内解释主体的确定。国内机构或个人对条约条款含义的解释既受制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又受制于国内法涉及法律(条约)解释问题的相关规定。条约的国内法位阶与解释主体采取何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关联性。条约的国内解释主体有可能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视角,极力寻找条约的漏洞,甚至故意曲解条约用语含义和效力。事实上,国际法解释方法与国内法解释方法之间既存在密切联系,也存在明显差异。DSU 已明确了解释WTO 诸协定所应遵守的国际公法规则——VCLT 第31 条、第32 条。为了增加条约下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使条约的国内解释方法与VCLT 规定的条约解释方法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协调,是有必要的。
尽管条约解释借鉴了国内法解释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但二者在解释效力方面仍存在某些差异,条约国内解释主体在解释中需予以关注。“与国内法解释相比,国际法解释在解释主体、效力、客体和方法等方面体现出自身特点。在国内法中,主体的解释权力与其解释的法律拘束力是紧密结合的,只要是有权主体的解释必然会相应的具有拘束力,而非有权主体所做的解释没有拘束力。对于究竟什么是条约的‘有权’和‘非有权’解释,国际法学界给出的较为清楚明确的界定却实在不多。”[58]韩燕煦:《条约解释的特点——同国内法解释的比较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1 期。李浩培先生根据条约解释的主体、解释的效力分别界定了官方解释和有权解释的含义。[59]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 页、第347 页。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组织中的司法机构对国际协定的解释可能具有立法特征。”[60]J.P. Trachtman and P.M. Moreman,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s: Whose Right Is It Anyway? (Winter) HJIL,2003, at 221-250.例如,国际法院判例的作用已超过个案范围;WTO 争端解决机构判例作为事实上的“先例”也时常被其他案件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引用。《国际法院规约》第38 条将司法判例作为国际法的辅助渊源。条约缔约方作出的解释未必有拘束力,而国内法的有权解释主体作出的条约国内法解释有相应效力,即其解释权力与解释效力是统一的,而非像条约那样可能是割裂的。“国际社会权力的分散反映到条约解释上,就表现为一个或部分缔约国的解释只能拘束该国或该部分国家,对其他缔约国则没有拘束力;而那些被国家授权的机构所做解释虽然是有权的,但是否有拘束力,还需视主权国家态度依具体情况而定。个别缔约国的解释具有拘束其本国的效力;而且这种拘束力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基于善意和禁止反言的原则,该国对于其解释不能够随意更改或违背。”[61]同前注[58],韩燕煦文。部分缔约国间的“嗣后协定”仅对该条约的解释起到与“上下文”大致相同的作用,单个缔约方的条约解释行为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可能会对条约解释具有意义,但其效力尚无定论。“缔约方的一致贯行是其对条约正确解释的最好证据。”[62]Supra note 5, at 225. 关于嗣后惯例的含义、形式、效力等问题,可参见冯寿波:《“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 条“Subsequent Practice”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 期。嗣后惯例构成对当事方就条约含义达成的谅解的客观证据。[63]Kasiki / Sedudu Island (Botswana / Namibia) (1999) ICJ Reports 1045, at 1076, para 49.
四、完善我国条约解释主体制度的立法建议
菲德罗斯认为:“国家宪法可以规定的,决不是国际法的国际效力,而是它在国内的实施。”[64][奥]阿·菲德罗斯等:《国际法》(上册),李浩培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6 页。在我国,包括条约解释在内的法律解释问题的解决目前可通过修订相关立法作为过渡,在条件成熟时,可制定我国《法律解释法》,进一步明确条约国内解释主体及权限。“在法治国家,法律解释制度通常由宪法予以原则规定,再由法律解释法予以集中、系统的专门规定。”[65]周旺生:《改善中国法律解释制度诸境况》,《法制日报》2007年4月8日。正如有学者所主张的,应当“在《宪法》与《立法法》中,以‘立法解释’概念取代‘法律解释’之概念,使语义表述更为精确性,另外,在《宪法》与《立法法》中确立‘司法解释’的地位”。[66]同前注㉖,汪全胜文。条约解释立法有助于使条约国内解释规范化,明确和澄清条约国内解释主体及权限,避免解释冲突,以促进条约国内有效实施,维护国家利益。“用宪法接受条约,即将‘经我国合法缔结和公布的条约,为我国国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我国宪法。”[67]同注⑰,王勇书,第79 页。对中国有效的国际条约实际上已构成中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应在我国宪法或法律中写入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的一般规定来确认这一事实。[68]赵建文:《国际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法学研究》2010年第6 期。
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规范性、抽象性的统一的法律解释和由法官在个案中作出非规范性的法律解释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69]魏胜强:《司法解释的错位与回归——以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为切入点》,《法律科学》2010年第3 期。我国应修改和完善《宪法》和《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权属制度的规定,给予最高司法机关主要的、经常的法律解释主体的合法地位,并进而完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制度,使法律解释主体的法律地位和实际作用呈现和谐的而不是分裂的局面。最高司法机关法律解释范围制度,同样需要以法定形式使其具体化和具有可操作性。至于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程序的法定制度尚付阙如的状况,当然更需要尽快转变。完善中国法律解释制度,需要简化和统一法律解释的名称,实现法律解释内容和形式的统一。[70]同前注②,周旺生文。“建议在《宪法》第127 条和第129 条分别增加规定最高院和最高检有权对于在审判/ 检察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71]同前注㉖,汪全胜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如何行使法律解释权及其制约问题、各自作出的法律解释冲突的解决,也需加强研究,尽早作出明确规定。应使《立法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范围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和具有可操作性。如果认为条约在国内法中的位阶高于宪法,则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解释我国缔结的条约,这显然与我国条约解释实践不符。如果认为其位阶低于《宪法》而高于或等于我国法律,则根据《立法法》第42 条,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解释条约。在广义的法律制定方面,国务院仅有权根据宪法和狭义的法律来制定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第43 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并无解释法律的权力。但这一规定又与我国条约解释实践并不完全相符。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解释条约的例证尚少,外交部、商务部也无解释法律的权力。但涉及条约解释的相关法律文件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等实际上行使了条约解释权力。如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87年发布《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该通知涉及对《公约》第4 条的解释,这似乎可视为现行法制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蚀。我国现行的“议行合一”政治制度决定了难以将法律解释权完全赋予最高司法机关,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事实上难以有效行使法律解释权。从长远看,将法律解释权赋予最高司法机关可能是未来发展趋势,但如何规范与制约其解释权的行使,尚需研究。当前可行的方案或许是进一步规范条约国内解释主体的现有解释权限,并加强相互协调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能。
我国宪法宜对条约的国内效力作原则性的规定。《立法法》在细化宪法的原则性规定方面应起重要作用。[72]同前注①,李鸣文。鉴于我国涉及条约解释主体的立法、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争议,而短期内修改《宪法》、《立法法》的可能性又不大,参照国外相关立法例,我国目前应完善《缔结条约程序法》中的条约解释(主体)条款,明确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并由此为确定条约国内解释主体和权限奠定基础,同时,应完善我国条约缔结、解释中的权力制约机制、解释程序。建议在《缔结条约程序法》修改草案中增加下列内容。其一,依法批准或参加的条约,自对我国生效后有高于国内法律的效力,但与我国《宪法》相抵触的条款,《宪法》具有高于该抵触条款的效力。其二,对具有基本法律性质的条约的解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解释权力;对具有契约性质的经贸条约的解释,国务院及相关部委拥有解释权力;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个案中对条约的解释不具有普遍效力。其三,应规范条约的汉译和国内法的外文翻译。其四,加强对条约国内解释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法律解释与制定、修改法律不同,因此,有必要划清法律解释同法律制定、修改之间的界限,否则,就会“使立法的严肃性受损害。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同法律修改和补充混同起来,就直接侵犯了立法权,堕入违法以至违宪的境地”。[73]同前注②,周旺生文。为了实现我国对条约解释的法治化,在我国《立法法》上明确国务院及其部委的法律解释权限、程序及效力也十分重要。正如有的学者所主张的,“《立法法》虽然是规定国家的立法制度,但也需要确立‘各制定机关对其制定的法规性文件的解释是立法解释,立法解释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性文件具有同等效力。’严格将司法解释限制在‘个案’上,其他解释权力可以由两高提出议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进行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限于其个案的范围。行政解释只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有约束力,不能对司法机关产生约束力。司法解释不能侵越立法权。建立与《立法法》、《监督法》规定相一致的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制度。”[74]同前注㉖,汪全胜文。“最高人民法院不时地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有关部委等联合发布司法解释,进一步损害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75]同前注[69],魏胜强文。目前,尚不清楚上述机构的条约解释间存在冲突的解决途径。同时,“行政机关的解释可以对法院适用条约具有参考价值,也可以具有决定性意义”。[76]同前注①,李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