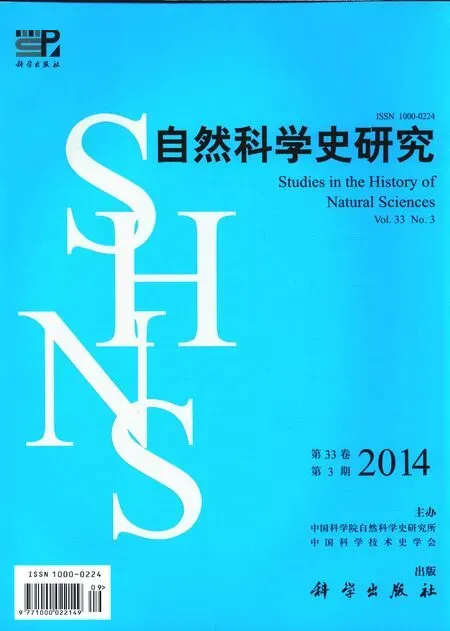中国古代的蚊香
2014-02-02罗桂环
罗桂环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
中国古代的蚊香
罗桂环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
基于传统的烧香和端午节的卫生习俗,以及对蚊子习性的了解,我国宋代发明了蚊香。当时称“蚊烟”或“蚊虫药”,主要制作材料是艾草、雄黄和浮萍,产品类似线香,并出现专门的作坊。明清时期蚊香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原材料不断增多,包括阿魏、羌活、川芎、硫磺、樟脑和烟草等等。产品类型也更多种多样。19世纪中叶,我国的蚊香配方曾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
发明 蚊香 端午 宋代
蚊子是我国各地常见的一类吸血昆虫,古往今来,国人深受其害。尤其是在夏天,它大量繁殖,嗡嗡乱“叫”,吸血散毒,严重影响人们的休息和健康。为此,古人曾煞费苦心地设法避其伤害,“蚊烟”亦即后来的蚊香是其中一项很有意义的发明。前些年,笔者曾在台湾的科普杂志《科学月刊》述及我国古代的此项发明[1]。考虑到蚊香发明的重要性,有必要详加考证、研究,故在此全面补充史料,系统阐述其发展史。
1 古人对蚊子危害和习性的认识
蚊子形体虽小,对人的危害却很大。其中之一就是叮咬人体,严重影响睡眠和休息。古代哲人老聃所谓“蚊虻噆肤,则通夕不寐矣”[2],是很多南方人都有过的切身体会。它繁殖迅速,能在短期内大量形成,故《汉书》有“聚蚊成雷”[3]之说。尤其在我国南方的许多地方,一到傍晚,蚊子就如影随形,团团围在你的身旁,伺机攻击,弄得你怒火中烧而又无可奈何。人们厌恶这种虫子由来已久,历史上细数其吸血并破坏人类正常生活恶行的诗文不胜枚举。晋代学者傅选《蚊赋》这样写到:“众繁炽而无数,动群声而成雷。……乃餐肤体以疗饥,妨农功于南亩,废女工于杼机。”([4],1683页)形象刻划出蚊子不但侵蚀人畜机体,让人疲于奔命,严重影响人们的睡眠和休息,进而影响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的种种“罪状”。唐代诗人皮日休也曾在《蚊子》诗中写道:“隐隐聚若雷,噆肤不知足。皇天若不平,微物教食肉。贫士无绛纱,忍苦卧茅屋。”生动地道出大量滋生的蚊虫,对缺乏蚊帐的贫穷民众的残害。当时另一诗人韦楚老《江上蚊子》更是不无悲情地写道:“飘摇挟翅亚红腹,江边夜起如雷哭。请问贪婪一点心,臭腐填腹几多足?”对蚊子的丑恶、发声的恐怖和叮咬吸血之无情和贪婪充满无奈。
蚊虫危害之严重,还在于其危害地域广且时间长,加上其行踪飘忽、隐蔽,善于攻击和潜逃,难以防范和消灭,越发让人感到郁闷。唐代吴融的《平望蚊子》写到:
天下有蚊子,候夜噆人肤。平望有蚊子,白昼来相屠。不避风与雨,群飞出菰蒲。扰扰蔽天黑,雷然随舳舻。……吾闻蛇能螫,避之则无虞。吾闻虿有毒,见之可疾驱。唯是此蚊子,逢人皆病诸。
诗人在比较了各地的蚊子之后,认为平望的蚊子最凶狠,在比较了各种毒物的情形之后,认为蚊子是让人最无奈的毒虫。
在述及蚊子危害周期之长方面,宋代诗人秦观《冬蚊》诗指出:“蚤虿蜂虻罪一伦,未如蚊子重堪嗔。万枝黄落风如射,犹自传呼欲噬人。”认为在各类害虫中,蚊之危害尤烈,直到寒凉的深秋初冬仍然还要叮人。而华岳(?~1221年)的《苦蚊》诗写道:“四壁人声绝,榻下蚊烟灭。可怜翠微翁,一夜敲打拍”。[5]它们都道出了对这种虫子危害的愤懑和无奈。
古人认识到,蚊子不仅叮人吸血,还传播疾病,致人和动物病亡。宋人的《物类相感志》记载:“鳖与蝤蛑被蚊子叮了即死。”[6]明代宋濂“逐鷆①传说中能吐蚊的一种鸟,又称“蚊母”。文”指出:“蚊,害物虫也,凡有血气者,恒病焉。”[7]有人指出“蚊蚋噆草间,人马俱病”[8]。宋代有人记载这样一件事:“秦州西溪多蚊子,……有厅吏醉仆,为蚊子所啮而死,其可畏有如此者”[9]。蚊子之毒,让当时的人不寒而栗。在环境卫生很差的社会条件下,有人不禁哀叹:“昼苦青蝇夜苦蚊,乾坤无地着闲身。”[10]著名学者欧阳修写的《憎蚊》也感叹:“虽微无奈众,惟小难防毒”![11]
由于蚊虫危害惨烈,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其形态习性。《东方朔传》②这个书并非《汉书》里的《东方朔传》,应该是《隋书·经籍志》提到的《东方朔传》,不过该书后来似乎失传了?说蚊子“长喙细身,昼亡夜存,嗜肉恶烟”。[4]五代诗人杨鸾《即事》诗所谓“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都说其昼伏夜出。宋代博物学者罗愿在《尔雅翼》指出:“蚊者,恶水中孑孓所化,噆人肌肤,其声如雷。东方朔隐语云:‘长喙细身,昼亡夜存。嗜肉恶烟,……。’其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吴兴号豹脚蚊子。”[12]当时人还指出:“蚊子初不能鸣,其声乃鼓翅耳。”[9]注意到它们主要在水中繁殖,常潜藏草丛中。此外,对蚊子喜欢在温热水域的生活环境也有一定的认识。南北朝时期有人指出“漠北高凉,不生蚊蚋”。[13]明代学者指出,南京“后湖……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湿,水泉污浊,监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14]
明清时期的学者对蚊子的习性和形态以及生长环境有更全面的认识。明代医家李时珍指出:“蚊处处有之。冬蛰夏出,昼伏夜飞,细身利喙,咂人肤血,大为人害。”[15]清代学者恰当地用如下字词描绘这种毒虫:体若粟,吻若锥;口衔钢针、利嘴迎人,目察毫端,飞扬跋扈、飞成市、聚若雷、趁暗幸昏、投间抵隙、觅膏腴,恶毒;污水是宫;蛛网收拾、伏翼扫除。[16]形象地综合出其形态特征,发育环境,以及其天敌有蜘蛛和蝙蝠等。其中颇为引人注意的是至迟从汉代(东方朔)开始,人们已经注意到蚊子怕烟。
2 蚊香的出现和制作材料
为了防止蚊子的祸害,人们逐渐发明了蚊帐和蚊香。蚊香的发明可能与古代烧香祭祀的习俗有关。众所周知,我国很早就有烧香祭祀的习俗。最早记载这一习俗的是《诗·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意思就是周人通过燔柴升烟来祭天,称作“禋”或“禋祀”。后来《周礼·春官·大宗伯》记有大宗伯之职包括:“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玄注:“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槱,积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当然,那时还没有香,烧的只是一些柴草和布帛以形成烟。《周礼·天官冢宰第一》提到“甸师”职责有“祭祀,共萧茅”。这里的萧是一种香草。汉代开始有真正的“烧香”,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香炉可以证明这一点。《西京杂记》记载西汉长安巧匠丁缓不但重新制作出“卧褥香炉”(也称“被中香炉”);而且创制“九层博山香炉”。[17]《汉官典职》也记有“执香炉烧薰”[18]这类事务。《汉书》提到“薰以香自烧”([3],3685页);《后汉书》有“香薰之饰”的说法。这些史实说明当时确有烧香习俗,但意义不仅仅限于祭祀,也包括改善起居环境。同书“贾琮传”有“交阯土多珍产,……异香美木之属”。[19]表明人们已经注意边远地区的香料产地。《博物志》记载,汉武帝时曾通过焚烧“香”以“避疫气”[20]。说明烧香从“与神明沟通”到“薰饰”、“避疫气”。香随材质的变化,功能也在扩大。由于蚊子危害剧烈,古人又知道它怕烟,因而在此基础上衍化出以“驱蚊”为目的的“蚊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蚊香的发明还可能与古人端午节的卫生习俗有关。《荆楚岁时记》记载:端午“四民并踏百草……采艾以为人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早年端午节人们除在门口插上艾草外,还常浸泡雄黄酒涂在身上。这样做可能使空气清新一些,其次还有防止蚊子叮咬的作用。记得笔者年幼的时候,村里的长辈常常会在端午节时,在小孩额头点雄黄酒,据说可以防止蚊子咬。当然一般家长还会给自己的孩子挂上一个香袋,再吃一些蒜头以增强防病和驱虫的效果。
蚊香出现的具体时间现在还不太清楚。欧阳修的《憎蚊》诗有“熏之苦烟埃,燎壁疲照烛”。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已用烟熏的办法驱蚊。虽然欧阳修的诗中没有提到用何种材料产生烟雾,但宋代的其他文献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
欧阳修的好友梅尧臣曾在诗中提到用艾驱蚊。在《和江邻几景德寺避暑》一诗中,他写道:“枕底夕艾驱蚊虫”;在《次韵和永叔夜闻风声有感》,他写道:“驱蚊爇蒿艾”。[21]另外,宋代《孙公谈圃》也提及用艾熏蚊。书中记载:“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烟熏之。”[22]上述史料表明,艾这种有特殊气味、很早就被用于“辟疫”(禳毒气)的菊科植物,至迟在北宋时已经开始被用于熏蚊。当然,它被用来制作蚊香,可能与其易燃,长期以来被中医当作灸的材料有关。《名医别录》记载它“主灸百病”。根据宋代《本草衍义》记载:“艾叶干捣,筛去青渣取白,入石硫黄为‘硫黄艾炙’”。很可能是在这种“硫磺艾炙”的传统制作工艺基础上,使人们联想到将其制作成实用的“蚊香”。
据宋代冒苏轼之名编写的《格物粗谈》记载:“端午时,收贮浮萍,阴干,加雄黄,作纸缠香,烧之,能祛蚊虫。”([23],15页)这里说的以浮萍和雄黄制作的“纸缠香”应是较早的蚊香,其形态为有芯的棒香(古代也称棒儿香)。同书还记载:“水中浮萍,干,焚烟熏蚊虫则死”;“烧鳗鲡鱼骨,蚊虫化为水。”([23],7、13页)。另一冒名苏轼编写的《物类相感志》记载:“麻叶烧烟能逼蚊子”([6],27页)。说明浮萍干、雄黄、鳗鱼骨和麻叶可能都是人们用作蚊香的材料。其中雄黄为硫化砷矿石,也是古代用途很广泛的杀虫剂。《神农本草经》记载雄黄“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唐代《本草拾遗》记载它“主恶疮杀虫”。浮萍,《神农本草经》记载它主治“暴热身痒”[24]。古人认为用之熏烟可以驱蚊,这二者的配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另据《东坡杂记》、《绍陶录》等书的记载,当时人们熏蚊的植物还有苍术、蒌蒿等。值得一提的是,《格物粗谈》还提到制作蚊香时,于端午节取材,不禁让人联想到“蚊香”的产生与这个节日的插艾草和使用雄黄酒“禳毒”有密切的联系。
在宋代“蚊烟”已经是一种常见的日用品。宋人陈藻《乐轩集》的“入寿昌县界”写下“野店蚊烟接,官途松吹长”。南宋浙江鲁应龙所著《闲窗括异志》记载:“海盐县倪生,每用杂木碎剉炒磨为末,号曰印香。发贩货卖。一夜,烧熏蚊虫药,爆少火入印香箩内,遂起烟焰。……奈何遍室烟迷而不能出避。须臾,人屋一火而尽。”[25]这里“熏蚊虫药”应该也是一种蚊香。不仅如此,南宋时期的《武林旧事》一书提到制作“蚊烟”的作坊和“小经纪”。[26]说明早年的蚊香叫作“蚊烟”。周密的《武林市肆纪》也记有“蚊烟”作坊。[27]这些史实都表明蚊香在我国宋代确已开始有规模的商品生产。
3 蚊香制作在明清时期的发展
利用蚊香驱蚊的方法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制作蚊香的形制趋向多样化,原料也进一步增多。这种情形在明初朱橚组织编写的《普济方》中有充分的反映。
《普济方》的“驱蝇蚊”方记载:“用锯末晒干,以硫磺多、信①指砒霜。少,用和作香筒烧之”。显然是一种制作线香的方法。书中“辟蚊子”方记述:用“臭樗皮(细切),阿魏、芫花、夜明砂(炒)、罗木(镑),右五味粗捣、筛,以慢火于房内焫之”;以及“苦楝花、柏子、菖蒲各一两,右为散,慢火烧,闻气自去矣”。([28],4937页)这两类则是“散香”。书中“熏蚊子”方记载:“香附子、苍术(半斤)、雄黄(别研)、樟脑(别研,各半两),右为细末,入雄黄樟脑和匀,重罗,打作香印,爇之。恐樟脑难打,临用时略焙令燥”;和“五月五日取浮萍草晒干,及三月收苦楝花、夜明砂合捣为末,作香印烧,蚊子尽去”。以及“驱蚊药方”“每用木屑一斗,入天仙藤四两,裁断剉碎同研为末,如印香燃之,蚊蚋尽去”;记述的都是印香的制法。另有用:“浮萍、厚朴、羌活、芎各等分,……为末,作香篆烧”。记述的是香篆制法。书中还记载可“用皂角、苍术、干浮萍等分为末,饭丸弹大,令干烧之”。说的是丸香的制法。
书中还记载有其他数种蚊香的配方。其中“驱蚊蚋壁虱”方用:“苍术一斤,木鳖子、雄黄各二两半”;“去蚊虫”方:“五月取浮萍阴干,烧烟”;“治蚊虫”方有:“以鳗鲡鱼干者,于室中烧之,即蚊子化为水矣。”又方“以浮萍、羌活捣为末,加苍术、白胶香亦得,如香焚之”;“辟蚊蚋“以送迷香合羌活,为丸散,夜烧之”。“驱壁虱”方有:“用雄黄一两,信二钱,为细末和匀木滓作‘蚊烟’烧之”。([28],4622—4626页)
《普济方》收录的都是迄于明初时制作蚊香的各种成分配方。其原料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通常是由杀虫剂构成。如上述硫磺是一种易燃、有特殊气味的杀虫剂;砒霜是古代著名的毒药,也可用作杀虫剂;天仙藤、木鳖子也是有毒的药物。臭樗即臭椿,和阿魏、芫花都是有特殊气味,是可用于杀虫的中药,可能因为其特殊的气味,焚烟能驱除蚊子。苦楝花、皂角中医常用于散结杀虫。还有一类芳香或特殊气味浓烈可驱虫的药物。其中苍术焚烟古人认为可以辟“疫气”;柏子、菖蒲、香附子、樟脑气味芳香可以驱虫,尤其是樟脑,至今仍为重要的驱虫药物,故也被用于蚊香制作。羌活、川芎、厚朴也都是气味浓烈的中药,用于烟熏蚊虫应该与艾有类似功效。还有一类是辅助性的成分,如锯末、夜明砂等。主要的着眼点在于毒杀和驱赶,还要能够燃烧。
为了便于人们记忆,《普济方》这部书中还收录了当时制作蚊香原料的歌诀三首:
夜明砂与海金沙,二味和同苦楝花。每到黄昏灯一捻,蚊虫飞到别人家。木鳖茅香分两亭,雄黄少许也需秤。每到黄昏灯一柱,安床高枕到天明。萍朴楝活芎,天仙术最雄。捣罗为香爇,一梦见周公。
除《普济方》外,明代一些养生类和本草著作,以及动物著作,甚至农书,都有熏蚊药物的记载。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用肉桂和薰陆香烧烟可以辟蚊。[29]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辟除诸虫(辟蚊蚋)”中也提到:“浮萍(烧熏,或加羌活)”([15],352页)。其后《农政全书》中则提到“鳗鲡鱼干,于室中烧之,蚊虫皆化为水。”[30]同一时期的《谭子雕虫》一书记载:蚊“性恶烟,旧云,以艾熏之则溃。然艾不易得,俗乃以鳗鳝鳖等骨为药,纸裹长三尺,竟夕熏之”。[31]上述记载说明古人确实认识到艾是一种很好的蚊香材料,但由于有些地方不易获取,人们就设法用其他代用材料。上面的史实表明,虽然明代的医家发掘了不少制造蚊香的新药材,但传统的艾、浮萍、鳗鱼骨等,依然是当时常用的材料。
明清年间,“蚊烟”仍然是一项可观的产业,售卖“蚊烟”也是小商贩的一种谋生职业。著名文人归有光的《可茶小传》中提到:“可卖蚊烟凉箑遣日”。[32]《浙江通志》记载杭州府的物产有“蚊烟”。书中记述:“万历杭州府志,蚊,土人以艾烟裹纸熏之,辄避。”[33]结合上述《武林旧事》等著作来看,杭州制作蚊香可谓历史悠久。
清代晚期,我国的蚊香制作技术开始逐渐为西方人所知。鸦片战争后,来华采集茶种的英国人福琼(Robert Fortune),在其著作《居住在华人之间》(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中有这方面的记载。1849年,这个英国园艺学者在从浙江西部到福建武夷山的途中,由于气候炎热潮湿,他和随从都被蚊子叮得整夜无法合眼。后来他的随从购买了一些当地人使用的一种蚊香,这种蚊香对驱杀蚊虫很有效。后来他把这一信息带回欧洲后,引起西方昆虫学家和化学家的极大兴趣,纷纷询问他这种蚊香是由何种物质所合成。后来,他在浙江定海了解该蚊香的配方,发现此种蚊香由松香粉、艾蒿粉、烟叶粉、少量的砒霜和硫磺混合而成。[34]从中可看出,当时,制作蚊香的药物又有增加,明晚期传入的烟草也被当时的人们用来制作“蚊烟”。
综上所述,我国发明的蚊香至迟在宋代即已出现,古代的名称是“蚊烟”。其产生可能与烧香的习俗和端午节的一些卫生习俗以及传统的针灸术有关。艾草、浮萍和硫磺等芳香、除痒的药物和杀虫剂是我国古人常用的原料。进入20世纪,与艾草同属菊科的除虫菊传入我国后,逐渐成为制作蚊香的主要材料。[35]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讨论范围,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1 罗桂环.中国古代蚊香的发明[J].科学月刊,2005,(5):412.
2 支伟成.庄子校释[M].天运第十四.北京:中国书店,1988.111.
3 班固.汉书[M].卷53.北京:中华书局,1997.619.
4 欧阳询.艺文类聚[M].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63.1683.
5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5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4374.
6 苏轼.物类相感志[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935.25.
7 宋濂.宋文宪全集[M].卷45//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920~1936.154.
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卷75.北京:中华书局,1977.1296.
9 袁文.甕牗闲评[M].卷7//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935.68~69.
10 侯克中.艮斋诗集[M].卷10//四库全书.12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501.
11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M].卷3//四部丛刊.19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64.
12 罗愿.尔雅翼[M].卷26.宋本重刊.5叶.
13 魏收.魏书[M].卷35.北京:中华书局,1974.816.
14 章懋.枫山集[M].卷1//四库全书.118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3.
15 李时珍.本草纲目[M].卷41.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2331.
16 何焯,陈鹏年.分类字锦[M].卷59//四库全书.100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681.
17 葛洪.西京杂记[M].卷1.上海涵芬楼借印江安傅氏双鉴楼明嘉靖孔天胤刊本,6叶.
18 徐坚.初学记[M].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62.606.
19 范晔.后汉书[M].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65.1111.
20 张华.博物志[M].卷3//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935.18.
21 梅尧臣.宛陵先生集[M],卷15,卷21//四部丛刊初编.189~19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1936.129,182.
22 刘延世.孙公谈圃[M].卷上//百川学海.北京:中国书店,1992.2叶下.
23 格物粗谈[M].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935.
24 名医别录[M].陶弘景,集.尚志均,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156.
25 鲁应龙.闲窗括异志[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935.23.
26 周密.武林旧事[M].卷6.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21,128.
27 陶宗仪.说郛[M],卷60下//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801.
28 朱橚.普济方[M].卷306.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29 高濂.遵生八笺[M].成都:巴蜀书社,1988.146.
30 徐光启.农政全书[M].卷42.北京:中华书局,1956.871.
31 谭贞默.著作堂集[M]//任继愈.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生物二.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617.
32 归有光.震川集[M].卷26//四部备要.集部.上海:中华书局,1920~1936.205.
33 程之章.浙江通志[M].卷10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823.
34 Fortune R.A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inland,on the Coast,and at Sea.London:John Murray.1857.109~115.
35 湖北省企业委员会……关于汉口化工厂创制驱蚊盘征购员工粮食、营业预算及修正组织章程的指令公函(1948)[R].湖北省档案馆,全宗号45-2-210.
Mosquito Repellent Incense in Ancient China
LUO Guihua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AS,Beijing 100190,China)
The mosquito repellent incense was invented by the Chinese in Song dynasty,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habitude of burning joss sticks and ceremony of sanitation in dragon boat festival,aswell as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behavior ofmosquito.The incense was called“mosquito smoke”or“mosquito drug”.It was made up of argy wormwood and arsenic sulphide as well as duckweed mainly,shape liked stick,and produced in special workshops.The production of themosquito repellent incense was developed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more and morematerialswere used to its production,including asafetida,notopterygium,wallich ligusticum,sulphur,camphor,and tobacco.Its types tended to becomemore varied.The composition of itsmaterials aroused the interest of western scholars in the 1850s.
invention,mosquito repellent incense,dragon boat festival,Song dynasty
N092
A
1000-1224(2014)03-0326-07
2014-03-28;
2014-08-06
罗桂环,1956年生,福建连城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生物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