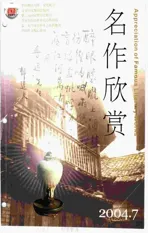河水带不走的敬畏
2014-01-28天津徐寅
天津 徐寅
作 者:徐寅,南开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生。
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出版已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而距离作家始于2011年的沿着沁河的行走历程也已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今天我们再次翻开这部厚重的散文集,仍然能感受到作家于沁河河畔双手默默合十,心怀虔敬地追忆那段被河水带走的乡土历史文化的心绪。这心绪中寄托着对于物的珍视,如石雕、铺首、雕花老床、银器,它们如同沉淀在沁河底的泥沙,经得住淘洗;饱含了对人事的追忆,小爷、父亲、祖婆、五爹、神汉李来法这些鲜活的形象今天看来仍是历历在目;温存了一份从历史中挖掘出的感怀,土改、“文革”、自然灾害都没有击垮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乡土中国就是凭借这片土地上人们坚硬的脊梁一次次被承托起来的。
葛水平出生于沁水县十里乡山神凹,贴着土地围着沁河成长起来的她知道——敬畏,是农民对土地、神灵的情绪,同样也是她对于乡土的情绪,所以无论是物、是人还是历史,就像她自己说的“我敬畏曾经在河岸活着的朝气和欲望”。这“敬畏”也构成了她的《河水带走两岸》的基调,整部集子中,作家十一次使用了“敬畏”这个词,还多次用到了“敬奉”和“虔敬”。如果说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沁河沿岸的今与昔,那是一种随着河水流失就不再的失落,那么,人们心中祖祖辈辈坚守的敬畏却是作家心中永恒的信念。这种敬畏之情是远行游子们对于乡土的精神守望。
葛水平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写作,历来被评论家看作乡土叙事的代表,她的代表作《甩鞭》《喊山》《裸地》无疑是三晋大地上乡土旋律的重奏。而回到散文创作中,《河水带走两岸》中的四十六篇散文,以沁河为主线贯穿,用河水串起了乡土,改变了她小说中以乡土、村庄为重心的叙述。河水代表了一种生命意象,她不仅仅浇灌了两岸的文化,更孕育了两岸的居民,从这点上看,河水就天然地与女性有着关联,而贾宝玉的那句“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不也道出了女人骨子里那份如水的特征吗?所以女性写水,男性写山,通过对河水的追述,结合散文写作这种更情绪化、更个人化的文体形式,葛水平是否想对沁河这条养育她的母亲河表达一种高于乡土情怀之上的对于女性生命历程的膜拜呢?我想,这种膜拜还是会归结到“敬畏”之上吧。《中国社会科学》编审王兆胜在谈到乡土文学出路的时候曾经说过:“作家应该让‘心灵参与写作’:对天、地、自然、人心存敬畏,融通诸如现代/传统等对立的二元概念,深入思考农村的结构现状进而超越现实。”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写作是一种城乡差异的直面剖析,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裂变,是一种对于乡土人性的张扬,那么在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中,我们很少会看到这种作家说教式的情感表述,在为数不多的篇幅如《秋苗和石碾磙干大》中她说:“这个世界存在的永远是遗弃的快感,转瞬即逝的遗弃让我们放弃了一切有利于健康的笨重方式,去追求生活狗撵兔子似的现代文明。”这里对于现代文明的取舍她也没有下结论,只是让我们看到了世俗的我们如何在“狗撵兔子”般地追求。在《山水有过自己的声誉》和《妈妈,领我去看河》这两篇的文末,前者作家直呼“理性的人们啊,请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环境变得已经很糟糕了”,后者则将儿子看不到河归结为“我怀你太晚”和“这是妈妈的错误”,作家没有疾呼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改变乡土环境时我们应该如何抵制这种现代文明或者回归乡土,而是以自己母亲的身份,释怀了人类的愚昧,就像沁河身为母亲河,“承担”了引领两岸文明的责任。男性作家们在进行乡土文学写作的时候,要么会更加有力地去揭露乡土中的破败,要么去挖掘乡土文明中存在的对于现代文明的补充,对于乡土文化的“革命”是男性书写的传统。到了葛水平这里,我们似乎很难在作品中看到她高举革“乡土”命的大旗,更多的是一份女性对于土地直观的敏感:经济发展带来的沁河两岸土地资源的日趋紧张,原有的乡土文化在逐渐消失,而河流在面对种种灾难后的宿命是——死亡。人类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总会自然表现出敬畏之情,作家本人也不例外,“走过河对岸,鞋面不小心会被水打湿,也许是故意的,此时的我居然对水生出了敬畏之情”。
厦门大学的王宇教授在《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一文中指出女性乡土叙事的崛起,一方面是性别意识被带入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另一方面是乡村/底层经验被带入女性文学之中。我认为,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则是一种全新的崛起,她开辟了一种女性在乡土叙事精神层面独特的气质,既不同于我们惯常意义上的性别意识,也不是单纯的乡村经验的传达,它是一种结合了乡土文化积淀的、拥有女性自然观照的、虔诚敬畏的类似宗教的情怀。就像她在和作家王祥夫的对话中说的:“河流带走了许多,我一直希望,守着一条河流,过世界上最美的日子,我知道我已不能,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的悲剧。”这种“类宗教”情怀我们在史铁生的笔下常常会看到,他的作品中散发出浓郁的宗教意味,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内涵。而在葛水平的散文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天堂”“神灵”“鬼魂”“佛”“上帝”这样的字眼,还有听到她关于“轮回”“欲望”“死亡”“命运”的论道,那么她究竟是如何演绎她的敬畏的呢?
关于天堂。在基督教的《圣经》中,是指神的国或天国中具体的一个地方,在六祖慧能《坛经》的“般若品第二”中,提到“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天堂”相对于“地狱”,指美好的世界。在《高于大地的庙脊》中,葛水平提出“这世间有天堂吗”的疑问,然后发现“天堂,是我们在从容与喜悦中拥有我们所得,而我们又必定是心感幸福的人”,而最终,作家惊呼“这些美好都在民间”,民间成了她心中的天堂。这天堂不是西方的极乐世界,不是历尽谦卑的人们方能往生的场所,它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只要我们用平和、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自己就可以营造出“天堂”。在这部散文集的后记中,作家更是喊出了“我的沁河,我的天堂”,并大胆断言“每个人都有一个天堂,那就是自己的故乡”。可以说,在面对沁河两岸土地的时候,葛水平是竭尽虔诚膜拜的。天堂,这一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世界,却恰恰是作家生长的地方,这种骄傲、自豪的情绪油然而生。不过作家还是有所节制的,在写到《我们周围的神灵》一篇时,她说到“我一直不相信有天堂,天堂在我的意念中该是旧时代的颜色”,这样的文字瞬间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天堂门前敬畏的凡人,毕竟作家笔下的乡土也正在逐渐远离我们,物质文明的冲击也许是“上帝有意设置了这样一种未来”,对此,“我们只能告别和放弃所有意义上诗意的原始了”。葛水平对天堂的想象,可以看成是乡土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就像沁河一样,包容着两岸文明的不断更迭,但无论是哪种文化,虔诚敬仰永远是对于其文化中所呈现的美好事物的态度。
关于佛。葛水平在《在寺庙里的阳光下微笑》中写道:“佛是一些涉及事实而不涉及一般的法则,我不够成熟,因此不悟。”然而作家真如自己说的那样是“不悟”吗?在散文集一开篇,面对素净的沁河,作家就说出了“我不能够欢喜”,一方面,她看到了作为孕育两岸生灵的沁河是如何丰沛了万物,使万物“生”;另一方面,作家又独具慧眼地发现,河水所流经区域的丰富自然资源,使得经济开发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土地缩紧、水土流失也相伴而来,某种意义上说,河水成为乡土在文明面前的终结,即“死”。对于生死的参悟,并没有引起作家的过分感叹,因为一边是生态发展的自然规律,一边是人类进步、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一切的因果其实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葛水平能做的就是:“我走沁河,我明白河流是需要怜悯的……我敬畏曾经在河岸活着的朝气和欲望。”透过作家的乡土,我们看到了沁河两岸曾经的庙宇,庙堂前的石雕、门墩,手艺人们精心打磨出的银器、雕花木床。而在今天,寺庙成了人们求得欲望满足的不二场所,石雕、门墩早已风蚀得看不清历史的面目,手艺人的杰出作品也只为多贩卖出几个银子而不断炒作。欲望随时随地地攫住了人们的灵魂,即便是曾经民风朴实的乡土也不例外。对佛“不悟”的葛水平,看出了“欲望”的可怕,乡村文明在面对城市文明席卷的时候,丢失的不单单是淳朴的乡土气息,它也逐渐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好在人赤条条来,也将赤条条去,这一辈子的时光很快就会过去。在面对众生命运忧虑的同时,作家看到“人来了又去,留下的手艺或许是对于死亡另一种安喜”。还有关于“轮回”,关于“缘法”,葛水平在这本集子中反复提到她对于“佛”的领悟:“人的心地若是佛,便看人也是佛。佛是谁?佛是对面。”这些都是她从乡土文化中汲取的营养,也是她怀揣着一份敬畏之情在重走沁河时所生发的感悟。葛水平的乡土写作,拥有着这种浓厚的“禅宗”思想的支撑,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乡土作家泥土气息浓厚的写作特征,同时,她又僭越了“佛教”这一被男性话语表述更多的领域,开辟出了乡土与宗教结合的语言表述和思维模式,使得她的《河水带走两岸》拥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于神灵。民间信仰是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灶神、龙王爷、娘娘庙、土地庙、关帝庙这些存在于民间的神庙,护佑着古代社会风雨飘摇的农村生产与生活,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中国广大农村中多神崇拜的信仰体系。与上面提到的西方宗教与佛教不同,民间信仰似乎离老百姓更近,神灵也与人更加亲和。三晋大地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成因,神灵与乡土更是紧密结合。葛水平行走在沁河沿岸,自然也会生发起对于神灵的遥想,从手艺人们做出的石头小兽、铺首、石雕等,就可以看出世居乡土的人们对于神灵的敬畏。在《寻常中有别趣》里,作家就提到了自己在晋城玉皇观旁关帝庙看到的石质圆柱,“雕花圆柱上布满人物,那样的手艺,打远处看真叫人敬畏和尊重”。这不仅仅是对手艺和手艺人的敬畏和尊重,更是作家对石柱所承载的精神性寄托的敬畏和尊重。而民间文化中也有很多对于女性的禁忌,可是作家仍然深入其中,打破了女性与神灵间的隔膜,在“敬畏神灵的日子,我始终认为人是幸福的”。乡土作家的写作中,往往会涉及民间信仰这个层面,但是葛水平与众不同的是,她敢于高呼“我想做一个鬼魂”,真正将个人的感情心绪与生养她的土地结合,形成了飘逸空灵的写作姿态,而非简单地述说人道主义价值观。从美学层面上来说,她既坚持了民间信仰中该有的严肃立场,又为其添加了女性的独特感悟,在面对寺庙时,她感慨:“对于寺庙来讲,人可以荒凉了它的容貌,却无法忽略它的势场。”就像面对沁河两岸的风物,今天她的容貌也许已经大不如前,但是这片土地仍然荫庇着生活在其上的人们。所以,葛水平敬畏着沁河,敬畏着这种母亲河无私奉养的精神。
《河水带走两岸》是葛水平恪守着敬畏之情的写作,她给我们呈现了沁河流域丰富的人文景观,挽留住了那些被“文明”冲走的真情。作家面对繁杂的人世,用女性特有的笔调,凭借自己乡土文化扎实的功底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谙熟,运用了大量的民俗谚语和民歌,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古代诗人对于沁河地区山川风物的描述,将感性认识与理性陈述相结合,归纳到她自己所提炼出的“类宗教”的情怀之中,这是以往的乡土作家们所未曾达到的。尤其是对于女作家而言,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她在精神层面实现了突破,破除了传统乡土文化中种种对于女性的规约,从民间信仰、佛教传统、外来宗教等杂糅的体系中建立了女性乡土文化散文的内在言说模式,满怀敬畏的情怀超越了乡土浪漫主义的表述。如果说葛水平的乡土散文写作还有什么不足,那么就在于她对语言的掌控上,她尝试着去摆脱北方文化下的浑厚与粗犷,但是又往往陷入了一种个人的沉思独吟,在这部散文集中,我们经常看到“我只知道”“我不能够”“我无法忽略”这样主观性极强的表述,文化散文还是不同于诗歌,作家应该在表达个人感情的同时让渡给读者足够的空间去体会文化的内涵。这部集子,让我们充分见识到了沁河区域文化的独特风貌和悠久历史,而同时,敬畏之情贯穿始终,就像作家说的:“敬畏,这是人体肺腑最健康的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