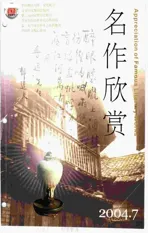临界点上的诗意呈现——郁达夫散文《钓台的春昼》解读
2014-01-28山东程鸿彬
山东 程鸿彬
作 者:程鸿彬,青年学者,现任教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既是闻名遐迩的小说大家,也是风格独具的散文巨擘。1921年,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问世,以赤裸裸地袒露自我灵肉冲突而震动一时,从而开启了“自叙传”抒情小说的潮流。20世纪30年代以后,郁达夫的创作重心逐渐转向散文,诸多为后世传诵的名篇佳构络绎笔端,如《钓台的春昼》(1932)、《故都的秋》(1934)、《过富春江》(1935)、《江南的冬景》(1936)、《北平的四季》(1936)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游记散文,不仅为数甚夥,而且文情并茂、亲切动人。郁达夫同时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散文理论家,他曾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将中国现代散文概括为三大特征:“个性”“范围的扩大”“人性,社会性,与自然的调和”。①郁达夫将“个性”称为“散文的心”,并认为它是现代散文区别于古代散文最重要的标志。古代散文受制于纲常名教,即“尊君”“卫道”“孝亲”三位一体,这一特性决定了散文形式上的因循模仿。经过“五四”启蒙运动的洗礼,个性、自我摆脱传统的桎梏上升为散文的核心要素,而散文的形式则相应具有了“自叙传的色彩”,从中可以看出“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②。必须指出的是,郁达夫所说的个性、自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他看来,个性、自我与社会人生具有一种密切互动的关系:
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
《钓台的春昼》③是郁达夫游记散文中最为人称道的代表作品之一。这篇散文记述了他1931年返乡暂住期间一次出游的所见、所闻、所感。这次出游始自郁达夫的故乡浙江富阳,行程包括乘船溯富春江西上,止宿桐庐县城,夜上桐君山,翌日探访严子陵钓台。严子陵,名光,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为东汉初年著名隐士。性情孤高耿介,年少时即有清名。曾游学长安,与刘秀有同窗之谊。刘秀称帝之后,屡召他入朝为官,均坚辞不就。文中描写的严子陵钓台,位于浙江省桐庐县境富春山麓,相传为严子陵隐居垂钓之地,建有严先生祠和东西二台,为当地名胜。
文章的写作时间是1932年8月,所记出游则在1931年3月间,属事后追忆。为便于了解郁达夫写作该文的心境,有必要大致交代一下此前的一系列背景。作者在文章起首处不无揶揄地写道:“1931,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1931年春,郁达夫为营救“左联五烈士”(即柔石、胡也频、李求实、冯铿和殷夫)而多方奔走,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不得已从上海返回浙江老家暂避风头。作者之所以使用“中央党帝”这一自创一格的称谓,一者由于文禁森严,不得不闪烁其词,二者意在揭露国民党统治的专制面目。作者继而把当局对革命作家的迫害暗喻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愤懑鄙薄之情溢于言表。“暮春三月,春服未成”,在措辞上套用了《论语·先进》中的一段话:“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④这描写的原本是儒家“礼治”的最高境界,而作者则巧妙地将“既”字替换成“未”,既交代了返乡出游的时令节气,又用以影射“虎狼成群,风沙扑面”的现实暴政。一字之差而反讽之意尽显。几乎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起不可谓不重大的事件:1930年底“左联”召开全体盟员大会,通过了开除郁达夫盟籍的决议。对于“左联”成立以来专事政治活动、忽视文学创作的“‘左’而不作”倾向,郁达夫曾屡次表示过不满,声言“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郁达夫在文人个性上的坚守姿态最终导致了他与“左联”关系的破裂。由此可见,郁达夫返乡之时,在社会关系方面,无论与敌与友都陷入了极度紧张、无法转圜的境地。因此,他的出游就不免带有寄情山水、放浪形骸,借以排遣胸中郁结的遁世色彩。尽管郁达夫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并为人猜忌误解,苦闷倦怠之意时有流露,但深入骨髓的人间情怀却每每如风筝的线绳,使他抽身乏术,欲罢不能。这种复杂的心绪也体现在这篇游记散文之中,作者徘徊在入世与出世的临界点上,远离尘嚣的恬淡宁静对他构成了难以抗拒的诱惑,但现实意识却不失时机地浮出水面,搅乱了他守拙归隐的清梦。
作者乘坐的轮船驶抵桐庐县城,已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分。在大略交代了桐庐的历史地理之后,作者将目光聚焦于县城南面对江的“十里长洲”和“花田深处”,并不无深意地引出曾在此居住的唐朝诗人方干,或许他在这位号称“身无寸禄,名扬万里”的桐庐才子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以至心生惺惺相惜之感亦未可知。趁着“淡云微月”,作者登上了临近桐庐县城的“灵山胜地”——桐君山。在背山面江的石墙之上,作者饱览着“桐江和对岸的风景”,而山上木鱼声声、孤寂空灵的桐君古观却引不起他的兴致。天上星云掩映,江心渔火明灭,眼前的景观“秀而且静”,“整而不散”,甚至与号称“天下第一江山”的镇江北固山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此刻,一种遗世独立的意绪在作者心头油然而生:
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征士,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哩?
城中的击柝之声,惊醒了作者“浩无边际的无聊的幻梦”,他不得不重返尘世,“跑也似的走下了山来”。及至翌日清晨,作者仍然沉湎在桐君山上美丽的“残梦”里,窗外“吹角的声音”尽管让他心生“怨恨”,但其“荒凉的古意”和催他早起探访钓台之功,又使他的脸上浮上了“一痕微笑”。
探访钓台是文章的主干所在。作者乘渔舟溯江上行,一路上忘情于富春江两岸的山光水色,以及沙洲之上绚烂的繁花、喧闹的蜂蝶。然而,如画的景致最终也不免令人疲倦,正当作者在船舱略作小憩之际,现实却化作梦境再次闯入他沉醉的内心世界:在一家临水的酒楼上,几位贵为“党官”的昔日好友正在高谈阔论,且有风情万种的“名花”陪侍左右,而他却不合时宜地吟诵了一首愤世嫉俗的“歪诗”: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⑤
在现代作家中,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堪称一绝,上引七律即为个中翘楚。这首诗不仅活画出作者狂放不羁的名士才情,而且将讥刺的锋芒指向暴虐无道的现实政治和与世俯仰的士林风气。它在上述场合的出现,自然使得作者和他的“党官”朋友们“心里各自难堪”了。与作者用生花妙笔编织起来的江南美景相比,这个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梦显然是令人不快的。然而,前者不也是另一种梦吗?一种只可远观遥赏,不可朝夕与共的白日梦。既然都是梦,那么孰真孰假?走笔至此,作者想必也会生出庄周梦蝶之叹了。
船家的呼唤使作者逃离了梦中的难堪。渔舟驶入一个峡谷,周遭的景致也为之一变:“清清的一条浅水,比前又窄了几分,四围的山包得格外地紧了,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并且山容峻削,看去觉得格外地瘦格外地高。向天上地下四围看看,只寂寂地看不见一个人类。”这里的一切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静,而且是不同寻常的静,是“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向往已久的钓台终于出现在视野之中,而作者却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怕在这荒山里要遇见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远离俗世的林泉世界纵然宁静,但作者深知,宁静达于极致便是“死灭”。富春江峡谷的印象显然影响了作者对于钓台的观感:“前面所谓钓台山上,只看得见两个大石垒,一间歪斜的亭子,许多纵横芜杂的草木。山腰里的那座祠堂,也只露着些废垣残瓦,屋上面连炊烟都没有一丝半缕,像是好久好久没有人住了的样子。”在作者看来,钓台的春昼是阴森幽冷的,尽管他承认这也是一种美,但却是一种缺少烟火气的“颓废荒凉的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严子陵素以蔑视名利而著称于世,而在供奉其牌位的祠堂里,四壁题诗竟然大多出自利欲熏心的“过路高官”之手。令作者稍感欣慰的是,其中一首出自同乡前辈夏灵峰之手,“夏灵峰先生虽则只知崇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像他那样的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作者由夏灵峰的“顽固自尊”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导演的伪满洲国闹剧,以及在其中扮演丑角的两个无耻文人——罗振玉和郑孝胥,心存厌憎地将他们斥为“官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相形之下,夏灵峰的人格操守就愈发让人肃然起敬,“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兴之所至,作者也动了操觚染翰之念,遂将上引七律题于夏灵峰的墨迹之下。“过路高官”们“俗而不雅”的手笔,固然是对严子陵高洁人格的亵渎和不敬,但作者缘事而发的七律却也贯穿着与隐逸精神迥然相异的现世格调。
从表面上看,作者以游踪结构全文,随性而发,任意点染,似乎予人走马观花的印象,但深究其实,我们也不难窥见一条统领全局的内在线索,即两种对立情愫——入世与出世——的此消彼长或相互激荡。按照王国维的观点,郁达夫散文属典型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或可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⑥作者写景状物无时无刻不在主观情感的潜在支配之下,而客观景物也因而被罩上了浓郁的主观色彩,作者鲜明的个性也借此跃然纸上,一个率真、敏感、孤高,具有几分消沉颓废而又满怀不平之气的现代文人形象,得以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文章还体现出郁达夫散文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即刻画对象侧重写意传神,善于捕捉富有特征的细节,遣词用字精练而内蕴表现力。同样是写静,严子陵祠堂西院的静就与富春江峡谷的静截然不同:“在这四大无声,只听见我自己的啾啾喝水的舌音冲击到那座破院的败壁上去的寂静中间,同惊雷似的一响,院后的竹园里却忽而飞出了一声闲长而又有节奏似的鸡啼的声来。”与富春江峡谷“太古的静”“死灭的静”相比,这里的静却是凡俗人间的静,前者使人畏惧,后者使人亲近。而对佛教用语的戏仿,对喝水之声和院后鸡啼充满谐谑、不无夸张的描摹,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苦中作乐、通脱达观的郁达夫。尤其令人叫绝的是,作者用了一个“飞”字来形容打破寂静的鸡啼,既生动贴切,又融入了作者的心理感受,同时作为一个饱含着不尽之意的象征,它还宣告了浮生之闲的终结,而作者不得不再次回到令他不堪直面而又不得不直面的现实人生。
本文承蒙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资助,资助编号:11070070612182
①②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60—269页,第261页。
③ 原载1932年9月16日《论语》第1期,收入《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196—203页。
④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9页。
⑤ 该诗作于1931年1月23日,原题为“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世,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后收入散文《钓台的春昼》,因易题为“题钓台壁”。参见《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265页。
⑥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