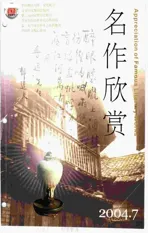言语之外——解读《河水带走两岸》的文化诉求与精神指向
2014-01-28天津景欣悦
天津 景欣悦
作 者:景欣悦,南开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生。
海明威曾在《流动的盛宴》中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对于当代作家葛水平而言,她的创作与人生中同样拥有这样一席“流动的盛宴”贯穿始终,宛如骨肉,难以割舍,那便是滚滚而逝的沁河、沁河哺育下的故乡、故乡中至真至诚的人与事,以及点滴人事中渐行渐远的魅性文化。
2011年10月,葛水平带着难以名状的情愫沿着沁河行走,寻访它所流经的村落、古镇,寻找那些即将淹没于历史洪流中的传统文明与古老技艺,一路行走、一路哀歌,一走便是一年有余,直至凝结其旅行感悟的散文集《河水带走两岸》亮相于世。这本散文集分为四辑,总共收录彼此独立的散文作品四十六篇。在作品中,葛水平秉持着一贯的民间立场,通过真挚哀婉的情思和细腻淡雅的笔触,为我们记录了这一路的风光见闻、所思所感。行文中,作者时而直面现实的萧瑟,时而轻抚历史的尘埃,时而追忆旧时光中的故人逸事,时而呈现历史洗礼中的苦难与消亡。别有情趣的石雕木刻、繁华一时的街巷庙宇、旖旎的弦乐、质朴的土炕、农民的沉默与倔强、历史的喧嚣与凋零、山水之性、神灵之魅等共同构成了作品的主干,同时亦交织成一幅融合了壮丽风光、传统技艺、质朴人情以及历史变迁的沁河文化图景。然而透过作品言语表层,这些记录和呈现的背后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诉求和精神指向?言语之外,又有怎样一番天地?
一
沁河的水奔腾不息,恰如巨浪翻滚的历史洪流,将旧时光中的人与事统统抛到了时间之外,传统的农耕文明之精髓亦在这样的进程中渐渐衰落,显得瘦骨嶙峋,然而“手艺是时间留在人世的信物”(葛水平《:河水带走两岸》,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此后所引原文不再重复标注),于是,一个个“藏着岁月的味道”的工艺品便成为传统文明遗留在沁河两岸的蛛丝马迹,这自然逃不过葛水平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真挚的念想,正如她在回答行走沁水动机之时所说:“我要在两眼炯炯有神时走过沁河两岸,看看那些村庄和即将消失的手艺。”(吴炯:《作家葛水平走沁河》,《山西日报》2013年9月4日)然而,行走的意义绝非这般草草地“看看”,而在于浸着深情的记录,同时更在于记录过程中赋予这些即将消失的手艺以全新的生命。
在《要命的欢喜》中,作者主要描述了旅行途中发现的“一张清中期富家小姐的闺床”。“闺床”不过是旧时代留下的一个物件,本身固然无生命可言,然而在作者笔下则不同:首先,作者通过对闺床上精致的木格花雕的描述,引出了匠人那双“美丽、绵长”的手,进而又置身床上联想出“许多人生幻景”,不禁由床入梦,又在历史追忆中体味到了床之艺术的繁复与丰腴,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出床所具有的“人性解放”和“身心舒畅”的功效,最后便是在酣畅的睡眠中得到“要命的欢喜”。从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可粗略得出以下叙述线条:床—→梦—→想象—→艺术—→人生—→欢喜。于是,通过层层铺陈,“床”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形式,而古老的手艺也似乎在这样的描述中复活。真可谓“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一路行走,一路观望,跟着葛水平的笔,我们看到百态千姿、活灵活现的“石雕”正在诉说着石匠们的“高贵心智”与“创造世界”(《寻常中别有趣味》)。步入高地,看到阳光下熠熠生辉的“五彩琉璃”正传递着神灵的箴言,“以简单大气横行民间”(《高于大地的庙脊》)。深入街巷,我们看到了建筑之间豁然的蓝天,以及“麻雀飞离树梢”的装点(《繁华深处的街巷》)。此外,我们还听到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于“文明喧嚣”中的呐喊(《风把手艺刮进了天堂》),听到了“与时间抗衡”的二胡之音铺满大地(《旖旎的弦乐铺满大地》)。总而言之,在历史上,“他们用自己的手艺繁华了沁河”,如今,它们又在作者的笔下重新绽放了生命的光鲜与亮丽。
在沁水,手艺和匠人是传承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背负着过往时代的种种记忆,然而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已迫使它们濒临灭亡,“曾经的手艺,消失得比风还快”,面对这样的局面,又怎能不让葛水平痛心,于是,她选择一边凝望着传统技艺走向衰亡的背影,一边用灵动的笔墨使得业已消亡的手艺渐渐复活。就这样,沁河的历史与神秘在尘封多年之后,被重新赋予了生命之光,静谧的传统技艺以最饱满的激情丰盈着葛水平的文学世界及其一意孤行的文化探索。
二
“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乡村,童年也在乡村,一辈子乡村都会给他以饱满的形象”,而乡村就是葛水平“生死不移的眷恋与诱惑”(《我有理由知道她的美丽》)。农民、乡村、民间,是葛水平文学世界的高频词,也是其创作不竭的源泉。在作品中,作者用情最深的一笔便呈现在对于故乡生活的回望中。行走在沁河两岸,破败的乡村图景暗示出曾经的人事早已在岁月更迭中远去,所有“催人泪下的故事,都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了”,那样自然而又那样轻易,甚至不曾有过丝毫的“挣扎”“难过”,而如此残忍的现实却恰恰触及了葛水平心底最敏感的那条神经,进而辗转成了其笔下的回忆与纪念,“动人心魄”、悲恸哀婉。然而深情脉脉的追忆并非仅仅是作者个人情感的流露与表达,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葛水平对于沦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道义、传统伦理的坚守与认同。
在《黄昏的内窑》中,作者叙述了祖母王月娥遵循着乡土世界的伦理道德,“寒窑苦守”四十多年,只为等待祖父从军归来的故事。在这样的守候中,祖母历尽坎坷,受尽屈辱,却无怨无悔。二十六岁就开始守活寡的祖母,纵然“年华如梦”,却始终能够“心静如水”,“她因传统而忠心于祖父,她因本分而体恤关心族人,从未滋生杂芜之念”。即便面对红卫兵的侮辱与拳脚,仍不卑不亢,因为她坚信“只要葛启顺还活着,就有我王月娥的一天”。如果按照现代实用主义的逻辑去分析,王月娥所作所为显然是蒙昧的、原始的;在激进的女性主义观念看来,她的一生都浸透着男权文化的苦难;即便是在同样质朴的乡亲心里,也会不禁感慨,此般磨难,究竟图个啥?但是在葛水平看来,她却用沉默、坚强与执着,书写了一个大地女人的传奇,弥漫着难以言说的美感与忧伤,正如文中所言:“春日和风使枣树抽枝开花,秋日萧飒使枣儿泛红透甜,一样的时空流变中,美丽的景致就这样保持了一生预约的守候。”
在现代化、城市化狂飙突进的当下,人们纵情于欲望的狂欢之中,却忘记了生活本身,特别是乡村生活依然充满了艰辛与苦难,那些埋葬在时代喧嚣中沉睡千年的悲恸,怎能不让葛水平惊愕与悲伤?在《好生活着》一文中,作者并没有书写“活着”的欢愉与喜乐,却无情地为我们呈现出死亡的阴冷与感伤。红红的妈妈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不肯花钱医病,最终在病痛的百般折磨中吃安眠药死了,死得那么突然,那么轻盈,历史不会为这样普通农妇的离世而掀起半点涟漪,那么在至亲的孩子心中,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又是如何?“孩子们知道妈妈没了,但是,哭不出来,红红爸照着孩子们的脸甩耳光,红红和哥哥脸上忍着愤怒,依旧哭不出来……红红妈过世半个月后红红和哥哥的泪来了,夜晚用被子蒙着头,闻着肥皂味道哭,闻着阳光味道哭。”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伤心?母亲就是他们的天地,无尽的泪水便是献给母亲的歌。乡土世界中的人常常缄默不语,然而真情一旦流出,便如奔腾的黄河,一路怒吼着翻滚。
此外,不论是诚恳逼真、自然野性的父亲还是质朴无华、勤勤恳恳的起富,不论是刚强的书林还是充满幻想的说书盲人,他们都在各自平凡的生活中,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民间传奇。他们倔强、朴素,令人心痛,他们的人生充满苦难与辛酸,然而却在苦难面前迸发出最强劲有力的生命之音。所有这些携带了泥土芬芳的人性之美便是葛水平所崇尚的乡土道德与传统文明。因此,即便“时间迅疾而过”,河流带走了两岸的世事纷扰,然而“亲情、友情、爱情,终于待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个去处直叫人呼吸到了月的清香,水的沁骨”(《河流带走与带不走的》)。时间的洪流看似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席卷而去,然而终究无法带走那些生命中饱含的魅力与激情。
柔情中带着那么点儿倔强,博大中夹杂了那么点执念,深情脉脉中坚守着乡土世界的道德与传统,这就是葛水平。
三
散文一直是葛水平文学创作的重镇,在《河水带走两岸》之前,葛水平已经出版了《心灵的行走》《走过时间》《今生今世》等散文集。与此前创作略有不同,该书中增加了对宏大历史和社会事件的记录与书写,葛水平也走出了“今生今世”的“爱、孤独、旅行、无奈与热闹”(葛水平:《今生今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纵身跃入历史巨浪之中。抗日战争、土地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朝鲜战争、城市化、工业化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浮于笔端,成为作品的主要构成。然而作为乡土逻辑的坚守者,葛水平的历史抒怀更多是来自满目疮痍的乡村现状,来自于历史留下的沧海桑田,因而历史话语之外包含了更多的隐性文化指向,即当代农民的焦虑与困境。
在葛水平笔下,城市化不断倾轧着乡村的生存空间,“丰收是一个昨日的词”,而在此过程中,“天下叫农民的人,从此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工”。面对着现代化的发展,农民自身的身份焦虑也迫使葛水平带着困惑与期许探宗溯源,然而一番彷徨之后,却终究未能在历史的记录中得出明确的答案,于是也只能继续行走在现代文明与传统复归这样两种文化欲望交织的道路上,显现出“浮动着的”焦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14页),任其飘落在当代繁复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当政治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一篇里,新型的阶级划分对于当时的农民而言,显然是难以理解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些历史的修辞性符号成为质朴农民在那段岁月中的精神困境与生存枷锁,最终,善良的农民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农民的身份焦虑却并未斩断于历史之中,而是延宕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里。又如在《一份资料上的“共产主义”》中,盲目的政治热情,促使整个乡村一时间进入了充斥着热闹、欢腾、激越的历史氛围里,然而几十年过了去,沁河两岸的凋零和萧条却与喧闹的历史形成了一种极具讽刺性的比照。这恰恰是因为“往往我们对于细节的荒疏,把社会的进步视为社会的必然进程而忘记了其中的挣扎”(《被荒疏了的日记》)。葛水平所做的便是再现历史中的“挣扎”,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作者与农民一同站在历史的悬崖,背负着时代赋予他们的悲剧与困惑,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抵抗。
对于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的洞悉与解读,或许并非葛水平之所长,然而她却以最为质朴的情怀和最为坚定的民间立场,再现了历史对于传统农耕文明的戕害,以及在这样的戕害中,农民的彷徨与无助。因为“民族和国家绝对不是大概念,它有时能具体到个人情感的最细部,让你脆弱的神经背起一段民族或某个历史时代,让你在不堪重负里体验生存的代价”(《一抹桃色腮红》)。看着乡村留守儿童的双眼,看着凋敝零落的乡村,看着几近枯竭的沁河,看着渐行渐远的手艺,葛水平不得不为农民的生存而担忧、而焦灼。
任何时代,但凡有良知的作家都不会放弃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索和描摹,悲悯乃是周身时代赋予每一位作家最生动的创作原料与生命体验。在技法上,葛水平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然而那份沉甸甸的真诚,却弥足珍贵。
四
西城村、端氏古镇、老马岭、定林寺、雨井山、西文兴村、武陟,一路行走、一路期许,却终成空梦一场。在河水的尽头,葛水平猛然发现所有流光溢彩的旧日繁华不过是残留在人们梦中的幻影,而现实中的河流早已被生活垃圾的阵阵恶臭和工业废料的肆意倾泻而覆盖、掩埋,沁河早已“不见流动”,而此时的作者也成为这世上“一只悲伤的鸟”,用杜鹃啼血般的哀鸣呐喊道:“那些主宰河流命运的手们,请缩一缩你们的贪婪欲望,用减法的形式找回幸福,好吗?”(《我几乎看不见流动》)此时,沁河不过是“远行人的眷念”,而河水荫庇中的故土,也只不过是“远行人的精神原乡”。
与葛水平的小说不同,其散文创作少了小说中的那种野性与冲击力,呈现出一副温婉中透露着睿智、知性中饱含着激情的书写姿态。行走在沁河两岸,每每抵达一个地方、遇见一个物件,葛水平都会追溯它的前世今生,并用博大的笔触书写那些远去的历史繁华。这种寻根探源的写作手法不仅使得作品显得厚重丰满,同时因其“类民族志”的属性而颇具文化价值。例如,在《老马岭上走过强人》一文中,从战国末年的长平之战到万历年间的强人出没,从崇祯年间的饥民造反再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一个强人,历史跨度惊人,内容颇为丰满。不动声色地叙述历史上的繁华,追忆河流两岸的人间沧桑,这便是葛水平在面对颓败现实之时作出的选择。
在现代与传统彼此对抗、博弈正酣之时,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陷入两难处境之时,《河水带走两岸》则为我们呈现出一种“天人合一”(《山水有过自己的声誉》)的宇宙气度。在葛水平笔下,沁河的文化传统总是对自然心存敬畏,万物平等。于是,人可以和动物称兄道弟,那是“庄稼人给予牲畜的爱”,是“大自然所具有的那种永恒、自在、单纯、朴素的性格,培植出了庄稼人的良善”(《驴是兄弟》)。有时,人们甚至相信自然中的物拥有超越人力的非凡:“那个年月,村庄里孩子的爹娘常常把自己的孩子许给一棵树、一条河或一块石头,乡下人相信自然的力量比人大,也相信人是永远改变不了自然的。”(《秋苗和石碾磙干大》)
然而,“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最终还是指向了那即将远去的古老文明,敬畏神灵的信仰,才是对深陷现代化泥潭中的人们所进行的真正救赎。马克斯·韦伯将现代化解读为“理性化”“祛魅化”的过程,而葛水平则在文中表达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坚守,形成一种“返魅”的文化诉求。在作者看来,“敬畏神灵的日子里,我始终认为人是幸福的,也是艺术的”,这些神灵“如繁星散落在穷乡僻壤,默默地闪烁着性灵之光,贫困和苦难如影相随,神们却报答给敬奉他的人们温暖的未来”,同时“给予人们深厚的历史情感和丰富的精神指向”(《我们周围的神灵》)。因此,在作者看来,这种类宗教的情怀与信仰,恰恰是当今这个欲望膨胀的人性荒原中所亟须建立起的精神家园。
现代化的洪流带走沁河两岸的历史沧桑,带走了心灵对于生命的敬畏,同时也带走了农耕文明时代的神灵信仰。于是,“我看到繁华露出瘦削刚硬的筋骨,素净的沁河与壮阔的秋风,无限扩大了村庄两岸衰落后的萧瑟,我不能够欢喜”(《沁河给了我天籁的声音》)。正是这样的哀伤,激发了葛水平行走的步伐。在这场精神的旅行中,作者不仅剥离了现代文明魅影下虚幻而空洞的繁荣,将传统文明濒临灭亡的哀歌演奏给世人,同时也仪式性地完成了自我的精神还乡,在看似温和实则决绝的文字中表达了自己鲜明的文化诉求。
言语之外,是葛水平更为宽广的精神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