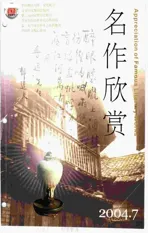林译小说风行原因初探
2014-01-28内蒙古王金双范晓霞
内蒙古 王金双 范晓霞
林译小说风行原因初探
内蒙古 王金双 范晓霞
林纾及“林译小说”①是中国近代文学乃至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作为一名不懂外语的翻译家,②林纾的翻译为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是学术界一直探讨的热点话题。尽管在后来尤其是“五四”以后,评论家对其翻译时有诟病,但作为一名不懂翻译源语的古文大家,林译小说在当时能成为“畅销书”就足以证明其独特性及存在的合理性。
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的风行,尽管主要原因是译者出色的译笔及极具个性化的“误读”,但与西方小说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爱国维新思想的时代主题合拍、近代印刷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及小说市场的初步形成和独特的读者定位等客观因素也密不可分。
一
人类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的相通的审美趣味,这一点在对文学(小说)的审美上表现最为突出。谈情说爱、社会伦理、探险猎奇、公案侦探、政治战争等都是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而这些主题都在林译小说中有所反映。其中言情小说为最多,以《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为代表。此外,社会小说、伦理小说、侦探小说、神怪小说、探险小说、战争小说、政治小说、讽刺小说、实业小说等,③都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或相同或不同的文学审美世界与经验。中国小说的“忠孝节义”思想已经给读者带来了审美疲劳,而域外小说的思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起码因其新鲜,对清末民初读者颇有吸引力。在当时,知名度最高的外国小说人物,一是福尔摩斯,一是茶花女。而后者知名度在中国的提高功劳当然首归林纾,不过与小说自身的艺术魅力也息息相关。
林译小说中的伦理小说都是以孝道为中心,颇能迎合中国清末民初的社会心理,侦探小说与中国旧有的公案小说相类似,神怪小说又有中国志怪小说的影子,这些都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大致相同的审美经验。而探险小说、讽刺小说等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这些小说首先以自身的艺术魅力,其次又经过林纾出色的翻译,赢得了当时中国读者的极大青睐。
当然,林译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那些或述男欢女爱(大都以悲剧结束),或悲个人生死,或哀种族兴亡的小说。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悲凉之雾遍及华林,读者特别能够鉴赏悲苦的故事。不仅翻译小说如此,就是新小说的创作也充满了血和泪。《苦社会》是“几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④,《湘娥泪》则是“一字一泪,一句一血”⑤。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林译的《迦茵小传》了。小说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除了与林纾出色的译笔相关外,更重要的就是原著本身提供给读者的“既熟悉又陌生”的理解与阐释空间,即原著自身的艺术魅力。
小说讲述的男女爱情故事类似于中国古已有之的才子佳人情节,这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尤其是小说最后,迦茵与亨利虽然相爱,但因两人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差距,在社会与家庭压力面前,他们注定不能幸福结合。这种结果正好契合了中国人“门当户对”的道德观和行为准则。才子佳人小说、狎妓小说的遗泽是《迦茵小传》风行的原因之一,但更让读者感兴趣的是小说所提供的陌生的审美空间,即小说所描写的西方男女的感情生活,所表现的排他的浪漫爱情与中国婚姻传统中一夫多妻制所形成的反差,个人追求自身婚姻幸福的权利与中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所形成的强烈对比,以及女主人公迦茵为爱人的牺牲精神,比起中国传统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才子佳人小说来,确实蕴含着不少新鲜的内容,使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中国青年大开眼界。
二
晚清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导致当时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爱国救亡成为上至官僚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辛亥革命以前的林译小说准确地抓住了这一时代主题,以救亡和爱国保种为出发点,使林译小说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新旧读者的喜爱,从精神上、思想上打动了读者。几乎在每部小说翻译当中,林纾都要加入自己的序、跋等,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与救国思想。1901年之所以翻译《黑奴吁天录》不是“巧于叙悲以博阅读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1907年翻译《爱国二童子传》是为了“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即使是翻译内容离奇、趣味庸俗的探险小说与鬼怪小说,林纾也不忘在序跋中讲出“微言大义”,提炼出更高一级的“政治”意味。1905年他所翻译的《鬼山狼侠传》写了一位苏噜酋长查革的故事,其中夹杂了许多神怪内容与血腥场面,但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林纾却大谈“尚武精神”与“盗侠气概”,联系到中国的现实,则令他想到“苏味道、娄师德,中国至下之奴才也,火气全泯,槁然如死人无论矣”。林纾在对《鲁滨逊漂流记》和哈葛德的一系列冒险与神怪小说的翻译与解读中,提出了一种与中国传统所倡导的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精神相背离的新的审美精神:对盗气、贼性与侠气的提倡,这是一种“恶”的精神。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所开出的药方。尽管这一药方是否灵验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但林纾通过自己的译作表达的这种政治化的诉求确实与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合拍,使译者与读者都达到了自己爱国救亡、改良社会的政治目的。这既可以说是林纾爱国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其小说的翻译策略之一。
三
清末民初,中国书馆报刊以风起云涌之势蓬勃发展。尤其是戊戌维新以后,中国的出版业更是大踏步前进,出版、新闻业已渐成规模。辛亥革命后,全国报刊达五百家之多,到了1921年则达一千一百零四种。但真正影响小说发展的是报纸文艺副刊与专业的文学杂志的出现。据统计,自1902年到1917年,在十五年的时间里,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其中包含两种报纸)就有二十九种。⑥报刊上风行连载小说,包括翻译作品,商业性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译作单行本。仅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11年至1920年间所出版的书籍中,有四分之一是文学书,而所谓的文学书,绝大部分是小说。小说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并日趋活跃和兴旺。经营小说也可以是生财之道。只有在这种出版商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作者之“吃稿酬”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清末民初,绝大部分报刊和书局都为译者、作者付稿酬。稿酬在当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大部分报刊都喜欢用“润笔从丰”之类的字样,但也有的给出了一定的标准。⑦
正因为译书和创作可以为业,加之晚清科举制度的取消,很多文人便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专业的创作和译述之路,把读书取仕的观念改为投稿译书的观念了。尤其对那些除了文字而外无他长的读书人来说,更是难得的机会。1916年,袁世凯为笼络人心,派徐树铮前往聘请林纾为高等顾问,林坚决拒绝:“请将吾头去,此足不能履中华门也。”⑧林纾之所以拒绝受聘,一方面与他效忠清室不愿附逆有关,同时也因为他译书同样能博得声誉与金钱,因而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翻译家、小说家,小说的商品化倾向使更多的作家翻译家摆脱了鄙视小说的传统偏见,积极投入到小说创作和翻译的热潮中去,并促成了清末民初小说的繁荣。
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均由私人赞助刊行,这是晚清社会一种普遍的形式,但是,林纾因其译作而名声大噪,此后,其翻译小说的出版几乎都集中于商务印书馆。在林译小说的巨大成功中,商务印书馆的作用也显得相当重要。林纾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大致开始于1901年,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则是在1905年。商务印书馆不仅为林纾出版译作的单行本,而且在自己主办的文学刊物中连载林译小说,最突出的便是《小说月报》。不仅如此,《小说月报》在一开始就几乎一直把林译小说作为自己的招牌,不但大量刊登,还在醒目位置为林译小说的单行本大做广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商务印书馆的积极介入,林纾对于小说的翻译才真正成为一种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行为。
辛亥革命后,林译小说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但其销售仍然占据着大量的市场份额。这一方面与受众心理对名人的潜意识认同及对林译小说的惯性审美期待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小说月报》不遗余力地进行商业炒作有关。林译小说与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合作的最终结果是双赢:一方面商务印书馆在林译小说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也因此增强了自身在翻译小说出版方面的实绩,甚至由此奠定了自己在清末民初时出版界不可撼动的“巨无霸”地位;另一方面林译小说依靠商务印书馆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声誉,迅速占领了读者市场,实现了最大规模的普及,林纾本人也因此奠定了自己在清末民初乃至后来“译坛泰斗”的地位。
四
与当时众多小说翻译家将读者定位于大众不同的是,林纾心目中对读者的定位是有文化的士大夫,特别是在各类学校中读书的青年学生。林纾译毕《爱国二童子传》,颇为动情地说:“畏庐林纾译是书竟,焚香于几,盥涤再拜,敬告海内: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若圣贤之青年,有志学生……存名失实之衣冠礼乐、节义文章,其道均不足以强国。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他接着说,翻译小说的目的就在于“冀以诚告海内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若圣贤之青年学生读之,以振动爱国之志气”⑨。林纾感慨道:“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敬告诸读吾书之青年挚爱学生。”⑩他告诫读者:“凡小说之书,必知其宗旨之所在,则偶读有过,始不为虚。若徒悦其新异,用以破睡,则不特非作者之意,亦非译者之意也。”⑪在序言中,他总是不忘阐释他的思想,借以引导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
实际上,林译小说的真正读者乃是“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这些人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亦中亦西”“亦新亦旧”。徐念慈(觉我)对当时的小说读者队伍作分析时指出:“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⑫徐念慈极为关注晚清小说市场情况,他的分析颇具说服力。当时,小说读者中士大夫与市民的比例即使不到十比一,但士大夫读者占绝大多数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审视林译小说的读者群,他们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为此,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常常将其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运用中国传统道德术语来解读,进而赋予其新的意义指向。
有了这种独特的读者定位之后,林纾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翻译策略了。而事实证明,他所采取的以古文译西书的技术层面的策略、以真情动人的情感层面的策略和 “有意误读”的思想层面的策略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林纾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策略,与其说他有“招徕术”的考虑,莫如说是他文化心理结构的自然显现。
林译小说之所以会风靡一时,是林纾的翻译契合了特定读者群在特定的文化交汇点上“亦中亦西”“亦新亦旧”的独特要求。一方面,林译小说满足了自己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反馈又反过来促成了林译小说的继续与深化,尤其是读者褒贬不一的书评,更无意中为林译小说做了比商业广告效果更强的免费广告,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如寅半生的《读〈迦茵小传〉两译本书后》: “今蟠溪子所谓《迦茵小传》者,传其品也,故于一切有累于品者皆删而不书。而林氏之所谓《迦茵小传》者,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迦茵有知,又曷贵有此传哉!”⑬
这种近似辱骂的批评,更是对林译小说的一种反向宣传,无形中更加刺激了读者对林译小说的购买及阅读欲望。见到这些让人血脉贲张的免费广告后,又有谁不会蠢蠢欲动地想去先睹为快呢?
五
在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中,小说就是为人开心解闷的工具,情节是小说的核心,更是它吸引人的重要手段,而长篇小说更利于情节的铺叙,这使得长篇小说一直占据着大部分小说市场。前期林译小说在选本上以长篇为主,这是当时中国读者在欣赏方面对作品篇幅的要求,林纾把握住了读者的传统“情节中心”⑭的阅读心理和欣赏特点,以长篇为主,便在选本上占了头筹。林纾的译本多以长篇作品为主,即使如《伊索寓言》的短篇,也以集子整体推出,这大体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鲁迅在重印本《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总结过他与周作人的译本在推广方面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翻译的是短篇小说:“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候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
①提到“林译小说”,大家都知道是指“林纾翻译的小说”,其实这是笼统的说法。严格地说,“林译小说”应指“林纾与其口译者合译的小说”。
②在中外翻译史上,不懂自己的翻译源语却因翻译成名并在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只有两位。一位是林纾,另一位就是美国的翻译家庞德。庞德不懂中文,而是由朋友将中文译成英文,他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古典诗歌进行加工润饰。
③所列小说的原著及作者请参阅张俊才:《林纾评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附录二“林纾翻译目录”,第268页。
④漱石生:《苦社会·序》,申报馆1905年版。
⑤鬘红女史:《湘娥泪·评语》,国华书局1914年版。
⑥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1页。
⑦如《小说林》杂志刊“募集小说”启事,明确写明“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
⑧林纾:《答郑孝胥书》,《林畏庐先生年谱》第二卷,世界书局1949年版,第58页。
⑨〔法〕沛那:《爱国二童子传·达旨》,林纾、李世中译述,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
⑩〔英〕哈葛德:《雾中人·序》,林纾、曾宗巩合译,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
⑪林纾:《钟乳髑髅·序》,林薇选编:《畏庐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 页。
⑫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⑬寅半生:《读〈迦茵小传〉两译本书后》,转引自陈锦谷编:《林纾研究资料选编》,福建省文史研究馆2008年,第157页。
⑭如时人关注的往往是“茶花女”,而不是《茶花女》。
作 者: 王金双,文学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范晓霞,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