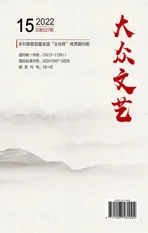浅析卡夫卡小说中的身体事实及其隐喻
2014-01-28石志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300000
石志光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300000)
卡夫卡在其充满隐喻与象征的作品里,灌注了对生存的各种知觉和体验。卡夫卡是孤独的,而他的孤独并非纯粹的,还有羸弱多病相伴。疾病的痛苦与精神的孤独相伴而生,他所有的照片都显示着纤细孱弱的身体,他曾患有胃病、头痛、精神衰弱以及严重的肺结核等疾病。卡夫卡的小说中也包含着关于身体的大量信息和隐喻,在一些主要作品中,我们很明显看到饥饿、疲惫、溃烂、变异、流血等许多残酷的事实。痛苦将日常隐匿的身体拉到了人的面前,人们要面对自己的身体并重新审视自我。
“人离不开他的身体。正是身体给予了它在世间的厚度与感觉。”[1]肉身的感觉成为人认识自我、知觉存在的一种手段。《饥饿艺术家》的主人公对饥饿以完美艺术追求的高度诠释了企图达到确认自我存在的目的。饥饿是人体对食物缺乏产生的生理需要,这种需要的客体——食物,来源于自身以外的物质世界,因此也表明了人自身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联系。饥饿艺术家进行饥饿表演的真正原因是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而且他只要一想到吃就恶心。这表明艺术家自身与外部世界具有双向拒绝的态势,他们之间业已失去了必要的联系。饥饿艺术家本身就已处于一种孤立封闭的境地。而且,他的饥饿表演也被看守人员所怀疑,得不到观众的赞赏。他的饥饿感觉从未被观众所理解,而他本身才是这种饥饿表演最满意的观众。他自身于此形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循环体系。在只有“自我”的体系中,身体的感觉成为确证自我的唯一途径。饥饿艺术家只有依靠饥饿的感觉才能确知自我,并要通过维持这种感觉来保持自我;而该行为的结果只能导致死亡——对自我最直接的毁灭。确证自我也就是毁灭自我,在此形成了一种悖论。
当饥饿艺术家与动物、器械共同作为马戏团的表演道具时,他的饥饿表演已经显现了一种“异化”状况,而这种“异化”在《变形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人变成动物是奇怪荒诞的,但却喻示了人的身份的丧失。格里高尔身上所有人的身体结构和语言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在西方文化里,人体是界定个人身份的边界。如果说人只通过自己的身体外形而存在的话,那么任何对其形体的修改都会导致其人性的重新定义。身体的界限在其范围内勾勒出了道德范畴以及世界能指。”[2]可以说身体是界定一个人最基本的条件,身体的改变意味着人的“自在”性及与世界之间关于道德的、文化的联系都将发生变化,此人已成为彼人。延伸来讲,发生彼此变化的人还意味着失去族属、集团或者家庭,失去代表稳定性的归属感。
正常人的身体本该隐退,然而突然的变异打破了宁静的秩序,为他人带来了恐惧和不安,引发了人们对“人之境遇的脆弱和一切生命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3]的焦虑。对身份本身的质疑将会导致人本身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价值和意义的错乱或断裂。一时之间,以格里高尔为中心的人际范围出现了骚动,他成为不稳定性的危险的核心。在这个核心的外围是所有象征性断裂的真空,来自关系最亲密的家人对他的怀疑、谴责、冷漠、虐待和排斥使其深陷孤独的境地。身体、动物、机器这是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时代可以相互等同的三种事物,身体被用来像机器一样从事生产活动。格里高尔的变异有身体机器化因素,内在的则是失去自我的生存困境,变异是对这种荒谬困境极致的揶揄。
疲惫使身体屈从环境的摆布,变得“身不由己”,暗示了与身体密切联系的意义体系出现紊乱。格里高尔感到疲惫不堪,而仍囿于异化的处境,这是他缺失自我的后果,而《城堡》中的K也只为得到“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而疲于奔波。“土地测量员”这一身份仿佛K的所有人格和存在意义,他的身体急于与之趋合。然而K在身体与身份的契合过程中,却遇到城堡体系的隔离。K希望进入城堡而获得身份——身体的意义。疲惫显示了K的身体与城堡存在严重分歧。K无法进入城堡,无法获得城堡颁发的“土地测量员”身份,表明了对身体意义追寻的不可能,身体将永远象征一个无意义的存在。
疲倦是身体负荷达到了极限,而超过极限的病变则更加残酷。《乡村医生》里生病的孩子,伤口溃烂却被描述成鲜花。这一令人震惊的描写,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将麻风病人外部的溃烂认为是内心亵渎神灵的标志的看法类似,也表达了对“内心亵渎神灵”的惩罚。乡村的人们已经失去了信仰,即使对被看作拥有神祇力量的医生也表现了不信任、失望和野蛮,也从未正确对待过神。如果再把这个溃烂的伤口理解为“克莱斯特式的伤口”①的话,那么人的生存之所以永远遭受痛苦的折磨就是因为人已不再有信仰,已经失去了正常感受世界并获得意义的体验。溃烂的伤口比作鲜花,痛苦成为感受世界、获得自知的唯一方式,也意味着毁灭。丑恶与美丽共生,获得与毁灭共存,这又是一个悖论性的结局。
溃烂的伤口布满血污,流血代表生命力的流失,是死亡的恐怖象征。《在流刑营》里流血的行刑过程也是对犯人进行审判、宣布判决的过程。这个惩罚过程,“其目的就是对一个拥有各种权利,包括生存权的司法对象行使法律,而不是对一个有疼痛感觉的肉体行使法律。”[4]在此,惩罚所施与的是身体与人格紧密结合的一元体。二元论模式下的心灵与肉体,在被宣判犯罪并被施以惩罚时,无论是从道义和法律的审判还是对肉体的刑罚而言,二者都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趋于统一。作为罪犯,他在惩罚中获得了灵与肉的结合,获得了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的“和谐”秩序。军官并未获得“公正”的判决,而被“谋杀”,原则上军官在其崇奉的司法制度下未实现灵与肉的合一,显示了该司法制度的不合理与执行者自身的荒谬。但就实际而言,我们大多数人会认同军官受到的惩罚是公正合理的。在此,不合理与荒谬的却实际是公正合理的,这不能不表明审判与惩罚整个过程是徒劳的,然而中间失去的是一个人的身体和人格,最终的结论将是人在徒劳中毁灭。
从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开始,直至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学说流行,人疯狂地将自己的身体抛弃了。分离的状况几乎伴随着从生至死的全过程。人离不开身体,也需要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而身份和自我需要人以其身体来追索和趋同。身体的饥饿、疲惫、病变和惩罚使生存成为一场苦旅,变成一场荒诞的皮影戏。当卡夫卡带着痛苦的身躯直面孤独时,他与世界、与神、与他人、与自己发生了某种象征性的断裂,困境造成了,悖谬也造成了。
注释:
①“伤口”是19世纪德国诗人克莱斯特思想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他把人的生存看做敞开的伤口,不断遭受日常生活中新的刺激、污染或破坏,永远难以愈合。卡夫卡与克莱斯特在创作上和基本立场的心灵上都有相似之处。参见林和生.犹太人卡夫卡[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1][2][3](法)大卫·勒布雷东著,王圆圆译.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引言,200-201,198.
[4](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4.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