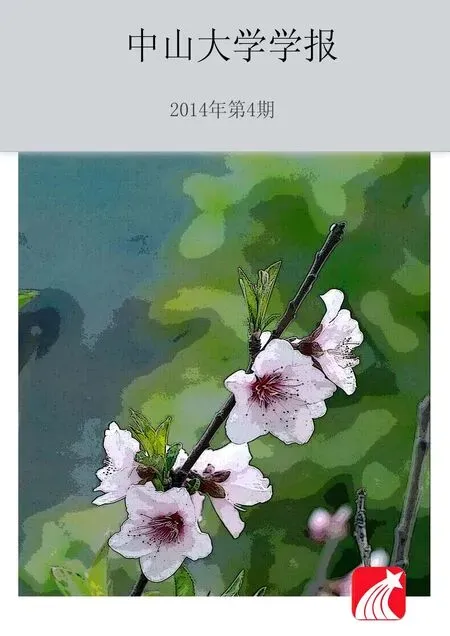杨炯事迹三考*
2014-01-23祝尚书
祝 尚 书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曾对“王、杨、卢、骆”的排序有意见,说“愧在卢(照邻)前,耻居王(勃)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①刘昫:《旧唐书》卷190《杨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5003页。。可见他自视甚高,但并非盲目自大,的确有其自大的“资本”,故连“当时议者”也不得不表示接受。然而,这样一位艺高群伦的才子,由于文集散佚②今通行本《盈川集》10卷,乃明万历时童佩辑刊本。,史传简略,故其生平事迹留下许多疑点或空白,只能靠发掘和连接历史碎片,方可让我们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史实。本文所考杨炯三事,就是三个“碎片”:首考他举神童(童子科)究竟在何年?笔者以为当前学界的结论恐不可靠。再考《梓州惠义寺重阁铭》的作年,它涉及古人以“十二次”纪年的方法问题。末考杨炯出任盈川令的大致时间,这关系到他的卒年和享年。
一、杨炯举神童时间考
杨炯举神童(即童子科)的时间,乃学界有争议、但近年来又似乎有了定论的一桩公案。杨炯举神童科事,载于两《唐书》本传,然皆未记在何年,故后代学者或以杨炯《浑天赋序》所述“显庆五年(660),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③杨炯:《浑天赋》,《杨盈川集》卷1,《四部丛刊》初编集部102。,为他举童子科之年;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4上(袁本,衢本在卷17)著录《盈川集》时,解题明确称杨炯“显庆六年举神童”。随后如《文献通考》卷231《别集》、通行本《唐才子传》卷1等,皆抄袭或附和其说。当代学者多疑之,以为唐童子科有年龄限制:《新唐书·选举志》规定,童子科参试者必须在“十岁以下”,而显庆六年,杨炯已十二岁,显然“超龄”,没有参试资格,故质疑其纪年是正确的。
于是有学者另辟蹊径,从明万历时童佩编次本《盈川集》附录中找到一条材料,称所附《文献通考》引晁氏语,谓杨炯“显庆四年(659)举神童”,显庆四年杨炯十岁,正好在规定的年龄限制之内*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杨炯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此说看似很合理,故学界差不多一边倒地赞同和引用,至今几成定论。然而若再深究之,此说虽克服了显庆六年与唐代科举制度的矛盾,看似圆满地解决了这个悬疑的问题,却仍有不小的疑点:通行善本《文献通考》记载的是“显庆六年”,与晁《志》相同,而明万历间刊本《杨炯集》附录所引版本不详的《文献通考》称是“显庆四年”,焉知“四”字不是刊误?况用晚出书纠正宋元古本,似有违校勘学原理。还可进一步追问:《通考》文字本来是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而晁《志》原作“显庆六年”,是否晁《志》也可以或应该据童佩本附录改为“四年”(按:现存晁《志》袁州本为宋刊)?就很值得商榷。质言之,《通考》既然是抄晁《志》,除非晁《志》被证明有误,可用晁《志》的校勘成果改《通考》,相反,《通考》相关文字却没有校改晁《志》的“资格”。总之,无论《通考》是何版本,如何记载,都是不可依凭的无效证据。
今从杨炯的作品中,似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考察出他登童子科的准确年份。《盈川集》卷10收有杨炯《祭汾阴公文》,其中有如下四句:
公夕拜之时也,既齿迹于渠阁;公春华之日也,又陪游于层城。*杨炯:《杨盈川集》卷10,《四部丛刊》初编集部102。
所祭“汾阴公”,即中书令薛元超,薛氏卒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十二月初。夕拜,指黄门侍郎。《初学记》卷12《黄门侍郎》引应劭曰:“黄门郎,每日暮向青顼门拜,谓之夕郎。”*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3页。按杨炯《薛振行状》:“(年)三十二,丁太夫人忧,去职。起为黄门侍郎,固辞不许。”④杨炯:《杨盈川集》卷10,《四部丛刊》初编集部102。《旧唐书·薛收传》附《薛元超传》:“永徽五年(654),丁母忧,解。明年,起授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刘昫等:《旧唐书》卷7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0页。渠阁,即石渠阁,汉代藏书处,后世代指秘书省。薛元超丁忧去职后,“明年”起复为黄门侍郎,固辞不许,只能受职,“明年”即永徽六年(655)。则杨炯“齿迹于渠阁”,当在永徽六年,其时六岁。六龄童而“齿迹渠阁”,其中必有原因,他当在是年中童子科,然后到秘书省读书,而非正授官职,故谓“齿迹”。这不是无端臆测,而是上引祭文的下两句,就与杨炯中制科关联(详后),这里也应相同,虽表述得不够明确,但意思是明白的,这是骈文行文的一个特点。考《唐六典》卷10《秘书省》有著作、太史二局,二局中唯太史局有学生:历生三十六人、装书历生五人、天文观生九十人、天文生六十人。李林甫注“历生”曰:“隋氏置,掌习历。皇朝因之,同流外,八考入流。”又注“装书历生”曰:“皇朝置,同历生。”至于天文生、天文观生,李氏注前者曰:“隋氏置,皇朝因之。年深者转补天文观生。”又注后者(天文观生)曰:“隋氏置,掌昼夜在灵台伺候天文气色。皇朝所置,从天文生转补,八考入流也。”*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03—304页。按杨炯《浑天赋序》道:“显庆五年,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76),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朝夕灵台之下,备见铜浑之象。”*杨炯:《浑天赋》,见《杨盈川集》卷1,《四部丛刊》初编集部102。弘文馆属门下省,而能“朝夕灵台之下”者,只能是秘书省太史局。因疑所谓“齿迹于渠阁”,当指杨炯自六岁起到待制弘文馆之前的五年间,曾在太史局读书。他已有了“科名”,应该不是“学生”,而是随同学生学习。比较而言,其跟随天文生的可能性最大(天文生“年深者”方转为天文观生,则天文生年龄最小)。在杨炯现存的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他对天文、历法极为热衷,由此或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再看《祭汾阴公文》的下两句:“公(薛元超)春华之日也,又陪游于层城。”所谓“春华之日”,“春华”乃用典,《三国志·魏·邢颙传》:“太祖(曹操)诸子髙选官属,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遂以为平原侯(曹)植家丞。颙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庶子刘桢书谏植曰:‘家丞邢颙,北土之彦,少秉髙节,玄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桢诚不足同贯斯人,并列左右。而桢礼遇殊特,颙反疏简,私惧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83页。则所谓“春华”,代指太子庶子,“春华之日”指薛元超为太子左庶子之时。《薛振行状》:“五十四,迁中书侍郎,寻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检太子左庶子。”*杨炯:《杨盈川集》卷10,《四部丛刊》初编集部102。薛氏年五十四岁时,为上元三年(676)。按杨炯《浑天赋序》曰:“上元三年,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杨炯:《浑天赋序》,《杨盈川集》卷1,《四部丛刊》初编集部102。则所谓“陪游于层城”,“层城”指皇城,谓二人同年升官,同在皇宫“上班”——尽管他们的地位、年龄相差很多,但作祭文时,固然要寻求共同点,以拉近自己与死者生前的关系,何况薛氏的确对杨炯有知遇之恩,曾表荐他为崇文馆学士。再回头看杨炯举童子科事。因举制科而“陪游”,前面与“齿迹”关联的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吗?因此可以认定,所引四句祭文,前两句由“齿迹石渠”而及童子科,下两句则由“同游层城”而及制科,这既是二者的逻辑关系,其实也是杨炯人生中的两个亮点,同时又是他自述的参加两次科举考试的时间点。
综上所考,杨炯举神童当在永徽六年(655),时年六岁。《郡斋读书志》著录《盈川集》20卷,其时杨集约存三分之二(原编本30卷),系年材料应还丰富,不应出错,而作“显庆六年”,疑乃晁公武误书年号,将“永徽”写成了“显庆”,遂铸成千古迷案。检《四库全书》本《唐才子传》卷1,正谓杨炯“六岁,举神童”,与上考结论完全相同。四库馆臣所用《唐才子传》底本为《永乐大典》本,当犹保存了《唐才子传》原本的面貌,而该书传世的其他版本(包括《佚存丛书》本等),则被后人据《读书志》妄改,踵谬承讹,不足为据。
二、杨炯《梓州惠义寺重阁铭》作年考
杨炯《盈川集》卷5《梓州惠义寺重阁铭并序》*杨炯:《杨盈川集》卷5,《四部丛刊》初编集部102。,称“大辰之岁,正阳之月,有郪县宰扶风窦兢……与禅师释智海……寓目于长平之山”云云;后又称“轮王所处,纯金为说法之堂;诸佛所游,众香作经行之地,亦未可同年而语也”云云,知是铭当作于重阁落成之后。傅璇琮先生《杨炯简谱》系该铭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理由是杨炯另有《为梓州官属祭陆郪县文》,“系垂拱二年正月作,此云郪县宰为窦兢,当系陆某卒后由窦兢继任,其时则当在垂拱二年正月以后”*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见卢照邻、杨炯著,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杨炯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9页。。此说虽无大误,似需进一步深考。另有学者注意到铭文序有纪年,即“大辰之岁,正阳之月”,于是释曰:“大辰之岁”,即“岁在大火”,岁星在“大火”星次。岁星在“大火”星次,则太岁在“玄枵”星次,即“太岁在子”,故为子年。垂拱四年,干支正为戊子,知此文必作于本年*见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42—243页。该《年谱》总体严谨,此条似偶误。。此说虽进了一步,但仍有问题。该学者所用纪年法,乃所谓“十二次纪年法”。该方法是古人为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和气节的变换,把黄赤道带天区自西向东划分为十二部分,并依次命名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又分别以十二次与十二辰对应(与岁星无关)。十二辰以十二地支命名,故十二次分别对应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玄枵”与“大火”同为十二次之名,十二次之间并无对应关系,即“大火”不能对应“玄枵”,故“玄枵”虽对应“子”,却与“大辰之岁”没有关系。
今按:序文称“大辰之岁”,《尔雅·释天》曰 :“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故这里应以“大火”与地支对应。“大火”对应的是“卯”*参见黄道周:《三易洞玑》卷16《贞图纬》下。其释《国语·晋语》“君(公子重耳)之行也,岁在大火”,谓“大辰为卯,卯为大火。董因(晋大夫)之言,皆指岁阳,不指岁星”。。如此说来,所谓“大辰之岁”,当为卯年,即天授二年辛卯(691)。考杨炯生平,他受从父弟杨神让从徐敬业起兵连累,贬为梓州司法参军,约于垂拱元年(685)秋冬入蜀,天授元年已任满回洛阳,在内侍省掖廷局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有宋之问《秋莲赋序》为证,而卯年(天授二年)已不在梓州。由此知《梓州惠义寺重阁铭并序》并不作于为梓州司法时,而是作于回洛阳后分直习艺馆的第二年。
又按《汉书·五行志》下之下:“当夏四月,是谓孟夏。说曰:正月谓周六月,夏四月,正阳纯乾之月也。”*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96页。则“正阳之月”为四月。知铭文当作于天授二年四月。 是时杨炯已在洛阳,而为惠义寺作《铭》,盖应窦兢遥请而作也。窦兢的前任陆某卒于垂拱二年正月(见前述),窦兢于同年继任郪县宰的可能性较大。唐代官员四考(四年)满任*《旧唐书·职官志》:“凡入仕之后,迁代则以四考为限。”刘昫等:《旧唐书》卷42,第1806页。,则窦氏应在永昌元年(689)去职,而他天授二年仍在梓州,疑因建重阁等事被留任。
三、杨炯赴盈川令时间考
杨炯最终卒于盈川令任上,卒年不可考。若能弄清他何时赴盈川令,便可大致推测其卒年。因此,考察他赴盈川的时间越接近真实,再据以推其卒年,才会大致靠谱。惜乎他赴盈川令的年份,文献也阙载。按《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杨炯》,校笺者引《金石粹编》卷101《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维贞)庙碑铭》*该文又见颜真卿:《颜鲁公集》卷16《补遗》。,其中有如下数句:“天授元年(690),糊名考校,判入髙等,以亲累,授衢州参军。与盈川令杨炯、信安尉桓彦范相得甚欢。”于是校笺者称:“此可知炯令盈川始于天授元年或次年。”*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页。今按:唐代举子取得科名后,并非马上授官,故天授元年颜维贞几不可能赴衢州任,当然也不能证明其时杨炯在盈川。况颜维贞授衢州参军乃因‘以亲累’,其亲(盖指其父)所犯何事而连累儿子的仕途,又何时洗白,不得而知。据文意,似乎无论“洗白”与否,都已影响到颜维贞的授官,可推测并非小事,中间必有一番曲折,折腾数年方授官,也毫不意外。这就是说,颜氏虽天授元年判入高等,但与授衢州参军并非同时,《庙碑铭》虽文字相接,而时间并不相接。史传、碑铭的行文,往往是跳跃的,举大而略小,其例不胜枚举。再考杨炯行年,天授元年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见下),天授二年作《唐赠荆州刺史成公神道碑》(《杨盈川集》卷7),天授三年作《杜袁州墓志铭》(《杨盈川集》卷9),如意元年(692)作《盂兰盆赋》(《杨盈川集》卷1)等等,都说明此数年间杨炯在洛阳、长安一带,并不在盈川,自然颜维贞在天授元年后的几年中,绝无在衢州与杨炯“相得甚欢”的可能。因此,谓颜维贞天授元年制科判入高等,遂定是年或次年在衢州参军任,并进而旁证杨炯为盈川令也始于是年或次年,当为误判。
学界一般认为,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任满回洛阳,于武则天天授元年(690)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这有宋之问的《秋莲馆序》*李昉:《文苑英华》卷148,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686页。为证,当确凿无疑。他分直习艺馆有多久?何时去盈川县?傅璇琮先生认为赴盈川当在如意元年(692)。理由是如意元年七月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杨炯献《盂兰盆赋》,“即于秋冬被选为盈川令”*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杨炯考》,第15页;又《杨炯集》附录载《杨炯简谱》,见卢照邻、杨炯著,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杨炯集》,第232页。。其他相关论著,多采此说。
但是,这个结论要在杨炯分直习艺馆后再无北方作品可考时,方才成立。而事实是,就现存论,在《盂盆兰赋》之后仍有可系年的北方作品。《盈川集》卷6《大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称墓主梁待宾“以长寿二年岁次癸巳(694)二月辛酉朔二十四日甲申,迁窆于雍州蓝田县骊山原旧茔”,显然这时他并不在盈川。如果以该碑文不排除作于盈川的可能性进行辩护的话,那他最后可系年的《老人星赋》(《盈川集》卷1),证明长寿二年后杨炯仍在洛阳,那就很难解释了。
《老人星赋》首句曰“赫赫宗周,皇天降休”;末句称“臣炯作颂,皇家万年”,知其非一般体物之作,而政治气味十分浓烈。按《文苑英华》卷561载武三思《贺老人星见表》:“臣守节等文武官九品以上四千八百四十一人上言:臣闻惟德动天,必有非常之应;惟神感贶,允属会昌之期。天鉴孔明,降休征者所以宣天意;神聪无昧,效嘉祉者所以赞神功……伏惟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陛下润色丕业,光赫宝祚。执大象而御风云,鼓洪炉而运寒燠。浃洽四海,辉华六幽。希代符来,超今迈昔。浪委波属,故合沓而无穷;日臻月见,尚殷勤而未已。伏见太史奏称八月十九日夜有老人星见,臣等谨按《黄帝占》云:‘老人星,一名寿星,色黄明,见则人主寿昌。’又按《孙氏瑞应图》云:‘王者承天,则老人星临其国。’又《春秋分候悬象文曜镜》云:‘王者安静,则老人星见。’当以秋分候之,悬象著符于上,人事发明于下。寿昌者知亿载之有归,安静者示万邦之必附。澄霞助月,非唯石氏之占;散翼垂芒,何独斗枢之说。臣等谬参缨笏,叨目祯祥,庆抃之诚,实倍殊品。无任踊跃之至。”*李昉等:《文苑英华》卷561,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868页。按《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证圣元年(695)……秋九月,亲祀南郊,加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天册万岁。”*刘昫等:《旧唐书》卷6,第124页。表称老人星见在八月十九日夜,盖先有老人星见,至祀南郊、加尊号时方上表为贺也。则该赋亦当作于是时之洛阳,盖武三思欲借杨炯之名以颂圣。如此看来,杨炯如意元年秋并不在盈川,而是在洛阳,其时盖仍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他赴盈川,最早当在献《老人星赋》的证圣元年九月之后。上文言颜维贞任衢州参军时与杨炯“相得甚欢”,当是此后之事。
上引《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说过,证圣元年九月武则天亲祀南郊时,改元天册万岁。如果祀南郊后即授杨炯盈川令的话,到盈川任盖已是次年初,而武则天又已改元为“万岁登封”元年(696)了。唐代为官,四考(四年)满任。杨炯卒于任,这无可怀疑,但已历几考不详,若姑以三考计,则已是圣历元年(698)。杨炯生于永徽元年(650),到圣历元年为四十九岁;而实际上,他出任盈川令未必与献《老人星赋》时间紧接,也许死时已过五十的“坎”。这较此前学界的推测(约享年四十四、四十五)“长”了好几岁。
应当指出,在杨炯生平事迹研究中,“长”了好几岁并非小事。比如,宋赵明诚《金石录》卷5载:“《周晋州长史韦公碑》,杨炯撰,孙希弼八分书,长安三年(703)四月。”*赵明诚:《宋本金石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4页。因碑文久佚,有学者据此将杨炯的卒年推迟到长安四年(704)或神龙元年(705),从而引起其他学者的激烈反对,认为该碑文绝非出于杨炯之手;但也有学者认为,长安三年当为立石立年,非撰文之年*以上所述,见王兆鹏:《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 陶敏:《杨炯卒年求是》,《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第6页。。两说皆难完全服人:《金石录》乃严谨、权威的学术著作,赵明诚似不可能误录非杨炯的作品。而说撰文在先、立石在后的话,韦公死前八九年就预求碑文,一般说来,又不太合情理。若杨炯卒于圣历元年或更晚些的话,韦公死于稍前,距长安三年下葬仅四五年,甚至可能只有三四年,而古人死后因各种原因,隔三四年、四五年方正式安葬,文献中并不少见*这在《盈川集》中也有其例。如卷8《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墓主魏哲卒于真宗总章二年(668)三月,葬于咸亨元年(670)某月,中隔三年。又如卷9《从弟去盈志铭》,墓主杨去盈卒于上元三年(676)五月,葬于仪凤四年(679)十二月,中隔四年。,则撰文在先、立石在后之说成立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而该碑文乃杨炯作,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