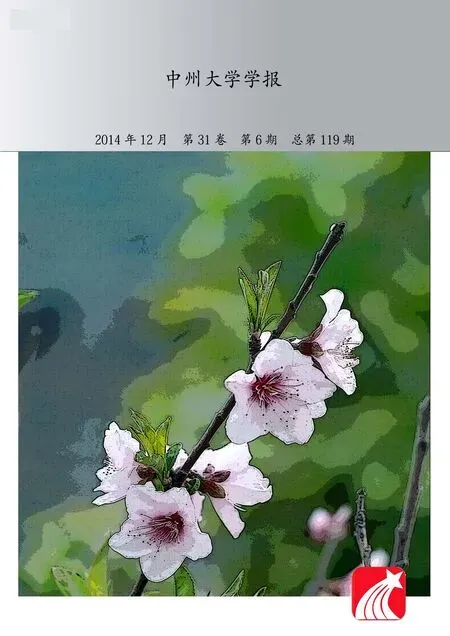清中叶豫北荒政与公共领域控制
2014-01-22单磊
单 磊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大清帝国的龙旗落地将近百年,学术界给它以莫大关注,尤其热衷讨论中央与地方争夺公共事务控制权的问题。学界多有认为,清代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呈现出逐步加强的趋势,形成前所未有的“绅权大张”之势,乡绅阶层由原来的控制对象转化为控制主体,甚至在公共领域控制中居于主导地位。笔者以为这些结论似乎不能涵盖国土广袤的清代中国,并曾以天理教起义为背景,讨论过这一问题,认为国家政权在豫北民众的社会认同中表现强烈,官方意识在豫北地区依然颇具影响力,并牢固地制约着地方意识的觉醒。[1]当然,这不足以说明清中叶中国的整体面貌,许多问题有待继续商讨。清中叶豫北灾荒频仍,通过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在荒政上的态度和发挥的作用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探讨清中叶豫北地区公共领域控制状况,同时对所谓“绅权大张”的泛化趋势加以遏制,依然很有必要。
一
清代中期豫北地区灾荒连年,水、旱、蝗、震不断,几乎每个县都遭到过重大灾害,灾荒的破坏也越来越惨烈。通常情况下,仓储充裕、蠲租劝赈、有序执行是应对灾荒的主要条件。面对灾荒,朝廷、地方官府、受灾难民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看朝廷和地方官府的态度。清初安阳城乡仓廒有二十余处,备荒周全。清嘉庆间安阳只有仓廒六处,储量似有减少。在国家储备减少的情况下,清廷对灾荒的反应还是及时的,各级官府对救荒赈灾工作也颇为重视。如嘉庆十八年(1813)河南发生大面积灾荒,清廷即下诏赈济河南灾区,河南大部分地区受到朝廷赈济。[2]道光一朝的荒政也是值得称道的,仅据《清史稿》一种文献就可看出道光帝数十次下诏赈灾救荒,着令地方官吏加强救民赈灾工作力度。[3]上情下达,地方官府也积极配合。嘉庆十九年(1814),时仪封大工未竣,黄、沁并涨,地方官吏姚祖同疏陈:“政务虽多,河工为重;学习河务,以履勘为先。”道光帝初即位,他又疏陈河南情形:“河工之敝坏显而易见,民生之凋瘵隐而难治。河工加价,自常赋三百六十馀万外,逾额摊徵。衡工未已,睢工继之;睢工未已,马工、仪工又相继接徵。此外复有各处堤工随时摊徵之款,民力其何以堪?请概停缓三年,以纾积困。”[3]姚祖同亲自深入施工现场参与工事修筑,更为可贵的是,他还能把“河工”与“民生”联系起来,在处理荒政上表现得非常干练。事实证明,救灾取得了较好成效。道光二年,漳水决安阳樊马坊,河流北徙,地方官程祖洛周历上下游,疏言:“漳水自乾隆五十九年南徙合洹以来,卫水为所遏,每致溃溢。今河流既分,不可使复合。议於樊马坊上下距洹水最近处,及南岸冲决成沟,并筑土坝,使二河分流,冀减漫溢之势。”[3]他首先疏清漳水改道症结所在,一举使得“漳、卫合并之患遂息”。这些都表现出清中叶朝廷和地方官府对地方社会控制的眼光和能力。不仅如此,朝廷和官府还非常重视灾后重建,采取各种善后措施避免灾祸蔓延。
二
再来看乡绅阶层。乡绅是有功名仕宦的人在乡村的称谓,是明清时期由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产生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乡绅可分缙绅和绅衿两种,缙绅指通过现任和退职的文武官员,以及封赠,捐买的实、虚之官;绅衿则指有功名却未出仕的举、监、生、员。[4]也有人认为乡绅指在朝官因丁忧守制、体衰请假、年老退休等居家在野,曾任高官或有较为丰厚财产的在野官员,乡野有名望者也可称为乡绅。尽管有种种不同,但他们作为乡绅的基础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掌握知识的文化人,其中很多是考取过功名,在地方有较高威望。乡绅熟悉地方情况,又通常是以强势家族为社会背景的,他们中很多与地方官吏甚至朝廷大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处理地方事务如灾荒面前他们总扮演着普通百姓难以取代的作用。乡绅为维护自己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灾害当前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一方面利用自己掌握文化优势为赈灾呼喊,另一方面亲自参与救济灾民的活动中去。早在乾隆五十三年,绅民王思孝等呈请官府批准并帮助河流近堤三十六村人民每岁修筑河堤,以资保障,并力请免其杂差。
兴修水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无疑,河堤修筑对防洪抗旱大有裨益。乡邑名望之士面对蓬勃发展的基础设施工程备加赞誉,也体现了乡绅阶层置身这一洪流之中,试图扮演防灾救民的主体。
荒政背景下地方官吏与乡邑名望齐心合力赈粮救灾在嘉道年间是具有普遍性的。栗毓美任河督时力主备荒抗灾,他计划收买民间砖块用来筑堤,“邑人浮言均谓不可,公持之不疑,工固而民赖以济,河工用砖料自此始”。栗毓美“督河兵堡夫及雇工自板张庄孙家堤三十里左右的广大区域筑砖石大坝,长短二十余道,河始南徙,保全河朔,栗公之力也”。栗公以朝廷命官的身份主持地方事务,在地方民众心目中具有执行权力的合法性。因此,“众人皆喜,度用有资”,治水获得成功。基层官员在维持一方安定中是较为成功的,乡邑绅士可以向地方官员出谋划策,但无力左右地方事务。曾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等职的李棠阶回家守制,时值道光二十六年豫北遭水灾,他力请地方官放赈,并“戒家人共节俭,而于本里贫人按日授米至次年四月止”。次年,温县又发生灾荒,他“于戚族里人之贫者量力周恤”,自云“薄宧余赀,适度凶年,至是尽矣”。因连年大雨成灾,亟需整修排涝工程,他遂“自勘验绘图”,上呈府县请施工,组织乡人挑治,并“躬往督率,徒步烈日中,或竞日不得食”,但他向地方官员的诸多建议并未被采纳,仅凭一己之力显然难以有效调动民众救灾情绪。
三
在灾荒频仍、环境恶劣的豫北农村,普通乡民持什么态度,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困难?除协助朝廷、官府应对灾荒之外,乡民还通过订立公约、勒石立碑的形式维护社区安定。原阳县境内道光二十六年立的杏兰科会碑有这方面的记载:
……自嘉庆二十四年马工漫溢,地稍被淤,风亦稍减。至道光二十年,飞沙又动。予恐复蹈前辙,遂与刘德、王义、杨福成约五村庄各出资财,共栽小杨树,棠科,以挡来沙,乃年未四、五,而树森茂,风沙已蔽。……共立会规:绑枝,罚钱一千;镰杀、斧砍,罚钱一千。如不受罚,禀官究处。异日数大辨钱,地主与会各得其半,永不许地主毁坏树木。
面对恶劣自然状况和“粮差追呼犹甚”的社会环境,基层民众并不指望官府和地主能为基层社区造福,而是设法自保。又恐所立会规无法真正行使效力而要“禀官究处”,这说明民众依然有较强的国家意识,也反映出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基层民众的复杂心态。
每逢荒年,都可看到中央和地方力量赈灾保民的记载,这反映出清中叶应对灾荒的机制依然是健全的,此时清廷在国家生活中权威犹存且仍旧能发挥巨大作用。在大灾荒影响地方正常秩序,危及一方平安时,地方官府和民间力量还必须依靠朝廷各项政策、救济品来处理荒政。故清中叶豫北地区尽管灾荒不断,甚至也有“人相食”的现象,但是从当时的各种文献记载来看,并未出现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大灾之后也未出现大面积的瘟疫。在朝廷、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救助下,民众饥荒往往可以得到缓解。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官方始终不肯把赈灾的主导权让位于地方士绅。嘉道之际豫北地区基层控制的主导权掌握在朝廷以及代表朝廷意志的地方官府手中,士绅阶层起很大作用,却并未出现士绅阶层普遍控制地方事务的现象。实际上,豫北方志中有多处关于乡绅向地方官吏建言献计遭拒绝的记载。在荒政背景下,豫北地区的基层社会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乡绅势力有所崛起却受到强大的中央势力的压制。
四
在关乎公共领域稳定的荒政问题上,朝廷及其在地方的代言者地方官府利用其传统统治特权紧紧操纵社会控制的主导权。当盛世不再,官方加紧了其对地方控制的力度,严防地方势力颠覆国家权威。乡绅势力利用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优势力图谋求控制权,并领导基层民众对国家政权实施反控制,随之而来的是其地方意识逐渐觉醒。然而,传统社会统治秩序的内在机制在豫北这一相对封闭的边缘地域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国家政权取得了巨大胜利:一方面维护了朝廷在这一地区的权威,另一方面朝廷趁机向豫北民众灌输了强烈的国家意识。乡绅只是国家正统权力在地方的陪衬,其权威实际上是国家政权赋予的。他们不经地方官府而去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需要得到国家政权的默认。乡绅阶层参与基层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管理是无力把统治触角伸向基层深处的国家政权对乡绅暂时的权力让渡。事实上,当乡绅意志威胁到国家政权在地方的核心统治利益时,国家会立即收回赋予乡绅的权威。把中国的乡绅与西欧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新贵等同有盲目比附之嫌。乡绅阶层崛起并非新生力量成长,也不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诞生。学术界津津乐道的“绅权大张”反映出国人对绅权向往的一种情结。
有清一代,在对重大公共事务的处理上,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力度都是比较大的。无论地方势力如何强大,中央势力都能利用其既得统治特权抑制地方的离心倾向,维护既有的统治格局,这是清代实现长期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重要基础。中央对地方灌输的国家意识成为基层百姓重要的历史记忆,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尽管屡遭列强宰割却依然具有强大的政权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与此有很大关系。假使明清以来乡绅阶层权力真的扩张到中央政权无法制约的地步,清中叶以后为何没有出现地方政权林立的现象?至于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尖锐对抗更无从谈起。太平天国运动虽另立政权,但它与乡绅权力扩张没有什么实质性关系。即便是近代之后崛起的湘淮集团也是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乏力的特定情况下,以维护大清统治利益的名号发展壮大的。虽然他们在国祚不兴的形势下对清廷有离心倾向,但始终没有能力另立政权与中央抗衡。大清帝国龙旗悄然落地之际,湘淮集团也作为满清的附属物随之殉葬。至于清亡后的旧军阀割据纷争则是由于更加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当另加探讨。
参考文献:
[1]单磊.天理教起义背景下的地方社会控制[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3).
[2]清仁宗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1962.
[3]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张仲礼.中国乡绅: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