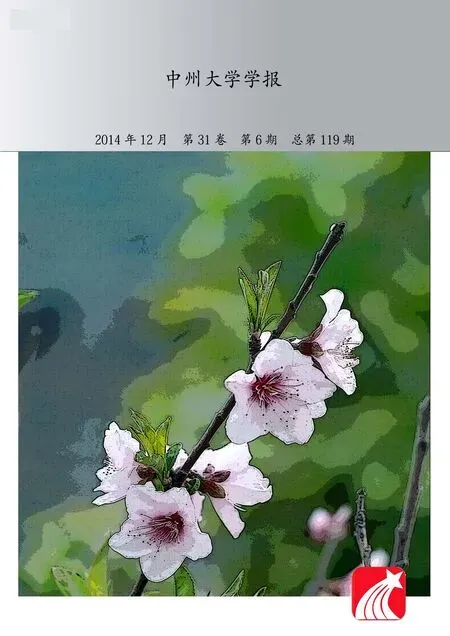知识分子精神的日常消解
2014-01-22张延文
张延文
(郑州师范学院 中原作家研究中心,郑州 450044)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在其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当中宣称,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是最后一批“公共知识分子”,而随着大学教育普及,知识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科技时代的来临,公共知识分子逐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也随之衰落。
在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专业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些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具有独立身份的作家、艺术家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已名不副实。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来临,在当下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已经逐渐被“意见领袖”、“媒体知识分子”等新名词所取代,甚至在很多社会评论当中被等而下之。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日益分层化。在学院里,随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日益清晰,人文学科通常不受重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得天独厚,风光无限。而“媒体知识分子”在网络时代里,具备了天然的传播方面的优势,慢慢占据了大众文化的前沿阵地。小说叙事,也因此受到了新闻叙事等大众传媒话语方式的影响,而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于“媒体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是如此评价的:“人们似乎接受了‘媒体’——报纸、书评、电视问答节目——的评判并信以为真;这有混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混淆电视曝光和知识分子真正的影响力的风险。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它一向趋附于金钱、权力或戏剧性事件,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们、评论家们就曾谴责出版社歪曲了文化生活。公共领域和市场比起来,更少自由市场的观念,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1]
对于叙事文学来说,今天的作家似乎更为津津乐道于“非虚构叙事”,力图以放弃部分虚构的权力来换取客观真实,以博取读者的芳心。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将叙事引入歧途。“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的处境尤为艰难,他们在丧失公众的公信力的同时,也在丧失自信心。
新时期以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作家,对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尝试,但对于学院化的、专业化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关注并不多见。然而,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作家,对于学院化的专业知识分子的叙事行为,其本身就颇耐人寻味,这种观察与探看的立场,容易流变为一种微妙的平衡术,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群体进一步细分的必然结果。
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正是打着新文化运动的大旗而展开的,随之而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出的硕果就是新政权的建立,也被当作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开端。知识分子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翻身得解放”,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指出,他们不过是依附在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所有制五张“皮”上的“毛”。这就是著名的‘皮毛论”,成为打击“右派”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里,大量知识分子纷纷成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右派分子的一员,而受到残酷迫害。当时,作家、艺术家等“公共知识分子”更是社会改造的重点,而对于科技类的专业化的知识分子通常是网开一面。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文革”导致的文化断层,知识分子一度很“紧俏”,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黄金十年。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局面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部改观。1989年,成了中国社会公共生活开始进入私人化时代的一个分水岭,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无所依附。那么,这批人要么转身离开,另谋出路;要么成为孤魂野鬼,被边缘化,进行精神流亡。
中国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令人有眩晕感,这岂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所能看破的玄机?从鲁迅的《野草》到巴金的《随想录》,贯穿其中的有自我反省的体验。1993年,《收获》刊登了青年作家李洱的中篇小说《导师死了》[2],这是李洱的成名作,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这部小说描述的是在一个阴沉肃杀的疗养院里,著名的民俗学家常同升及其弟子吴之刚的死亡历程。常同升作为“导师”身份的体现者,具有强烈的“家长制”和“老人政治”的隐喻在内。“导师之死”不单纯是“知识分子”穷途末路的挽歌,更带有对于某种权力和精神控制互相结合的社会并发症的厌恶和恐惧。这部作品可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做出的精卫填海式的拉风之举,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社会批评本身。
李洱在随后写出了《午后的诗学》[3]等一系列关于学院化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的作品,其使用“饶舌”的语言显示出强烈的个人思辨意味。2002年,李洱推出了长篇小说《花腔》[4],这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来关照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有着宏大企图的作品,之前有螳臂当车之嫌的堂吉诃德粉墨登场,唱起了花腔。葛任在被限制的自由和被消除的生命里,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吟咏风月,不免让人联想起鲁迅《故事新编》里《补天》中在女娲两腿之间顶着古衣冠的油滑“小丈夫”,他们互相映照,呈现出古老民族独特的荒诞的喜剧性。
《小说月报》(原创版)2014年第3期刊载了青年女作家孙瑜的中篇小说《危险时请敲碎玻璃》[5]。这部小说为我们描绘了学院化的知识分子群像。如果说李洱作为一个“60后”作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之间,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我们打造了一系列的外表亦喜亦嗔、内里却庄严肃穆的知识分子的“群芳谱”,那么孙瑜的这部小说就彻底撕毁了先辈们小心翼翼、竭力维护的遮羞布。当然,这里的知识分子是完全学院化的“技术精英”。在一个标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社会里,人文学科为主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由于所面临的生存境况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而逐渐出现了分裂。这部作品恰恰就反映了这种分裂的趋势,它代表的就是作为作家——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所能做出的,对于专业化的知识分子精神沦丧、毫无操守的生存现状的揭露和批判。这既是对于知识分子题材疆域的延展与扩充,更是知识分子内部分裂的第一现场;同时,也是古老中国正在发生的灵与肉的裂变的文化象征。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当中,描绘了一个农村知识青年从乡村进入城市,铩羽而归的故事,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农民的出路问题,在今天仍然非常突出。
《危险时请敲碎玻璃》的男主人公梁鸿安通过寒窗苦读,获得了博士学位,一帆风顺,兼博导、研究所所长和学院的院长于一身,却是一个典型的“鸡蛋”,“外皮是红色,中间是白色,而内核是根深蒂固的土地黄。这样的‘鸡蛋’,有着体面的红色政治身份,也具备资产阶级们的鼓涨腰包,骨子里却仍然是农民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这段人物素描,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复杂的社会身份和多元的文化心理,他们经历过“文革”“改革开放”和网络社会的新时代,被“农民”“红色政治”“资产阶级”等多重因素所制约和困扰。梁鸿安身上无法洗刷干净的泥土气息,成为了他家庭生活当中的一大障碍,他和城市出身的老婆格格不入,在生活习惯上一直无法互相融入。和高加林比较起来,梁鸿安无疑是幸运的,他升官发财养小三,有一个还算完满的家庭。这也使得他的私欲极度膨胀,最终走向了不归路。
梁鸿安和妻子之间的感情不咸不淡,本来是可以维持的。问题出在:苏影生了个女儿,双方都是公职人员,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不敢生二胎。迫于各种压力,苏影不顾一切再次怀孕,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流产。这些都坚定了梁鸿安包养二奶的决心,如果不能生个儿子,他作为梁家的独子,就感到无颜面对死去的母亲。梁鸿安的母亲共生了十个孩子,只有他一个男孩,母亲就像一个生育的机器,为梁家传宗接代就是她一生最为重大的使命。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宗法社会的家庭伦理观念,并没有因为中国社会进入到了21世纪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当梁鸿安的父亲拿儿媳妇没有能耐为梁家生个男丁,以古时候还兴三妻四妾来说服儿子另谋它就时,梁鸿安就默认了父亲的建议,他甚至一度荒唐地认为所有生了儿子的男人都比他幸运得多。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高等院校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在思想意识方面,梁鸿安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农民,更为可怕的是,他是一个掌握了资源和权力的“农民”。那么,他的作为就会远远超出重男轻女、包养情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了。事实上,他还玩弄权术,贪污腐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官僚毫无二致。如果我们将梁鸿安的悲剧归因于他的成长背景,那么围绕在他周围的其他知识分子,是否就会遵守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城市,在关系着一个民族未来的教育大计的高等院校,依然在生长着一个又一个的“梁鸿安”。
作为梁鸿安精心培育的弟子胡海洋,在上大学时就学会了给老师送礼,把恩师的家当成了他的另一门政治选修课,溜须拍马,低三下四,没有任何道德底线。而胡海洋的忠心也得到了恩师的回报,梁鸿安之所以对胡海洋加以培养、重用,并不是因为胡有多么优秀,而是因为胡的忠心。这种任人唯亲,学术近亲繁殖,毫无节操的选人准则,在高校的行政机构里形成了典型的“竞劣机制”,真正的人才怎么可能得到重用?而在这个高校机制里生存的知识分子们,又怎么可能保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精神?节操尽失就不可避免了。
胡海洋申请科研项目,评职称、分房子、升迁,都需要“恩师”的关照,这也是梁鸿安控制手下的“技能”。在梁的威逼利诱下,胡海洋陷入了失语的状态。作为一个被剥夺了正当生存权的受害者,胡海洋甚至被迫和“恩师”的小三假结婚,并且莫名其妙地当了“恩师”和其小三的私生子的爸爸,还面临着“被离婚”的人间闹剧。面对诱惑,胡海洋丢盔卸甲,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奴隶”。梁院长神通广大,长袖善舞,不仅能够买通相关人员违法办理结婚证和离婚证,还真的帮胡海洋马上申请到了省级的科研项目。就是这样一个人,还在首都积极活动,要申请院士。这整个学术链条,包括社会行政,都存在着极大的黑洞,令人发指。科研项目,职称评定,论文发表,甚至连院士都可以通过“运作”,而不是靠真才实学来获取评定,那么,这个学术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就存在着致命性的缺陷。生存于其中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摆脱被控制、被精神奴役的宿命?小说最终提供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网络来反腐倡廉,梁院长像现实当中的很多贪官一样,倒在了女人的石榴裙下,而给予他最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他一手扶植的、最为信任的手下——胡海洋。
互联网作为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的工具,有效地扩大了普通民众言论自由的空间,这对于封闭环境的社会舆论来说,效果会更为明显。但我们也明白,通过网络反腐,并对权力机构进行舆论监督,即便能够达到一定效果,其发生的语境本身也不免令人警惕和失望。胡海洋之所以会举报自己的“恩师”,也是事出偶然,并非其本意,胡海洋只是想借机敲诈,这本身就带着犯罪动机。事实证明,这种通过利益驱使达成的人身依附,建立在不道德不正当的渠道上的人际关系,是不可能持久的。这个结局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对于当下仍然存在的类似现象敲响了警钟。胡海洋的出现,绝非偶然,如果他能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生路径的选择。对于学院里的知识分子来说,严格管控的学术环境,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和学术空间。
从传统社会里的“士”开始,知识分子作为具备了一定社会地位的特殊阶层,虽然一直有着依附的特点,但毕竟还算有一些生存的资本和依凭,并且会有一部分的“士”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主流社会,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到了21世纪的今天,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不再拥有特殊的身份,更无任何社会资源可谈,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其生存的困境更相对突出,必然会产生自卑感。只有改变知识分子的这种生存状态,才有可能产生出传统社会里“士大夫”那种为民请命的社会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日知识分子的精神现状不仅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进步,反而更加萎缩,以至于到了精神猥琐的地步,几乎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自满清覆亡以来,知识分子命运的升降起伏,一度成了中华民族国运兴衰的晴雨表,也是华夏儿女精神生活的温度计。当下的文坛,相当一部分作家具有独立的职业,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不像学院化的知识分子必须依赖高校机制来维持基本生存,反倒更容易获得超脱的立场,创作出具有较强批判意识的文学作品。还有像作协会员和签约作家,虽然也会受到相关部门的制约,但这种关系毕竟松散得多,他们民间的身份属性也更多一些。
教育改革,在今天来讲,不单纯是改变应试教育,消除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这么一些具体的问题,更为深入的还在于如何理顺教育制度,比如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提升,高校制度改革等等。如果能够取消现行的机械、僵化的职称评定方式和科研考核机制,学术腐败就会少得多,这样就会减少相关部门对于知识分子的控制力。事实上,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层问题还是权力机制问题,只有高校的民主化建设进程能够持续地向纵深推进,才能让学院里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机会得以精神上的重生,才能培养出富于独立精神和创造意识的生机勃勃的一代新人。
孙瑜的这部小说,为我们揭开了高校知识分子生存的一个横断面,触目惊心的现实击碎了一贯温情脉脉的假面,让我们意识到了背后存在着的危险。但愿这能够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除非有关部门能够举起安全锤,才有可能敲碎在无形之中束缚着我们的无处不在的玻璃墙。这已经不仅仅是精神独立的问题,还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诸多方面。在《危险时请敲碎玻璃》中,既有社会分析的精准和冷静,也有欲罢不能的温情和怜悯,叙事人以尺水微澜的方式呈现出了人物复杂多变的精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透视当代中国社会精神内涵的诊断书。
参考文献:
[1][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M].洪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2]李洱.导师死了[J].收获,1993(4).
[3]李洱.午后的诗学[J].大家,1998(2).
[4]李洱.花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孙瑜.危险时请敲碎玻璃[J].小说月报,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