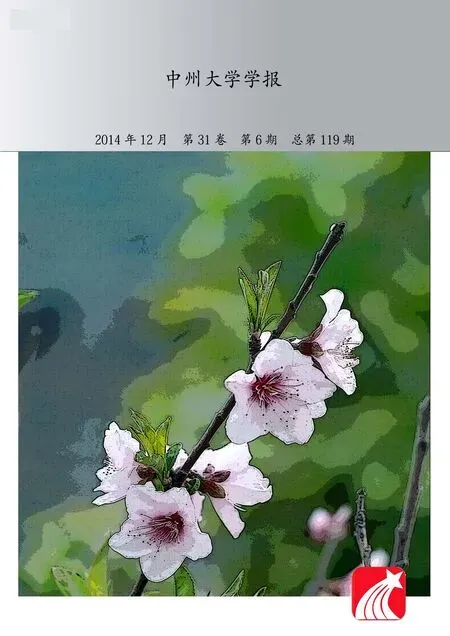我国古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初探
2014-01-22付传军
付传军
(河南警察学院 学报编辑部,郑州 450046)
一、引言
刑法中的自首制度,一向被认为是中华法系所特有的刑法制度。[1]323其理论基础是“过则勿惮改”。正如《唐律疏议》中对自首律条的疏文所说:“过而不改,斯成过矣。今能改过,来首其罪,皆合得原。”
根据现存刑法史料,自首规定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中:“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守即“首”,自首之意。整句话的意思是:凡是处罚庶民的犯罪,对预谋犯罪的,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后自首的,要区别这些情节,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罚。
秦时称自首为“自出”。《秦简·法律答问》载:“把其段(假)以亡,得及自出,当为盗不当?自出,以亡论。其得,坐赃为盗……”即携带借用的官有物品逃亡的,如果是自首的,以逃亡罪论处;被抓捕的,则计赃按盗窃论罪。[2]277由此可知,自首者可以减轻处罚。
汉时称自首为“先自告”,汉代首先在法律上规定“先自告,除其罪”的原则。据《汉书·衡山王传》记载,汉武帝元狩元年衡山王太子刘孝就因向官府自首自己以及其父诸人的谋反活动而得以免除其参与谋反的罪责。
自首制度经历代相因,至唐朝时已规定相当完备,在明清两朝又有发展。以下以《唐律》规定为基础,兼顾明清两代的发展,从几个不同的方面简要探讨一下我国古代刑法中自首制度的具体规定。
二、自首的主体
自首的主体即依法律规定应由谁去自首才是法律所认可的自首。唐律将罪犯亲自首告称为“身自首”。除此之外,唐律又规定了“遣人代首”和有关容隐关系的亲属自行代为自首两种形式,“即遣人代首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亦同身自首法”。法律同时又规定,罪犯遣人代首,或知道亲属出首及告发,在官府追传时本人不归案的,不得适用自首原罪之法。第37条的疏文解释说:“犯罪之人,闻有代首,为首,及得相容隐告言,于法虽复合原,追身不赴,不得免罪。”在这种情况下,代为出首及告发的亲属仍以自首免罪处理,“首告之人及余应缘坐者,仍以首法”[3]150。
《唐律》对“遣人代首”情形的规定比较简单,对所遣之人也无特别规定。但《唐律》“于法得相容隐及相告言”的规定则较为复杂,下面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
根据儒家“父子相隐”的思想,唐律规定了“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根据《唐律·名例》总第46条:“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凡同居大功亲之间及部曲奴婢对主人适用容隐制度,在这个范围内的人员出首或者相告发的,罪犯以自首免罪,“亦同身自首法”。但其中依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若是有相隐关系的亲属出首告发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出首告发主人,倘若首告之罪不是谋反、大逆、谋叛以上之罪,出首告发之子女、孙子女或部曲奴婢要处以“绞”刑,而被出首告发之人以自首论处。如《唐律·斗讼》总第345条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处绞;谋反、大逆、谋叛以上之罪,虽父祖听捕告;告余罪者,父祖得同首例。”据此条可知即使是卑幼首告尊长,若首告之罪为谋反、大逆、谋叛之罪,则首告者无罪,被首告者要“听捕告”。本条疏文又进一步解释说:“谓谋反、大逆、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告亦无罪,缘坐同首法,故虽父祖听捕告。”如果主人犯谋反、大逆、谋叛之罪,奴婢也可控告而无罪。因反、逆、叛及其他罪缘坐的亲属及犯反、逆、叛等罪中不缘坐的期亲,起来捕捉、告发罪犯,出首告发人皆以自首论处,不再受缘坐。《唐律·名例》总第37条注文:“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本服亲,虽捕告,俱同自首例。”
关于自首主体的规定,明律并无特别变动,清律沿用明律规定,但在实际应用中以条例的形式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五年纂定的条例:“小功、缌麻亲首告得减三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其谋反、逆未行,如亲属首告或捕送到官者,正犯俱同自首律,免罪,若已行者,正犯不免,其余缘坐人亦同自首律免罪。”在清律“犯罪自首”条中“得相容隐者”作为自首主体是不包括小功、缌麻及无服亲在内的,条例的这个补充扩大了自首主体的范围,有利于充分发挥自首制度的作用;同时根据本条例的补充,对于谋反、逆等严重的犯罪,于律得相容隐的亲属首告正犯,对正犯以谋反、逆“行与未行”来确定自首的成立与否,而对应缘坐的出首人来说,不管反、逆是否已行,俱按自首免罪,这有利于促使缘坐的人首告反、逆等严重的犯罪,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对“于法得相容隐”的人,如同居之父、兄、伯、叔与弟,明知为匿或分受赃者,自身亦构成犯罪,若据实出首,如何处理?雍正七年定例规定:“强盗同居之父、兄、伯、叔明知为匿或分受赃物者,其据实出首,均准免罪,本犯亦得照律减免发落。”出首不仅对自身有效,而且效力还及于本犯。此例补充了律条及律注之不足,有利于鼓励自身亦构成犯罪的人据实出首其同居亲属强盗罪行。
三、自首的时间与对象
自首的时间即法律对自首在时间上的要求。《唐律·名例》总第37条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本条的疏文解释说:“犯罪已发,虽首不原。”可见唐律对自首的时间要求是“犯罪未发”。而所谓案件“未发”唐代司法实践中有两种基本情况:其一,是指官方未发现犯罪并进行追究。如果官方自行发现犯罪并进行追究,唐律中称为“案问欲举”,属于已发的情况。其二,是指未有人去官府指控告发犯罪。有人指控告发也属于“已发”,疏文解释说:“若有文牒言告,官司判令三审,牒虽未入曹局,即是其事已彰,虽欲自新,不得成首。”所以其界线是官府受理告发,即使状子文书未正式送达有关部门,也属“已发”。[3]147应注意的是,这里犯罪未发的核心是指犯罪事实是由谁实施而言的,若是仅知受害事实而不知犯罪人是谁,并不能认为是犯罪已发。[1]324
自首是在犯罪未被发觉的情况下而先自首告所犯罪行,那么知人欲告而自首、亡叛而自首以及亡叛后归还本所应如何处置?这里的“亡叛”疏文上说是“逃亡之人”或“叛已上道者”即叛者已经出走上路的情况。依《唐律·名例》总第37条规定:“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处之。即亡叛者虽不自首,能归还本所者亦同。”这对防止犯罪人知人欲告而逃亡及分化瓦解亡叛的犯罪人具有积极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逃亡有两种情况:一是单纯的逃亡罪;二是犯罪之后因事发而逃亡。第二种情况下就同时存在本罪与逃亡罪,自首对本犯之罪不起作用,仅逃亡之罪可因自首而减二等处罚。
在自首的时间规定上,明清律沿袭唐律的规定,而清律又以条例的形式增加了“闻拿投首”的情形。乾隆三十八年所定条例规定:“凡闻拿投首之盗犯除律不准首及强盗自首有正文外,其余一切罪犯俱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闻拿投首是指犯罪已被官府发觉,并派人捕捉缉拿。因闻拿投首比之闻拿不投首是有差别的,故条例增此一条,规定减轻处罚,以体现区别情节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
自首的对象是指依法律规定自首应向谁进行。唐律规定接受自首的官府是所在地非军事的官府。《唐律·斗讼》总第353条规定:“诸犯罪欲陈首者,皆经所在官司申牒,军府之官不得辄受。其谋叛以上及盗者,听受,随送随近官司。”疏文解释说:“但非官府,此外曹局,并是所在官司。”
此外,作为变通规定,《唐律·名例》总第39条规定:“诸盗诈取人财物而于财主首露者,与经官司自首同。”即犯盗罪及诈骗罪的罪犯到财物主人那里去归还财物自首,同到官府自首一样有效,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对于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财物“悔过还主”,唐律则有不同规定:“其于余赃应坐之属,悔过还主者,听减本罪三等坐之。即财主应坐者,减罪亦准此。”即对本人只能减轻处罚,财主亦不能免罪,但自首效力及于财主,同样可以减罪,这较之于后来明律在这一问题的规定“受人枉法不枉法赃,悔过回付还主者与经官司同”更科学一些。明律律注指出:“枉法不枉法赃,征入官……”既属应征入官,就不应还于主,而且依照律例,出钱求人枉法,与受同科,财主亦有罪名,故于事主处首服不应与经官司同,“悔过回付还主”,更不应按自首免罪,此应属立法技术上的失误。
四、自首的内容
犯人自首后根据自首的内容不同,法律规定给予不同的对待。《唐律·名例》总第37条规定:“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问所劾之事而别言余罪者亦如之。”根据此规定,在犯有数罪的情况下,如轻罪已发而重罪未发而自首重罪的,则重罪可被认为是自首而免罪。疏文举例解释说,假如一人轻罪盗牛被发现,又自首了未被发现的私铸钱币的重罪,那么私铸钱币免罪,而盗牛照规定处罚。同样在犯有数罪的情况下,在推问已发觉的罪行时,又自首了其他未发现的犯罪的,则未发现的罪,按照自首免罪。
《唐律·名例》总第37条规定:“自首不实及不尽者,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律注称“自首赃数不尽者,止计不尽之数科之”。所谓不实,是指所犯之罪为重罪,而以轻罪自首;所谓不尽,是指犯赃十匹,自首犯赃五匹。“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即原犯重罪而以轻罪自首者,以重罪应处的刑罚减轻罪应处的刑罚,以所得的余刑处罪之。若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仍要处死刑的,可宽大减死一等处理。疏文解释其理由说:“为其自有悔心,罪状因首而发,故至死听减一等。”
明律中对“因问所劾之事而别言余事”的规定进一步设律注解释说:“谓因犯私盐事发,被问,不加考证,又自别言曾盗牛,又曾诈欺人财物,止种私盐之罪,余罪俱得免之类。”即别言余罪必须是在未加考证,即拷讯的情况下自动陈述余罪,所陈述的余罪才能按自首免罪。如果是在对其所劾之罪进行拷讯的情况下别言余罪,则不能免其陈述之罪。这使对“别言余事”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更加完善。
五、自首的特别情况
无论是唐律、明律,还是清律及条例都有关于自首的特别情况的规定,从而使法律关于自首的规定更加细致,自首制度适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唐律·名例》总第38条规定:“诸犯罪共亡,轻罪能捕重罪首,及轻重等获半数以上首者,皆除其罪。即因罪人以致罪,而罪人自死者,听减本罪二等;若罪人自首及遇恩原减者,亦准罪人原减法;其应加杖及赎者,各以杖赎例。”罪人共逃亡,是指罪人在犯罪后结伴逃亡,对社会威胁很大,故本条规定只要轻罪能够捕获重罪,轻重罪相等的能获半数以上而去自首的,皆可“除其罪”,借以对犯罪人实行分化瓦解。对“轻罪能捕重罪者”的律注指出:“重而应死,杀而首者,亦同。”重罪人犯应处死重罪的,轻罪人杀之而自首的,也免除其刑。对以上两种情形,律注又指出“常赦所不原者,依常法”,即如果所犯为常赦所不原的犯罪,则依常法处理,不适用本条规定。对因被株连而入罪的人,若本罪人死亡,则被株连人将减本罪二等;若本罪人自首及遇恩赦减刑的,被株连人适用本罪人原减法。
明律对于“犯罪共逃亡”的规定除沿用唐律规定外,又在“其轻罪囚能捕重罪囚,轻重罪相等但获一半以上首告者,皆免其罪”条加律注规定:“谓同犯罪事发,或各犯罪事发而共逃者,若流罪囚能捕死罪囚,徒罪囚能捕流罪囚首告。又如五人共犯罪在逃,内一人能捕三人首告之类,皆得免罪。若损伤人及奸者,仍依常法。”规定伤人及奸罪不适用本条自首免罪规定,而唐律仅规定“常赦所不原者,依常法”,由此可见,明律对适用“犯罪共逃亡”自首规定的条件要求更严。
明律在“犯罪自首”条规定:“强、窃盗若能捕获同伴经官司首者,亦各免其罪,又依常人一体给赏。”本条规定的情况同上述“犯罪共逃亡”条规定的情况差别在于,在本条中罪人是在所犯强、窃盗罪未被发前即捕同伴经官司首,这同“共逃亡”后再行投首性质是不同的,所以规定在“犯罪自首”条,不仅免其罪,而且与常人一体给赏。这是自首又有立功表现受赏政策的体现。强、窃盗罪是封建社会常见而又被视为极为严重的犯罪,在“犯罪自首”条增此规定正是加强对强、窃盗犯罪作斗争的表现。
《唐律·名例》还规定了过失犯罪自首的条文。在总第41条规定:“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原之。其断罪失错,已行决者,不用此律。其官文出稽程,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原之,主典不免;若主典自举,并减二等。”公事失错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渎职犯罪,属于过失犯罪。这类犯罪“自觉举”成立自首。觉察举发后,能有效地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一人自觉举,效力及于连坐之人。“公事失错”在没有发生危害结果时,自觉举可原其罪,但若危害结果已经发生则不能适用本条,即官员断罪出现失错后,按判决执行刑罪,若笞杖已决,徒流已配,自觉举后不能纠正,则“官司虽自觉举,不在免例”,仍以过失入人罪论处。延误官文书传送的官文书稽程罪也是由过失构成,自觉举能够防止或减少危害的结果,故应负连坐责任的有一人自觉举的,皆原其罪。专司官文书收发责任的官员“主典”则不能免除处罪。主典自觉举的,主典减二等处刑。主典自觉举的效力及于连坐的人,所以律条规定余人亦减二等。
明清律多沿用唐律规定,但清律在“犯罪自首”条增加“叛而自首者减二等坐之”,意思是“叛去本国”而能自首其罪行,减谋叛罪二等处刑。这是针对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而实行的以民族软化为目的的刑事政策。清顺治十八年条例规定:“被掳从贼,不忘故主,乘间归来者俱著免罪。”但在后来清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并未贯彻这一刑事政策。
关于监斩、绞重罪囚犯及遣军、徒、流罪人因变逸出而后投首的情况,清嘉庆五年改定的条例规定:“在监斩、绞重囚及遣军、流、徒人犯,如有因变逸出自行投与首者,除谋反、叛、逆者之犯,照原拟定罪,不准自首外,余照原犯罪名减一等发落。”“事发在逃”不在自首之律,但“因变逸出”并非有意脱逃,与“事发在逃”是不同的,故除了谋反、逆、叛之犯不准自首外,余犯自首减一等发落,以示区别对待。
如果人犯在配及中途脱逃的,后又自首或者其父、兄禀首拿获的,如何处理呢?清嘉庆六年改定的条例规定:“由死罪减为发遣的盗犯并以药迷人的窃盗在配及中途脱逃被获应即行正法者,如有畏罪投回并该犯父兄赴官禀首拿获,均准其从宽免死,仍发原配地方。若准免死一次之后复敢脱逃,虽自行投回及父兄再为首告,均不宽免。”
诱拐妇人子女脱离家庭的犯罪是封建社会常见而又多发的犯罪,对于此类犯罪的自首,根据清嘉庆三十五年刑部奏所定的条例规定,要根据犯罪的结果来确定是否成立自首。若被拐妇人子女被罪犯自为妻妾,或者典卖于人已被奸污的,则不准自首;若尚未被奸污或典卖于人,悔过自首后使之同家人团聚的,则减二等发落;如果被拐之人已经典卖于人,罪人自首之时尚无下落,则按律拟罪,监禁从到官司自首之日起三年限内仍无下落的,或者在限内拿获而已被奸污的,即按原拟罪名发落。原处绞监候的,入于秋审办理,拟流罪的,即确定向发配地发配。如果在限内拿获未被奸污的,则在原罪名上减一等发落。[1]338
此外,针对鸦片犯罪,清道光十九年所定条例规定:“凡鸦片案内人犯,如有事未发而自首及闻拿自首的,各按律例分别减罪、免罪。首后复犯加一等治罪,不准再首。”但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这一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六、不适用自首的情况
《唐律·名例》总第37条规定:“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即事发逃之,若越度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此规定亦为后世刑律所沿用并加以发展。归纳起来,我国古代刑律中规定不适用自首的犯罪情况有:
(1)“于人损伤”即伤害罪不适用自首免罪。伤害罪自己出首不减不免,因盗而伤人自首,盗罪可免,伤害罪仍不免。注文说:“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疏文说:“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若过失杀伤,仍从过失本法。”
(2)“于物不可备偿”即标的物为“不可偿”之物不适用自首。侵犯别人不可偿还而事后又无法追回和复原的物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免罪的规定。但法律同时还规定,罪犯能带原物自投官府的,是自首,可免罪。注文说:“本物见在首者,听从免法。”疏文说,所谓不可偿之物是指宝印、符节、制书、官文书、甲弩、旌旗、禁兵器之类私家既不合有之物。
(3)非法度关罪中“私度”“越度”罪不适用自首免罪。
(4)侵犯良人的奸罪不适用自首免罪。唐律律注规定:“奸,谓良人。”疏文说:“若奸良人者,自首不原。”未言奸贱奴,可知属于侵犯贱民的犯罪可自首。
(5)私习天文罪不适用自首免罪。私习天文之所以作为自首不原的犯罪,是因为古人认为天文星相之事涉于社稷祸福及帝王气数,习学此等技艺,必须严加控制,私自学习,即为大罪。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清律中即已删去此规定。
另外,在清朝乾隆年间,为杜绝强、窃盗犯与捕役勾结,串通舞弊,欺罔官司的弊端,乾隆五年改定的条例规定:“不论强、窃盗犯有捕役带同自首者,除本犯不准宽减外,仍将捕役严行审究,倘有教令及贿求故捏情弊,照捕役照受财故纵律治罪。”但这种不区分情况,捕役带同自首,概不宽减,是不符合律设“犯罪自首条”的本意的。[3]151
参考文献:
[1]宁汉林,魏克家.中国刑法简史[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
[2]陈鹏生.中国古代刑法三百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钱大群.唐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