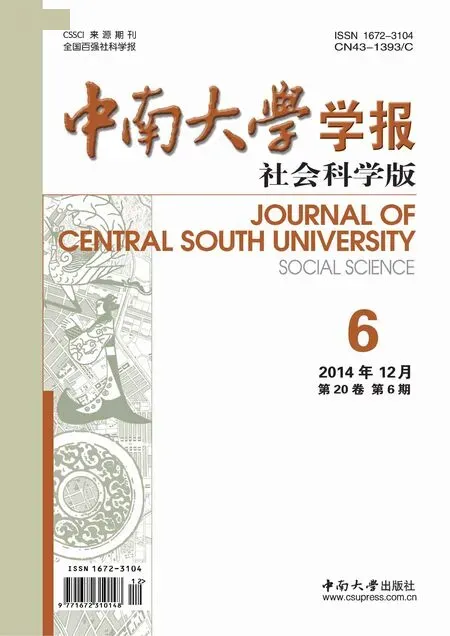从王世贞对扬雄赋论的“误”引看明中期的赋学复古
2014-01-22程维
程维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从王世贞对扬雄赋论的“误”引看明中期的赋学复古
程维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王世贞引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为“诗人之赋典以则”,明代以来都没有得到注意。实际上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改动,代表着王世贞与扬雄截然不同的辞赋观,也反映了明代中期辞赋领域的一场复古运动。而通过对“典”的独特的学术内涵的解析,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这场复古运动的本质:一方面是古典的经学精神对当代轻浮淫靡文风的反哺,一方面又是朝廷吏治精神在文学界的延伸。而在赋学领域,“典”与“丽”的交错有着清晰的演进历程,反映了两种文化精神的平衡和较量。
王世贞;辞赋观;丽则;典则;文化;复古
扬雄《法言》中有一段有名的赋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49)。考《法言》诸本,包括以清代秦恩复刻的北宋治平二年国子监刻晋李轨注本(《四部丛刊》有影印本)、清末聊城海源阁杨氏藏宋本李轨注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为代表的十三卷本,和以宋景祐三年刊宋咸《扬子法言注》本(无求备斋藏)、南宋景定元年建阳书坊刊《纂图互注扬子法言》本(无求备斋藏)为代表的十卷本①,均无异文。而作为汉兰台令史的班固和东晋秘书监谢灵运,援引此论时亦无疑义。可见此论当是扬雄本论无疑。后代论赋者继承、发扬此说极多,反对者亦有一些。然而不论继承或是反对,在援引此说时大都能忠实于扬雄之元典,只有王世贞除外。
王世贞《艺苑卮言》曰:“扬子云曰:‘诗人之赋典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2](6)改“丽”为“典”。查安徽省博物馆藏明刊《艺苑卮言》八卷本、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邹道元刊《艺苑卮言》十二卷本、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十七年武林樵云书舍新安程荣刊《新刻增补艺苑卮言》十六卷本,均作“典以则”。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万历刻本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说部亦作“诗人之赋典以则”。从明嘉靖四十四年《艺苑卮言》的初刻到万历五年《弇州四部稿》的定稿,王世贞在此期间的不断修改、增补、重刊都没有对“典以则”这一明显的“援引错误”有任何校正。王世贞乃藏书大家,胡应麟记其“小酉馆藏书凡三万卷”,藏有宋本精椠过三千卷,所以不可能不熟悉扬雄的原本。从其著作可知,他还是研究扬雄的专家,其著作中不少讨论扬雄及法言的文章②;同时,前人引用过扬雄此语的书籍,他也所藏所读甚多,比如他最为珍视的“斋中第一宝”宋本《两汉书》中,扬雄“丽以则”之论也赫然椠列。所以,以他对赋的了解和学问之细致深博,如果说他不清楚扬雄原句或者援引错误,实在说不通。从王世贞自己的数个刻本,到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曹溶《学海类编》、王启原《谈艺珠丛》等各个诗话本的引用,都对王世贞此句无任何异文。明万历十一年进士周子文曾刻印自辑明人论诗说曰《艺薮谈宗》,其“体裁各异,有论诗、说诗、谈诗、序诗、自序等;旨归则一,大致以王世贞为圭臬”[3](1802),引王氏语亦曰“诗人之赋典以则”[4],所以说也不太可能是后人的校勘失误。可见,王世贞对于“丽以则”的“误”引绝非偶然的校勘失误。既非失误,又有何内情呢?
一、“典以则”与“丽以则”
“丽以则”与“典以则”的区别,主要在“丽”与“典”的差异。
《说文》曰:“丽,旅行也。鹿之性,见食必旅行。”段玉裁注曰:“两相附则为丽,《易》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是其义也,丽则有耦可观。”[5](471)《小尔雅·广言》曰:“丽,两也。”[6](卷二)故“丽”之义由“两”引申为“附丽”,进而引申为“美好”。至汉代,“丽”的“美好”一义渐兴,司马相如《大人赋》:“滂濞泱轧丽以林离。”颜师古注曰“丽,靡也。”[7](1574)张衡《西京赋》:“纷瑰丽以奢靡。”薛综注曰:“丽,美也。”[8](71)《吕氏春秋·达郁》:“公姣且丽。”高诱注曰:“姣、丽,皆好貌也。”[9](565)以致扬雄将其引入文学批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文丽用寡,长卿也”[1](507),“少不得学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10](264),都是指文学作品辞章之美。
而“典”一词,《说文》曰:“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5](200)《玉篇·丌部》曰:“典,经籍也。”[11](3436)《尔雅·释言》曰:“典,经也。”[12](45)孔安国《尚书序》:“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颖达疏曰:“典,常也。”[13](卷一)《仪礼·士昏礼记》:“吾子顺先典。”郑玄注曰:“典,常也,法也。”[14](卷六)《周礼·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郑玄注曰:“典,则,亦法也。”[15](卷二)可见,“典”的涵义,大致由“典册”引申为“经籍”,又引申为“经典”,引申为“常”,引申为“法”与“则”。又由于“典”一直与前代的经典有关,故而又有“旧”义,《尚书·梓材》“后式典集”,蔡沈集传曰“典,旧典也”[16],《诗经·大雅·荡》“尚有典刑”,朱熹《集传》曰:“典刑,旧法也。”[17](203)。
因为“典”涵义的这种由来,使得它进入文学批评后,仍然带着“典范”“规则”“复古”这样的文化烙印,而且带有庄重的仪式感。“典”所批评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有一定的体裁倾向,王充的《论衡》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将“典”放入文学批评的:“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17](1187)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中说:“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19](158)二者都以“颂”为“典”形容的对象。而颂本为宗庙之正歌。刘勰谓:“容告神明谓之颂。”又曰:“颂主告神,义必纯美。”[21](157)颂多庄严,多净化,多赞美,而刘勰多以“典”作形容,可见“典”这一词语的美学偏向。其次,《文心雕龙·体性》说,“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21](505)《文心雕龙·定势》:“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21](530)又可见“典”作为批评术语,隐隐携有经学的痕迹。
汉代从先秦继承来的有两种文化系统,一种是以先秦理性精神为主宰的五经系统,一种是以楚汉浪漫精神为主宰的楚辞系统。徐复观先生说:“‘雅’是来自五经的系统,所以代表文章由内容之正大而来的品格之正大;‘丽’是来自楚辞系统,所以代表文章形相之美,即代表文学的艺术性。”[20](143)汉赋正存在于这两个系统的关系中,刘勰概括得很清楚:“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21](134)因此,“典”和“丽”的纠结和交错,正代表着辞赋领域里,五经系统与楚辞系统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排挤。
复次,“丽”与“典”古义有相通之处。《尚书·多方》云:“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清人孙星衍解释道:
丽者,丽于狱也。《周礼·小司寇职》:“以八辟丽邦法,附刑法”,注:“杜子春读丽为罗”,疏云:“罗则入罗网,当在刑书”。《吕刑》云“越兹丽刑”,又云“苗民匪察于狱之丽”是也[21](461)。
杨筠如《尚书覈诂》进一步论证《尚书》中的“丽”说:
丽,《吕刑》郑注:“施也”。按本书言“丽”,或为法则,或为刑律,皆不作“施”义,《吕刑》:“越兹丽刑并制”,又曰:“苗民匪察于狱之丽”,与本篇下文“慎厥丽乃劝”,“丽”,皆谓刑律也。其义与“刑”大同小别。《顾命》:“奠丽陈教”,与此文“不克开于民之丽”,“丽”皆谓法则也。《汉书·东方朔传》:“汉文帝之时,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丽”与“准”对文,亦取法则之义。以声类求之,疑即后世之律令。“丽”之得转为“律”,犹“骊”之得转为“黎”也。古律、黎同部,《广雅·释草》:“茟,藜也”,是其证。此文“民之丽”犹言“民之则”。《诗·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是其义也[22](256)。
“刑”亦可训作法则,《诗·大雅·文王》“仪刑文王”,毛传“刑,法也”[23](卷16),《礼记·礼运》“刑仁讲让”,郑玄注“刑,犹则也”[24](卷21)。如前所述,“典”亦有法则之义,在此意义上,“丽”与“典”相通。扬雄《甘泉赋》曰:“德兮丽万世。”《羽猎赋》赞叹“丽哉神圣”,几乎都可以换作“典”字。此其一也。
其二,“丽”由两鹿旅行引申出“附著”之义,一方面有“附丽”的内涵,一方面又包涵“显著”的意味。《易·离》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陆德明释曰:“丽,著也。”[25](卷三)《素问·五运行大论》曰:“五行丽地。”张志聪集注:“丽,章著也。”[26](333)“著”有“大”义③,因而先秦乃至汉代所用的“丽”字,几乎无有形容琐小之形。《诗·大雅·文王》:“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丽言数目之大;《庄子·徐无鬼》:“列于丽谯之间。”成玄英疏曰:“丽谯,高楼也。”[27](827)《荀子·富国篇》:“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唐代杨倞释“夸丽之声”为“夸大之声”[28](175)。汉代言“丽”,多与“宏”“巨”“崇”等联用。《史记·高祖本纪》云:“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汉书·扬雄传》曰:“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两都赋》曰:“世增饰以崇丽。”《鲁灵光殿赋》称“丰丽博敞”,《二京赋》谓“帝王之神丽”。曹胜高先生认为汉赋的“丽”当为“巨丽”,即“宏大之丽”“壮阔之丽”,是极有洞见的[29](61)。
如此,我们来理解扬雄的“丽则丽淫”说,就可能有更多一点的思考了。在礼乐传统较为强大的先秦两汉时期,“丽”与“礼”一样,都成文而有条理,都饰外而有所谕内;意指“美丽”,而往往隐含典范、繁富、宏大的内在指标。所以扬雄所谓的“丽”,绝非如南朝雕虫琢米般的小家子气,而是有着汉家气象的,即便“丽以淫”也是如此。由于礼乐传统的渗透,“丽”就内在地有着“度”的要求,一旦过度就沉迷其中,失去讽谏的本来意义。所以汉代虽然礼乐传统已经不处于支配地位,但在士人心中仍然有着强大的力量。扬雄的“丽则丽淫”的提出,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楚辞传统的冲击,但主要还是礼乐系统内部的调节,使得礼之为礼,丽之为丽,而不失其本心。
然而,随着礼乐的逐渐外化和形式化,“丽”的内在精神逐渐剥离,最终在六朝时定型和凝化[30](68-72),成为一个纯形式的范畴。对比“丽”与“典”这两个范畴的批评倾向,“丽”附着了“骈”“美好”等义项④;与此相比,“典”则偏于“经典”“法则”“复古”“庄重”“颂”的意味。
反观“丽则丽淫”与“典则丽淫”的区别,前者主要是“则”与“淫”的对立,而“丽”是共通处;后者则是“典则”与“丽淫”的整体对立。前者是以辞赋家的“丽”为前提,而以儒家的“合度”与“过度”为考察点;后者是直接将“典”与“丽”“则”与“淫”针锋相对,仿佛“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势不能两立一般。故而王世贞将扬雄《法言》这段赋论掐头去尾,单独拎出此句,又有意改动一字,看似蜻蜓点水,实则地动山摇。这是借古人之喉,发贞我之声。
二、“典”与赋学复古的学术与制度背景
那么王世贞的赋学观念究竟与“典以则”又有什么关联呢?试看下面几则材料:
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律赋尤为可厌。白乐天所载玄珠斩蛇,并韩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学究语[3](203)。
《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3](87)。
显然,王世贞在反对律赋的同时,对古赋是推崇备至的,他认为“屈氏之骚,骚之圣;长卿之赋,赋之圣也”[3](67)。这股赋体复古的思潮,从元代祝尧“祖骚宗汉”,到李梦阳的“唐无赋”说,到徐师曾的“其变愈下”说,由来已久。学者多有论述。许结先生认为:
明代前期,朝廷惩于元帝国对汉文化的摧残,实施两项重要的文化政策,一是明太祖诏复唐制(包括被元代削弱的考试制度),以追踪汉唐气象,振复汉族文化;二是太祖、成祖相继颁令以“四书”、“五经”为国子监功课,倡扬程朱理学。……出现了近百年文风以应制之敷演加理学之空疏为主流的僵沉局面。……其赋学主张祖骚宗汉,又恰以反思明初两项文化政策导致的敷演空疏赋风为逻辑起点[31](79)。
可见其赋学之复古,以空疏浮泛之风为对象。而“典”正对治此病。“敷演”的反面为“简古”,“空疏”的反面为“质实”,而“典”皆能涵括之。王通《中说》云:“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32](10)可知“典”与“冶”相对;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33](365)是知“典”与“质野”义相生;《中说》又云,“君子哉,思王也,其文也深。”[35](10)又可知“典”与“深”相联。而王世贞常将“典”“实”并用。《钟太傅荐季直表》曰:“其辞极典实。”[34](卷130)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四曰:“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实。”[35](卷84)又卷八十三曰:“就将中式文卷其纯正典实足为程序者,依制刊刻……以示重实学之意。”[40](卷83)深沉、质实,亦恰能对治空泛之文风。
赋风之轻巧浮泛盖自枚皋始。所谓“枚速马迟”者,枚皋过速而失却沉淀、考量,相如文迟故而典懿厚重。王世贞认为:“词赋非一时可就。《西京杂记》言相如为《子虚》、《上林》,游神荡思,百余日乃就,故也。梁王兔园诸公无一佳者,可知矣。”[3](86)所以“枚皋拙速,相如工迟”[39](卷151)。他称赞相如不遗余力,尊为“赋圣”,而评枚皋则曰:“枚皋轻冶媒贱。”不过“滑稽之流耳”[39](卷151),其扬马抑枚,正有以典重对治轻浮的意味。他批评复古派前贤李梦阳的文章说:“献吉之于文,复古功大矣,所以不能厌服众志者,何居?一曰操撰易,一曰下语杂,易则沉思者病之,杂则颛古者卑之。”[3](309)意亦相通。
“典”本指“五帝之书”“经籍”,故而文论中“典”之一词,常带有“根柢经义”的意味。《文心雕龙·定势》云:“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司懿。”[21](529)《体性》云:“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21](505)王世贞也认为“典”出于深于经术,其文《书三苏文后》曰:“吾尝谓子瞻非浅于经术者,其少之所以不典,则明允之余习。”《永城知县张君暨配赵孺人合塟志铭》曰:“生而敏悟,能受诸博士家言。己遂属为文,醇鬯有典则。”所以文能称“典”,必须有学问之根坻、经义之涵养,否则,即使是复古派,亦不能称为“典”。王世贞曾批评韩愈之复古是“欲求胜古而不能胜之”,究其原由,“盖公于六经之学甚浅,而于佛氏之书更卤莽,以故有所著释不能皆迎刃也。”[36](卷三)韩愈之大才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而明中期以后,学问经术渐被冷落。一则由于王学末流之带动。王世贞在《弇州史料后集》中描述道,“嘉隆之际,讲学者盛行于海内……读书不能句读,亦不多识字,而好意见,穿凿文义,为奇邪之间。”[37](后集卷35)他担忧地说:“今世之学者于书偶有所窥,则欲废先儒之说而出其上;于道未有所得,则已为排先儒之诣而闰其统。不学则借圣门之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愚之所甚忧者此也。”[39](卷144)六经皆是注我,得一意便废书,于是不学之风渐起。其二则由于科举之弊端。王廷相在任鲁、蜀提督学政时,针对当时之文风,而作策问曰:“夫自科举以来,在上者以文取士,而士之为学者,一切为文辞之工,以应上之求;虽日教以《六经》、孔孟道义之实,然不工于文,则无进身之阶,而士之习固自若也。”[38](卷36)进而导致“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39](968),顾炎武甚而认为“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45](1044)。无经术之根柢,只能骋辞竞巧,因而浮而不实;只读时文,便无有创见,因而模拟成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载,嘉靖十一年时,“礼部尚书夏言上疏请正文体,诸刻意骋词、浮诞磔裂,坏文体者摈不得取。”[40](卷82)正是针对此现象而论。万历十六年沈鲤上疏指出:“近年以来科场文字渐趋奇诡。”“以清虚不实讲为妙,以艰涩不可读为工。用眼底不常见之字谓为博闻,道人间不必有之言谓为玄解。”而“及一一细与鲜明,则语语都无深识”[40](卷82)。
此种竞巧骋辞、浮泛不实的时文之风,也影响了当时的赋风。时文与赋本为近亲,从科考继承上讲,元代考古赋,而明代继之以古文;从文章体制上讲,“制义源于排律”[40](卷三),清邱士超《唐人赋钞·总论》说:“应制之体以律赋为正宗……有明制义,此其滥觞。”赋与时文有此关系,因而其恶习极易相互侵染。万历进士袁黄《群书备考》论明代赋曰:“后世诸君子,爱椟忘珠,极意镂画,无疾而呻,人为掩耳。晚近尤甚,字取骇目故必艰,文取斗靡故必冗。险韵在几,类书充栋,一经翻问,可就万言,宁须厕溷置笔硕哉!”赋家斗靡夸巧,无病呻吟,与时文无异。所以他强调赋体应当尽量避免为时文所影响:“盖赋体弘奥,非可取帖括铅椠语。”[41](前编卷11)赋家摹拟之风,古来已有,此时更与科场剽袭之习交叉感染。万历间解元陈山毓抱怨道,“胡为后世辞人,疲精赋颂,辄乃前者造规,继者蹈矩,互相规仿,无复新裁。”[42](卷五)可知明赋积习之重。王世贞为文坛之魁首,论赋主“典”,正可矫正此风。
应该指出的是,王世贞对辞赋须“典”的引导,与当时文人的整体赋风相左,却与朝廷所提倡的文风相一致。明初大学士丘濬认为:“取士刊文,必以明经合传为主。所传诸程墨,凡理学题必平正通达,事实题必典则浑厚。”任国子监祭酒时,他“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43](4808)。嘉靖十一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谓:
近年以来,文章日趋卑陋……而纯正博雅之体,温柔昌大之气,荡然无存……乃昨岁天下进呈录文,类皆猥鄙不经,气格卑弱,背戾经旨,决裂程式。其刻意以为高者,则浮诞谲诡而不协于中;骋词以为辩者,则支离磔裂而不根于理。文体大坏,比昔尤甚。今年望敕考官,务取醇正典雅、温柔敦厚之文,一切驾虚翼伪、钩棘轧茁之习,痛加黜落,庶几士知所向,文体可变[44](3176-3178)。
万历时,大学士张居正希望力矫科举文风,《明会典》载:
万历元年奏准,试录序文,必典实简古,明白正大,俱若成化弘治年间文体,督抚等官,不许妄加称奖,以蹈浮靡之弊[45](449)。
可见朝廷所推举的科举文风,正是典实醇正。而在奏议疏策方面,朝廷也要求力改浮缛习气,令行典则简古之风。洪武时,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一万七千言之疏论而被杖责,朝廷因而制定“建言格式”“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嘉靖十五年,御史胡世宁上书声讨奏议之空泛繁缛:“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数纸,虽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读者。”世宗接受其建议,要求“诸司奏章,不许繁词,第宜明白,开陈要旨,庶易省阅”[46](卷110)。隆庆年间,比王世贞大14岁的大学士高拱上书称:“近来章奏,日趋浮泛,铺缀连读,徒烦至览。”穆宗也加以采纳,遂令“所司通行严禁,违者部院及科沉劾治之”[47](卷18)。高拱还曾提出对翰林教育的要求:
其一在辅政,则教之以国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详,古今治乱安危必求其故……于是乎教之以明解经书,发挥义理,以备进讲;教之以训迪播告之辞,简重庄严之体,以备代言。[48](413)
朝廷是吏治与法制的代表,他们为了行政的效率,在科举选官上以经义取士,不用诗赋;在公文上讲求简古明白,反对浮词丽藻;在学术上崇尚实学,摒黜虚学。这是明代朝廷的整体倾向。然而士大夫们未必买账,不然这种法令就不会一直颁布,由此也可知其效果未佳。而文人们尤其是野文人的文学性的创作,则更加不在朝廷的操控范围之内。王世贞曰:“今士子之为文……文体则耻循矩矱,喜创新格。以清虚不实讲为妙,以艰涩不可读为工,用眼底不常见之字谓为博闻,道人间不必有之言谓为玄觧。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题不必合。”[40](卷84)隆庆进士于慎行说:“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奇,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49](卷八)清代顾炎武说:“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41](1061)是知是时文风之修正革新,尚待文学内部之催化。王世贞所提倡的“典”的文学风格,正起到了这种内部催化剂的作用。
由此可见,“典”这样一个文学符号,一方面是古典的经学精神对当代轻浮淫靡文风的反哺式革新,一方面又是朝廷吏治在文学界的延伸。一方面代表了以礼乐精神为内核的古典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一方面反映了以法制精神为根本的朝廷系统对文学的渗透。韩非说:“喜淫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50](267)可见法家从一开始就反感淫丽戕害了办事的效率。明代统治者追随韩非的美学,不断要求为文典雅简洁,以求提高行政效率。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世贞的“典则丽淫”说,隐喻着法制系统借古典经学对现存礼乐残余的整体批判。在汉代扬雄的赋论中,是否适应讽谏的功能,是评判辞赋“丽则”还是“丽淫”的重要指标;而王世贞以带有歌颂传统的“典”置换了“丽”,就一方面确认了辞赋歌颂皇权的合理性,一方面成功地将“淫”全部转嫁给辞藻的过分铺张。实际上是冷冻了辞赋讽谏皇权的功能。可以说,王世贞的“典则丽淫”说大体上引领文学走向一条正统的道路,同时又侵蚀了文学的某些面向,压榨了文学的空间。
三、典则说进入辞赋的历史进程
“典”“则”合用起于汉代。扬雄《逐贫赋》:“昔我乃祖,宣其明徳。克佐帝尧,誓为典则。”蔡邕《文烈侯杨公碑》:“纠合朋徒,稽诸典则。”[51]三国时期管辂的《管氏指蒙》有“学不达于师资,业不通于典则”[52](卷上),萧子显《南齐书·东昏侯》赞曰:“乃隳典则,乃弃彝伦。”[53](110)开始皆作名词用,意为“经典”,盖指五经。
而“典则”参与诗文评论,大概始于唐朝。魏征《隋书·文学传》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54](1730)此处“典则”与“新巧”“淫放”相对抗,而与“雅道”相牵连。唐刘肃《大唐新语》:“韩休之文有如太羮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55](130)这是“典则”较早使用于文学批评的例子。
到宋代开始,已经大量使用“典则”评论诗文,而到了明代,“典则”已经成为诗文评的“熟语”。 王九思《康德瞻集序》云:“乃其骚赋诗歌,典则不诡。”[56](卷八)张璧《资政大夫户部尚书致仕赠太子少保谥庄简邹公文盛神道碑》:“为文典则庄重。”[57](卷29)陈鸣鹤《东越文苑》:“慈为文丰赡典则。”[58](卷六)陈懿典《周声仲经书义序》:“晚近之体诡,能不诡而典则者为杰。”[59](卷三)而王世贞也是习用此语。其《翰林院侍读学士鸿山华公寿藏记》文曰:“公为诗故多应制赠送诸什,以宏丽典则称。”[39](卷77)《答陆汝陈》文曰:“陆之叙事,颇亦典则。”[39](卷128)《艺苑巵言》卷七:“二子文实淸雅典则,非它琐琐比也。”[39](卷150)《永城知县张君暨配赵孺人合葬志铭》:“遂属为文,醇鬯有典则。”[63](卷130)数量极多。
相对“典则”来说,“典以则”的使用在明代以前极为稀少,入明之后,便渐有兴貌。宋濂《林伯恭诗集序》:“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61](卷三十三)徐伯龄《叶龙溪诗》:“所谓雅人之词典以则欤?”[62](卷八)皇甫汸《题吴纯叔坚白藏稿》:“其抒思优以俊,其援事典以则。”[63](卷39)
“典则”和“典以则”成为评论诗文的习用之语,使得它带有一股约定俗成的力量,而王世贞在此时置换“丽以则”,更有可能性与合理性。
而实际上,在文义层面,“典以则”一直悄悄地渗入扬雄的“丽则丽淫”说。《西京杂记》曰:“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所谓“诗人之作”,即扬雄 “诗人之赋”, 而此处以“典而丽”代“丽以则”,初显“典则”渗入“丽则丽淫”说的迹象。其后,唐令狐德棻《周书》曰:
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64](744)
令狐德棻虽然引用扬雄本句,然而批评之对象已变了。其所言体之淫放、词之轻险,皆非扬雄“丽以则”所可矫正,而皆与“典”相抗。“典”有规范义,正对治体之淫放;庄重义,正对治词之轻险。宋代陈旸《乐书·乐图论》云:
古人之于乐,盖不可以为伪。故志于色者,其歌诗淫以丽,其音咏薄以思,其舞节促以烦,其色婉而冶;志于德者,其歌诗典以则,其音咏和以畅,其舞节舒以缓,其色温而雅。[65](卷180)
此则虽非言赋,但已明确将“典以则”与“淫以丽”相对照,并归于儒家“德”“色”之辨,我们从中也可知“典则”和“丽淫”之间的分野,不只是度的问题,而是存在极大的鸿沟。宋史浩《及第谢秦内翰启》云:
探义理于圣人之言、贤人之言,辨典则于诗人之赋、词人之赋[66](卷二十六)。
判别诗人之赋、词人之赋的标准本是“丽则”,而史浩易之为“典则”。而元祝尧《古赋辨体·两汉体下》曰:
昌黎曰:“诗正而葩。”子云曰:“诗人之赋丽以则。”愚谓:先正而后葩,此诗之所以为诗;先丽而后则,此赋之所以为赋[67](卷四)。
正,典也。葩,丽也。诗人先典而后丽,辞人先丽而后则。前者以“典”为主,后者以“丽”为先。祝尧此论实际上将诗人、辞人的“则”与“淫”的分别,转嫁为“典”与“丽”的分别。
由此可见,王世贞的“典则丽淫”之说不是天外来客,而是有所承传和接受的。自王氏以后,“典则”逐渐成为赋学领域的熟语和赋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孙梅《四六丛话·赋话》批评唐宋律赋的“祗乖典则”[68](69),而李调元《赋话》赞扬了李子卿《水萤赋》“字字典则,精妙无双”[69](卷四)。清代周日涟在《本朝馆阁赋后集》序中评价王褒《洞箫》、杜甫《大礼》等赋作时说:“靡不本相如之旨,纂组成文;参子云之言,典则为上。”[70](卷首)则完全承袭了王氏对扬雄赋论的概括。
王世贞的“典则”观是明代中期赋学复古中的一环。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代的赋学复古不但有着学术和政治的现实背景,而且与文学和文化的传统演进也息息相关。同时,我们也能了解到,复古的形式是非常多样的,有时候虽然只是看似微不足道的语词的调整,也蕴藏着两种文学和文化态度的平衡和较量,也凝聚着现实的计较和流传着传统的血脉。
注释:
① 关于《法言》这两种版本系统的区别,请参见张兵《扬雄〈法言〉的版本与流传》,《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
②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二有《读扬子》,卷一百二十九有《刻扬雄太仆箴跋》,《读书后》卷二有《书扬雄传后》,又有诗曰“十载扬雄赋,诸生伏氏书”,“十载扬雄赋已奇”,“竒人纵可敌扬雄才”等等。
③ 《礼记-中庸》曰“形则著”,郑玄注曰:“著,形之大者”;《说文解字》:“倬,著大也。”
④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丽即骈也,故凡对偶谓之骈丽。”
[1] 汪荣宝撰, 陈仲夫点校. 法言义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 王世贞著, 罗仲鼎校注. 艺苑卮言校注[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2.
[3]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4] 周子文. 艺薮谈宗[M]. 台北: 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影印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万历二十五年梁溪周氏自刻本卷四.
[5]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6] 胡承珙. 小尔雅义证[M]. 清道光七年求是堂刻本.
[7] 班固撰, 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8] 萧统编, 李善注.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9] 许维遹集释. 《吕氏春秋》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0] 张震泽校注. 扬雄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11] 胡吉宣校释.《玉篇》校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2] 郭璞注, 邢昺疏编, 黄侃句读. 尔雅注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13] 孔安国. 尚书注疏[M].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14] 郑玄. 仪礼疏[M].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15] 郑玄. 周礼疏[M].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16] 陈泰交. 尚书注考[M]. 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17] 朱熹. 诗集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8] 黄晖校释. 论衡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9] 范文澜注.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20] 徐复观. 中国文学精神[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21] 孙星衍撰. 陈抗, 盛冬玲点校. 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2] 杨筠如核诂. 尚书核诂[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9.
[23] 孔颖达. 毛诗注疏[M].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24] 郑玄. 礼记注疏[M].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25] 王弼, 韩康伯注, 孔颖达疏. 周易注疏[M].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26] 张志聪集注. 黄帝内经集注[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
[27] 郭庆藩集释.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28]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9] 曹胜高. 汉赋“丽赡之美”与礼的外化[J]. 天中学刊2003(3): 61.
[30] 吴功正. “丽”谈——六朝美学的范畴概念及其演变[J]. 南京社会科学1991(5): 68-72.
[31] 许结. 明代“唐无赋”说辨析——兼论明赋创作与复古思潮[J].文学遗产, 1999(4): 79.
[32] 王通著, 阮逸注. 中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3] 王先谦编. 骈文类纂[M].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34] 王世贞. 弇州四部稿[M]. 明万历刻本.
[35]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 王世贞. 读书后[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王世贞. 弇州史料[M]. 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38] 王廷相. 王氏家藏集[M]. 明嘉靖丙申家刻本.
[39] 顾炎武著, 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40] 李调元. 雨村赋话[M]. 清乾隆刻嘉庆重校印函海本.
[41] 王之绩. 铁立文起[M]. 清康熙刻本.
[42] 陈山毓. 陈靖质居士文集[M]. 明天启刻本.
[43]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4] 明世宗实录[M].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1962.
[45] 申时行. 明会典[M]. 中华书局,1989.
[46] 徐学聚. 国朝典汇[M]. 明天启四年徐与参刻本.
[47] 余继登. 典故纪闻[M]. 清畿辅丛书本.
[48] 高拱. 本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49] 于慎行. 榖山笔尘[M]. 明万历于纬刻本.
[50] 陈奇猷校注. 韩非子集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51] 蔡邕. 蔡中郎集[M]. 四部丛刊景明活字本.
[52] 管辂. 管氏指蒙[M]. 明刻本.
[53]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54]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55] 刘肃撰, 许德楠, 李鼎霞点校. 大唐新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56] 王九思. 渼陂集[M]. 明嘉靖刻崇祯补修本.
[57] 焦竑. 国朝献征録[M]. 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橒曼山馆刻本.
[58] 陈鸣鹤. 东越文苑[M].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59] 陈懿典. 陈学士先生初集[M]. 明万历刻本.
[60] 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续稿[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 宋濂. 宋学士文集[M]. 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62] 徐伯龄. 蟫精隽[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 皇甫汸. 皇甫司勋集[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4] 令狐德棻等. 周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65] 陈旸. 乐书[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 史浩. 鄮峰真隐漫录[M]. 清乾隆刻本.
[67] 祝尧. 古赋辨体[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8] 孙梅. 四六丛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69] 李调元. 赋话[M]. 清函海本.
[70] 程奂若, 周漪塘编. 本朝馆阁赋后集[M]. 乾隆三年困学斋本.
Thoughts of Wang Shizhen’s intentional error quotation “Fu in the Book of Odes are elegant and orthodox”
CHENG Wei
(School of Liberal and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Wang shizhen changed Yang Xiong’s statement “Fu in the Book of Odes are beautiful and orthodox” into “Fu in the Book of Odes are elegant and orthodox”, which didn’t get enough attention since the Ming dynasty. Actually this seemingly casual changes, represents Wang Shizhen and Yang Xiong different views of Fu, it also reflects a retro movement in the field of Fu in mid-M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academic connotation of “Dian”, we can know more clearly the nature of the retro movement. On the one hand it is the classical spiri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frivolous decay style of feedback. On the one hand, it is an extension of the spirit of government bureaucracy in the literary world. And in the field of Fu, the crisscross of “Dian” and “Li” has a clear evolution course, reflecting the balance of two kinds of cultural spirit and fight.
Wang Shizhen; view of Fu; elegant and orthodox; Beautiful and orthodox; culture; retro
I206.2
A
1672-3104(2014)06-0284-07
[编辑: 胡兴华]
2014-04-27;
2014-08-2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1340);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历代赋汇》校点(14CZW072)
程维(1984-),男,安微桐城人,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中国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