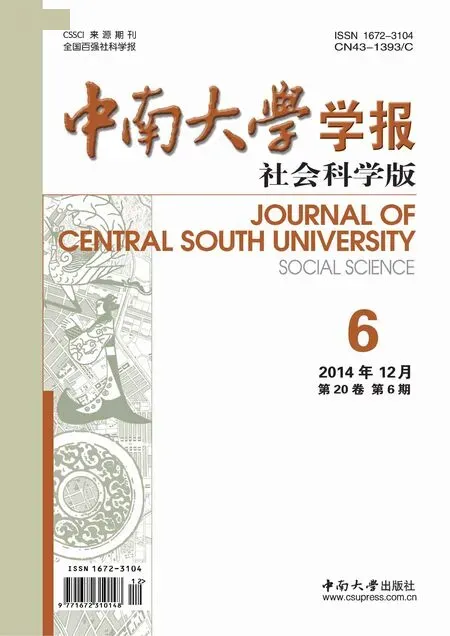民初大理院刑事司法创制探颐
2014-01-22施玮
施玮
(巢湖学院经管法学院,安徽合肥, 238000)
民初大理院刑事司法创制探颐
施玮
(巢湖学院经管法学院,安徽合肥, 238000)
北洋政府时期,刑事审判法律相对稳定然而并不完备,导致刑事审判法律渊源的多元化。为了有效适用法律,维护刑事审判的公正,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大理院通过司法创制的形式确立了大量判例和解释例,成为这一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重要法律依据。这种体现司法权本质的司法创制具有拘束个案的效力,并起到统一法律的作用,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大理院;刑事法;司法创制;判决例;解释例
北洋政府时期,政治局势混沌、社会环境动荡,特别是司法审判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之间、法律调整与社会生活之间呈现出纷繁复杂、参差交错的局面。虽然期间各界政府先后宣布暂时有条件地援用既有法律,也制订了一些单行法规,但面对转型中的社会,现行法规已明显不能适应审判机关的需要,审判活动中甚至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刑事判案依据既有国家的制定法,也有部分尚未生效的法律草案,甚至西方国家流行的近代法律理论、法律原则、外国法律等也成为法院审判案件的依据。为改变这种状况,维护刑事审判的公正,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大理院运用其法律解释权,通过司法创制的形式确立了大量判例和解释例,并成为这一时期各级刑事审判机关审判案件的重要法律渊源。就当时而言,司法创制因其具备特定的要素、体例以及典型性,具有拘束各级法院裁判的效力。本文主要关注大理院刑事判例与解释例的运行情形。
一、大理院刑事司法创制的法理基础
依据法理,刑事司法创制的主体应该有法律授权,否则就是违反法律程序,也不会产生法律效力。通过检视史料,我们发现这种授权可以追溯至清末。
《大理院审判编制法》第19条规定“大理院之审判,于律例紧要处表示意见,得拘束全国审判衙门”,但有“按之中国情形,须请旨办理”之补充规定。[1](202)即大理院所作相关法律解释必须经清政府认可,才能够具有法律拘束力。随后颁布的《法院编制法》第35条规定“大理院卿有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但不得指挥审判官所掌理各案件之审判”[2](218),明确赋予大理院解释法律的权利。该条也是民国时期“统一解释法令”制度的渊源。
清帝逊位,民国建立。民国元年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其中并没有一般法律解释权的规定。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通令暂行援用前清法令,其中包括《法院编制法》,后将大理院正卿改为大理院院长。大理院为北洋政府时期最高审判机关,继续拥有统一解释法令的权利。在之后公布的《参政院组织法》中,将中华民国约法的解释工作交由参政院,不过一般法律的统一解释之权,仍是由大理院掌理。北洋政府虽然历经张勋复辟、曹锟贿选以及军阀割据等各时期,统一解释法令一直由大理院实施,直至民国16年最高法院成立。其时法制初创,“法有不备,或于时不适,则藉解释,以救济之。其无可据者,则审度国情,参以学理,著为先例”[2](210),判例或者解释的创制应运而生。
由大理院统一解释法律,一方面是由于民国法制变革不久,许多法律尚未制定,另一方面是各级法院在刑事案件审理中对已颁行法律有诸多疑义,而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拥有法律的统一解释权,其所作的解释或判决,对于各级法院裁判均具有约束力,在具体法律适用上也有相当的助益。民国学者也持有相同观点:“法院所为裁判所造成的成例,是法律的实质的渊源之一种,或为最高法院的裁判有一般的拘束力,或为通常法院的裁判因反复施行而发生法的效力。”[3](77)意指司法创制经反复援引,自然就可以产生“法的确信”,因而产生法律效力。司法创制除可以补充现行法律的不足,也可以统一法令见解,达到维持法律秩序稳定性的作用。当然,司法创制也可以供民国立法机关在制定、修改或废除法律时的参考,由此意义言之,其成为法律的间接法源也是顺理成章。
二、大理院判例运作解读
北洋政府时期是西式法律理念与我国固有法律传统碰撞较为剧烈的时期。在这个阶段,西式法院体系已经筹建,刑事审判法规正在完善,以刑事裁判的角度观察,刑事司法的重点在于如何使完全崭新的西式审判制度和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调和,因此,这一时期成为判例发展的重要时期。
1919年12月,在大理院长姚震主持之下,大理院出版了该院的第一部判例要旨汇编《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后被称为正集)。其例言谓:“本汇览系节取大理院自民国元年改组至七年十二月底之裁判文先例,经曾与评议之推事再三审定,认为确符原意,凡援引院判先例者,除将来续出新例未经刊印者外,应专以此书为准。至司法讲习所旧设编辑处刊行之二年度判例,业经分别编入此书,幸留意焉。”[4](848)
1924年12月出版了《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续集》,“本汇览续编系赓续前编,就大理院民国八年一月至十二年十二月之裁判成例,节取编辑,本编所载,有与前编抵触者,无论有无变更先例字样,概以本编为准”[4](856-857)。正续两集共收入判例“计三千九百九十一条”。判例要旨汇览一经公布,因其简明且易于检索,为当时地方各级审判机构推事们所青睐,奉为圭臬,“承法之士无不人手一编,每遇诉争,则律师与审判者皆不约而同,而以‘查大理院某年某字某号判决如何如何’为争讼定谳之根据”[5](36)。
(一)大理院判例的界定
首先要明确的是,本文所研究的大理院判例特指大理院分别于1919年以及1924年出版的《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正集和续集中的判例,并不是所有大理院的判决都是本文研究的判例。汇编所选之判例,系属大理院裁判当中为了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具有创新价值的裁判。依据1918年8月7日大理院颁行的《大理院编辑规则》,判例“编辑处由院长指定现任或聘任曾任本院推事人员担任编辑判例汇览或解释文件汇览”。并且将“判例汇览、解释文件汇览,大别为二类:一民事二刑事,民刑事之分类,除依现行法规编定目次外,得参酌前清修订法律馆各草案及本院判例所认许之习惯法,但先实体法后程序法,先普通法后特别法”,“判决录、解释文件录,刊载裁判或解释文件全文,但得以该各汇览已摘取要旨之文为限”[6](1834-1835)。由此可知,本研究之大理院判例,均是由庭长或推事经过审慎筛选加以取舍,摘录其要旨,并送交院长检阅,所选取的皆为具有阐明法律蕴藏之真意,又具有抽象规范意义见解的代表性大理院判决。
判例的汇编方式是,将不同时间段的同类判例,依照现行各类成文法的目次以及条文序号进行编排整理,以法为类,以条为序,即首先区分民刑事两大类,又以本类法律条文的先后为顺序排列。这就使得几千个判例要旨仍然处于原有成文法典的编纂体例下,纲目井然,繁而不乱。一方面体现了判例完全以成文法为依托,对于成文法仅具有辅助性质;另一方面法官裁判案件时,也可以非常方便地查找到适用于当前案件的判例,大大减轻了法官查找判例的工作量,有利于及时判案,迅速解决纠纷。同时,以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的判决为汇编的编辑方式,使得被收入汇览中的判例具有事实上的权威性与拘束力。
(二)大理院判例的解读
近代中国法制引进西方司法理念,其价值理念与中国固有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与当时社会现实也难以契合。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既不能无视社会的现实机械地适用法律,又不能违背法律以迎合社会现实。大理院的判例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创制法律的作用,其对于缓和两者之间的冲突,弥补法律空缺,调整社会大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应该说效果比较显著。那么大理院是如何通过判例来对成文法进行解释和补充,以其所特有的阐释性填补成文法的“漏洞”,弥补法条的欠缺?以下我们通过几则判例进行阐释。
1. 民国四年上字第1005号:和奸寡妇在补充条例颁行前者不论罪
查刑律总则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凡犯罪在以前法律不以为罪者,虽未经确定裁判而认为有罪之律颁行,仍难援用新律论罪,被告人和奸寡妇,在刑律补充条例颁行以前,既无论罪明文,该条例又应适用刑律总则,为刑律总则第九条所明定,则被告人等和奸行为按之该条例现虽有罪,而依刑律第一条第二项仍难论罪。[4](394)
《暂行新刑律》第1条规定:“本律于凡犯罪在颁行以后者适用之。其颁行之前未经确定审判者,亦同;但颁行以前之法律不以为罪者,不在此限。”[7](1)这是关于刑法溯及力问题的规定。新刑律在溯及力上采从新兼从轻原则,但其“从轻”的情形中不包括新旧刑律都规定是犯罪,旧律处罚为轻用旧律的内容。即该律在溯及力上采从新为原则,从旧为例外的规定方式。但是该规定过于原则概括,不易被审判人员掌握,加之新型法官对于新式审判又缺乏经验,对于新的法律条文在内涵理解方面尤嫌不足,有关成文法的原则和一些条文的含义也就含混不清。大理院通过判例认为,案中寡妇和奸行为发生在刑律补充条例颁行前,依照当时法律并无明文确定其有罪,而新颁布法律虽然认定该和奸行为有罪,但是依照刑律总则,颁行以前的法律认为不是犯罪的行为,不适用新刑律,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不能认定其和奸行为为有罪。大理院通过这样的解释使得裁判官对于法律条文有了明白、清晰的感性认识,改变了法律条文过于抽象而难以把握的状况。
2. 民国二年上字第117号:刑律所谓故意为犯人对于犯罪事实有一般认识预见之谓
查刑律所谓故意者,为犯人对于犯罪事实有一般认识预见之谓,以铁锆殴击谓为无杀人之认识则可,不能谓为无伤害人之认识。[4](396)
《暂行新刑律》第13条第1款规定:“非故意之行为,不为罪;但应论以过失者,不在此限。”实际上确立了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之近代刑罚基本理念,费解的是其总则并未给故意下定义,这就给民国初期的司法官如何判断“故意”出了一个难题。同样大理院承担起了以案例来进行阐释刑法原则与精神的责任,通过此种方式确定了故意的适用范围,做到法律适用的统一,消除了出入人罪、同罪不同罚的隐患。判例中故意的认定是以达到对于犯罪事实有一般认识预见即可,也就是故意的成立仅需要认识因素,不需要意志因素,也就是认识主义[8](82-83),即故意。意志因素是指,在认识到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后,对实现这种客观事实的决意。如本案,用铁锆击打他人,以一般人之见,肯定预见到会给他人造成伤害的事实,而没有杀人的决意,这种心理状态就成立故意。在以后的几年里,大理院又陆续就涉及故意判断定罪的案件作出解释[9](400, 510-511)。该解释同样采取认识主义,使得审判官员对“故意”这种专门法律术语有了直接、清晰的感性认识,更加准确理解相关法律条文的本旨,标志着民国时期刑事法学理论的逐步成熟。
3. 民国四年上字第176号:骚扰罪以妨害一地方安宁秩序为成立要件
按骚扰罪之性质,系出于内乱罪以外之目的而为多众之集合,以行其强暴胁迫,即所谓暴动是也。故其程度必有足以危害一地方安宁秩序,始为本罪之成立。观本罪之分别首魁、执重要事务者种种阶级而所科刑罚亦复较重,立法之意至易明了。[4](469)
《暂行新刑律》第九章第164条规定骚扰罪为:“聚众意图为强暴胁迫,已受当该官员解散之命令,仍不解散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附和随行仅止助势者处拘役或五十元以下罚金。”那么依据本条如何确定骚扰罪,其与内乱罪、妨害公务罪如何区分,程度怎么掌握,也就是应该怎么定罪?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既然为聚众,应该有首犯,首犯如何确认?鉴于本罪罪名较抽象概括,缺乏细致的认定标准,大理院通过上述判例具体地明确提出骚扰罪成立必须具备的要件,并将其与其他犯罪行为区别开来,同时也通过判例就如何认定首要分子进行了说明,从而避免由于认定标准不明确,导致对同一类不同程度的犯罪处罚量刑有失公平的情况发生。
4. 民国三年上字第2号:民刑事诉讼不得混合审判
民刑事诉讼程序现行法上已显然划分,除私诉程序外,不许混合审判[4](818)。
中国传统审判制度的最大弊端之一是民刑不分,使用刑事审判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造成滥施刑罚的现象,既增加了审判官审判工作的负担,无形中也加大了人力、物力等审判资源的投入。近代中国的司法改革使得我国由重刑主义的传统中走出来,重新规划国家的司法审判体系,民事诉讼作为一种独立诉讼体系从原来的刑事法律体系中被分离出来,正式确立了民刑分立的原则,强调诉讼审判应该区分为分民事刑事诉讼。民国初期,法制初变,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极为复杂,民刑事诉讼案件繁多,诉讼中不可避免存在着大量的疑难问题。其中基层各级法庭常因民刑事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产生疑惑,于是请求大理院裁决。为了解决疑问避免人为的诉讼纷繁,大理院以判例的形式,对已经设立地方审判厅的地区依照上述判例办理,而对于没有设置地方审判厅的县域,发布民国三年上字第170号判例,就相关诉讼程序做了明确的阐述和必要的指导。判例谓:
未设审判厅各县地方刑事采用私人诉追主义,故人民递状欲辩别其应属民事抑属刑事,当审察其请求之目的若何而后可予断定,至其请求者若系办罪,固不必引举法条开示罪名,即应归刑事,依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则审判,其人民对于县判声明上诉者,若系被告自可依法为刑事受理,若系原告诉人,仍应呈由该管高等检察厅依法办理。而要不许以刑事被告之上诉误作为民事依民事法则受理,更不能因被告之误认诉讼关系而即为转移也[4](818-819)。
可以看出,如果在审之民事诉讼中,该案当事人涉嫌犯罪嫌疑,而且其犯罪嫌疑已在侦查中,则应该立即中止该诉讼程序[4](643)。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民刑事诉讼不再混合进行,同时也可以培养审判官吏的民刑事分立意识,对当时社会大众的法制理念与意识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北洋政府时期正值民国初年,刑事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相关刑事法典未及公布,各级审判机关断案依据未足,因而大理院参照暂行新刑律以及刑事诉讼等法,审时度势,融合西方法理,通过判决以及判例弥补了法律欠缺,并创制出一些新的法律规范。通过上述几则判例的分析,我们注意到大理院不但对实体法律规范予以创制,对于程序法律规范有时也以判例进行创制,似乎说明大理院“以司法之名行立法之实”。但正如前文讨论的,北洋政府时期的判例,法律层面没有明确的拘束力,但在实践中确实有事实的拘束力。作为法官们的创作,虽然没有绝对的法律效力,而却依附律文而存在,对律文起到解释补充的作用,但也绝不同于中国传统判例制度的“以例破律”“因例废律”,而是深深打上大陆法系判例制度的印迹。
三、大理院解释例运作解读
大理院自民国2年1月15号统字第1号起至民国16年10月22日第2012号止,十多年的时间共制作了两千多件解释,均依序冠以统字,在我国近代法制上占有重要地位。斯时纠纷日益纷繁,法律又缺而不备,为避免司法审判无所依凭,发挥大理院的统一法律解释之权便显得尤其重要。《大理院解释例全书》编者郭卫在“编辑缘起”中指出,其时“正值我国法律改良之时期,各级法院对于民刑案件之疑义滋多,而大理院之解释亦不厌长篇累牍论述学理。引证事实,备极精详”[9]。可以说大理院解释为法律新旧交替之际,法官素质不敷要求而颇生疑义之法令提供了准确的法律阐释。
大理院统一法令解释权的法律根据是民国4年公布的《修正法院编制法》,该法第35条规定:“大理院长有统一解释法令,作出必应处置之权,但不得指挥审判官所掌理各案件审判。”同法第37条又规定:“大理院各庭审理上告案件,如解释法令之意见,与本庭或他庭成案有异,由大理院长依法令之义类,开民事庭或刑事庭或民、刑两庭之总会审判之。”[10](35-36)至于大理院所作之法令解释的具体效力,民国8年4月21日大理院解释例第975号明确表示“本院解释除法院编制法第35条但书情形外,自有拘束效力”[10](545)。同年5月29日公布的《大理院办事章程》第203条也有同样之规定:“大理院关于法令之解释,除法院编制法第35条但书情形外,就同一事类均有拘束之效力。”[11](32)可见大理院解释例中有关法令的解释,对同一类型案件在审判过程中可以参照适用,且具有法律拘束力。至于对下级法院的拘束力,大理院解释例于第1378号[10](812)重申了《修正法院编制法》第45条的规定,亦即下级审判厅对于大理院及其分院院所发交之案件,不得违背该院法令上之意见[10](38)。加之“大理院又有最高审判的权限以为贯彻法令间接的后盾,故此种权限实足增长大理院的实力;而大理院解释例全国亦均奉为圭臬,用作准绳”[10](33)。
(一)大理院解释例之形式性
根据民国9年12月修正颁行的《大理院办事章程》第50条规定:“依法院编制法第三十七条应开民事庭或刑事庭或民刑各庭之总会时,该庭庭长应将主任推事提出之内容报告书连同全案卷宗及附件送交院长召集会议,其会长由院长临时定之。对于解释法令之成案有疑义时准用前项之规定。”第52条:“各庭庭长认案件之裁判为重要时,得商请院长将该裁判文登载政府公报,并将副本送交关系公署。”[6](584, 585)也就是在解释程序上,就刑事案件而言,主任推事提出的解释文件由大理院院长召集刑事推事全员会议(总会)讨论,同样,如有与大理院裁判或解释成例有抵触者,也应由大理院长举行总会最后定夺,对于认为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重要性的裁判则商请院长将该裁判文登载于政府公报。由此可见,大理院对解释例态度的审慎,其程序的严格性也足以保证解释上的严谨,同时也可看出对于解释成例的尊重态度。
大理院解释例的格式一般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解释例全文,第二部分为附件,这里以大理院统字第25号解释例为例进行说明。
民国二年五月十六日大理院复浙江湖州第三地方审判厅函
湖洲地方审判厅鉴:
寒电悉。
刑律所谓供犯罪所用之物,以动产为限,房屋当然不能没收。
大理院铣印。
附湖州第三地方审判厅原电
大理院钧鉴:
浙江第三地方审判厅印寒。[10](16)
可以看到,第一部分是解释例全文,其结构依次是抬头、主文、解释机关(印)。抬头一般为地方请求机构(主要为审检厅)的名称,也有以“迳复者”“迳启者”作为抬头,主文则是对所请求解释事项的说理性回复,最后即为作出解答的机关大理院并签印。为了让阅读解释例的审判人员全面了解所解释的事项,在全文之后一般均附上地方请求机构的函电,便于其理解查照。但以“迳复者”“迳启者”为抬头的解释例,其后并不附有函电。这是因为大理院在作解释时,将请求来函之主要事项已经引用于其中,所以不再附录。这样就使得解释行文简洁紧凑流畅,另一方面也看出大理院的法官们对解释例的灵活处理方式。
有必要指出的是,大理院之统一法令解释权,仅仅限于法令中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或者有关法令中虽有明文却因条文抽象于审判中产生疑问者。如果针对具体个案如何处理而请求解释,大理院则依“本院向例,关于具体案件概不答复,该厅纵依一定程序请求解释前来,亦不在本院答复之列”[10](1010-1011)。
(二)大理院解释例之实证
法律解释的目的在于,法律概念不明确、涵义模糊时,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使法律规范具体、明确,从而维护法律的稳定,确保法律功能的充分发挥。而由于法律本身的一般性与抽象性,当进行具体案件时,也往往需要对相关法律之构成要件作出解释而加以适用,因此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盖法律之意义,未能确定,则无由适用,而适用之当否,一视其解释如何。”[12](73)
大理院正是基于立法者可能因立法技术有限或是文字表达粗略,以致于法律条文内容不够周全,抑或因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变迁以致于法律条文之本旨不相符于当前社会要求而产生疑义之际,通过解释使得法律条文具体化、明确化,对各级法院审判人员面临之适用困窘起到释疑指导作用。诚如姚震之言曰:“民国以后,大理院一以守法为准;法有不备,或于时不适,则藉解释,以救济之。”[4](848)
(1)民国大理院统字第252 号:民国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大理院复江苏高等审判厅电。
江苏高等审判厅鉴:
沁电情形,依本院判例,应以窃盗着手未遂论。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定价高的任务完成的情况较好,在城市中心的任务完成情况也较好。在市中心是因为交通便利,会员容易到达,也因为市中心的人员更加密集,周围分布的会员多,任务更易被完成。
大理院印宥。
附江苏高等审判厅原电
大理院鉴,窃盗指明目的地,至中途被获者,应否以窃盗未遂犯论。苏高审厅沁。[10](161)
本件解释例涉及未遂犯的成立与否问题,依据《暂行新刑律》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发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其中“已着手”为解释的中心问题,关系到犯罪分子实施之行为是否既遂,因而成为认定的关键。大理院通过第252号解释例明确指出“依本院判例,应以窃盗着手未遂论”,意指已经动身去实施犯罪,但是并没有得逞即被俘获,也就是窃盗未遂,应为未着手。而是年大理院所作的第348号解释例也指出“强盗虽预定某日强抢某家,而于未起身时被捕者,尚系在预备时期,并未着手,不能以未遂犯论”[10](213),则是从相反的方面揭示了未遂犯如何认定,也区分开了预备犯与未遂犯。再看民国4年大理院统字第359号解释例对未遂犯的解释,“强窃盗之共同正犯,中途因别故不行,其所谓别故,系出于自己任意中止者为准未遂犯,非出于己意,而因他故不行者,为未遂犯”[10](217)。这就更加明确了未遂犯的认定标准,从而更有利于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裁判。
大理院法官们进行法律解释的方法主要为两种: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文理解释是指根据法律条文字句含义进行的解释,包括对条文中字词、概念、属语的文字字义的解释,故又称文义解释;而论理解释是不拘泥于法律条文字句的含义,而就法律之整体原则理念,采用逻辑推理方法寻求立法的本意,更依据法理探究来阐明法律的真实内涵。据此观察,本件未遂犯相关解释采用的即为文理解释方法。法官们在解释案件时,依据法律条文字面的意义以及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以案件情节阐明法律条文内容的实际内涵,使得如何认定犯罪行为切实明了,便于各级法官裁判时准确把握。因此文理解释被广泛地使用于北洋政府时期的解释例当中,成为一种基本解释方法。
(2)民国大理院统字第370号:民国四年十二月二日大理院复湖南巡按使电。
湖南巡按使鉴:
感电悉。刑律二十九条正犯、准正犯法定刑范围虽同,而同一条之共同正犯,或准正犯,科刑原不必定须相等。得由承审官斟酌犯罪情节、犯人性质,分别处断。至强盗把风,乃实施行为之一部,自系共同正犯。则在房门外堂屋门口,无论认为把风与否,与罪名出入无关。大理院冬印。
(附件略)[10](222)
《暂行新刑律》第29条有关共同正犯的规定是:“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各科其刑;于实施犯罪行为之际,帮助正犯者,准正犯论。”[7](9)条文中“共同实施犯罪之行为”如何认识,正犯、准正犯其科刑是否应予区别,刑律中并没有说明,这就给法官判案带来困难,审判中不免产生疑义。在湖南巡按使请求解释之案中,几人共同图谋抢劫,而且抢劫过程中有分工,其中有人行劫,有人在门口以及门口外各自把风,之后共同分赃,便产生以上问题。大理院的解释指出,为强盗把风,乃实施行为之一种,认为是共同正犯,同时,共同正犯与准正犯定刑不一定必须相同,应该由承审官根据犯罪情节、犯人性质,分别斟酌裁判。民国5年大理院第411号解释例指出:“事前同谋图劫,事后得赃,虽未行劫,应以共同正犯论。”[10](239)如上两例解释均是对共同正犯的扩张解释。扩张解释是论理解释之一种,指当法律所规定的范围较其所应适用的范围为小时,可以依据立法者的意图,扩大文字的意义进行解释。但就刑事法而言,扩张解释之扩张,只能被限制在相关词汇的可能解释文义的范围内,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扩张解释的过度化,从而维护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论理解释还包括狭义解释,即对法律规定的用语作小于其字面含义的解释,以便体现立法本旨,通常是法律条文所规定的文义失之过宽而与社会实情不符,于是将法律条文所能表达的内涵予以限制,又称限制解释。例如民国2年大理院第25号解释例称:“刑律所谓供犯罪所用之物,以动产为限,房屋当然不能没收。”[10](16)供犯罪所用之物,如果我们由字面意义理解,应该包括动产与不动产,但上述大理院解释将其仅仅限制在动产的范围内,是对供犯罪所用之物的缩小解释。大理院的法官们通过限制解释,缩小了一些法律尤其是刑事特别法的适用范围,抑制了当时重刑化的趋向,对于社会大众无疑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四、余论
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基本上是西化,清末开始的法律变革,脱不了一味模仿、全盘照抄的底色,于是司法实践中便产生如何在传统法笼罩的氛围里适用西式法律制度的问题。刑事法律制度自然也不例外,遂有司法创制的产生。实际上司法创制源于法律解释,是基于对法律发生疑义提出申请而产生,而作出的解释具有统一拘束力,是由于法律解释机关的中立性与独立性。事实上,北洋政府时期的大理院作为司法权的行使主体,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并未受到其他机关的干涉,因而其可为最客观的考虑并作出客观正确的解释,这种体现司法权本质的解释也因之具有拘束个案的效力,正说明由大理院进行统一解释乃当时最恰当之选择。同时,大理院创设的大量判例及解释例,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统一法律的作用,而且这种司法创制不仅对于国民政府的司法机关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会审公廨等也具有同样约束力。这种权威一直延续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 大清新法律汇编[M]. 杭州: 麟章书局, 1910.
[2] 杨仁寿. 法学方法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3] 朱采真. 中国法律大辞典[M].上海:世界书局,1935.
[4] 郭卫. 大理院判决例全书[M].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 1931.
[5] 胡长清. 中国民法总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6] 余绍宋. 改订司法例规[M]. 北京: 司法部, 1932.
[7] 中华六法(一)暂行新刑律[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3.
[8] 石松. 刑法通义[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9] 郭卫.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M]. 上海: 会文堂新记书局, 1932.
[10] 周东白. 中华民国宪法法院编制法合刻[M]. 上海: 世界书局, 1924.
[11] 黄源盛. 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1912—1928)[M]. 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 2000.
[12] 陈瑾昆. 刑法总则讲义[M]. 北平: 好望书店, 1934.
On the criminal judicial creation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SHI 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d Law, Chaohu University, Hefei 238000, China)
In the period of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riminal trial law was relatively stable but not complete, so the sources of criminal trial law was plural. In order to make the law effective and maintain fair, the then Daliyuan, as the highest judicial organ, used its power of interpretation, and esta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precedents and interpretation cases, which became important legal basis in this period. This is an authoritative criminal judicial creation which reflected the nature of the jurisdiction with effect and played the role of uniform law.
Daliyuan; criminal law; judicial creation; precedents; interpretation cases
D909.2
A
1672-3104(2014)06-0154-06
[编辑: 苏慧]
2014-04-22;
2014-05-23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民国时期刑事司法创制研究”(SK2013A117)
施玮(1971-),男,安徽巢湖人,法学博士,巢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