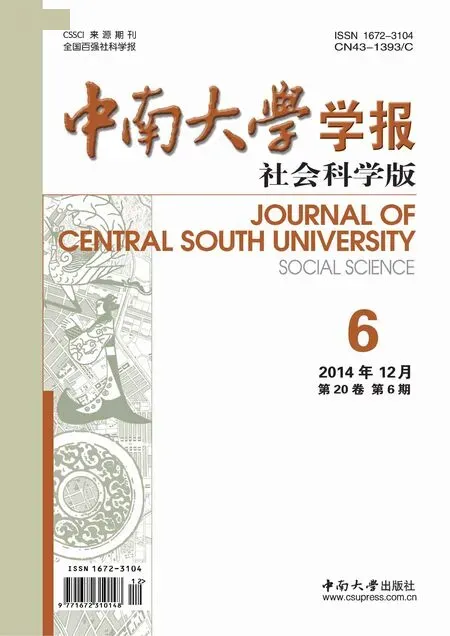美国“云计算”“数据流”技术的数字娱乐版权保护及其启示
2014-01-22马驰升
马驰升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12)
美国“云计算”“数据流”技术的数字娱乐版权保护及其启示
马驰升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12)
随着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版权保护法治已不再适应数字娱乐版权领域的发展。美国“云计算”和“数据流”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数字娱乐版权保护法治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与个人计算机模式相比,“云计算”一方面更能有效地防止数字娱乐版权盗版行为,另一方面能为窘境中的数字版权理论提供新的路径。因此,美国相关法制研究的启示,对于完善我国数字娱乐版权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云计算;数据流;版权保护
近几年来,“云计算”与“数据流”在我国信息技术领域飞速发展,是继1980年大型计算机到主机服务器的大转变之后的又一种巨变。随着这种巨变带来的技术革新,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娱乐版权保护法治。由于我国网络技术和数字娱乐版权保护理念双重落后,使得通过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存在严重的滞后性,而且现行有关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也并未涉及“云计算”与“数据流”领域。而作为信息技术强国的美国,“云计算”与“数据流”已经发展到更深领域,数字版权保护法治更是走在前列。因此,有必要分析美国数字娱乐版权保护制度,为我国数字娱乐版权保护提供可借鉴的理念和路径。
一、美国“云计算”“数据流”技术的数字娱乐版权保护的勃兴
(一)法学视角下的“云计算”与“数据流”的发展
美国学者发现消费者期望视听娱乐节目能够随时随地观看。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多数消费者倾向于将已获得版权的娱乐作品的复制件上传或下载至个人电脑或移动设备中,当然这种再次复制行为并未得到版权所有人的授权。对此,娱乐业试图通过提起诉讼、呼吁立法、发展技术以及通过市场予以阻止上述擅自复制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收效甚微[1]。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云计算”为娱乐作品的所有者提供了另一种保护作品的方法。在“个人电脑”模式下,用户将文档储存于各自的电脑中,而对该数字作品的访问以及传播则需要用户把作品复制到其他电脑中,这样显得十分繁琐,而且浪费网络资源。而在“云计算”模式下,以集中处理模式为基础,消费者可基于个人需要通过网络访问“云计算机”并下载数据而无需实际储存该信息到个人电脑中。
“云计算”的集中处理模式为娱乐作品的所有者管理用户访问、体验与使用提供了“个人电脑”模式所没有的新路径与新方法,从而放弃传统分配方式,转而通过“云计算”服务获得新作品,由此使娱乐作品的所有者对作品拥有更强的保护措施[2]。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云计算”服务授权访问作品并不属于《美国版权法》定义的“复制”范围,“云计算”与“数据流”的运用可延长作品的保护期限。另外,此种模式可以避免实体物品的销售,所有者可绕开发行权穷竭原则并通过消除二级市场,完全控制其作品的价值。这样,既促进了反侵权技术的发展,还可以阻止娱乐产业非正当性的经济损失。
(二)“云计算”与“数据流”概念的再认识
“云计算”作为一种新型网络技术,可以使消费者更加便利地共享或利用网络资源。通过“云计算”,资源即刻可得,服务提供变得十分简易[3]。然而“云计算”已经发展多年,但是各学科并没有明确“云计算”的定义。这主要是因为“云计算”在各学科中的要求不一样。在法学研究领域中,“云计算”技术的核心在于,通过位于世界各地的数据处理中心的服务器将服务传递至个人电脑中,并集中处理、储存用户可访问的数据[4]。另外,由于“云计算”运行模式与主机运行模式类似,“云计算”通过网络使“无信息处理能力”的个人终端可访问“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主机,以及含有消费者需要的且储存于主机中的信息,从而使用户可随时随地通过网络访问处理好的数据。
如果说“云计算”是一种信息储存方式,那么“数据流”则是用户与主机传递经“云计算”储存信息的方式。与完整保存数据供日后访问的传统下载不同,“数据流”将个人数据传输给消费者使用后,消费者的电脑会在使用完毕后删除该数据。从而,“数据流”增强了用户对音乐或电影等动态数据的体验,而无需在个人电脑中永久拷贝该作品[5]。一般而言,“数据流”类似于特定时间、特定频道的现场直播或“按需供应”点播,使消费者可随时获取数据流。如美国网络影音网站HULU根据用户需求提供的节目便是“按需供应”,主要通过给予消费者可随时访问的“数据流”以便消费者自主选择完成[6]。换言之,“数据流”类似于有线电视的传输模式,可使用户获取正在播放的视频,但想获取之前的电视内容则不行[7]。
如上阐述,“云计算”与“数据流”可以使娱乐作品所有者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掌握作品的访问、使用。因无需将内容存于个人计算机中,上述方法使消费者若想复制该内容将极为困难[8]。更重要的是,“数据流”的“按需供应”性,限制了传输途径,从而减少了复制的需要。另外,因作品的所有者即“云内容”提供者要求消费者注册并以注册账号登录的方式获取该“云内容”,所以所有者可通过撤销用户授权以阻止恶意用户访问。对访问的控制亦可使所有者、创作者、提供者对消费者的体验进行管理以及对作品的数据进行控制。
因此,“云计算”与“数据流”等混合云计算技术的相互运用,一方面可赋予消费者更便捷的网络消费,另一方面可促进作品的所有者、创作者及提供者管理其数字作品,从而进一步控制娱乐作品在互联网中的传播。
二、美国“云计算”与“数据流”保护数字娱乐版权的法律适用
(一)美国“云计算”与“数据流”传递数据不属于复制
对于美国数字版权领域而言,2012年是不平静的一年,对数字版权的侵权层出不穷。随着“云计算”和“数据流”等数字技术的发展,《美国版权法》不得不做出一系列的变革。
1. 法律原因
首先,《美国版权法》给予版权所有者对固定在有形介质上的原创作品独占使用权,包括复制、发行、发表、表演该作品的权利以及通过租赁或许可转移这些权利,任何人未经版权所有者允许,擅自行使上述权利即为侵权。[9]其次,《美国版权法》将“复制作品”定义为实物。因此,根据《美国版权法》的规定,与作品成为有形的表达不同,娱乐唱片、录影带等数字载体要体现足够持久、稳定,从而该作品不能在短暂瞬间内被复制或通过其他方式得以传播。[10]那么通过单纯的从一个实物中复制数据到另外一个实物就会构成侵权,因为数据固定存储于原媒介的同时,同样的信息也可以在另一媒介或可无限制地复制并固定于其他存储器中。而“云计算”与“数据流”同时传递数据并不需要复制任何数据,仅仅只是传递,因此,“云计算”与“数据流”传递数据不是《美国版权法》中定义的复制侵权行为。
2. 法理原因
相反,“云计算”与“数据流”使消费者无需复制信息至个人设备便可访问,因为该信息在用户设备中体现时间极短。因此通过“数据流”交换云储存作品并不属于《美国版权法》所定义的“复制”范围。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美国版权法》关于“复制”的定义中“极短暂时间”用语的立法表明,电脑暂时捕获的数据并不符合该定义。其二,最近的判例表明数据信息流并不止于短暂瞬间内有形媒介中的复制件,因为该数据在传递时极快,很快就会被自动覆盖。因此,即使“数据流”会在用户电脑中产生少量数据存留,但该数据实际使用时,数据便会被清除,即使有数据也不会是完整数据,并不属于《美国版权法》规定的“复制”行为。
例如,卡通频道案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判决认为数据在缓冲器中停留仅1.2秒,不属于较长时间的“复制”,但节目数据转至远程服务器中供日后观看的行为构成了侵权。第二巡回法院分析认为,《美国版权法》中的“复制”要求表达体现性的同时,还需具备可感知性、可复制性以及不止于短暂瞬间。法庭认为数据从缓冲器被复制到有线新闻网的服务器中已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该内容具有可复制性。[11]但法庭最终认为,因数据在处理完成后都会被自动覆盖,无任何数据在缓冲器中的停留时间超过1.2秒,所以并不符合“不止于一个短暂瞬间”的要件,因而不构成“复制”。
此外,上个世纪80年代的几起利用视听动态组件“复制”数据的版权案件中,都表明只要不向多数人传播,仅仅通过屏幕显示试听作品并不构成“复制”。因为该作品版权的获得与计算机程序类似,虽然作品内容是从电脑硬盘中直接获得,但只是通过一个主机传播,多个屏幕显示而已。这一系列案件中,藉由计算机程序传播作品的一个独立的授权版本时,该作品并不属于复制件[12]。照此,当多屏幕显示一个版本或一个程序时,只要所有屏幕显示一样,多屏幕中任一屏幕显示就不构成《美国版权法》中的“复制”,反之亦然。
(二)美国“云计算”与“数据流”保护数字娱乐版权理念的变革
一系列数字版权案中,缓冲复制并不“固定”的结论被认定为从“云计算”服务者传播至联网设备的音频与视频数据内容并非“复制件”,因为联网设备并不“复制”该作品,且所有作品演示都来自“云计算”服务者。当“云计算”与“数据流”两者共同使用,不包括其他数据交流方式时,娱乐业版权保护的性质会发生三种变化:
1. 发行方式再定义
发行作品的复制件通过销售或其他转移所有权的方式分配于消费者。所以所有者为日后发行、公开表演或公开展示作品,需先向部分人提供作品复制件进行市场运作后才能达到发行的目的。通过“云计算”所存储的数据,如长期存储于该服务器上,无疑属于“复制”;而按需供应的“数据流”是通过设备直接展现、演示其作品,“云计算”储存作品后将其提供给不确定多数人使用,并不构成“发行”[13]。主要原因有两个:
其一,根据《美国版权法》的语义解释并不能认为向“云服务”提供作品的版本或复制件属于发行。该法要求先需向一部分人提供作品复制件以便日后发行,而“云计算”只需所有者提供一份复制件,而不是多份,因而不是“发行”。而且该作品内容不是直接上传至一台电脑,而是提供给一个以法人为实体的企业,所以实际上除“云服务”外,并没有所谓的“一部分”人获得该复制件。
其二,通过“云计算”将内容提供给不计其数的消费者并不构成发行。尽管“数据流”环境下传输作品数据的确是表演或展示作品,但法案明确表示仅公开表演或展示本身并不构成“发行”。再者作品通过“数据流”按需供应的表演或展示本质上也并不公开。《美国版权法》定义的“公开”要求表演或展示是在公众场所或在同一场所或同一时间在不同场所或不同时间向公众公开。
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考虑作品的表演是否为公开时,认为应关注能够接收表演的消费者而非该作品的潜在消费者。因而即使同一作品的表演内容被传输至不特定消费者,此传输行为并不一定构成公开,除非该传输能够被不特定消费者所接收。卡通频道案中,将已播放于公共广播节目的内容从远程录像机传输至某个人的行为并非“公开表演”,因为接受该视频回放传输的仅为该消费者一人;同样按需供应所传输的“云内容”亦只能被提出订阅该传输需求的用户或设备接收。从第二巡回法院的判决看,“传输行为”非公开性的解释可以认为公开需求是对数个复制件的分配。显然“数据流”并不会产生任何“复制件”。另外即便被不特定消费者所接收的内容被认为是一种公开表演,其传输行为本身并不构成作品的“发行”。所以,仅通过“云计算”与“数据流”传输作品并非“发行”。
通过回避作品发行,作品所有者可在两个方面增强对数字版权的保护:其一,因为所有者并未行使其发行权,根据《美国版权法》第106与501节,当有人未经授权擅自下载或散布作品复制件时,所有者被赋予额外的诉权。其二,当作品为雇佣作品时,不发行该作品可使版权保护期限从35年延展至120年。对于电影电视业及出版业这类以传统模式发行作品的行业来说,似乎上述方法并不可行。更实际的做法是改变商业策略,即电影制片厂可尝试将其影片置于中央服务器,影院则通过“数据流”在本地放映,但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音乐人可自行经营网站并通过“数据流”技术控制对其作品的访问。随着“云计算”与“数据流”技术的普及,以及互联网传输数据能力的增强, 娱乐业应通过调整销售策略的方式来保护版权。
2. 发行权穷竭原则的再适用
以作品有形复制的发行为前提,首次发行权穷竭原则将对授权的表达使用方式与已被固定的有形媒介相区分。根据该原则对包含作品的有形物所有权的转移,包括复制在内,其本身并不包含对该版权作品任何权利的转移。例如买一张CD,可任意送给或借给其朋友,CD的版权所有者并不能控制CD本身的流转,而买了CD的人则不能一边保有该CD的同时将CD内的作品复制给其朋友,不然这样就会侵犯CD的版权所有者的复制权。因而经作者同意的复制件进入商业流程后,发行权穷竭原则限制了所有权人对自己权益的控制能力[14]。有形介质的购买者可将其出售、出租,根据发行权穷竭原则,该作品的次级市场应运而生。这就为原本需在初级市场购买的消费者提供了其他选择,这样必然会减少版权所有者的潜在收入。反之版权所有者可通过避免授权任何含有作品表达的复制件以阻止次级市场的产生,使作品仅能通过“数据流”获得,版权所有者可禁止复制件的发行,充分规避发行权穷竭原则,从而消除次级市场,并有效控制次级市场。
3. 控制权的再调整
借助“云计算”与“数据流”,版权所有者可重掌对作品的控制,继而重掌尼默教授所说的版权即“无冕之王”的控制权[14]。尼默教授认为作者在载有其作品的有形介质,如磁带、DVD等公开发行前仍保有其对公众体验作品进行控制的权利,或事实上享有该权利。如1930至1970年,美国多数电影公司控制产品在影院发行并对电视播出时间施加限制[14],于是观众只能在固定的时间里去剧院或在电视上观看节目。正如尼默教授所猜测,人们一定常在脑海中回味其中某些片段,可惜观众无法购买其作品以便个人观看,因为当时并没有发行商业版本供个人消费使用[14]。此类控制消费者体验的权利,使版权所有者得以控制何时、何地以及公众访问该作品的时限和权限,从而使公众得先预定该服务以便体验该作品。
学者安德森进一步研究了由电视及电影等以服务为导向型的娱乐与由DVD、IPods等产品为导向型的娱乐两者的差异。当该娱乐内容为某产品时,消费者可随身携带而无需借助外力。而当娱乐内容为某服务时,消费者需提供者同意才能访问该内容。如音乐过去便被视为一种服务,消费者需要音乐家演奏或电台播放唱片。当消费者能够购买电子设备以便重放该音乐时,音乐便成为一种产品导向型娱乐。[5]而版权所有者必须让渡对有形载体的控制,以便消费者阅读、获取该作品,所以书或其他文字作品历来被视为产品导向型娱乐。
决定一项娱乐是否属于安德森所称的服务,关键在于谁对消费者体验拥有控制权,尤其是对于作品的储存、回放与表演。当由消费者控制时,该娱乐作品偏向于产品导向型。而由版权所有者主导控制时,则属于服务导向型。于是当作者将其作品固定在能够传播、供公众回放的有形介质上时,消费者便获得了对体验该娱乐内容的控制。而作者则通过预扣其作品的复制件或回放方式以维持对用户体验的控制。
可以说“云计算”与“数据流”将娱乐体验推向了服务导向型。作品的获得取决于所有者是否提供该服务,即访问并储存了该作品的云途径。如2009年亚马逊在版权所有者的要求下,从电子书网络中删除了未获授权的“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15]。因此即使亚马逊电子阅读器用户在亚马逊上购买了该复制件并下载至设备中,亚马逊作为电子阅读器的服务提供商仍然可通过禁止对该作品的云访问而将用户设备上的内容移除。随着书籍的数字化发展蒸蒸日盛,作者与出版商对公众访问的控制权愈强,从网络移除该作品,使得前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皆可从消费者处取回其作品。
电影业已经采取此技术以控制用户访问。例如网飞公司采用中央服务器模式通过流媒体服务更新用户所需的节目。尽管用户支付7.99美元便可获得该服务,但网飞公司有权控制置于网络上的内容。[16]因此,过去数字版权所有者并不能使其作品得到广泛使用,而当前技术的实现可以有效达成前述目标:第一,由于授权访问作品的版本并非发行,作品可获得包括更长的版权保护期限在内的额外保护。第二,“数据流”通过颠覆发行权穷竭原则排除了次级市场,数字版权所有者可增加其原损失于次级市场的收入。第三,由于作品只有一个版权,所有者主张的控制权,通常在发行与首次销售时进行审核,从而可以积极地以变革性的商业策略适用上述新技术,娱乐业可以有效增强数字版权保护,减少盗版并扩大盈利。
三、美国数字娱乐版权保护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实施的《著作权法》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数字娱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娱乐版权保护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最新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也未对数字娱乐版权进行针对性的修改。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技术革新将进一步加剧我国数字娱乐版权保护的不平衡。“云计算”与“数据流”技术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将为窘境中的数字娱乐版权保护带来一个福音。
(一)以“云技术”“数据流”延长数字娱乐版权的保护年限
数字娱乐版权其重点在于规范娱乐行业,娱乐节目的网络传播主要围绕经济利益展开,保护数字娱乐版权无非是保护所有者的经济利益,数字网络只是保护的一种途径或者媒介。目前我国处于网络盗版横行的时代,网络盗版给娱乐版权所有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现行的法律体制很难遏制这种情况的发展。但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云计算”和“数据流”技术的双层环境下,数字娱乐版权可以向一种服务转变,可消除产品导向型娱乐作品,使消费者只能选择版权所有者控制的服务才能访问其版权娱乐作品。通过“云计算”集中处理数字娱乐版权,及版权所有者通过“数据流”控制消费者访问作品,从而版权所有者可进一步控制消费者对作品的使用与体验。特别是经“数据流”交换所得的作品内容并没有实际固定在消费者的电脑中,所以不存在任何作品的复制件。此种情况下,消费者体验娱乐作品或其他需求仍可以得到满足,因为该内容可随时通过消费者的个人电脑或者电子设备联网服务器获得。所以,“云计算”与“数据流”技术赋予所有者一个崭新的权利池以增强其版权保护,无需实际向消费者发行其作品,就可以将娱乐版权所有者享有的版权保护期限延长至所有者死后的几十年。当然,由于我国现有的经济、文化、社会群体等因素,全面赋予数字版权所有者无限期的拥有版权显然不现实。但如上文所述数字娱乐版权重在娱乐,娱乐严重依赖市场,完全可以把数字娱乐版权保护交给市场调节,这样既让数字娱乐版权所有者拥有无限期版权又不影响我国整体知识产权的发展。在此,数字娱乐版权只是数字版权的一种,建议在相关著作权法中细化版权的分类,规定现有的传播媒介,从而达到全面地、有效地保护数字娱乐版权的目的。
(二)以“云技术”“数据流”平衡数字娱乐版权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在我国著作权法架构下,社会公共领域所支持的信息是可以自由使用的,但始终被认为与版权的排他性权利处于相对的立场,特别是在互联网模式下,数字娱乐版权保护中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如何平衡是值得深思的。“云计算”与“数据流”环境更有利于数字娱乐版权所有者控制其权利,对于这种权利的控制,是法律赋予版权所有者排斥、限制他人非法获得其版权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是基于我国现有社会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考量,并非来自公权力无条件的给予。换而言之,只有当特定的数字娱乐版权延伸到我国公民既有知识的范畴且符合法定要件,并正面提升整体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发展时,才能被赋予排他性的权利。
公共利益在我国社会提供共有信息的功能与效益是多元复杂的,而且可能随着社会需求会大幅变化。根据财产权理论,版权所有者的财产权诞生,除了必须证明自身能有效地管理特定资源外,还须取得社会对其存在价值的肯定。版权所有者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界线,并不取决于消费者对于信息流通及使用上的需求,而是基于管制思想的目的。其后在娱乐版权保护标的排他性权利内容的扩张过程中,社会内部信息产生者与使用者的需求,也未成为立法者的主要关注对象,相对地,商品贸易的结构对于特定国家经济的依存度,以及长期以来受国外立法的影响,以及创作娱乐作品、构建公民娱乐等文化面的考量,成为影响公共领域范畴的重要因素。因此任何一个单一的公共领域理论或版权政策,无法断然地都属于法律的强行规定。“云计算”与“数据流”控制下的数字娱乐版权保护,必须基于社会价值、群体意识与政治主张等本土性元素。也就是说,我国保护数字娱乐版权的公共利益只有在版权所有者的利益界定清晰后,才能追求公共利益内涵的差异,发展迥异的数字娱乐版权政策,以及独特的公共利益规范。就算是“云计算”与“数据流”加强了版权所有者对于其版权的控制,政府、企业、教育机构等组织基于不同利益目的,也在既有规范结构下,各自享有不同程度的数字娱乐版权权利。
综上所述,只有在数字娱乐版权所有者权利界线固定以后,数字版权中的公共利益才会相对固定,而公共利益之间的部分利益,会随着各自的需求不同,通过公权力再次分配。因此,在“云计算”与“数据流”环境下,数字娱乐版权所有者的权利界线更加清晰,公共利益架构也就随之明朗。
[1] Lauren Spahn. EMI v. MP3 tunes: business model proposals for the music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technology [J]. Berkeley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Law, 2013(2): 154-162.
[2] Jay P Kesan, Carol M Hayes, Masooda N Bashir. Information privacy and data control in cloudcomputing: consumers, privacy preferences, and market efficiency [J].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2013(70): 345.
[3] Mark Wilson. Castle in the cloud: modernizing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for cloud-stored data on mobile devices [J]. Golden G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3(43): 267.
[4] Kate Greene. Think you know cloud computing [EB/OL].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view/412043/think-you-knowcloud-computing/, 2013-11-02.
[5] Jay Anderson. Stream capture: returning control of digital music to the users [J].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2011(25): 159-167.
[6] Hulu. Hulu overview [EB/OL].http://www.hulu.com/about, 2013-10-29.
[7] Sage V Heuvel. Fighting the first sale doctrine: strategies for a struggling film industry [J]. Michiga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Law Review, 2012(18): 661-689.
[8] George Jiang. Rian or shine: fair and other non-infriging uses in the context of cloud computing [J]. Journal of Legislation, 2010(36): 395-414.
[9] Thomas J Loos. Fair use and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J]. Michiga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Law Review, 2007(13): 601-616.
[10] Blake Evan Reese. Fixing through legislative fixation: a call for the codifi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doctrine as it applies to copyright law [J].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2007(11): 446.
[11] Vivian I. Kim. The public performance right in the digital age: cartoon network LP v. CSC holdings [J].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09(24): 263.
[12] Tyler T Ochoa. 1984 and beyond: two decades of Copyright Law [J]. Santa Clara High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03(20): 167.
[13] Nick Scharf.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and fair use [J].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2010(1): 8.
[14] David Nimmer. Brains and other paraphernalia of the digital age [J].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1996(10): 15-19.
[15] Brad Stone. Amazon erases Orwell books from kindles [EB/OL].http://www.nytimes.com/2009/07/18/technology/comp anies/18amazon.html?r=0, 2013-05-29.
[16] Netflix. Netflix company overview[EB/OL]. https://pr.netflix.co m/WebClient/loginPageSalesNetWorksAction.do?contentGroup Id=10476&contentGroup=Company+Facts, 2013-06-30.
On the system of digital entertainment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America——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oud computing and content streaming
MA Chisheng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With the soaring growth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law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has not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ntertainment of copyright. Howev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ramatic development of“cloud computing” and “content streaming” has brought about a new perspective. Compared with the personal computer model, “cloud computing”, on the one hand, prevents more effectively from copyright piracy of digital entertainm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developing digital rights theory through the dilemma. Therefore, related legal research on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of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entertainment copyright system in China.
cloud computing; content streaming; copyright protection
D923.41
A
1672-3104(2014)06-0148-06
[编辑: 苏慧]
2014-03-19;
2014-07-22
湖南省知识产权研究项目“长沙市知识产权评估市场的现状与对策研究”(HNR20111207)
马驰升(1986-),男,湖南益阳人,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