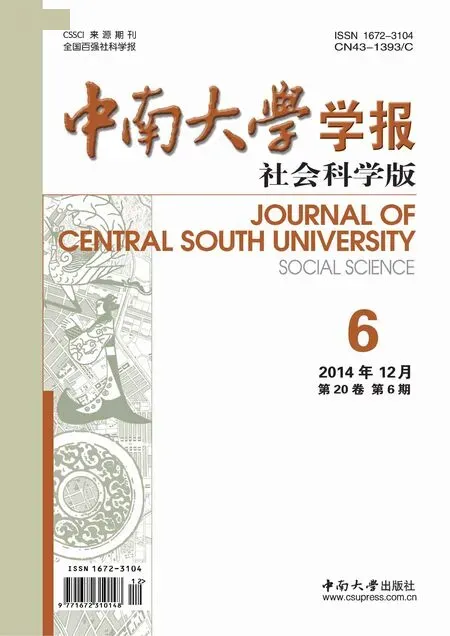肉体里隐匿着灵魂自身的秘密
——灵肉二元论之身体维度探析
2014-01-22王建华张再林
王建华,张再林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肉体里隐匿着灵魂自身的秘密
——灵肉二元论之身体维度探析
王建华,张再林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灵肉二元一直是西方文学和西方哲学的核心议题,受制于伦理和宗教语境的主宰和束缚,在过往的文学叙事、宗教隐喻和哲学思辨中,肉体往往被认为是灵魂的桎梏和监狱,这一思想导致了清教主义思想的盛行,也使得身体沦为人类文明书面记载中一个面目模糊的存在。于是,身体在“德”与“礼”的束缚中进退无据,既没有理论话语的表达权,也没有现实存在的着陆场。但可感、可欲的身体却一直是人类思想的精神沃土,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身体哲学的凸显为身体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同时,中国哲学中身心一体的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生命本身的关注都为解决灵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灵肉二元;肉身之罪;身心纠结;梅洛·庞蒂;身体哲学
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中,将近百岁的杨绛先生曾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在灵与肉的斗争中,灵魂显然在肉的一面。”[1]这句话概括了她一生的生命体验,但这句看似简单却不无中肯的判断牵涉到人类文明史和精神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灵魂—肉体之困境”的问题。
一、伦理与宗教语境中的肉身之罪
一直以来,除了在医学领域或在生物学意义上之外,“身体”一直是“人类精神史上的盲点”[2],未曾在哲学的精神领域内得到过应有的重视。身体甚至被排斥和压制到了几近黑暗和丑恶的深渊,一度被视为罪恶的源泉、精神上的污点。对于哲学史上的这种身体现象,张祥龙指出,“西方哲学对身体的歧视实在是太大了。从古至今,无论是希腊传统还是基督教传统,身体都备受贬低。”[3](303)
身心纠缠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伦理(文明)观念对人类的肉身属性的强制性压迫乃至摈弃,与此同时,灵魂和精神的纯粹与至高无上则被无限地提升,成为了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和标签。当这一观念随着柏拉图的哲学观念和基督教思想的广泛传播,心性、灵魂、精神都带上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面具,身体被彻底地摈弃,灵魂和精神的复杂性也被抽空简化,并一度成为伦理的代名词,或者说,伦理道德取代灵魂成为了人的内在属性。基督观念所强调的禁欲、苦行思想都显示了伦理至上的这一现实。正如刘小枫所言,“伦理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在世的态度,伦理中的成文或不成文规例就是道德规范。”[4](73)
但伦理是以牺牲人类的肉体需求为前提的,并要求一个有德行的人要尽量克服肉体的需求和诱惑。因此,肉体和性被烙上了不洁和羞耻的道德标签,只能成为一种私底下的隐秘欲望,不得在公开的场合抛头露面。
这一点在但丁的《神曲》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但丁在步入地狱之前遇到阻止他前行的第一只动物是象征淫欲的豹子,地狱第二层①也将“情欲压倒理性的犯邪淫罪者”关押在内,爱欲的亡魂需要饱受凄风苦雨的侵蚀和惩罚,毫无解救的希望[5],与人类身体欲望相关的七宗罪也需要在炼狱中予以净化,而贪色者则被置放在炼狱顶层的伊甸园之下。从但丁这一描述来看,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中,人的灵魂想要得救和净化,不论是在进入地狱之前,还是在进入地狱之后,更甚而是在炼狱即将结束之时,人类首先要面对的是人的身体之欲,尤其是色欲对人的诱惑和考验。而事实上,这种本能的欲望往往会左右人类的选择和行为。古希腊“不和的金苹果”神话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选择无疑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面对权力、智慧和女人,帕里斯毫不犹豫地将金苹果判给了允诺给他女人的爱神[6]。身体的本性是一种潜意识的生命动力,女人对男人而言不仅仅只是肉身的诱惑,更是一种伦理的抉择,“对命运的理解就是对个体肉身在世的理解,就是个人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4](91)而如何安置身体在生命中的位置往往成为个体肉身伦理和社会灵性伦理相互争执的核心议题。
如果我们仔细考量,会发现即使在基督教的《圣经》传统中也依然存在着上帝对身体的不信任和敌意。作为耶和华神的儿子耶稣,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父亲的,他母亲马利亚身为处女却可以感怀圣灵,无需男女之交媾就可以生下人子耶稣②。可以说,道成肉身的耶稣的身体是一具灵化的身体,更是一具无性的身体。《圣经》中的这一记述,与《旧约》中对身体的叙述一脉相承。《创世纪》中提到了人类获得知识的起源,人吃了智慧之树上的果子之后,因而能够拥有智慧和知识,才能知羞耻,辨善恶,而羞耻感的产生恰恰是以身体的裸露为前提的,知识的起源伴随着的是对身体的排斥,当人类穿上文明的外衣之后,裸体便成为了道德的禁忌。可以说,在基督教的观念中,身体是罪恶之源,是人类的苦难之源,更是人类灵魂无法真正净化的障碍。于是,后来天主教的神甫将严格遵守教义和教规视为铁律,力图放弃俗世的婚姻,并杜绝身体之欲的享受。但历史的真实却是,中世纪的教堂不仅沦为公开的妓院,而且神甫和主教们不仅没有按照教规去舍弃己身之欲,反而变本加厉放纵着肉体的欲望。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就曾描写过太多这样虚伪的神甫和主教[7](31),这些教职人员的纵欲行为无疑从现实层面抽空了基督教贬低肉体思想的理论根基。
在基督教的灵肉二元论中,肉身的享乐是必须要克服和禁止的,身体的净化和灵魂的纯粹最终指向的是对上帝的圣爱。一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言,“基督教的主导思潮就是要玷污并压抑人类的身体。……基督教传统荣耀的是灵魂之美而非肉体之美。苦行戒律通过对肉体之欲的制服从而释放了人的灵魂。”[8]这种灵肉二元的思想源于古希腊的奥尔弗斯教和柏拉图。在奥尔弗斯教的教义中有这样明确的描述:“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人生是死亡的演习。只有通过死亡,灵魂才能从它的禁锢之中解脱出来,才能从它身体的罪恶之中得到解放。生就是死,死就是生。死亡之后,灵魂要受审判。……灵魂在世上经过三世之后,不受肉体玷污,就被永远开释,去和天上的快乐神共同交游。”[9]这种灵肉二元论认为身体是灵魂的束缚和泥沼,灵魂必须经过三世的磨砺和轮回之后才能真正解脱。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则认为身体是灵魂的桎梏,只要身体存在着,灵魂很容易受到肉体的沾染而丧失其纯粹和完满,更无法去获取真知,真理只能经由灵魂才能通达,在柏拉图眼中,肉体处于灵魂的对立面,要想获取知识、保持灵魂的纯粹性,要尽量避免和肉体接触[10]。他同时也看到了于欲望而生的激情往往是人类变得软弱的根源,于是柏拉图否定了艺术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禁欲和苦行观念在中世纪的盛行,身体逐渐被看作是邪恶的东西,成为一种有缺陷的存在,也沦为了人类的堕落之源。于是,在基督教的这种思想和语境中,人类的身体其实已经被悄悄地转化成了肉体观念,进而,只有摆脱肉体的牵绊,趋向上帝的灵魂才能避免堕落并得到上帝的恩典[11]。
这种论断不仅在中世纪一统天下,即使经过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在19世纪也还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托尔斯泰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在托尔斯泰看来,人活着不能纵情于声色犬马,要尽量简朴以保持灵魂的宁静,需求越少,生活越幸福。在身体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略有微词,“让肉体娇嫩,就得让灵魂粗劣。”“对于有理性的生命,对于人来说,沉湎于色欲不是出于本性,人的本性所固有的是与色欲斗争,任何一个人凭体验都可得知,人对肉体需求满足得越多,他灵魂的力量就越发虚弱。与此相反的是,伟大的哲人和圣徒都自我节制,保持纯贞。”所以,托尔斯泰认为,痛苦只是因肉体而生,因为“灵魂没有痛苦。”不仅如此,托尔斯泰还认为,“性爱是诱使人违背上帝法则的最常见的因素。”身陷其中的人们只会毁坏了自己的生活。因此,“人真心想要过善的生活的一个最可靠的标志是严格控制自己的性生活。”已婚的男人和女人要“共同致力于把自己从性欲之中解放出来”。而若想获得解放,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童贞”和“一生不结婚”。[12]
宗教语境强调灵魂的圣洁和纯粹,而伦理观念则极力强化肉体的低劣和卑污,二者在现实生活中以社会的正统价值观自居,成为传统社会维护政权稳定的道德武器。因此,心性和德性,乃至对上帝的圣爱成为衡量个体生命价值的唯一准则,人的肉身则必然成为要束缚和压制的对象。这种传统伦理观的根本缺陷在于:它通过语言编织的方式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尊灵魂而贬身体,视身体为障碍,并力图根除人类所有的肉性需求,把“善”和“德行”预设为人类最高的追求,要求“使身体成为心灵的仆人”[13](49),经过文学作品的不断演绎和哲学思考的进一步纯化,于是,牺牲自己的身体就被内化为个体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4](91)。而且为了强化自身的绝对权威,这种伦理观排除任何与之相左的思想。正如尼采所言,“在道德面前,正如在任何权威面前,人是不允许思考的,更不用说允许批评了。”[14]当伦理道德习惯性地以审判官的角色来发号施令时,往往会干预人类的理性判断,使得身体问题变得逐渐复杂起来,同时也使得关于身体的描述和思考成为了19世纪之前文学和哲学书写中一个面目模糊的存在,而伦理的极端化则往往导致对生命本身的漠视和忽略。
二、个体生命中的身心纠结
但问题在于,人类不可能消除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纯粹的灵魂和精神无法脱离身体而存在,璀璨的文明往往诞生于身体的沃土之中。灵魂的困境在于向上升腾的信念往往受到肉体的牵制和内心欲望的诱惑,愈是强烈地、极端地排除身体的欲望,就愈绝望地走向了精神的对立面,纵欲的享乐远比纯粹的精神要生动、鲜活,它更具吸引力。一个鲜活的明证就是卡夫卡,在一般人看来,卡夫卡是一个精神的殉道者,但在私下生活中,他靠收集情色图片来缓释身体的欲望,他拒绝婚姻和女性,却无法抵挡身体的欲望和诱惑③。于是他的内心便被撕扯成碎片,孤独而自虐。也正是这种身体和精神之间的撕扯和争斗,才让卡夫卡的思想变得异常尖锐和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欲望)不仅是精神产生困惑的根源,同时也是思想得以深刻的土壤。
同样是在《神曲》中,但丁看到彼此深爱的保罗和弗兰齐斯嘉因爱遭受凄风冷雨的折磨而感同身受,甚至昏死过去。地狱之惨相给但丁带来的是肉身的沉重,而灵魂的净化和升腾伴随的却是肉身的抽离和隐去。但刻板教义的宣扬和内化无法真正让人的欲望消隐和冷冻,薄伽丘《十日谈》中关于“母鹅”的故
事[7](218-219)也非常形象地告诫人们,自然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更是无法根除的。
凝结在个体生命中的这种身心纠结和生命抉择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剌克勒斯在十八岁的人生十字路口,曾遇到两位名为“恶行”和“德行”的女人的纠缠,体态丰盈的“恶行”许诺给赫剌克勒斯以人生的欢娱和享受,而衣着素朴的“德行”则告诫赫剌克勒斯若想获得人世的尊荣和显贵,必须辛勤努力、付出汗水,力行善举[13](47-51)。这一善与恶的抉择既是人生的难题,也是哲人关注和思考的重心,在赫西俄德看来,通往“恶行”的道路平坦而易行,而获取“德行”却要历经辛劳和汗水,路途漫长而艰辛[15]。这一抉择也往往是每个个体在各自生命中所无法逃避的,若看重身体的享受就有可能背负“恶”的道德谴责,但一心向“善”却不得不压抑身体的欲望。于是,关于身心纠结的文学主题一再被演绎。而最具哲理的形象描绘莫过于歌德的《浮士德》。在《浮士德》一书中,歌德通过浮士德博士两度人生的经历深入探讨了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必将遇到的这个复杂难题:一个是“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执著于尘世享受的肉身,另一个是试图超凡脱俗、飞向崇高灵境的灵魂,二者共处一身,彼此牵涉却妄图决绝[16]。
第一生的浮士德博士把生命中所有的精力放在了对哲学、法律、医学和神学的研究上,没有家庭和婚姻,更没有生之所欲的满足。但是对精神和灵魂的崇尚并不能抹去他身体的肉性之欲;第二生的浮士德一反之前的严谨和禁欲,变得轻浮和纵欲,虽然他在逐欲的过程中意识到了生命的真谛在于不断地奋斗,但是这种矛盾中的纠结和抉择中的痛苦恰恰彰显了个体生命的真实状况。
生命的张力也恰恰孕生于这种身心纠结的实然。苦痛的人生才是真实可感的,没有身体的灵魂轻飘无据。正如歌德本人所坦诚的,“只有在他感到欢喜或苦痛的时候,人才认识到自己;人也只有通过欢喜和苦痛,才学会什么应追求和什么应避免。”[17]欢喜和苦痛是肉身的温度和呼吸,灵魂和思想是通过可感的身体来思考的,也是通过可欲的身体来体现的。身体的肉性和灵性既是一种纠结,也是一种张力,还是一种梅洛·庞蒂所说的“交织”。二者不可偏于一隅,重视灵魂的纯粹只能是导致对身体的敌视,而放纵身体的享乐只会让人褪去人性的可贵品质。一如刘小枫所言:“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4](93)肉体和灵魂是身体属性的两个维度与面向,道学家看重的是灵魂,享乐主义者则注重的是肉体的享乐。
在道德主义者看来,肉体和性都是不洁的、羞耻的,身体的性和欲望则容易导致罪恶的产生。即使是一些伟大的人物也未能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列奥纳多·达·芬奇对性和人的本能就怀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他认为“性交的行为及其使用的器官如此丑陋,倘若没有面容的美,亲历者焕发的光彩和迸发出来的无度的热情,自然便毁掉了人类。”[18](1)乔治·巴塔耶指出了这种观点产生的原因,“人类的存在决定了对一切性欲的恐惧;这种恐惧本身决定了色情诱惑的价值。”[18](8)事实上,在身体中,尤其是在色情中,我们才能发现人类的秘密。莫里斯·布朗肖就认为,色情狂比普通人“对自身的状况的真实和逻辑了解得更加透彻,他有最深刻的理解力,能够通过帮助普通人改变一切理解的条件来帮助他理解自身”[18](1)。这一观点在作家萨德和哲学家福柯身上有着直接的印证。身体现象学的代表人物梅洛·庞蒂就认为人类带有“害羞和无耻”感的性欲不仅“内在地与认识的和能作用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与“生命同外延的”[19],因而是内在于身体的一种辩证运动,也是彰显个体存在的生命象征。而对“作为一种原始意向性的性生活”的研究可以为哲学找到活生生的“生命根源”,因此性欲还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人类的生命和存在也只有通过真实可感的欲望和爱情、以及性欲才能真正存在[20]。
我们的身体是“社会的肉身”[21],一个离弃了日常生活和爱欲情仇的身体是不真实的身体,只有正视身体的日常性和爱欲性,才能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同样,割裂了灵魂和肉体联系的文化也必将是缺乏活力和信服力的文化,美国女权主义学者艾德里安娜·里奇因此断言, “文化:纯粹的精神与灵魂……已经……将自身与生活剥离开来,成为只能进行定量分析的、具有抽象性质并表现出对权力的欲望的僵死的文化,这一文化在本世纪已经的的确确走向了毁灭的边缘。”[22]
三、身体哲学的凸显与身体之澄明
在灵魂和肉体关系的问题上,19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存在的最大弊端在于,它忽视甚至摒弃了身体,要么视身体为障碍,要么剥夺身体的正当合法性,将灵魂提纯为思辨哲学和意识哲学的抽象主题,成为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空洞所指,光芒四射却了无生机。费尔巴哈把这种哲学称之为旧哲学,并总结说,旧的哲学以抽象的、思维的实体为其出发点,而新的哲学则树立了一个感性的、肉体的始基,即:“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们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在费尔巴哈看来,“身体属于我的存在;不仅如此,身体中的全部都是我自己,是我特有的本质。”[23](169)因此,费尔巴哈反对“身体和灵魂、精神和肉体的二元论”[23](191)的传统旧哲学,而赞成爱的哲学、感性的哲学,认为只有将身体和灵魂无矛盾地溶化于“人的心情之中、人的血液之中”以及溶化于“完整的,现实的,人的本质之中”[23](182)的哲学才是真正的新哲学。
费尔巴哈虽然指出了传统旧哲学的问题和弊端,但身体并不是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主要议题,他提倡的感性哲学也没有成为19世纪哲学的主流思想。真正把身体作为一个核心的哲学问题是从尼采开始的,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尼采高调声称:“我完完全全是肉体,而再非其他;灵魂只是肉体上某个东西的代名词罢了。肉体是一种伟大的理性,是具有一种意义的一个复合体……被你称为‘精神’的小理性也是肉体的工具,是你的伟大理性的小工具和小玩具。”“在你的思想和感觉后面,站着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一个不知名的智慧者——他名叫自己。他住在你的体内,他就是你的肉体。”[24]在此,尼采一反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意识哲学,也摒弃了基督教鄙视身体的旧识,提出“要以肉体为准绳。……因为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25],并且视欢乐的身体为强力意志产生的伦理基础。从尼采开始,尊灵魂贬肉体的思想开始解体,肉体不是灵魂统治下的奴仆,也不是伦理语境中的负罪之身,它开始拥有了登台露面的机会。
继尼采之后,在现代性思想的启蒙和激发之下,人的自我和非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此相应,人的身体欲望也逐渐开始得到正视,哲学也摒弃了那种非此即彼灵肉二分的观念,力图在身与心的统一中寻求一种可能。福柯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思考了权力对身体的规训,德勒兹探讨了身体的欲望生产机制,让·鲍德里亚透视了后现代社会中身体的消费属性,舒斯特曼则从审美的角度提出了身体美学这一概念。在20世纪的思想发展脉络中,这些关于身体的审视和重新思考,使得身体哲学成为一种新的哲学致思取向,也为克服传统灵肉二元论的对立与偏颇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
身体哲学的崛起得益于胡塞尔开启的现象学“悬置”历史和现实的先见主观判断以及“回到事物本身”的直觉把握。梅洛·庞蒂在借鉴胡塞尔“意识意向性”和“生活世界”理论的基础上,让哲学回归人与世界源初的生命根基,即“身体意向性”。在梅洛·庞蒂看来世界的问题始于人自身的身体,身体沟通着世界和人的联系、交织着内与外的分别,这个身体是存身于世界的在世之身,是生命体验和意识形成的具化之身。“身体既是可见者又是能看者。这里不再有二元性,而是不可分割的统一。被看者与能看者乃是同一个身体。”[26]这种身体是一种具身化、处境化的身体,是有性别的、有感情的、“能受一体”的、感性的身体,也是一种克服了主客对立而融合为一的的身体。与西方传统身心分离的学说不同,“在梅洛·庞蒂的学说里,一种身心二分理论业已被一种身心一体理论取而代之,其结果不仅使西方所谓的形而上学传统难以为继,也最终导致了有别于唯心主义超越的生命自身的超越这一全新的超越观的发现。”[27]因此,主宰和制约西方哲学传统的肉体和灵魂二元对立的思想在梅洛·庞蒂的学说中才得以真正地勾销,肉体不再是灵魂的桎梏,灵魂也不再轻盈地漂浮无据,二者无间地溶汇于人与人、人与世界“交织”的身体之中。在梅洛·庞蒂的后期思想中,他认为身体是遍布生命和艺术、是一种类似于宇宙元素的“世界之肉”,这种身体已经超越了物质和观念的传统区分,是一种广义的“事物的测量尺度”(étant le mesurant des choses)[28],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梅洛·庞蒂已经把身体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29],进而赋予了身体以全新的生命价值和哲学意蕴。可以这样说,“梅洛·庞蒂把思想的最深奥的一些东西深入到了身体,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3](279)因此身体哲学在梅洛·庞蒂手中得到了真正奠基。更重要的是,梅洛·庞蒂的这些深刻思考清欠了两千多年西方哲学对身体的债,把这么一个“脑袋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小”的、“畸形的西方哲学”[3](283)做了一次康复性的矫正。
但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裹挟之下,肉体狂欢和身体消费成了当今时代的显性话语,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大行其道,身体的消费性和享受性得到了强势彰显,原来身体的灵性维度却颓而隐没。这使得经过现象学还原过的身体蒙上了消费的阴影。如何应对消费意识形态的强势挑战,使得“身体”重归“身体本身”,成为当前身体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华人学者取道于中国古典哲学丰富的思想资源,并借鉴中国古人的生命智慧,对身体问题做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台湾学者杨儒宾抓住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生机勃发的“气”之特性,指出:“儒家身体观的特征是四种体的综摄体,它综摄了意识的主体、形气的主体、自然的主体与文化的主体,这四体绵密地编织于身体主体之上。”[30]身体的浑然一体性使得这四体自然地交织于形—气—心于一体的有机身体之内。还有杜维明提出的“体知”概念和吴光明提出的“身体思维”都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身体是一种身心合一的身体。在这个问题上,张再林教授曾做出过一些积极的思考,在张再林看来,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是一种“至为本我”“天人合一”“身心一如”“知行合一”“即用显体”“以生训身”“阴阳男女”“族类生成”“身神相通”“以文明身”[31]的身体,这些身体的特征和面向使得中国古代哲学从根本上消解了西方意识哲学中灵肉二元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一部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身体哲学的发展史”[32]。具体而言,在中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中,个体的立身之本首先在于身体的修行,这种修行不同于基督教对身体的禁欲,而是身与心的共处和并进,是实践中的知行合一,也是内与外的融会和合,这种修行观背后深隐的是中国哲学一元论的思维模式,因之身与心的融会离不开具体之身的依凭,故中国哲学更强调对身体的呵护和修为,注重将心性和生命的理解外化为对身体的安顿。同时,中国哲学擅长将玄妙高蹈的世间之理形象化为着实可见故事与实物,倾向于将形而上的虚实有无的思辨悬解于身体的撄宁。而西方灵肉二分思想的形成源自于西方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在意识的纯粹思辨中,很容易将灵魂的神圣和纯洁视为生命的最高追求,进而力图抛弃肉体的低劣和束缚,但身体的事实性存在使得灵与肉的二元根本矛盾无法予以消除。因此,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和对待身体的不同态度来思考灵肉二元的问题可以发现其背后的症结所在。同时,从身体哲学的维度来研究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全新范式的研究取向[33]对克服当今时代“欲望之身”和“符号之身”的思想泛滥也有着积极而有益的借鉴价值。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关于生命、感性、身体的论述与身体哲学的内在思路不谋而合。马克思同样承认感性生命之于历史的优先性,他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4]这个活生生的有温度、有情感、会呼吸的生命在现实生活中首先呈现为一种感性的存在。曾经被柏拉图鄙视过的激情和感性不再是污浊不堪的了,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原本就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35](107)。而恰恰是这种感性的、肉体的身体才赋予了生命以坚实的肉身性基础,也正是通过人自身的这种“全部感觉”才得以在对象世界中确证自己的存在[35](87),进而才使得认识和科学得以成为现实,“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35](8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肉身不在是孤立于人生和社会之外的自然之身,人不仅是自然的一份子,同时自然界也因生命的渗透、经由身体的劳动和实践成为了人的无机的身体[35](56)。与后来的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身体的劳动和实践不同,青年马克思更加强调人生命的肉身和感性,他指出:“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35](105-106)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反对灵肉二元的对立思想和哲学,而认同身心一如的统一,在1846年12月28日致信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就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蒲鲁东的灵肉二元论思想,他写道,“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36](541)恩格斯同样也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愈加意识到人自身和自然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36](384)。因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视野聚焦于现实人的生命存在”[37],他的“身体的逻辑是一种生命的逻辑”[38],是从“身体开始”对历史和社会做出了深刻的重新思考[39](193),因为这个缘故,晚近的西方马克思代表性人物特里·伊格尔顿甚至认为,“马克思是最深刻的‘美学家’”[39](197)。在当今欲望张扬的现实境遇下,重新践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这种身体思想,有助于消解当下社会以及思想界对身体的种种迷雾。
四、结语
哲学(philosophy)的本义是爱智慧,但这种爱智慧的哲学不能仅仅钟情于灵魂和精神,更不能摈弃对身体的思考,因为“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40]。身体是灵魂的载体和基石、人类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因此,保尔·瓦雷里宣称,“一切人体未在其中起根本作用的哲学体系都是荒谬的、不适宜的。”[41]身体的重要性在于,“身体是一个问题,而且是相关于每一个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42]。既然身体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认真考量这个切身的问题。
身体不仅验证了生命的内在品性,也为真理的认知提供了可能。我们在思考灵魂的问题时不能不加区别地脱离与其密切联系的身体本身,长久以来,身体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对灵魂与肉体、身心关系的简单化,剥离了灵魂的肉身性土壤。事实上,二者的关系不能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否定或拔高其中的一方,更不能僵化地用“辩证”一词含糊处理。正如杨绛先生所言,二者不是谁控制谁的问题,而是谁倾向于谁的抉择,其中生命自身的感觉和身体自身的逻辑会做出判断。只有正视身体的复杂性,承认身体对生命体验的重要性,我们才能借身体明了世界的意义。肉体里隐匿着灵魂自身的秘密,对身体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理解人类自身。
注释:
① 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中,地狱第一层关押的是诸如荷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没有受洗和信奉异教的人,所以真正的地狱应该从第二层开始。
② 关于这一点,有西方学者指出,上帝既非男、也非女,是一个超越了性别的存在。参阅Letty M. Russel. The Liberating Word: A Guide to Nonsex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M].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6: 17-18.
③ 米兰·昆德拉就认为色情主义对理解卡夫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参阅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118.
[1] 杨绛. 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45.
[2] 徐保耕. 电影讲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7.
[3] 张祥龙. 现象学导论七讲: 从原著阐发原意[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4] 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 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5] 但丁. 神曲: 地狱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27.
[6] 古斯塔夫·斯威布. 希腊神话和传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227.
[7] 薄伽丘. 十日谈[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
[8] Mike Featherstone. The Body in Consume Culture [C]// Mike Featherstone, Mike Hepworth, Bryan S. Turner.The Body: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1991: 182.
[9] G. 汤姆逊. 古代哲学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268-269.
[10] 柏拉图. 斐多[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17.
[11] 布莱恩·特纳. 身体与社会[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17.
[12] 托尔斯泰. 生活之路[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92-113.
[13] 色诺芬. 回忆苏格拉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4] 尼采. 曙光[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0: 2.
[15] 赫西俄德. 工作与时日神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 9.
[16] 歌德. 浮士德·第一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54-55.
[17] 爱克曼. 歌德谈话录[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93.
[18] 乔治·巴塔耶. 色情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9]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2.
[20] 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56-178.
[21] 约翰·奥尼尔. 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17.
[22] Adrienne Cecile Rich.Of Wome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M]. New York: Norton, 1976: 284.
[23]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4] 尼采.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一本为所有人又不为所有人所写之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68-69.
[25] 弗里德里希·尼采.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重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152.
[26] Maurice 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1951—1961 [M]. Paris: Éditions Verdier, 2000: 197.
[27] 张再林. “身体意向”: 审美意象的真正所指——中国审美意象之身体现象学解读[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 10-21.
[28] Maurice Merleau-Ponty.Le visible et l'invisible[M].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64: 197.
[29] Dillon M C.Merleau-Ponty’s Ontology[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3-244.
[30] 杨儒宾. 儒家身体观[M]. 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1996: 9.
[31] 张再林. 中国古代身体观的十个面相[J]. 哲学动态, 2010(11): 35-38.
[32] 张再林. 身体哲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生命辩证法——兼论中西辩证法的理论之辩[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3(3): 39-46.
[33] 张兵. 中国哲学研究的身体维度[J]. 世界哲学, 2010(6): 131-139.
[34]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11.
[3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7] 崔永和, 程爱民. 身体哲学: 马克思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生活旨归[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 1-6.
[38] 燕连福. 从资本的逻辑到身体的逻辑——对马克思哲学的另一种解读[J]. 教学与研究, 2012(10): 34-41.
[39] 特里·伊格尔顿. 审美意识形态[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0]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79.
[41] 米歇尔·昂弗莱. 享乐的艺术——论享乐唯物主义[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103.
[42] 彭富春. 身体与身体美学[J]. 哲学研究, 2004(4): 59-66.
Secrets of the soul hidden in flesh: an analysis of dualism of flesh and soul from body dimension
WANG Jianhua, ZHANG Zai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Duality of flash and soul has been the core issu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e contexts of ethics and religion, the body used to be considered the shackles and prison of the soul. This idea led to the prevalence of Puritanism, making the body absent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s record. So the body loses the right to express and does not exist in the field of reality. But the sensible and desirable body has been a fertile ground for the spirit of the human mind, with the body philosophy springing up and Merleau-Ponty’s thought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rationality of body presence has been obtained the most powerful defense.
duality of flesh and soul; sin of flash; raveling of body and mind; Merleau-Ponty; body philosophy
A
1672-3104(2014)06-0057-07
[编辑: 颜关明]
2013-02-27;
2014-10-25
王建华(1978-),男,山西沁县人,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哲学比较;张再林(1951-),男,河北南皮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哲学比较,身体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