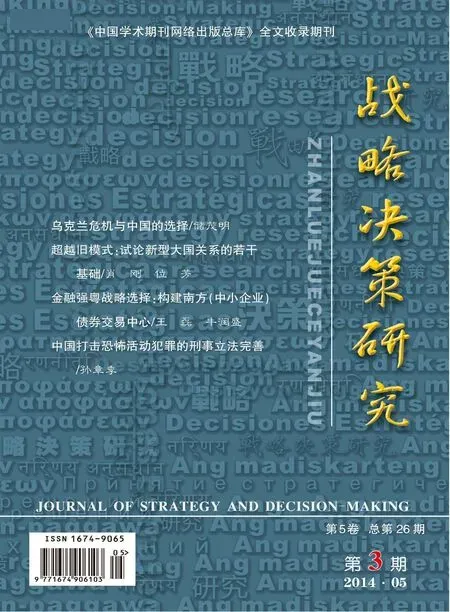超越旧模式:试论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基础
2014-01-11肖刚位芳
肖刚位芳
今天,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外交新理念不是偶然的,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对新型国际关系长期探索和实践的结果。从毛泽东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到向苏联 “一边倒”,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和艰苦实践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定型,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到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外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服务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是今天中国提出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的、实践的、价值观和道德的基础。当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的治理上发挥作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要使治理取得成效,建立在新型大国和强国关系基础上的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
一、中国新型国际关系探索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基础
什么是外交的 “中国梦”?从发展目标上看,一方面是为中国自己国家主权的巩固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国人民和平安稳的生产和生活造福,另一方面就是发展起来的中国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发挥中国建设性的、甚至是某种主导的作用,为世界人民和平安稳的生产和生活造福;从发展方法上看,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外交目标与造福世界的外交目标是同时进行的,因为中国所追求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必定建立在中国与所有发生交往的双边或多边关系都是和平、合作双赢或共赢状态基础之上,所以中国渴望的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建构,本身就是建构和平与繁荣的过程。中国又是大国,其举手抬足都会极大地影响国际政治发展方向的好坏。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始终把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视为中国发展的最为希望的外部环境和外部条件,所以,国际政治总体上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西方世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虽然时不时抬头,有时也很疯狂,往往造成世界和平已无希望的错觉,但有中国等一大批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未取得绝对优势。当然,营造中国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的举措,重心还是在为了国内的发展,这是客观现实的严峻态势所决定。中国政治上的统一还必须以强大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为基础才能得到巩固,客观现实要求中国必须埋头苦干,发展自己,而发展自己的核心是整合自身的力量,调动自身内在的积极因素,巩固自身的团结,使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使中国自身的发展不被打乱,不被严重分心,中国特别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且新中国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们一直都是在为此作努力。但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混杂交织在一起的对抗多而和谐少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只能一边搞建设,一边要想方设法地应对恶劣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压迫态势,中国不得不一边选边站队,一边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之道,国际环境最为严峻之时甚至同时出现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自身的发展,要完全做到从容不迫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出现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966年开始发生 “文化大革命”,外部环境恶劣的诱因恐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中国意识到,中国自身的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封锁状态下的发展。在国际环境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多、世界随时都可能爆发新的战争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梦想自身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甚至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几代领导人作出种种的外交努力,结束两极对抗,培育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扩大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几代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使中国自身发展的战略机遇及差强人意的国际环境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来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于迎来了外部环境相对有利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外交的中国梦实现了阶段性的目标,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现在可以说进入到了外交的中国梦的第二个阶段,那就是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为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伟大事业,发挥自己的强大作用和影响力。建构推动和谐世界走向实现的新型的国际关系,理所当然地成为外交的中国梦的第二个里程碑意义的目标。外交目标的选择往往因时因地因自身的实力条件而不同。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外交目标重点确实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稳定的周边和平环境,以便使自己能够安心地发展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军事国防,为此目标还要培养一大批各个领域建设自身国家的人才。
中国必须充分利用难得的和平机遇发展自己,而当时的和平局面又是很不稳定的,是经常流变的,稍不留神和平的局面又可能失去,所以,中国当时花了很多精力去稳定国际局势,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阻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图谋,总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还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世界总体处于一个中国可以相对安心地发展自身的国际环境。但是一个值得今天的世界共同思考的问题是,国家间关系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那种不冲突就不能浑水摸鱼,不对抗就不能显示自己的霸权威势,不搞意识形态的对抗就不能标榜损人利己的所谓国际影响力的旧的国家间关系,确实是必须在中国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努力下加以根本地改变之。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新中国建立一开始,中国外交所开辟之路就是新型的国家间关系之路,中国倡导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要求建立的国家间关系如果能够在全世界扎扎实实地落实,那么,整个世界必定是新型的世界,和谐的世界了。自然国家间关系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国家间关系了。正如习近平主席2013年10月3日访问印尼在印尼国会演讲谈到 “万隆精神”对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意义时所指出的, “1955年,中国和印尼两国同其他亚非国家携手合作,在万隆会议上共同倡导了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万隆精神至今仍是国与国相处的重要准则,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①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新华社2013年10月3日雅加达电。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凡是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度影响下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比较和平,国家间关系比较良好的,也就是说,发自中国的外交价值观,已经形成强大的软实力,积极地影响着世界朝和平与和谐方向发展。
《纽约时报》1997年3月13日发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媒体顾问的来信赞扬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美国 “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要调查 ‘96大选’报道了一个官员如是说该委员会将调查 (examine) ‘中国的情报机构是否……扮演了美国政治进程中的某种作用’。你们也报道政府官员说联邦调查局已开始调查中国政府在合法或非法的白宫和国会的游说 (lobbying)上可能扮演的角色’,这样的断言(allegations)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政府是1950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之一,在其中,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和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中国始终如一地坚持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这一基本原则和克制以任何方式卷入美国政治,美国更多的人已开始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提倡更频繁的接触。两国的交流应该在不同层次上扩大。”②“China Has Played No Role in U.S.Politics: [Letter],” New York Times,Late Edition 13 Mar.1997:26.在美国如此重要的报纸上报道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少说明美国的媒体想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对事物判断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当然,就整个西方世界来说,它们的外交哲学最爱好的是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全局,以一时否定整个历史时代的哲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行为规范,发明它的国家也好,接受它的国家也好,都应该模范遵守。但是,我们不能期待它在实践的过程中绝对不会出现一点问题,即使是倡议它的中国和印度,由于老殖民主义者英国遗留给印度的负资产,导致中印曾因边界问题发生战争。中印两国发生短暂的边境战争就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失效了?其实不然,这只能证明,即使是好的东西,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好的东西,也往往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不会一帆风顺,但是,由于它是先进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生命力一定是顽强的,所以它只会越来越趋于强大。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20世纪消极和负面影响国际政治最大的、最严峻的因素,因此,中国所倡议的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构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难有根本性的作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刚刚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取得民族独立的亚洲国家,充分意识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价值,也完全愿意按照它来规范国家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治国经验不足,容易受到狡猾的帝国主义和老殖民主义者的挑唆,使得正在实践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崭新理念的国家之间出现一时的严重冲突,这样就为西方帝国主义者和老殖民主义者们找到了诋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机会,由此,西方世界虚伪的 “自由、民主、人权、博爱”观又可以大行其道了。西方国家诋毁和歪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手法之一是否定中国的这一高度的战略性原则,认为她不过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是暂时的权宜之计。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终将放弃之。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视为策略而不是中国长远战略的西方学者,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访问研究员保罗·希尔 (Paul Heer)算得上是突出的一位,他在2000年美国影响很大的 《外交》杂志上撰文说, “在过去的20年中,北京描述其总体外交战略 (overall international strategy)为基于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手段的关键因素已经包含了北京在其政策进程中将能够服从包括军事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事情 (subordinate everything),要达到经济发展目标,和平的外部环境对于其目标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等理念,北京能够对经济发展给予关注以应对其它关注的损害 (detriment),因为北京不能面对严重的外部威胁。”③Heer, P.(2000).A house united, Foreign Affairs, 79.4, Jul/Aug p21.也正是因为西方国家这样的思维作怪,所以,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自身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突破性发展时, “中国威胁”论马上就占据了西方的舆论与政治领域,此种情形最大的负面作用,就是使本来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新型关系失之交臂。
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指导思想基础
2000年1月20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十年所作的总结中指出, “这十年中,我们还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
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建立了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④《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6页。在江泽民所指的国家中,除了俄罗斯外,其它国家都是西方国家。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在江泽民所指的要建构的新型大国关系中,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发展是平稳扎实的,而中国和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面向二十一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虽然建立起来了,但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和它们的新型关系目前还处于比较艰苦的探索之中。不过,要找到中国和它们建构新型关系的方法,关键的还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比如,日本也是中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对象之一,对于和这样一个国家如何建立新型关系,建立什么定位基础上的新型关系,确实是应该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深入探讨的。马克思在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指出,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今天我们在建构和日本的新型关系时,要弄清楚建构的方式、新型关系的定位等问题,必须跳出今天时代的的局限,必须与日本过去的历史相比较,这样,我们就发现,中日新型关系的建构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持日本和平发展的势头,保持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继续发展某种关键的作用,使日本和平的力量始终压倒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力量。判断日本历届政府及其行动,我们发现越来越右倾的日本政府和 “和平”与 “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和日本近代以来对外扩张特别第二世界大战日本法西斯给亚洲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而形成的日本人民反战争、求和平的良知,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今天中国和日本建构新型大国关系,首先得提醒和促使日本政府从尊重人民的良好意愿开始,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问题不解决,中日新型关系的基础就不存在。邓小平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指出, “日本应该知道自己的历史。它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还进一步提出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军事大国的含义是什么?日本想在一千海里内承担军事义务,这个性质就变了。如果形成政策,不但中国人民,整个东南亚人民都会提出问题的。”⑥《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32页。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指导思想基础。
三、反霸权与强权是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础
邓小平指出, “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威胁、颠覆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⑦《邓小平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邓小平这段重要的谈话,可以视为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因为中国今天已初步将自己建设成为政治、科技、经济和文化的综合性大国,这样的大国如果选择做超级大国,也是具备一定的实力条件的,如果那样,中国和西方世界大国的合作越是紧密,越是愉快,就越是反动和腐朽。在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进程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随着中国和西方大国新型关系的确立和战略合作的深入,我们外交中一贯重视的基本原则也可能会被淡化。邓小平在两极对抗的时代曾坚定地指出, “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现行政策不能变。只要坚持现行政策,搞它几十年,中国会发展起来的。”⑧《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9页。今天我们同美国建立新型的关系,邓小平的这个重要的基本思想同样要坚持之,而绝不做好好先生。孔子说过, “乡原,德之贼也。”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孟子也说过, “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像宦官那样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人,就是好好先生。
1982年12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说, “中美两国发展关系符合两国自身的利益。我是主张中美交朋友的,这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从战略角度出发,中美关系应该发展,但必须相互信任。有没有令人鼓舞的消息,恐怕主要是这个问题。大家努力吧。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美国有不少人问,为什么现在中国也批评美国是霸权主义。你们在黎巴嫩搞的事情,使我们没有办法不讲。”⑨《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77页。1983年9月,邓小平对来访的金日成说, “美国人说,你们为什么批评我们是霸权主义,不要这样讲,太刺耳了。我说,你这个 ‘航空母舰’是什么东西,什么政策? 《与台湾关系法》是什么政策?这不是霸权主义是什么?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技术转让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尽管我们这个时期关系好起来了,而且我们希望关系发展,但是 《与台湾关系法》存在的本身就会带来危机。美国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这就是对中国实行霸权主义,那不行。”⑩《邓小平年谱》(下),第935页。邓小平还指出, “从一九七二年起,我们同美国的关系逐步开始发展,尽管有曲折,总的还是发展了。有发展并不意味着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不反对,不批评。我们多次批评美国 ‘四个航空母舰’政策。台湾问题是中美间最大的疙瘩,可能今后还是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带来某种冲突都可能。”《邓小平年谱》(下),第 977页。中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从来也没有放松过批评,邓小平的这种拒绝平庸和拒绝充当好好先生的外交气质,在倡导新型大国理念的今天,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永恒的理念,永远贯彻下去。
四、新型大国关系的哲学基础
中美这两个各方面差异都很大的国家如何建立具有创新意义的、超越过去时代经常出现的大国之间冲突的关系,这是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的问题。邓小平在中美尚未建交的1975年4月会见美国国会领导人时指出,中美 “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国际政治的许多主张也不同,但我们两国还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甚至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些共同的语言。”《邓小平年谱》(上),第 31页。正是因为两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共同语言,中美才在几年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样,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是因为两国在国际问题上存在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的强大动力。1988年9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部长卡卢奇时就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对卡卢奇说,“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全心全意地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我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中国是一个守信用的国家,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问题上,我们欢迎谋求缓和的趋势,我们反对谋求霸权。最近几年的历史证明,所有谋求霸权的都遭到了失败或正在失败。中美关系近几年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我们应该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这样两个大国,不友好是不行的”。《邓小平年谱》(下),第 1246-1247页。中美两国要做到 “不友好不行”,没有创新的思维,没有中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顽强恪守,没有美国的洗心革面,那将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今天强调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强调和长期受到西方世界排斥诋毁的、和中国有传统长远战略关系的核心价值观如何扩展到西方世界基础上所建构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和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这里的关键是中国和西方大国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如何稳定地向前发展。要发展两个社会制度和现代化发展阶段完全不同的中国和西方世界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其核心是中国如何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打交道的问题,因为中美关系确实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美国经常用计谋、用设陷阱的方式来对待一贯真诚对待美国的中国,这样的严重不平衡和不对称的双边关系要处理好,的确要有新的创造和新的举措。
今天,美国可以说是破天荒地积极回应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美国国务卿克里就说, “中美已同意面向一个由我们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在阳光之乡峰会 (Sunnylands Summit)上所宣布的新型的关系模式 (a new model of relations),它是基于务实的合作和和建设性的对分歧的管理,我们承认需要避免掉入视另一方为战略对手 (strategic rivals)之陷阱。值得赞誉的是我们正在推动我们在从气候变化到野生动物的走私到军事的磋商和整个世界平衡增长的促进上之伙伴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新型关系的一部分是承诺致力于坦率地对特别是我们不同意,误解可能导致误判等敏感问题的讨论。”Kerry, J.(2013).Remarks With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Before Their Meeting,Secretary of State,Benjamin Franklin Room,Washington, DC,September 19.克里对中国领导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承认,实际上间接地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核心精神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今天时代的创造性应用,如果美国不但在态度上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念,在行动上也遵守之,那么,就意味着新型大国关系真的在中美这两个世界上可能差异最大的大国之间实现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最有生命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原则,终于攻克了世界上国家间关系交往原则和准则上死守强权和霸权僵尸最为顽固的堡垒。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美国倾向于称霸而不惜对抗的对外政策文化会有根本的改变。 《纽约时报》的新闻分析就指出,中美 “两国领导人将展示习近平所称 ‘新型大国关系’(new type of great-power relationship)是无保证的。美国总统的遗产 (比如把和它国保持低级的武力对抗视为传家宝)是不能随便受到损害 (damage)的。要知道,人人皆有赞成掌控武力以保持低级别对抗的动机。”Sanger,D.E. (2013). Xi and Obama See Pitfalls That Might Be Difficult to Avoid: [News Analysis], New York Times, 10 June,A.8.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句话来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说切中了要害,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深入探讨两国如何建构新型的大国关系,怎样建构才能使两国成为地球上两个特性差异很大,按照传统的观念和历史的经验,往往会走向严重冲突甚至战争的国家不但保存了各自的特性,而且还实现了真正的共赢,给世界的和谐发展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标杆。
这里不妨用老子 《道德经》第十五章的哲学意境来探讨新型大国关系的哲学基础。老子说,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此段话的现代汉语大意是:“古时善于实行“道”的人,微妙、高深而又通达,深奥得不可记述。因为不可记述,所以只能勉强对他作一描述:(他)谨慎缓慢啊!就像冬天(冒着寒冷)涉水过河。谋划盘算啊!就像害怕四邻(的围攻)一样。严肃庄重啊!就像宾客一样。涣散疏松啊!就像冰凌消融。混沌无知啊!就像未经雕琢的素材。积厚深沉啊!就像浑水一样难以看透。空旷深阔啊!就像(空虚的山谷)一般。浑浊的水静下来,慢慢就会澄清。安静的东西动起来,慢慢就会产生变化。保持这个“道”的人,不追求盈满。因此能吐故纳新去旧更生。”今天,中美两国都要善于找到发展两国新型关系之道,新型关系之道可以说是有基础的,至少中国一直在用新型方式处理中美关系,而美国一直是用它的传统方式应对中国,只不过美国传统的霸权式的、傲慢式的方式越来越脱离其人民,越来越和国际政治的发展大趋势背道而驰,从根本上讲,也越来越损害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国政府只有成为采取有利于美国人民之国际关系之 “道”的政府,它才会真正找到和别国建立新型关系的办法和路径。
邓小平在谈到解决人事问题与国家稳定的关系时说, “解决人事问题,也是改革问题。我们党的领导成员有大幅度的更新,这件事很重要。……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出了乱子就是大乱子。中国出了大乱子,收拾起来很不容易。”《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7页。所以邓小平说, “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7页。邓小平还说过,“十亿人口的大国,应力求稳定。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0页。2013年10月7日,习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的主旨演讲中指出,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新华社2013年10月7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电。邓小平和习近平都是从 “治大国”小心谨慎如 “烹小鲜”这样的意义上考虑的。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前面对俄罗斯等媒体引用过此句话,无独有偶,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在其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过此句话以作为治国重要警示。“President Reagan 1988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History records the power of theideas that brought us here those seven years ago.Ideas like the individual's right to reach as far and as high as his or her talents will permit, the free market as an engine of economic progress and, as 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Lao-tzu, said, ‘Govern a great nation as you would cook a small fish; do not overdo it”.http://www.janda.org/politxts/State%20of%20Union%20Addresses/1981-1988%20Reagan /rwr88.html 。 This isthe Home Pageof Kenneth Janda,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五、以 “人本”对话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价值观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2年22期,第22页。新型大国关系的人文交流,重点应该抓住以 “人本” (西方国家话语为 “人权”)为核心内容的交流与对话; “人本”可以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基础。中国不但要为自身 “人本”的全面实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在自身的 “人本”建设和发展的同时,让 “人本”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而 “人本”思想一旦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主旋律,必将造福于整个人类社会。正如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美国 《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题为 “实践中国梦”的署名文章中指出的, “中国承诺通过和平发展实现中国梦,自从中国梦紧密地和世界范围内的其它人民的梦联系起来以来,中国就承诺帮助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邻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他们的发展,中国也将和其它国家共享发展机遇,使得他们要实现的梦想之努力增多更多的便利条件,中国希望和外部世界一道,看到双赢的合作与共同的发展。”Yang Jiechi, Implementing the Chinese Dream, The National Interest,September 10, 2013,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 /implementing-the-chinese-dream-9026.中国的 “人本”理念既然可能为世界人民的精神正能量的提升提供强大的支持,中国就不能让它永远只为中国所独享,藏在深闺人不识,而应该无私地奉献给世界,为世界人民的梦想服务。
首先是以 “人本”为核心内容而非西方的 “人权”的交流与对话。诚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 “人权”理念的正面价值是持肯定立场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写的重要著作 《神圣家族》中,就对 “人权”理念有过系统的论述: “至于说到 ‘人权’,那我们已经向布鲁诺先生证明过 (‘德法年鉴’上的 ‘论犹太人问题’):不是群众的辩护人,而是 ‘他自己’不了解这些 ‘权利’的实质,并且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们。同布鲁诺关于人权不是 ‘天赋的’这种发现相比较 (这种发现近四十多年来在英国有过无数次),傅立叶关于捕鱼、打猎等等是天赋人权的论断,就应该说是天才的论断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页。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 《神圣家族》中进一步指出, “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5页。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还指出, “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5页。恩格斯指出, “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6页。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看到了 “人权”概念的合理价值,而且认为它是“天赋”的,同时特别强调 “人权”之道的理性价值,换句话说,没有理性的 “人权”那是一文不值的,还肯定了人权是对教条和神权的代替,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 “人权”概念看作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它存在明显的时代性,是新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封建桎梏提出的响亮口号,不但如此,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新兴资产阶级的 “人权”观看作也只是资产阶级为达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的而提出来的,内容十分肤浅的东西。恩格斯在他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的遗稿中针对法学教授安东·门格尔博士从 “法哲学”的观点来 “教条地详尽阐述”社会主义史时有这样一段话, “够了。教授先生是力求用法哲学的精神来解释社会主义,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些简短的法权公式,社会主义的 ‘基本权利’,人权的十九世纪的新版。这种基本权利当然只有 ‘微小的实际效果’,但是作为 ‘口号’, ‘在科学领域中也不无益处’。这样一来,我们已经降低到我们现在只有和口号打交道的地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3页。也就是说, “人权”的理念并不具有超越时代的普世意义。特别是资产阶级在战胜封建阶级取得政权的主导和掌握其国家的命运之后, “人权”就演变为新兴资产阶级自身独有的特权,别国的人权和民族的生存权就成为 “人权”概念发明者随便践踏的目标,使 “人权”堕落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遮羞布而已,这更加显示了西方 “人权”理念的虚伪性和反动本质。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 “人权”时代局限性的重要观点说明, “人权”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和其非 “人”的、但是决定人的生存与命运的 “天然”权力协调起来,比如和 “自然生存权”、 “宇宙生存权”统一起来,因为人的权力如果是牺牲自然的生存权力和宇宙的生存权力,比如,人类把地球的大气环境都破坏了,人类连呼吸都不可能了,还谈什么 “人权”?为了人类短期的利益或者是某些大国为了在国际上显示自己的权威,对宇宙空间进行破坏性开发,使宇宙空间的运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严重的情况导致宇宙的毁灭,同样也将毁灭人类本身,哪里还谈得上什么 “人权”?也说是说,西方的 “人权”理念已经严重地落后于时代,而能够充分适应时代发展的高于西方 “人权”思想的理念,在今天的地球上就是中国的 “人本”思想,因为中国的 “人本”思想,不但包含了对人的权力的追求,同时高度重视人的权力与自然的权力和宇宙的权力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 “人权”的宝贵论述,确实是中国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重要思想,当然也自然是丰富中国 “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 “人权”理念的认可完全照单全收,我们必须将 “人权”理念中国化,中国化后的人权观念,很自然地就是 “人本”观念,因为 “人本”的理念,不但包含了 “人权”的合理成分,更有数千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对人类幸福和自由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追求。如果开发出来并进行国际交流,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六、群众基础是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根本
“贵而以贱为本,高矣而以下为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国的人民必须对此充分支持和理解,只有这样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才会有根基,根深才能叶茂。同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也是新型大国关系重要的群众基础。由于中国长期注意与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友谊,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信赖的朋友很多,当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关系时,这些朋友发挥了有力的杠杆作用。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美国发展同中国的正常关系的动力之一,就是看中了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关系。一旦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就可以发挥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重建关系时的桥梁作用,从而软化美国长期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反动性所造成的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长期形成的紧张关系。卡特在回忆录中说, “同中国交朋友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潜在的益处,其中之一是中国能够悄悄地左右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而我们同这些国家交往是很困难的。大多数革命政府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向美国,而苏联人有时候可以毫无障碍地同它们建立新关系——主要是通过向它们出售武器。中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信誉很高;我们认为,同中国合作是促进美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和平和了解的一种手段。”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很显然,中国不能放弃和第三世界的传统友好关系,而巩固和他们的友谊的最有力的办法,就是要坚定地支持他们所追求的包括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内的一切进步事业,特别是要鼓励他们重新团结起来。试想,如果中国和第三世界在团结问题上投鼠忌器,患得患失,因为担心支持第三世界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进步事业会造成得罪美国,而减弱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支持甚至放弃支持,中国不但会在第三世界中失去朋友,陷入孤立,同时也会因为和帝国主义国家交往时缺少有力的杠杆而为实用主义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轻视,当然,更加严重的是,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形势就会更加严峻。由此我们可以充分地理解邓小平在1975年2月会见冈比亚外长时说的 “我们现在说我们属于第三世界,就是到将来我们比较发达了,也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和1977年10月会见法国媒体界人士时说的 “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不管它发达到什么程度,永远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年谱》(上),第229页-第230页。这两段话,完全是出于对国家的根本利益考虑的、深远的战略价值所在。由此说来,中国无论如何发展,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身份不能丢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中国外交立足点的战略地位不能丢掉。为了中国的利益,为了第三世界的利益,甚至为了达到和西方国家发展务实的、正常的和有吸引力的新型关系,中国都必须牢牢坚持自己的第三世界身份不动摇。如果丢掉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这就好比庄子对惠子关于 “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的发问一样, “大地广且大”就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 “厕足而垫之”地即脚能踩踏的一小块地盘就是中国本身。中国外交要发挥强大的作用,如果只是中国单兵作战,也就是只留下脚能踩踏的一小块看似最 “有用”之地,而忽视 “大地广且大”的看似 “最无用”的广大第三世界的价值和作用,就象是把脚踩踏的一小块之外的地全都挖掉,甚至一直挖到“黄泉”——彻底失去第三世界的依托,中国外交本身就不能存在,中国外交之 “足”就立不住,中国外交的作用就很受局限。如果没有广大第三世界的战略依托作用,中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和美国的新型关系,就难有大的作为。
当然,在向美国等西方大国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如何既能够使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可持续,又能使霸权主义受到恰当的遏制,同样得有新型的手段和新型的对策,过去和现在的手段绝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模式,毕竟今天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对话的、合作的时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疯狂也主要是通过对话和交流遏制之和消解之,同样如邓小平所说, “中国对超级大国,对霸权主义,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也不管霸权主义来自哪一方面,都是采取反对立场的。当然,我们有时侧重于这方面,有时侧重于那方面。我们同世界上所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要加强合作。”《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29页。
七、大国对弱国和小国尊重所形成的道德基础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凌辱弱国。”《邓小平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新型大国关系一个很重要的道德基础,是中国承担着推动西方世界大国对小国和弱国的尊重。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的中国先哲老子曾经研究过当时应该建构的以处理好大国与小国相互关系、建立大国与小国和谐关系的新型国家间关系问题。他作为周朝 “守藏室之官”,目睹周天子的权威尽失,天下已是列国林立,出现了 “超级大国”,而当时的大国对弱小国家可能往往采取的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政策,故老子希望改变这样的严峻状况,于是提出了他的新型国家间关系的主张。他说,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的意思是,大国好比江河的下游,天下的牝雌。天下雌雄交合,雌柔常以安静战胜雄强。因此雌柔安静无争,所以宜居于下位。所以大国屈己尊重小国,就得到小国的归顺和信赖。小国屈己尊重大国,就被大国所容纳。因此,有的谦让而有所得,有的谦让而归附他国。所以,大国谦让不过是想兼并蓄养小国,小国谦让不过是想要侍奉大国。如果要使双方都满足他们的愿望,那么,大国宜居于谦卑的地位。
新中国完全摒弃了旧中国时代对小国的那些不恰当的政策,做到了真正的平等和尊重,既继承了老子的大国应该处于谦卑的地位,同时又扬弃了 “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对小国谦下,不是为了取悦小国而使小国心甘情愿 “屈服”中国,即今天的中国既不追求老子所说的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也不希望 “小国不过欲入事人”的状态。毛泽东曾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表示, “如果泰国愿意,我们可以同泰国结成友好关系,根据五项原则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中国有三百万华侨在泰国,其中很多人反对中国政府。如果我们同泰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否要把蒋介石分子赶出泰国呢?我看不必,只要他们不侵入我国国境。在缅甸的华侨中也有蒋介石分子,他们至今不挂我国国旗,而挂蒋介石的旗子。”《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从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中也可看出,新中国对待小国的外交政策,是谦下但不谋求 “下以取”,中国作为大国对小国实践谦恭但不谋求支配小国,使中国通过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真正地达到了大国和小国 “两者各得所欲”的双赢局面。大国真诚地、平等地对待小国和弱国,才能使大国间的新型关系在伦理上和道德上立得住。
八、全球治理紧迫形势所造成的基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文明的发展要求必须采取全球治理的方式,人类的各项事业才能可持续发展。这是形势的需要,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的紧迫现实和唯一选择。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单打独斗、只关心各自利益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各种双边关系,或者是区域性的排它军事政治同盟体系,都无法解决未来人类由于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资源等的过度开发所造成的,足以在不久的未来造成人类文明毁灭的可怕前景。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使人类的共同家园能够可持续地存在下去,不但要使人类共同体文明生存下去,同时也要使动物的、植物的生命共同体文明生存下去。从一定意义上讲,动物的、植物的生命共同体的生存价值和道德天然地高于人类本身 (因为动物和植物没有制造过像人类那样对地球的严重破坏),人类不能再以自己是文明的动物自居而继续无休止地破坏性开发。全球治理首先就是要治理人类自身的行为,而拥有巨大实力的大国和强国首先要担当治理的首要责任。而真正能够担当起全球治理责任的大国,一定是早已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关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如果中国所倡议的新型大国关系取得成功,全球治理也将会获得更大的动力,使全球治理形成合力。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社会日益形成一个强烈的共识,就是希望中国等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九、结束语
今天中国提出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是有着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构的新型关系的实践基础的,虽然先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的先进是外交原则所建构的新型关系的发展,一时倡议国之间非 “和平共处”的状态而受到西方世界的揶揄,但用历史的长镜头来看,它确实是最有生命力的,是处理国际问题、处理和建构新型国家间关系最好的原则和价值规范。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又进一步成为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规范。在探讨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对构成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基础进行梳理和研究,以便我们在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发现新亮点,找到新办法,作出新举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对接,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