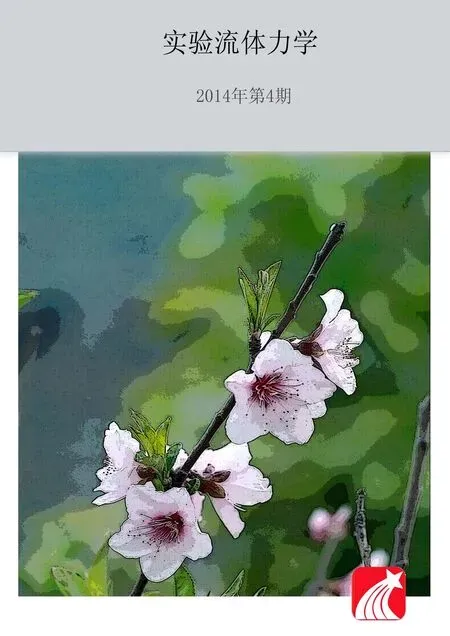凌云沛先生的一生经历
2014-01-10蔡德麟,邓学蓥
(一)书香门第严母调教有方
个人奋斗孤僻性格形成
凌云沛先生,1920年5月8日生于广东省钦县城内村书史塘。他父亲凌志鹏号凌霄是秀才,被同乡公认为当地的有志青年,早年离乡在外面闯荡,对清朝末年的时局不满,崇拜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拥护者,非常赞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当时曾多次给广东省官员上“如何富国强兵”的意见书。父亲的这些开放意识对凌云沛后来世界观有着很深的影响。他母亲郑荣英又名郑伟卿则是另一类型的女性。她是清朝一知县的女儿,本是千金小姐,但在她17岁时父亲因其任上的管账人携款外逃而受牵连。遂倾其家中所有钱财变卖还款,尚不足抵债而很快气死。家中留下她和母亲、弟弟3人,几乎沦为乞丐。这时的郑荣英便承担起家中的顶梁柱,辍学承接一些刺绣的活来维持3人的生活。到了19岁,为了解决家庭的困难且还想继续上学,她同意了媒人的介绍,与凌志鹏结婚。婚后虽然经济仍十分困难,但比起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却有了改善,还能如愿继续上学,直到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教师。郑荣英是位有个性、有主见的人,在家中无论生活还是教育孩子方面,都是按她的意见办,凌志鹏不太参与。她要把孩子培养成“饱学之士”,经常以她的经验、年轻时的遭遇教育孩子们,常说一切必须要依靠个人奋斗,凭本事才能站住脚跟。他要求孩子必须好好学习,凡学习成绩好的,给予奖励,各方面予以优待,学习差的必有惩罚。凡有孩子在外与别的孩子争吵发生矛盾,不论是非曲直,先打自己的孩子,致使凌云沛小时候就只顾埋头读书,很少与人交往,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原来的成绩不如哥哥,在家中母亲总是袒护哥哥,后来凌云沛因只顾读书,成绩上去了,当他把成绩单拿回去后立即就改变了母亲对他的态度,老师同学也对他刮目相看。不仅使他养成了靠个人奋斗以实力争取权益的意识,而且也培养了他喜欢大量阅读各种书籍的好习惯,特别是后来读了大量的科技、数理、天文及名人传记等书后,便立志要成为科学家。
1936年面临考大学的选择,凌云沛先生准备报考中山大学的理科,父亲同意他按其兴趣选择专业,但他母亲表示反对,认为理科不好找工作,应以实际出发,报考工程类型的专业,于是他同时报了中山大学理科专业和南京中央大学航空工程专业,并以优秀的成绩被两校均录取,但他最终还是到中山大学就读。1938年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凌云沛为准备抗日,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军训。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要航空救国,决定牺牲大学两年的时间,重新考取了已经从南京搬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航空系。但是航空系一是要求全体学生参军、二是要加入国民党、三是纪律极严很不自由,使他在很郁闷的状态下勉强学习了4年,毕业后去向仍是很有限的,他很想去民航(大家都认为是最好的出路),但没有关系是进不去的。其次是去空军,但中央大学的大学生军人不是正统军,算是杂牌,也是不易进去的。于是他走进了滑翔机厂,由于和他想搞航空研究的愿望不符,同时与领导关系又不睦,只干了两个月就离厂了。后来经考试又进了航空公司当练习机械员,并被派往印度加尔各达飞机修理厂实习1年,1年后可以继续留在那儿工作。虽然工资很优厚,但是凌云沛亲眼看到英国人对待印度人的蔑视态度和印度人对待中国人的加码使用,在那儿工作等于是当别人孙子的孙子,所以凌云沛也不愿留在那儿。回国后先后到成都空军研究院飞机层板厂及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当设计员,计算飞机性能等工作。
1947年经朋友介绍到昆明云南大学任教,这是凌先生多年的愿望。在云大他先后讲授“实用空气动力学”、“飞机仪表”等。解放后云大的航空系与四川大学航空系合并,从昆明转入川大。在川大他编写讲义,讲授“空气动力学”和“飞机设计”等课程。通过解放前几年的工作,凌云沛深感国民党的腐败和治国无方,对新中国充满希望。在云南大学他除了讲授3门专业课外,还给学生讲政治课,担任一年级的级主任,虽然肩上担子很繁重,但心情是愉快的。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全国8所高校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川大航空系是其中之一。当时凌先生认为这一举措对我国的航空工业发展有利,建立一所专门培养航空人才的高校也是他和许多老师的愿望,从而主动参加北迁的筹备工作。
从1952年到北京后凌先生就一直献身于北航的空气动力学专业。
(二)科教兴国科学进军热潮
高教事业气动实验奋斗
从50年代初到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里,凌云沛先生在实验空气动力学领域中无怨无悔地辛勤耕耘着,执着地探索着。凌先生到北航后,分配在师资雄厚的飞机系空气动力学教研室,这里有著名的陆士嘉、伍荣林、张桂联、徐华舫、曹金涛等一批留学归来的学者,相对年轻的凌云沛先生积极筹备实验室的规划和建设。时任北航副院长的沈元教授也是气动专家,他和陆士嘉等老教师深知气动实验基地的建立对北航的发展极其重要。所以在建校后不久,就不断将50年代初入学的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留在教研室内,其中大部分用于实验室的建设。另外,又招聘了一批责任心强、积极进取、热情肯干、能吃苦耐劳的青年实验技术人员。凌云沛先生就是与这样一批人一道,经过短短几年艰苦努力建成了从D1到D5一系列低速风洞和形象化教学的陈列室,成为北航的优秀教学和科研试验基地,有些设备直到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凌先生还筹建了水力学实验室,并为学生开出“水力学及水力机械”课程。凌云沛先生在1956年被评为院先进工作者,出席二机部(当时北航属二机部领导)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会议。
1956年是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年初中央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周总理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对我们国家经济和文化诸方面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周总理还指出应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给他们应有的信任和支持,应该同全心全意依靠工农一样最充分地依靠这些更多地掌握人类智慧的知识分子。周总理讲话给所有知识分子极大的鼓舞,凌云沛同样深受感动,他同几位老先生交谈时认为总理的话句句说到我们心里,我们这些人就是希望国家强盛,而强盛一定要发展科学,发展科学自然是应该依靠知识分子的,所以周总理是深深懂得、理解知识分子的。凌云沛在此前曾对高校政治活动多、开会太多有意见,并在“三反”运动时提出“反浪费”在高校首先应反对对时间的浪费。为此,曾受到过批评。然而,对这次会议,特别是周总理的讲话,他深感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信任,是国家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庄严任务,认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本来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力,做得不错了,现在却感到客观形势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与主观之间的距离相差很远,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争取多做一点贡献。此后组织上让他担任实验室副主任,继之担任102教研室主任,成立气动研究室时又任命他为研究室副主任兼高速风洞实验室主任等职务。虽然他过去一直不愿意担任行政工作,认为自己不适合做组织领导工作,更认为行政工作耽误时间,影响业务工作,也易得罪人,吃力不讨好。由于思想认识的转变,一次次地接受了这些工作,并暗下决心,努力做好,全身心地投入到G3高速风洞的筹建中。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北航在周总理亲自关心并批准15万元经费自行设计制造“北航一号”的鼓舞下,沈元与气动教研室的领导们提出建造一座中型超音速风洞以填补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要建这样一座高速风洞,在当时确实是十分困难的,这一任务又一次落到了凌先生头上。凌云沛先生不畏艰险,狠抓关键技术攻关,积极组织测量、调压等为风洞运行配套的5项技术工作,并到处跑材料,与学校实习工厂老工人商讨加工问题等等。虽然困难重重,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洞体的建造。而后续工作仍是很艰巨的,如流场改善和测量设备建设等。又是通过大家埋头苦干共同奋斗,最终于60年代初验收,该风洞的各项性能指标与当时刚引进的同类型高速风洞相同。当时有位苏联专家到G3参观时深感震惊,认为一个学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力更生造出如此高水平的超音速风洞实属不易!G3风洞的建成及之后的一系列成功试验,获得航空部多次奖励。凌云沛先生于1960年被评为北京市第一届文教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G3风洞验收之后在校内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接受歼5性能实验、某飞机设计所的型号研究和气动布局实验等,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凌云沛先生结合超音速风洞的设计建造和调试工作,还先后写出了“超音速风洞设计从误差分析提出各项技术指标”、“B4拐角六分力天平”、“B4天平设计及使用问题”等论文。以后又结合设计单位提出的任务,进行了“双立尾对高速飞机横侧安定性影响的实验研究”、“尾喷流(冷、热)对翼身组合体气动特性影响的研究”,给设计单位提供了有价值的实验数据。
1960年以后凌先生还兼任了国防科委航空技术委员会成员,参加国家风洞规划工作;兼任国防教材编委会气动小组成员,进行规划和审定空气动力学统一教材;参加规划及审议全国风洞建设等。
文化大革命10年中虽然教学科研处于停顿状态,凌云沛先生仍坚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如对六分力拐角天平的研制和改善、进行了“降落伞超音速性能和超音速尾翼颤振试验”研究、接待朝鲜留学生的教学和为他们单独编写教材、亲自给他们授课。
文革之后凌先生虽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着严重的气管炎老顽疾和新添的冠心病,但他心情舒畅,鼓励大家多承接课题,努力开展研究工作,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在大量调研和撰写“引射驱动式跨音速风洞的最新发展及现实意义”报告的基础上,他同青年教师张华(现已是流体力学所教授)一道设计、研制了验证性引射式跨音速模型风洞,写出“混合与扩散同时进行的环行引射系统引射性能实验研究”的论文,在第八届全国风洞试验会议上(1989年成都)获大会优秀论文奖。该研究探讨了引射器“混合与扩散同时进行”新模式的可行性和适用范围,研究了该系统的引射性能;提出了引射系统高效率及小型化的有效途径。这一研究为后来气动中心正式建造大型风洞提供了经验。
凌云沛先生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贡献,用徐华舫、赵世诚两位资深教授在80年代初的评价是很恰当的。他们说:“凌云沛同志几十年来在实验室建设上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先后主持筹建水力实验室和高速风洞实验室。高速风洞建成后又致力于流场改善和测量设备建设等工作,其中许多工作是在国内没有经验的情况下首创进行的,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说明了他对超音速风洞实验技术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并有较高的水平。”
(三)体弱多病慢支心衰缠身
置之度外探索规律有效
凌云沛先生是一个喜欢探索、办事认真的人,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养成了严谨、一丝不苟、潜心研究以寻找规律的习惯。这里介绍点滴他在对待自己疾病方面的研究收获,供大家借鉴。
凌云沛先生在10多岁时就得了慢性支气管炎,几十年未能治愈而成为顽疾,尤其每年秋风起时必反复感冒咳嗽,剧烈发作数月,在家人及同事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位体弱多病的老病号。到70年代初又被戴上冠心病帽子。他曾回忆说:当年我上楼梯需分两段演“蜗牛爬树”(即停顿两次来休息)。因当时是文革时期,教学科研处于停顿状态,他感到有时间研究自己的病,经他反复调研观察,选择中西医各一位,与他们合作。他所选择的医生并非名医,因名医不会有很多时间与长期病号周旋,而是选择责任心强,比较有耐心,又有一定水平并愿意与病人讨论问题的人。他逐渐提出了自己的合作方案和原则,对医生要依靠而不依赖,力求参与掌握自己的命运,依靠西医检测、扶危、治标;依靠中医固本培元根据病情变化经常调整药方。与此同时自己也摸出一套自我监控调节病情的方案。例如以经常自测心率的监测手段,来调控各种诱因对心率的影响,通过调整活动量的大小、饥饱程度、情绪波动等来自我调控心率以保证心肌不受伤害。当心率偏低时就增加活动量。通过十余年坚持,到80年代初他竟从岌岌可危的“低谷”逐步上升到平稳、到两种疾病均无大发作,体质大幅度改善。到90年代已达到能常速不停步登上十多层楼,慢性支气管炎也不发作了,甚至连感冒也不找他了。整天精神奕奕、不觉疲倦,与20年前相比判若两人。两位医生非常高兴,他们不约而同地说:“这个病人是自己把自己的病治好的!”凌云沛先生说:我很明白,当一个人得了重病,特别是不可逆转的顽疾,不能坐以待毙,要有平衡的心态,要依靠医生而不是依赖医生,我的这两位医生在十多年中精心研究不断调整治疗方案,对病起了关键的指导治疗作用。而我自己依靠而不依赖的方针和心态平静、不急不躁地配合医生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凌云沛先生自己的身体有了奇迹般的变化,又看到有些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不幸英年早逝,故于1995年写了《与痼疾作斗争的20年》介绍其亲身经历及体会。之后他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体会,用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各方面知识写出了10多篇数万字的文章,用以启示后人。如他写了《论心理平衡》、《论命运》、《泯仇记》、《生死观》等等。通过这些研究升华了他的人生,在他“泯仇”的历程中悟到一条至为重要的真理:“宽厚待人才能解放自己”,所以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原谅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从而放下了多年的思想包袱。因此他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虽然老伴早他10年离去,而他在一双儿女的精心照料下,能心态和逸、优游娴雅地达到94岁高龄,在加拿大平静地驾鹤西去。凌云沛先生曾写《耄耋吟》,抄录于下以共勉:
青鬓恍如昨
倏忽已寿喜
七十今不稀
八十何足奇
九十差不离
期颐亦可喜
若能追彭祖
观尽沧桑奇
人生贵有益
徒寿圣所讥
生优短亦贵
赖何寿可悲
四有勿缺一
身心健为基
唯真贯此生
常怀顽童意
老骥虽伏枥
志常在穹宇
人生必有死
譬如日落西
悠悠散入极
寿夭无庆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流体力学研究所 蔡德麟、邓学蓥